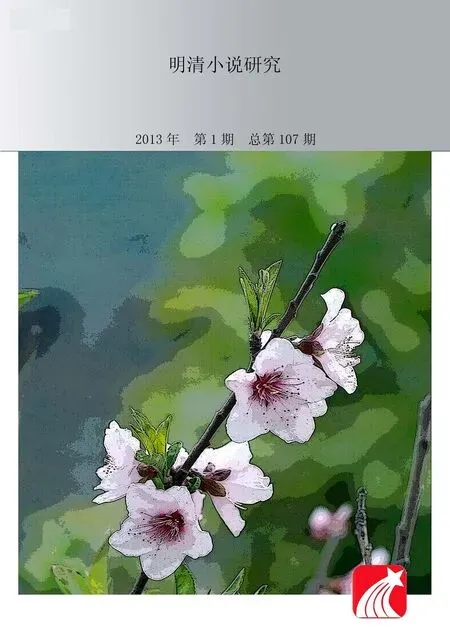论《水浒传》文学性与语言形式的同构性
2013-12-12··
··
摘要本文试图将《水浒传》的文本放置于文学与语言交叠的领域,来考察其在文学特点与语言形式上所体现出来的同构性和一致性。通过对《水浒传》的线状情节结构、对比性人物塑造、全方位自由转换的叙事视角的探讨,结合对《水浒传》前18回共计7740条句子的统计分析,本文认为,线状的情节结构与流线性的动态施事句存在着焦点散落、线性发展的同构性;人物形象塑造重平行、比较,与耦合类的关系句重对偶、并举则有着民族文化心理上的一致性;而全知全能的叙事方式与角度,与评论性主题句对范围广泛的话题选择具有相似的自由度与灵活性。这说明,白话小说《水浒传》能够印证文学与语言具有一致性这个命题,并且提示我们突破传统研究范式、探索文化与语言关系研究领域的新方向。
关键词文学 语言 文本结构 句法结构 同构性
《水浒传》是中国白话文学的里程碑。从其诞生之初至今,人们就以不同的视角和阅读方式,挖掘着它在文学语境与语言范畴中的价值和意义。作为一部成熟的白话小说,《水浒传》的主题思想、社会背景、时代特点、政治伦理等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价值判断,及情节结构、叙事模式、人物塑造、语言运用等艺术成就的得失估量,一直都伴随着时代语境的变迁而始终成为“水浒学”研究的热点。对于后进的研究者而言,如何超越传统研究范畴,调整视角,建构新的研究模式,其意义并不亚于研究的本身。本着这一目标,本文试图跨越文学与语言的界限,在二者交叠的领域内,对《水浒传》进行文本分析,以探索其语言特征中所包含的文化意蕴。
一、文学与语言的一致性
维特根斯坦曾经说过,“想象一种语言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方式”①。如何理解这一命题?笔者以为,文学起源于人类的思维活动,是用语言文字表达社会生活和心理活动的艺术形式。从这个角度看,维特根斯坦这句话可以理解为:“语言代表着一个民族看待世界的方式,代表着他们描绘世界的特有的眼光”。
关于语言与文学的关系,最经典的表达似乎可以用萨皮尔在《语言论》第十一章“语言和文学”中的有关论述来代表。萨皮尔认为,文学包括精神层面和语言表达层面,优秀的文学作品是“直觉的绝对艺术和语言媒介在内的特殊艺术完美地综合”②,而与语言(语种)无关。他说:“语言是文学的媒介,正像大理石、青铜、黏土是雕塑家的材料。每一种语言都有它鲜明的特点,所以一种文学的内在的形式限制——和可能性——从来不会和另一种文学完全一样。用一种语言的形式和质料形成的文学,总带着它的模子的色彩和线条。”③萨皮尔还具体地指出了语言的因素对于文学的影响:“每一种语言本身都是一种集体的表达艺术。其中隐藏着一些审美因素——语音的、节奏的、象征的、形态的——是不能和任何别的语言全部共有的。”④这就是说,文学创作离不开语言,文学中的种种特质跟语言的特征密不可分。正如雕塑家用不同材料来塑造形象,造就了石像、青铜像、泥俑等雕塑作品,文学通过语言来描绘它的世界图景,有多少种语言,就有多少种这样的世界图景,语言为文学提供了多种可能性,使文学成为丰富多样的艺术表达模式和审美模式。
在文学与语言的关系上,罗兰·巴特的表述更加直观,他认为,“叙事作品具有句子的性质,但绝不可能只是句子的总和。叙事作品是一个大句子,如同凡是陈述句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小叙事作品的开始一样”⑤,强调“语言和文学之间的一致性”。所谓语言与文学的一致性,笔者的理解是,一个文学作品的结构其实等同于一个句子的结构,一个句子如何选择词语,如何安排句子成分的顺序,如何组织句子的结构,往往意味着一部作品对原始素材的选择,对各类述题的排序,乃至对整个视野图景的组织和架构。也就是说,一个文学作品的创作者在叙述或描写对象时,其词句的选择、语言的运用、表达的方式等等,必然与其对母语的感觉和领悟是一致的。例如:汉字的表意性及一字一音节的特性,使得汉语诗歌的字数可四言,可七言,句子可整齐可参差,语序灵活,音韵合乐,成为了一种重意境、有声韵、可歌咏的文学品种。历代诗歌作者正是凭借汉语的特性去感悟生活,探索生命意识,描绘他们眼中的世界景象。因此,汉语诗歌无论是绝句、律诗,还是楚辞、乐府诗,并不仅仅是语言技巧的产物,更是汉语的特性本身所带来的多样意趣和不同的审美力量。
文学作品需要传达生活内容的信息,更要表现生活之上的精神特质,要蕴含感悟生活之美的审美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的语言既是工具、载体,又超越其上,具有了审美功能和民族文化的通约性。
二、《水浒传》的线状结构与线性施事句
《水浒传》的结构特点,是“把许多原来分别独立的故事经过改造组织在一起,既有一个完整的长篇框架(特别是到梁山大聚义为此),又保存了若干仍具有独立意味的单元,可以说是一种‘板块’串联的结构。”⑥所谓“板块串联”,从根本上说就是一种线性结构。这种线性结构是以情节为中心的古典小说的典型结构特征。兹维坦·托多里夫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叙事的时间是一种线性时间,而故事发生的时间是立体的。在故事中,几个事件可以同时发生,但是话语则必须把他们一件一件地叙述出来;一个复杂的形象就被投射到一条直线上。”⑦这种体现时间一维性的直线式叙事方法,往往成为史诗及古典小说中最为普遍的布局方式。写事件,从发生、发展到全局;写人物,由少年、成年到老年。例如:18世纪的英国启蒙小说大多沿用了海上漂流的史诗及陆地旅行的流浪汉小说中遗留下来的情节结构模式,将客观现实中人物直线运动的规律,固定为小说创作的结构模式。
《水浒传》的线性结构同样遵循时间的自然顺序和事件的因果关系顺序,将各个情节部分从头至尾串联起来,最终形成一个统一的结局。但中西方古典小说线性结构的不同之处在于:英国启蒙小说中流浪汉式的主人公是贯穿首尾的,他们始终行进在情节主线上,成为故事的惟一焦点。而《水浒传》的人物则是众多的,一百零八将的座次虽然有别,但每个英雄都有自己的故事和经历,每个英雄都有独特的个性和特质,而他们奔赴梁山泊的动因则无一例外:官逼民反。于是,这些众多人物的不同情节板块犹如条条涓涓细流,在时间的流程上陆续汇入“官逼民反、梁山聚义”这一情节主线中。
以罗兰·巴特的“叙事作品具有句子的性质”这一观点来考察《水浒传》的语言,我们会发现,《水浒传》在叙事结构上的线性特点,也在其句法结构中大量地显现。笔者对《水浒传》前18回共计7740条句子的结构进行了逐条分析,分离出了4056条施事句,发现其中存在大量流块状的线性句。这些句子大多为多个动词或动词词组铺排而成的施事句,动词或动词词组在意义上都与同一主语存在施-动关系,但它们之间无需关联词语连缀,甚至无需语音停顿,其结构形态与西方语言以一个动词为焦点的主谓句句法结构形神迥异。例如:
1.宋江出到庄前,上了马,打上两鞭,飞也似望县里来了。(4个动词或动词词组)
2.鲁智深把直裰脱了,拽扎起下面衣服,跨了戒刀,大踏步提了禅杖,出到打麦场上。(5个动词或动词词组)
3.众人吃了一惊,发声喊,都走了,撇下锄头铁锹,尽从殿内奔将出来,推倒攧翻无数。(6个动词或动词词组)
4.杨志就弓袋内取出那张弓来,扣得端正,擎了弓,跳上马,跑到厅前,立在马上,欠身禀复道:(7个动词或动词词组)
5.智深相了一相,走到树前,把直裰脱了,用右手向下,把身倒缴着,却把左手拔住上截,把腰只一趁,将那株绿杨树带根拔起。(8个动词或动词词组)
6.过了一夜,次日天明起来,讨些饭食吃了,打拴了那包裹,撇在房中,跨了腰刀,提了朴刀,又和小喽罗下山过渡,投东山路上来。(9个动词或动词词组)
据我们统计,在7740条句子中,这种流水般的线性动句超过2000条,在施事句中所占比例甚至多于西方语言那种典型的“主-动”或“主-动-宾”结构的句子,其中7个以上动词(词组)连续铺排的句子竟也达到了20条之多。这种流块堆叠的线状句子结构几乎无法直译成任何一种西方语言,说明汉语句子结构的组合视角具有汉民族的独有特性。如同线性的叙事结构中散落着一百零八位人物,这种线性的句子结构也随着时间的顺序或事理逻辑的顺序,引领读者的视点不断在铺排的动词之间迁移转换,随走随停,从一个地方来到另一个地方,遭遇一个又一个的人物,参与一个又一个的事件,体现了重时间的线性运动的内在文化精神。正如文化语言学者申小龙先生所言:“汉语的流块建构与汉民族其他文化艺术形式在‘流’态动感上具有通约性。我国古代的雕刻、书法与绘画都不重视立体性,而注意流动的线条、飞动的美。于疾徐波折、自由流转的线条之中透出勃勃的生气和生命的旋律,于‘移视’中可体会它的流动气势。”⑧
三、《水浒传》人物塑造的对称性与句法结构的偶意
《水浒传》塑造了众多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体现了传统小说中群像设计及类型化的特点。作者在这些人物之间建立起一种平行、比较的关系,像武松的勇武豪爽,鲁智深的嫉恶如仇,李逵的戆直鲁莽,林冲的刚烈正直,都能够同时得到渲染烘托,于对比中凸现完整而姿态各异的人物群像。
我们发现,在《水浒传》的每一个章回中,出场的重要人物通常都是两个,这从回目中也可见一斑,如第三回“史大郎夜走华阴县,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第十回“林教头风雪山神庙,陆虞候火烧草料场”,第十七回“花和尚单打二龙山,青面兽双夺宝珠寺”,第六十回“公孙胜芒砀山降魔,晁天王曾头市中箭”等等。不仅人物的名号或绰号及地名两两相对,连事迹与事件也有偶合之功。这固然有汉字一字一音及表意性的特点所带来的便利,但我们不能不说“偶合”的思维方式是造成《水浒传》从人物形象到结构布局,乃至句式表达上趋于两两成双的主要动力。试看第十三回杨志与索超比武一节对二人出阵前的描写:
只见第三通战鼓响处,去那左边阵内门旗下,看看分开。鸾铃响处,正牌军索超出马,直到阵前兜住马,拿军器在手,果是英雄。……
右边阵内门旗下,看看分开。鸾铃响处,杨志提手中枪出马,直至阵前,勒住马,横着枪在手,果是勇猛。……
再看第十三回对朱仝、雷横出场时的描写:
本县尉司管下有两个都头:一个唤做步兵都头,一个唤做马兵都头。
这马兵都头管着二十匹坐马弓手,二十个土兵;那步兵都头管着二十个使枪的头目,一十个土兵。
这马兵都头姓朱名仝,身长八尺四五,有一部虎须髯,长一尺五寸,面如重枣,目若朗星,似关云长模样,满县人都称他做“美髯公”。原是本处富户,只因他仗义疏财,结识江湖上好汉,学得一身好武艺。……
那步兵都头姓雷名横,身长七尺五寸,紫棠色面皮,有一部扇圈胡须。为他膂力过人,能跳二三丈阔涧,满县人都称他做“插翅虎”。原是本县打铁匠人出身,后来开张碓坊,杀牛放赌。虽然仗义,只有些心地匾窄,也学得一身好武艺。……
作者对杨志与索超、朱仝与雷横的形象描写与叙事构造,几乎都是在一种左右(前后)对称的框架内进行的,甚至词语的选择、字数和句数的铺排,都呈现出一种整齐划一、偶合对称之势,让我们无法忽视作为一种思维定式的“偶意”,对于《水浒传》形象设计、组织布局以至句法结构的影响。
在我们对《水浒传》前18回所作的句型统计中,有着偶合之意的关系句达到了192条之多。例如:
1.史进上了马,正待出庄门,只见朱武、杨春步行已到庄前,两个双双跪下,擎着两眼泪。
2.鲁提辖看那五台山时,果然好座大山。
3.出得那“五台福地”的牌楼来看时,原来却是一个市井,约有五七百人家。
4.随着那山路行去,走不得半里,抬头看时,却见一所败落寺院,被风吹得铃铎响。
5.林冲心疑,探头入帘看时,只见檐前额上有四个青字,写道“白虎节堂”。
6.晁盖却去里面拿了个灯笼,径来门楼下看时,士兵都去吃酒,没一个在外面。
这些句子从语义上看,(加点文字)前后两个部分都可以独立成句,或者纳入传统语法中“并列复句”或“联合复句”的范畴,然而细细品味,它们既无法在语感上断开,也不能用“并列”、“联合”一以概之。它们只有“两两成对,句意上互为映衬,节律上互为依托,才成一完整的表述单位”⑨。申小龙在他的汉语句型系统中将这类句子命名为耦合句,以“只见”、“看时,只见/果然/却是”等为形式标记。
早在《周易》、《淮南子》等古籍中,中国古人辩证统一的思想就清晰可辨:认为太初之时浑然一体的元气可判分为二,形成天地等物质实体。有天地,就有阴阳,阴阳分立而又相合,它们的运动贯串于各个方面,由一而二,由二而四,由四而八……呈现出矛盾双方永不间断、两两分而相合的状态。“偶意”因此贯穿在中国各类传统文学艺术(如诗歌、曲赋、戏曲、建筑)的精神气质之中。而另一方面,汉字的表意及单音节特性又顺应了这种“偶意”,为词语构造、句子构造,乃至文本的组织构造提供了对偶、对称的便利。可以说,汉语和汉字从产生伊始,就自然而然地为对偶创造了条件。
那么,汉民族是先有了“偶合性”思维方式,才有了汉字的特点,还是因为汉字特点造就了“偶合性”思维的惯性?这也许已经很难辨清,但可以肯定的是,“对偶”、“对称”早已成为汉民族组词造句乃至安排文本结构时的一种惯用思维模式。因此,人物塑造、结构布局与大量“耦合句”在“对称”、“偶意”上的一致性,在《水浒传》中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实质上正是汉民族认识世界、感知世界的特有模式。
四、《水浒传》的叙事角度与话题评论句式
《水浒传》取材于民间传承的历史故事,反映了市民阶层的欣赏趣味。罗贯中、施耐庵虽是文人,但他们都曾在元末繁华的杭州城生活过,因此,他们对水浒故事的艺术加工仍然延续了宋元话本讲史、说经的模式,留有说话艺术的痕迹。作者仿佛就是说话人,面对着听众,娓娓地讲述着动人的故事给他们听。这使得《水浒传》的叙事方式与叙事角度带有某种引导读者(听众)的性质,表现在行文之中即为随处可见的“话说”、“且说”、“但见”、“只见”、“话休絮烦”、“不在话下”、“看官听说,有诗为证”之类的篇章语,这实际上就是说话人对听众所做的提示性语言。这种话本残留遗迹在章回体小说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那就是控制叙事的节奏,布局情节的走向,掌控读者的注意力,便于作者于紧要关头突然停下,设置悬念。于是,“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或“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就成了章回之间的程式化套语。
上述因素为《水浒传》造就了中国传统小说那种以全知视角自由转换时空的特长。说到鲁智深,视角就是鲁智深的;说到林冲,视角便转为林冲的;说到武松,读者便随武松喝酒、打虎、杀西门庆。这种叙事方式无需关注人物内心,只需聚焦外部信息,如人物之间的对话和行动,周围的环境等等即可。当然,作为说话人的职责,作者还需不时地点评、议论、解释,这是代替内部信息如心理活动、思想情绪的最好方式。
如人们谈论最多的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一节,作者就充分调动了视觉、味觉、听觉诸感官的叙事角度,为读者带来了极为直观的感受,可谓淋漓尽致的审美享受:
扑的只一拳,正打在鼻子上,打得鲜血迸流,鼻子歪在半边,却便似开了个酱油铺:咸的、酸的、辣的,一发都滚出来。(味觉视角)
提起拳头来就眼眶际眉梢只一拳,打得眼睃缝裂,乌珠迸出,也似开了个彩帛铺的:红的、黑的、绛的,都滚将出来。(视觉视角)
又只一拳,太阳上正着,却似做了一个全堂水陆的道场:磐儿,钹儿,铙儿一齐响。(听觉视角)
《水浒传》这种叙事角度全方位的自由转换,也可以在一类以评论话题为功能的句式中找到同构。按照申小龙建构的汉语句型系统,主题句是与施事句、关系句鼎足而立的一个大句类,具有名词趋向,其功能主要在于评论,其句子焦点往往是一个话题。在主题句中,话题的范围极为宽泛,如同移动的视角,视野所及,无论是人物、事物,还是事件、经历,抑或属性、特征,都可以成为评论的话题。因此,句子中的主题语(话题)可能是一个词、一个词组,甚至是一个句子。例如:
1.洪大尉倒在树根底下,諕的三十六个牙齿捉对儿厮打,那心头一似十五个吊桶,七上八落的响,浑身却如重风麻木,两腿一似斗败公鸡,口里连声叫苦。(主题语:洪太尉,人物)
2.你是个卖肉的操刀屠户,狗一般的人,也叫做镇关西!(主题语:你,人物)
3.那里是镇守边庭,用人之际,足可安身立命。(主题语:那里,方位)
4.小人房钱,昨夜都算还了。(主题语:小人房钱,事物)
5.这浮浪子弟门风,帮闲之事,无一般不晓,无一般不会,更无一般不爱。(主题语:这浮浪子弟门风,帮闲之事,并列短语)
6.踢毬打弹,品竹调丝,吹弹歌舞,自不必说。(主题语:踢毬打弹,品竹调丝,吹弹歌舞,并列短语)
7.量些粗食薄味,何足挂齿。(主题语:量些粗食薄味,句子)
8.我这里五台山文殊菩萨道场,千百年清净香火去处,如何容得你这等秽污。(主题语:我这里五台山文殊菩萨道场,同位语短语)
由此看来,《水浒传》自由转移的叙事视角和叙事方式,与主题句以评论话题为目标的功能具有很强的同构性。
在我们统计的7740条句子中,除去存现句、祈使句、呼叹句、有无句、名词句及篇章语句等小句类,施事句、关系句、主题句合计所占比例接近90%,其中施事句(含多段动词句)4056条,关系句(含耦合句)1554条,主题句1250条。由于本文本分析只涉及《水浒传》部分内容,而非穷尽性专书分析,所以各统计项目与穷尽性分析的结果可能会存在某些差异或出入,但我们相信,三大句类的基本格局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从文学与语言的一致性角度看,这似乎可以说明《水浒传》的时代,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和描述,更集中于对人物行为、事件发生等外部动态信息的关注,与此同时,人们对人物的评价、事件的评述等静态信息也具有相当的兴趣。随着时代的变迁、文学的现代转型,这一点在后世的小说(如《红楼梦》、晚清谴责小说等)中可能会越发凸显出来,这将是笔者进一步探索的方向。而汉民族在文本结构与语言组织模式中所体现的心理特点等文化精神内涵,同样是我们在任何文本分析过程中无法忽略的因素。
注:
① [英]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2页。
②③④ [美]爱德华·萨皮尔《语言论》,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01、199、201页。
⑤ [法]罗兰·巴特《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见《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第2卷),胡经之等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76页。
⑥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下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92页。
⑦ [法]热·热奈特《叙事语式》,见《美学文艺学方法论》,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50页。
⑧ 申小龙《当代中国语法学》,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33页。
⑨ 申小龙《汉语与中国文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