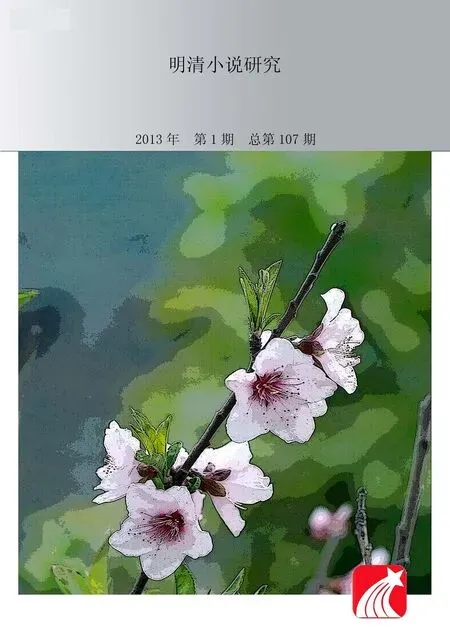李绿园《歧路灯》的佛缘与“谭(谈)”风
——作者、书题与主人公名义考论
2013-12-12··
··
摘要李绿园字孔堂,名海观,一得自于儒,一得自于佛;《歧路灯》之书名借自佛教“歧路”之喻和“灯喻”,而书中主人公姓“谭”即“谈”,“谭孝移”名“忠弼”为作者藉以谭(谈)忠与孝关系的人物;“谭绍闻”、“谭绍衣”之名,取自《尚书》“绍闻衣德言”,则专为谭(谈)孝,所谓“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全书基本思想倾向为儒佛互补、以佛济儒的儒佛合一。而谭家著籍之祖命名为“谭永言”者,乃寓说是书自上古以降“谈”与“谈说”之小说源头取义,实为此书体裁之提示,创作风格之宣言。《歧路灯》的“谭(谈)”风促使其形成自觉写人生和以全面描写一个人的命运为中心的结构,是当时章回小说艺术的一个进步,同时也促使其刻意追求理趣、雅趣,平中见奇,“谭”言娓娓,醇厚剀切。
关键词李绿园 《歧路灯》 佛缘 “谭(谈)”风
清乾隆间李绿园著白话长篇小说《歧路灯》一书问世百余年间,曾若存若亡,几近埋没。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经栾星先生整理出版,才引起较多学者的关注,至今30年来,形成并积累了一定数量的研究论著。但是,这项研究毕竟为时尚短,专注者不多,相对于“四大奇书”、《红楼梦》等的研读,还不够深细。从而仍有些本是显山露水的问题,也还被熟视无睹,亟待揭出和探讨。这里仅就此书之作者、书题与主人公三者名义所标示或含蕴与佛教的缘分和“谈说”风格等,试为考论如下。
一、“李海观”之“海”与“观”
李绿园,名海观,字孔堂。《颜氏家训》云:“古者,名以正体,字以表德。”①绿园字孔堂,当取《论语·先进》载“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表明其有志儒学的人生期待,可以无疑。这从《歧路灯》中人物论学首重《五经》和推崇“端方醇儒”②(第十一回)也可以得到旁证。至于绿园名“海观”,《歧路灯》的整理校注者栾星先生曾据绿园《宦途有感寄风穴上人二首》之二的自注数语说:“原来他的学名海观,与佛赐法名妙海有关。”③其说甚是。但进一步推敲起来,却是只揭出了他学名“海观”之“海”字的由来,那“观”字还是没有着落,需要别寻出处的。
这个问题经台湾学者吴秀玉教授考证,发现李海观之“观”字,是由于李绿园的祖父“玉琳卜居宋寨后,为答谢河沿李李姓的美意,遂与之联宗,除绿园的父亲李申辈,出生于新安,用新安‘田’字部首排行命名……外,自绿园这一代出生于宋寨开始,皆采用河沿李李姓的世次命名,如绿园取名海观,‘观’字即是”④。吴教授的这个结论也是可信的。
至此,合栾星与吴秀玉二先生的考证,绿园学名“海观”的出处大概已明。然而绿园得有此名,是否还有什么更深层的意义?笔者以为有,并且是值得讨论的。而为着讨论的方便,仍录绿园《宦途有感寄风穴上人二首》如下,其一曰:
竹筇扶步叩禅关,峰岭千层水一湾。祸不可撄聊远害(余以运铅之役,缺匮部项,几频于险),盗何妨作只偷闲。犹夸循吏频摇首,但号诗僧亦赧颜。易地皆然唐贾岛,两人踪迹一般般。
其二:
上引诗中括号内文字为作者自注。另外原诗题下也有作者自注云:“乾隆癸巳暮春印江署中作。”栾星《〈歧路灯〉研究资料汇编》五《年谱》据此系此诗于乾隆三十(1773)年绿园六十七岁之“夏秋间辞官他去”⑥之前所作,是可信的。但从这两首诗所能够知道的,除了栾先生从第二首首联末句自注得出“海观”之名取“海”字的出处之外,尚有以下三点:
首先,从第一首诗中“余以运铅之役,缺匮部项,几频于险”的自注看,作者虽当时侥幸免祸,但至此仍心有余悸,因生退意,是其诗题“宦途有感”内容的核心。由此引发对以往宦途的反思,自觉能有“循吏”之誉,“诗僧”之号,平生“踪迹”有似于唐代先是为僧后又为官的贾岛,也值得欣慰了。这里提到“诗僧”,或因为诗是寄僧人的,不免有为了切题而牵合僧人的意思,但即使如此,也不一定非牵合于僧人才可以作诗,尤其不会为了一首诗写得真切的缘故,而硬是把自己与“诗僧”联系起来。所以,读这首诗,正如对于绿园的自谦于“循吏”,我们由其一生行状不能不承认他真的是一位“循吏”一样,对他的赧颜于“诗僧”,我们也不应认为仅是一个词藻,而应当看作是绿园对自己平生与佛教关系密切的的郑重确认。他这种一身为“循吏”而兼“诗僧”的品格,恰与其字“孔堂”而名“海观”,以及和所作《歧路灯》一面讲儒家的“三纲五常”,一面又侈谈因果报应的儒、佛相济,是高度一致的。
其次,从第二首诗,我们在栾先生考据的基础上,还可以就“绿园与浮屠的这桩因缘”在其一生中的影响作进一步的思考。即一方面是,绿园诗注以自己“生弥月”即寄名佛寺非为偶然,而是命定为“菩萨座下法派”即佛弟子。这样的说法虽然因出现于诗中似不必太看得认真,但诗注的直陈略不同于诗句意义的婉道,基本上还应该视为作者正式的声明而予以重视;二是也不应忽略的是,三、四句承上说自幼寄名佛寺的诗与注,实是追忆自己幼年在风穴寺一段佛弟子生活。我们除了由此知道绿园一生“疏荤酒”的生活习性,可以补绿园传记一个方面的细节之外,还可以知道这习性正如其名“海观”之“海”,也来自于“绿园与浮屠的这桩因缘”,而佛教对绿园一生的影响之大,实不亚于当时儒学所注重的文行出处等方面的教养,而在于对其淡泊心境的塑造;三是诗之尾联末句自注“时年六十有七”,不能单纯看作是为诗纪年,而应当看到是照应着首联末句自注“余生弥月”云云的佛缘,而以垂老自念感慨系之。因此,这一诗注所传达的讯息,应是他自“生弥月”而寄名僧寺,名中的这个“海”字,就时时提醒他为佛弟子,至今垂老犹未忘此“前因”也。这实是绿园在以事实向风穴上人诉说己身所受浮屠影响之大而且深。这在当时恐怕也鲜为人知,至今李绿园与《歧路灯》的研究中也未见人道及,而显然是此一研究中不应忽略的一个重要事实。
最后,从绿园本诗为年届七旬时所作,尚且感慨自注幼年即得有法名“妙海”来看,他对于后来自己俗名“海观”之“海”的意义,应不仅是作自然地理风光来看的,而肯定念念不忘其为佛门之“海”。佛门之“海”虽亦取譬自然之海,但多用作比喻人世之苦为难以自拔之境,曰“苦海”,乃佛法诸喻中之“海喻”。如胡吉藏撰《法华义疏》卷第六《譬喻品之二》曰:“众苦如海。众生没在苦海内也。”又法显译《大般涅槃经》卷下曰:“一切众生,沉沦苦海。”玄奘译《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曰:“一切有情,沉沦苦海。”以及已成俗语的“苦海无边,回头是岸”等等,都是在以人世为“苦海”的意义上用“海”字的。李绿园得于僧人所赐法名“妙海”之“海”,即当作如是观。而“妙”字在佛典中多形容佛法的高明,如《长阿含经》有云“微妙希有之法”、“深妙法”、“佛法微妙”、“微妙法”等;或如释智圆述《佛说阿弥陀经疏》所谓“妙则三智圆融”。李绿园法名“妙海”之“妙”也非此二义莫属。如此说来,李绿园法名“妙海”之义,当即“妙法”行于“苦海”,乃佛菩萨所谓“苦海慈航”之意。绿园因此自认“实菩萨座下法派也”,不亦宜乎!
综上可知,李绿园自幼得僧人赐“妙海”之法名,俗名仍沿用此“海”字,确曾使其念念不忘“菩萨座下法派”的“前因”。因此之故,我们不能不怀疑其名“海观”之与“海”组名的“观”字,虽因于河沿李姓的辈分,但既已组为名词,也就可以并且应该与“海”字联系起来看。从而“海观”之义,就有可能成为表达与绿园“前因”相一致的以人世为“苦海”的佛教观念,即人世如“苦海”,当作如是“观”也!
如上考证倘得成立,则我们便多了一个角度即从佛教影响的角度来解读李绿园及其《歧路灯》。
首先,佛教给李绿园以“苦”观人世而为小说以救世的创作心态。《歧路灯》写谭孝移那种对家庭前景似乎无端而至之莫名的忧虑,他那种“心里只是一个怕字”的悲观情绪,“把一个孩子,只想锁在箱子里,有一点缝丝儿,还用纸条糊一糊”的教子弟法,虽然明是说得自“眼见的,耳听的,亲阅历有许多火焰生光人家,霎时便弄的灯消火灭”的阅历,但子夏有云:“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同是绿园笔下的儒者娄潜斋对谭孝移的担忧也能不以为然道:“人为儿孙远虑,怕的不错。但这兴败之故,上关祖宗之培植,下关子孙之福泽,实有非人力所能为者,不过只尽当下所当为者而已。”(第三回)可知谭孝移即作者的“怕”字,并非纯粹儒者所必有,而是谭孝移即作者李绿园思想个性上的某种特殊因素使然。这个使李绿园对家庭前景极度忧虑的特殊因素,应主要就是他自幼所受佛教以人世为“苦海”的把人间视为充满危机苦厄世界的“海观”观念的影响。若不然,他写一个五世乡宦广有田产年仅三十一岁的拔贡生谭教移,有什么理由不能做到如寒门学子娄潜斋尚且能够有的“达观”呢?
当然,这里也要说明的是,谭孝移与娄潜斋都是李绿园创造的人物,如上把谭孝移的“怕”字主要归结到绿园所受佛教影响之“海观”的个性特点,而认为同是作者所写人物娄潜斋的“达观”性情却较少是李绿园所有,原因无它,即这部小说立题就在于那么一个“怕”字之上。李绿园对他笔下的人物,固然推许娄潜斋的“达观”,但显然更倾向于与谭孝移共有一个一味谨慎对人生近乎悲观的“怕”字。因此,我们认为促使绿园有《歧路灯》一书的这一个“怕”字,并不能仅从其一般居安思危的预后心理进行解释,而更多应该是他名“海观”所标志的思想上受佛教观念的影响所致。若不然,他也许就不会写这“满天下子弟八字小学”(第九十五回)的小说,或者写谭孝移即使“怕”也不至于有“午睡,做下儿子树上跌死一梦,心中添出一点微恙”(第十回),并终于因此而死的那种近乎夸张性的描写了。这也就是说,李绿园所受佛教思想影响的“海观”人世的心态,部分地成为了他为《歧路灯》小说以救世的基础。
其次,佛教成为《歧路灯》描写主人公谭绍闻命运转变的关键。与以上绿园以人世为“苦海”之“海观”的意义相联系,并作为对自己幼曾寄名风穴寺一段出家生活深刻印象与怀念之情的反映,《歧路灯》在写谭绍闻出走的第四十四回《鼎兴店书生遭困苦,度厄寺高僧指迷途》中,特别命名收留并给他以帮助的佛寺为“度厄寺”,并对寺僧尤其是“小和尚念经”的日常生活有较为细致的描绘。虽然这一回书中有关度厄寺具体描写的文字不多,也并无高僧给谭绍闻切实的教诲,但回目仍把谭绍闻能够脱却这一段流浪之苦的原因归结到“高僧指迷途”,更可见其用心只在突出佛教的这一“度厄寺”,以彰显佛教对谭绍闻迷途知返所起的作用而已。无独有偶,书中第一百零四回《谭贡士筹兵烟火架,王都堂破敌普陀山》写谭绍闻为平倭立了大功的火箭,是他“住在海口集市约有五百户人家一个定海寺内”密制的。书中不仅把谭绍闻所住的地名设为“海口”,把寺院的名称设为“定海”,而且接下来写奏凯报功还特别把“定海寺”写进表章,以彰显“定海寺”在谭绍闻参与平倭立功中所起的作用。
还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处关于佛寺与僧人的描写,前者在谭绍闻“迷途”知返、浪子回头之时,后者是谭绍闻为重振家业而立功边陲之地,皆其命运发生重大或根本性转变的关键⑦。所以,虽然《歧路灯》也写有地藏庵范尼姑之流不守戒规的僧尼,但绿园作为儒者,不把其主人公谭绍闻改过向善并以边功起家之人生关键的描写,安排在书中所多有的所谓“满院都是些饮食教诲之气”(第三十九回)之类“正人”聚集的场合,而置于佛门的“度厄寺”与“定海寺”中,高调宣示“高僧指迷途”的作用,仍不能不说其有在明确以人世为“困苦”的同时,宣扬对佛法广大、救世度人之信心的用意。而由此可见,绿园名“海观”决非虚有其名,而实已成为其思想上受佛教的影响一个明确的标志。这也就是说绿园名“海观”的佛教渊源与上述《歧路灯》叙事写谭绍闻命运先后以佛寺为转折之地的设计,实骑驿暗通,血脉相连。
最后,是影响到《歧路灯》有较多因果报应的描写。《歧路灯》虽以“用心读书,亲近正人”为“满天下子弟的八字小学”,以“端方醇儒”、“贤良方正”为立身之楷模,但具体描写中真正成就这类儒家“正人”与“子弟”之事业的关键,却也与上论谭绍闻命运转折一样,不仅在儒,而更在于佛教,具体说即不仅在“圣贤书”或关键不在“圣贤书”,而在于佛教的因果报应。如第一百零二回《书经房冤鬼拾卷,国子监胞兄送金》写与主人公谭绍闻少年时形成对照的贤子弟娄朴参加会试,阅卷中三复被黜,但因“冤鬼拾卷”,感通考官取其为第一百九十二名进士,“嗣娄朴谒见房师,邵肩齐说及前事,娄朴茫然不解。或言这是济南郡守娄公,在前青州府任内,雪释冤狱,所积阴骘”;又,第一百零八回《薛全淑洞房花烛,谭篑初金榜题名》写谭绍闻的儿子篑初中进士,也是靠祖德得到了阴助。学者多以这类情节是作者手法拙俗的表现,诚然是对的;但俗套多有,舍彼取此,毕竟还是他思想上认同佛教因果报应之“海观”意识的真实体现。研究者不当仅以其为落了那时小说家的俗套,而应该深一步看到其背后李绿园与《歧路灯》的佛缘。
二、《歧路灯》之“歧路”与“灯”
李绿园《歧路灯》的佛缘还体现于《歧路灯》书名组词之“歧路”与“灯”,也是从佛教典籍借用来的。
先说“灯”字。三十年前,我在京读书做大学毕业论文《〈歧路灯〉简论》,投稿有幸得到时任《文学遗产》副主编的卢兴基先生指教。他给我的一个重要点拨是,《歧路灯》一书名“灯”,是从《五灯会元》的“灯”即佛教的“灯喻”来的,希望我把它写到论文中去。但当时就业忙碌,顾不上深入查考,不便也就没有把自己还不甚明白的这一认识写到论文中去,遂使这一并非深藏的出处及其意义,似乎至今未见有学者揭出。如今结合了上论李海观“海”字的由来及其意义,便深切感到卢先生的指教,实是对此书顾名思义,探讨其所受佛教影响的一大灼见,试为广说之。
拙见以为,我国古代小说在《歧路灯》之前,固然已经有了《剪灯新话》之类标题含“灯”字的小说,但那“灯”字明显是从正统诗文中“何当共剪西窗烛”之类涉“灯”的文句来的。《歧路灯》之“灯”则不然,是从《五灯会元》之“灯”,即佛教的“灯喻”来的。佛典中“灯喻”文例甚多,如姚秦三藏鸠摩罗什译《维摩诘所说经》上卷《菩萨品第四》:
于是诸女问维摩诘:“我等云何止于魔宫。”维摩诘言:“诸姊有法门名无尽灯,汝等当学。无尽灯者,譬如一灯燃百千灯,冥者皆明,明终不尽……”
又,隋章安顶法师撰《大般涅盘经疏》卷第二十六《师子吼品》之三有云:
佛前言灯喻众生,油喻烦恼。今难此语有两解:一云灯览众法,明、油、器等共成一灯。明名灯明,器名灯器。二云明与油异,正取明为灯。灯是火性,油是湿性,正取后意为难。灯之与油二性各异,众生烦恼本来不异。
又,释智圆述《佛说阿弥陀经疏》云:
日、月、灯喻三智。故名闻光者,名称普闻如光遍照。大焰肩者,肩表二智,焰表照理。须弥灯者,须弥云妙高。妙则三智圆融,高则超过因位。灯则喻三智之遍照也,难沮者。
释廷俊序《重刊五灯会元序》云:
昔王介甫、吕吉甫同在译经院,介甫曰:“所谓日月灯,明佛为何义?”吉甫曰:“日月迭相为明,而不能并明。其能并日月之明,而破诸幽暗者,惟灯为然。”介甫击节称善。吾宗以传灯喻诸心法而相授受者,其有旨哉。
又,《古尊宿语录》卷二十四《潭州神鼎山第一代洪諲禅师语录》云:
僧问石门:“如何是和尚家风?”门云:“解接无根树,能挑海底灯。”后其僧入室问:“学人不解挑灯意,请师方便接无根。”门云:“贾岛笔头挑古韵,下笔之处阿谁分。”
由上举诸例之议论可知:一是佛教“灯喻”自古印度传入,源远流长,至中国佛教禅宗“以传灯喻诸心法而相授受”,“灯”即成为了佛教禅宗“心法”的象征;二是“灯喻”在佛教诸喻中比“日”、“月”之喻为更高一境,即从时间的延续上说,超越日月之不能“并明”,而“一灯燃百千灯……明终不尽”,是所谓“无尽灯”;从空间之照顾上说为无所不至,所谓“灯则喻三智之遍照也,难沮者”;三是“灯喻”之“灯”的价值在“明”,所谓“取明为灯”者,乃因“灯”燃“油”而明,“油喻烦恼”,“灯”之“明”乃“油”即“烦恼”消除的结果。这犹之乎油耗而灯明,世人烦恼的逐渐祛除,也就是禅宗所修行“明心见性”的过程。因此,“灯喻”是禅宗“心法”最好的说明。此喻为儒、道诸家之论所未有,佛门中也为禅宗所独有。从而《歧路灯》之“灯”,不仅从作者李绿园名“海观”的角度说竟似偶合了上引“海底灯”之喻,当来源于佛教,而且从清中叶以前儒、释、道三家学说史上看,也只是佛门禅宗的传统。以致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一《大学》论“格物”讥佛教空虚之论为“翠竹黄花、灯笼露柱,索觅神通,为寂灭无实之异端”⑧。其所讥“灯笼”即佛教禅宗“灯喻”中内容,而王夫之斥为“异端”。可见李绿园《歧路灯》之“灯”,虽实际写来是主弘扬儒家的教化,而非尽禅宗“灯喻”之正义,但至少是假佛家之“灯喻”以行儒家之道,其做派也就不是什么完全“正经理学”(第三十九回)的“真儒者”(第三十八回),而是儒佛互补、以佛济儒的儒佛合一了。这是我们把握《歧路灯》一书思想时应该注意的一个特点。
应是与《歧路灯》以“灯”名书不无联系,此书中除大量涉“灯”的描写之外,还较多运用了涉“灯”的比喻。如第三回写谭孝移说“霎时便弄的灯消火灭”,第十回写柏永龄说“将来必有个灯消火灭之时”,第七十九回议论道“这正是灯将灭而放横焰,树已倒而发强芽”等。尽管这些用法与佛教“灯喻”之义不同,但也可以看出作者对“灯”之意象的执着,进而想到海观先生隐以佛教的“灯喻”命名其书,即使不从“必也正名”(《论语·子路》)的方向上作推考,也应该认为《歧路灯》的“灯”字不仅是一个词藻的偶用,而必然对其叙事写人有某种实质性的影响。如上所述论书中有关度厄寺与定海寺的描写,正就是表明了佛教“灯喻”之义不仅嵌设在了是书题名之中,而且深化成为了故事肌理与灵魂,似未曾实用,而实已大用了。
后说“歧路”。《歧路灯》书名“歧路”之称,今见文献中亦先秦儒家所不道,诸子所罕言,而出于被认为是伪书的《列子》卷第八《说符篇》曰:
杨子之邻人亡羊,既率其党,又请杨子之竖追之。杨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众?”邻人曰:“多歧路。”既反,问:“获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杨子戚然变容,不言者移时,不笑者竟日。门人怪之,请曰:“羊,贱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损言笑者,何哉?”杨子不答。门人不获所命。弟子孟孙阳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他日与孟孙阳偕入,而问曰:“昔有昆弟三人,游齐、鲁之间,同师而学,进仁义之道而归。其父曰:‘仁义之道若何?’伯曰:‘仁义使我爱身而后名。’仲曰:‘仁义使我杀身以成名。’叔曰:‘仁义使我身名并全。’彼三术相反,而同出于儒。孰是孰非邪?”杨子曰:“人有滨河而居者,习于水,勇于泅,操舟鬻渡,利供百口。裹粮就学者成徒,而溺死者几半。本学泅,不学溺,而利害如此。若以为孰是孰非?”心都子嘿然而出。孟孙阳让之曰:“何吾子问之迂,夫子答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歧亡羊,学者以多方丧生。学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异若是。唯归同反一,为亡得丧。子长先生之门,习先生之道,而不达先生之况也,哀哉!”⑨
这就是著名的“杨朱歧路”或曰“歧路亡羊”故事。其义在讽刺儒家之学,自诩为“大道”,而从之者议论纷纷,各执一端,不得其本,结果于人于己都没有好处;救治之道,“唯归同反一,为亡得丧”。这一思想取向,显然与孔子等先秦儒家力倡的“学道”(《论语·阳货》)、“兼善”(《孟子·尽心上》)不同,而与《庄子》“绝圣弃智,大盗乃止”(《胠箧》)取向一致,是道家“清静”、“无为”、“抱一”等思想的流衍。
《列子》此说,后世学人虽儒、道互补,但正统儒者也较少道及。有之,隋唐间文中子(王通)《中说》卷九《立命篇》载:“子曰:‘以性制情者鲜矣。我未见处歧路而不迟回者。《易》曰: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则不疑其所行也。’”⑩其言“歧路”似用上引《列子》语义,但仍归于按儒家“六经之首”的《易》说有“直方大”的德行就可以临“歧路”而“不疑”;又明代王阳明《传习录》卷上载阳明先生曰:
天理终不自见,私欲亦终不自见。如人走路一般。走得一段,方认得一段。走到歧路处,有疑便问,问了又走,方渐能到得欲到之处。
这里阳明“歧路”之喻,虽不免也与上引《列子》有瓜葛之嫌,但毕竟他说“问了又走”云云,仍是儒家学道求进的取向。《歧路灯》则不然,它写人当“歧路”彷徨之际,尽管不似杨朱的止于“戚然变容”,也主张是要选择以前行的,却与阳明所主张由行路人即学者“有疑便问,问了又走……渐能到得欲到之处”的自强不息有异,而是要由“正人”给他一盏“灯”以照引正途。这虽然不免是李绿园做小说的由头,但是何以想到要给“歧路”挑出一盏“灯”来?拙见以为,这个念头的根源就是上论海观先生“菩萨座下法派”的“前因”;而进一步考察可知把一盏“灯”置于“歧路”的书名“歧路灯”之总体构想,也同样有佛典的渊源。
按据慧琳撰《一切经音义》卷第四十八引玄应撰《瑜伽师地论》、卷第六十七引《阿毘昙毘婆沙论》第一卷、卷第七十五引《禅法要解》上卷、卷第九十三引《续高僧传》,均唐代高僧玄应撰,而均用“歧路”一词;又赜藏主编集《古尊宿语录》卷第三《黄檗(希运)断际禅师宛陵录》云:“若无歧路心,一切取舍心,心如木石,始有学道分。”《五灯会元》卷第十八《南岳下十三世下·道场居慧禅师》有偈云:“百尺竿头弄影戏,不唯瞒你又瞒天。自笑平生歧路上,投老归来没一钱。”《法相辞典》释“歧路”引“《瑜伽》五十八卷二十一页云:问:何缘故疑说名歧路?答:似彼性故,障思智故。”如此等等,可说与在儒典中的少见和用意不同,“歧路”一词早自唐宋以降已经成为了佛典常用概念,堂上说法的寻常词藻。
由上所述论可知,中国典籍中“歧路”一词虽出《列子》,但后为汉译佛典引为法相之称,用指修行中使智性不明的疑惑之心,即“歧路心”。由此结合《佛学辞典》释“灯喻”云:“谓灯因膏油而焰焰无穷,以譬众生妄识,依贪爱境界而生生不绝也。论云:譬如灯光,识亦如是,依止贪爱诸法住故。”可知“歧路”与“灯”之关系,亦如“膏油”之于“灯”,“灯”因“膏油”而有光之明,也因“歧路”而有了存在的价值,并反过来照亮“歧路”之人。从而“歧路灯”即佛教禅宗的“心灯”,《禅宗语录辞典》引《虚堂和尚语录》云:
元宵上堂:世间之灯,莫若心灯最明。心灯一举,则毫芒刹海,光明如昼。
《歧路灯》之作,在作者就是“心灯一举”!这也就是为什么《歧路灯》的结局必然是谭绍闻能够回头向善、家道复兴的道理了。同时也就是作者在故事的开篇就感慨说“多亏他……改志换骨,结果也还得到了好处。要之,也把贫苦熬煎受够了”(第一回)的原因了。这里海观先生说谭绍闻“歧路”上所受贫苦拈用“熬煎”一词尤可玩味,即不由使人想到佛教“灯喻”中“油”与灯光即“明”的关系,用日常说法不过就是点灯熬油的“熬煎”而已。以此说“歧路灯”,其全面的名义不正是佛教“灯喻”的一个变相吗?而《歧路灯》一书作为小说中一部教子弟书,用笔多从反面写其受“熬煎”的过程的叙事写人特点,似也与其题含佛教“灯喻”之旨有一定的关系。
三、“这人姓谭”之“谭”
李绿园《歧路灯》虽“空中楼阁,毫无依傍……绝非影射”,但它成书在“四大奇书”之后,承前代小说家的传统,于人物设姓、命名、择字,都颇有讲究。如“王中”、“智周万”、“侯冠玉”、“钱万里”之类,皆有所谓,不必细论。这里但说书中所写这一“极有根柢人家”何以姓“谭”,并由此探讨绿园为此小说有些什么用心与特点。
《歧路灯》开篇入题说:“这话出于何处?出于河南省开封府祥符县萧墙街。这人姓谭,祖上原是江南丹徒人。宣德年间有个进士,叫谭永言,做了河南灵宝知县,不幸卒于官署,公子幼小,不能扶柩归里”云云,似只在引出正传。但读罢全书,回头来看,便不觉恍然有悟其“谭永言”之谓,实含有对此书体裁之提示,是其创作追求“谈说”风格的宣言。
按古代“谭”通“谈”,“永言”出《尚书·舜典》“诗言志,歌永言”,即长言,——长言诗人之“志”也。绿园博古通经,于小说开篇给他主人公著籍之祖以“谭永言”的大名,岂不是比附“歌永言”以寓说其欲追本《尚书》所称诗人之志,以所作小说为“永言”即一篇长“谭(谈)”吗?答案是肯定的。事实上作者也曾于书中作有“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提示:
王少湖心有照应,道:“谈班长,尊姓是那个字?”皂役道:“我自幼读过半年书,还记得是言字旁一个炎字。”少湖没再说话。姚皂役接道:“是谭相公一家子。”谈皂役道:“我可不敢仰攀。”姚皂役道:“何用谦虚。王大哥,夏大哥,咱举盅叫他二人认成一家子罢。”谈皂役道:“你年轻,不知事。这是胡来不得的。”姚皂役道:“一姓即一家。谭相公意下何如?休嫌弃俺这衙门头子。”谭绍闻见今日用军之地,既难当面分别良贱,又不好说“谭”“谈”不是一个字,只得随口答应了一个好。(第三十回)
这里借谭绍闻之口说作为姓氏的“谭”、“谈”不是一个字自然是对的。但“谭”字多义,有的义项上却正与“谈”相通,为同一个字的不同写法。《辞源》释“谭”字义项:“说。同谈。《庄子·则阳》:‘彭阳见王果曰:夫子何不谭我于王?’《释文》:‘音谈,本亦作谈,李云,说也。’”即可以为证。而“谈”即“谈说”(详后),《史记》载:“太史公曰:鲁连其指意虽不合大义,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荡然肆志,不诎於诸侯,谈说於当世,折卿相之权。”(《三家注史记》卷八十三《鲁仲连邹阳列传》)。因此,“谈说”本是称先秦游士以口舌取名位的一种手段。后世泛指,义近乎闲话。古代几乎为小说或近乎小说类杂书题名所专用,如唐代有胡璩撰《谭宾录》,明代有洪应明《菜根谭》,近代有许承尧《歙事闲谭》等,都是在“说”的义上以“谭”为“谈”的显例。李绿园决非不知“谭”字通“谈”有“说”字义,反而可能是他太清楚这个意思了,而做小说又需要曲径通幽,所以写书至第三十回思路已畅之际,借写一个皂役顺笔设作“谈班长”,把主人公姓“谭”与谈班长之“谈”略一牵缠,给书中主角“这人姓谭”之“谭”通“谈”之义作一提点,以期读者会心,恍悟其“谭永言”即“谈永言”,乃长篇之“谈说”也!此乃小说家的一点狡狯而已。
《歧路灯》以主人公“这人姓谭”之“谭”为宣示创作风格为“谈(说)”的寓意,还可以从李绿园曾著有戏曲《四谈集》(包括《谈大学》、《谈中庸》、《谈论语》、《谈孟子》四种)剧本的事实得到旁证。但那是以戏曲的形式“谈”学问,而在《歧路灯》来说,就是一本“谭(谈)永言”即长篇小说了。而对于这部长篇小说来说,这个“谭(谈)”字作为创作内容与风格上自律的一个原则,绿园《〈歧路灯〉自序》中有所说明云:
……填词家……藉科诨排场间,写出忠孝节烈,而善者自卓千古,丑者难保一身,使人读之为轩然笑,为潸然泪,即樵夫牧子厨妇爨婢,皆感动不容已……仿此意为撰《歧路灯》一册,田父所乐观,闺阁所愿闻。
由此看出绿园作《歧路灯》在内容上的用心明确是教忠教孝,惩恶扬善;在形式上所追求的则是“田父所乐观,闺阁所愿闻”,即“谈”即“谈说”的的风格。把这两点合起来的,恰好就是《歧路灯》中两代主人的名字即“谭孝移”、“谭绍闻”以及“谭绍衣”的寓意,和全书叙事最突出的特点。
按《歧路灯》写谭孝移字忠弼,“孝移”即移孝作忠之义,“忠弼”即为君之辅弼的忠臣。因此,谭家这老主人名“孝移”字“忠弼”的意思,合起来就是《孝经》所谓“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於君”之近乎全面的表达。古代所谓“求忠臣于孝子之门”,依据的正是儒家看来“孝移”与“忠弼”间的必然逻辑。按照这一逻辑,书中写谭家这位老主人就该移孝作忠、舍家为国了。再说他也早没有了父母,“孝”的事体已了,更应该一心在“忠弼”上做事业了。然而不然,谭孝移尽管并非没有做官行政一展其能进而为辅弼大臣的机会,却临场自动退却了。这是什么原因呢?书中第九、十两回写得清楚,一是天下无道,时机不利,只好学柏公识时务“奉身而退”(第十回);二是退而求其次,不能出为“忠弼”了,仍回来做祖宗的孝子也是要的。这在全书叙事来说,固然是为了使这个人物尽快淡出读者的视野,以迅速转入写他儿子谭绍闻失教的叙事中心的需要,但如此一来,客观上岂不是作者命他名“孝移”字“忠弼”的安排就成虚设了吗?其实不然!关键就在那个“谭”字!作者以谭孝移字忠弼者,不过借这个人物“谭(谈)”一下“孝移”与“忠弼”即“移孝作忠”的事理罢了,何至于一定是他真的移孝作忠了呢!书中第九、十两回中写柏永龄与谭孝移议论朝廷时局与士人出处的描写,正就是这位老主人公名字为“谭(谈)孝移”即“谭(谈)忠弼”的形象注脚。其意若曰,“孝移”、“忠弼”的事一“谭(谈)”而过,这位为作者写出“忠孝”而设的老主人形象也就完成任务该退场了。因此,《歧路灯》写谭孝移这个“纯儒”形象虽着实不令人喜欢,特别是写其进京面君的部分甚至显得枝蔓而有些沉闷,但从作者欲“谭(谈)”忠“谭(谈)”孝的立意来说,正是不可少,还恐怕是他自以为得意之笔呢!读者于此,也当对作者之心有所体谅也。
以此类推,“谭绍闻”和他的族兄“谭绍衣”取名自《尚书·康诰》,上下有关文字作:“王曰:‘呜呼!封,汝念哉!今民将在祇遹乃文考,绍闻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据注家说这是成王命康叔就国时的话。“绍闻衣德言”,孔《传》以为是对有“文德之父”,“继其所闻,服行其德,言以为政教”。《歧路灯》开篇即道“只因有一家极有根柢人家,祖、父都是老成典型,生出了一个极聪明的子弟。他家家教真是严密齐备,偏是这位公郎,只少了遵守两个字”,前说祖、父皆为“老成典型”,后说“这位公郎,只少了遵守两个字”(第一回),照应起来就是“这位公郎”名为“绍闻”,却没有好好“绍闻”。全部书的中心人物是“谭绍闻”,也就是“谈‘绍闻’”。所以今之学者大都认可《歧路灯》是一部教育小说,无疑是对的。因为“谭绍闻”之为“谈‘绍闻’”,“谭绍衣”为“谈‘绍衣’”本来的意思也就是“谈”如何造就一个好子弟,和如何做一个好子弟。这从作者的主观上来说是为世家子弟指出一条“绍闻衣德言”的正路,在客观上说就是教育。这一教育的中心则是接续了谭孝移教子尽孝的遗愿,做到《礼记·中庸》所谓“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所谓“绍闻”、“绍衣”者,其意义即在于此。只是谭绍闻为失足歧路而又浪子回头的典型,而谭绍衣却一直受到良好的教育又个人修持不失正路,因能“善继”、“善述”,“服行其德”,出仕后更能够“言以为政教”,是一个顺利成长的典型。所以有关谭绍衣的“谈”即笔墨虽然不多,但都是正面描写,只成“谈‘绍闻’”的陪衬。这一结果就是使《歧路灯》虽可以称之为“教育小说”,却与西方教育小说以正面描写教育的内容与过程不同,多是写反面的教训,而少有正面的经验,终于只是清中叶一位教书先生所作挽救失足青年的形象的教科书。倘非谭绍闻后来改过迁善和有谭绍衣正面形象的对照,这部书简直就成了彼时教育的反面教材。因此,书中谭绍衣的形象虽然着墨不多,却无论是作为提携谭绍闻的援手或作为谭绍闻的对照,都是不可或缺的人物。这一人物的明里暗里贯穿全书,实与谭绍闻的人生命运形成平行对照而又交叉互见的双线结构。这一人物的存在形态及其在结构上的地位与作用,与同时《红楼梦》中有甄宝玉似曾相识;而在外国文学中,后来可见俄国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中作为与安娜夫妇对照的列文与吉提,则与此有些相似。
从形式上看,“谭”即“谈”本是我国古小说悠久的传统。先秦至汉魏盛行的“谈”与“谈说”的风俗,曾是古小说产生于“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重要源头之一。例如战国齐人“驺衍谈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司马贞《索隐》),而有“谈天衍”(《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之称,其所称海外九州,开道教小说“十洲三岛”描写之先河。唐宋以降,士人中“谈”风渐息,但以“谈”字题名笔记小说者如《谈林》、《谈录》、《谈苑》、《谈薮》等等,指不胜屈,都是“谈”字通于小说的明证。李绿园于《歧路灯》所标举的“谭”即“谈”的用意,即在表明其欲直承上古“谈”即“谈说”的小说传统。为此,他虽然在力诋“四大奇书”,尤视《金瓶梅》为洪水猛兽的同时大量模拟借鉴“奇书”手法,但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脱出了“奇书文体”的牢笼与羁绊,而形成了明清小说中独特的“谭(谈)”的风格,本文简称曰“谭(谈)风”,并以为《歧路灯》的“谭(谈)风”固然有使其行文议论多而陈腐的毛病,但也至少促使其有了以下两个长处:
一是自觉地为人生而写作,全面完整地描写一个人物一生的命运。《歧路灯》之前的小说自然也是以这样那样方式写人生的。虽然比较《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的离现实人生较远,而《金瓶梅》写西门庆一生命运,已是更加贴近人生的主题,但《金瓶梅》于人生“单说着情色二字”(词话本第一回)。因“单说”之故,《金瓶梅》只从西门庆成家立业以后写起,重笔在其纵欲以至暴死的经历。所以《金瓶梅》作为我国第一部最贴近人生描写的长篇小说,却主要只是写了以性为中心的成人生活的一面。《歧路灯》则不然,作者李绿园于全书开篇即云:“话说人生在世,不过是成立覆败两端,而成立覆败之由,全在少年时候分路。”又说:“这话出于何处?出于河南省开封府祥符县萧墙街……”具体则是“这人姓谭(谈)”。这就等于说全书为“话说人生在世”内容的中心就是“谭(谈)”的“这个人”,他是“一家极有根柢人家”(第一回)的令郎,其五世曾祖为“谭(谈)永言”。可知作者下笔伊始,就明确其所写为“人生在世……成立覆败两端”,故从“少年时候分路”写起,以至其壮年和迟暮。这就比较包括《金瓶梅》在内的“四大奇书”有了一个明显的不同,即其所写是一个现实生活中人物全面的人生故事,是一部以一位世家子弟自幼至老起伏跌宕命运为中心的大开大合的长篇小说。这就构成了《歧路灯》结构的创新意义,正如八十年前郭绍虞先生称赞此书与《红楼梦》一样,“书中都有一个中心人物,由此中心人物点缀铺排……实是一个进步”。虽然郭先生未作深论,但现在我们可以说,这在《歧路灯》而言,是与其作者专为“话说人生在世”,而“谭(谈)”“这个人”和这“一家极有根柢人家”的“谭(谈)”旨,是分不开的。
二是刻意追求理趣、雅趣,平中见奇,风格凯切。《歧路灯》的理学气甚重是不争的事实。但是,除了某些陈腐的议论之外,其理学气主要是在欲以理服人的“谭(谈)”所谓“布帛菽粟之言……饮食教诲之气”中显现出来。却又要“田父所乐观,闺阁所愿闻”,这就不得不努力甚至刻意于追求通俗的风格,结果形成某种理趣、雅趣,郭绍虞先生评为“能于常谈中述至理,竟能于述至理中使人不觉是常谈。意清而语不陈,语不陈则意亦不觉得是清庸了。这实是他的难能处,也即是他的成功处。这种成功,全由于他精锐的思路与隽爽的笔性,足以驾驭这沉闷的题材。所以愈磨研愈刻画而愈透脱而愈空超。粗粗读去足以为之轩然笑而潸然泪;细细想来又足以使人惕然惊悚然惧。这是何等动人的力量!老死在语录文字中间者,几曾梦想得来”。笔者也曾引黄山谷跋陶渊明诗卷曰:“血气方刚时,读此诗如嚼枯木;及绵历世事,知决定无所用智。”认为“《歧路灯》大概即小说中之陶诗”。其意境在“四大奇书”的“奇”趣与《红楼梦》的“情”趣之外,似与《儒林外史》同属鲁迅所感慨的“伟大也要有人懂”一类以“理趣”见长的小说或曰学者小说相近。唯是《儒林外史》因高度“写实”而多成“讽刺”,故婉而多讽,清新峻峭;《歧路灯》意主劝世,故“谭”言娓娓,醇厚剀切。
综合以上考论,一向被认为深蒙儒学影响的李绿园《歧路灯》除因果报应的俗套之外,似无更多佛教的影响,但从人们往往熟视无睹的作者、书题的名义并结合于文本的实际看,李绿园与佛教的“前因”对是书创作影响的深重,远过于我们粗读此书后一般的感受。由此可见《歧路灯》思想有外儒内佛、以佛济儒和儒佛合一的特点;而是书命名主人公姓“谭”和设主要人物为“谭孝移”、“谭绍闻”、“谭绍衣”之意,既表明其创作以教忠教孝为旨的用心,也自定了“谈(说)”的风格,在“四大奇书”之后,《红楼梦》之外,别具一格。倘本文的考论无大不妥,则知《歧路灯》一书,虽不必如《红楼梦》可能引起过多的“索隐”、“揭谜”,但其某些方面内涵的深邃,创作用心与手法的精微,也非浅尝略观所容易明白,有时也还需要一点精研深究的考据功夫,才可以得其真义,与作者会心。
注:
① 颜之推《颜氏家训·风操》,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② 李绿园著,栾星校注《歧路灯》,中州书画社1980年版。本文以下引此书只在引文后括注回数,不另出注。
⑥ 吴秀玉《李绿园与其〈歧路灯〉研究》,台湾师大发行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13页。
⑦ 参考潘民中《浅证李绿园的佛缘》,《歧路灯》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组委会编《〈歧路灯〉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0年8月。
⑧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一《大学》,《船山遗书》同治本。
⑨ 严北溟、严捷译注《列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15-216页。
⑩ 王通《中说》,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