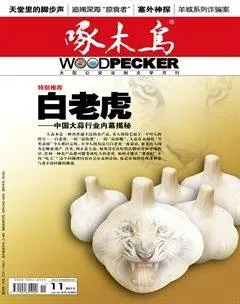蒜志
2013-12-02宋长征


你入瑶台,我落民间
“兄弟七八个,围着柱子坐,大家一分手,衣服就扯破。”你知道,我说的是一个比较低智商的谜语,也可以叫作民谣或儿歌。乡村穷,但从来蓬蓬勃勃,孩子多,且年纪相差不了几岁,兄弟姊妹,一帮小孩儿在母亲周围团团围坐,听母亲讲那过去的故事。
灯光昏黄,我偏爱这种乡村抒情。灯光一昏了一暗了,旧年的情境也便温暖起来。我们都是好孩子,我们都是土生土长的乡村接班人。
蒜也是。
蒜属百合科,托生的人家不错,但除了葱就是蒜,就是洋葱,韭菜,说来说去,离不了一个辣字。火辣辣,像极了乡下人的禀性。水仙则不同,水仙属于石蒜科,也有一个蒜,但有一个蒜字并不代表就和蒜一样低调。你看,水仙,文殊兰,君子兰,龙舌兰,听名字就让人咋舌。同样是蒜,为什么差别就那么大呢?别抱怨,天生万物,自然有序,每一株草木都有命中注定的气质。水仙作为花卉繁育的石蒜科,名字虽然不错,但生性娇小,没了大家风范。哪像我们蒜,大蒜,大大咧咧,清爽、火辣、甘辛,入心入肺。
母亲也种蒜,小小的菜畦,白露间,夜晚落了一层薄薄的霜雪,被太阳舌头一舔就化了。蒜,一瓣瓣剥好,只留一件象征性的内衣裤。我好奇,反正是长,不如让蒜拿大顶,倒栽葱栽进菜畦。来年春,菜畦里多是留白,看是好看,却引来母亲的疑惑,问我怎么回事。我支支吾吾。母亲发现是我的恶作剧,吃饭时说,你倒过头来试试,去拔菜畦里的草。我脸一红,没敢跟母亲顶嘴。却原来,蒜也不容欺哄。
凡是泥土里长出来的草木,都好看,水灵。是大地写下的诗。蒜也是,初生的蒜苗,移栽进花盆,不会比水仙门下的那些姊妹稍有逊色。只是委屈了蒜。乡间多好,土地多好,朝食清露,暮饮晚霜。雨声敲着鼓点,一瓣蒜就探出了嫩芽。燕子剪裁着家园之春,蒜叶青展展伸向天空。一碧如洗的天空,相信城市里的人是很难见到的。土地,无论丰腴或贫瘠,蒜不嫌弃,生在乡间的农人不嫌弃,那是安身立命的根本啊,人忘了根本,即使住进瑶池有何意义?
蒜能听懂我的话,围在一起,听母亲讲那过去的故事的孩子们已经慢慢长大。谁都记得,哪一天离开风中的柴门,哪一天母亲将新收的蒜,辫结成记忆的绳结,挂上门楣,每一个结扣,都记着一个乡下孩子成长的光阴。每一头蒜里,都有因清贫而储存起来的泪光与艰辛。
蒜的辣,想必总有一些渊源,说又说不出,放又放不下,除夕夜的鞭炮响过之后,新桃换了旧符,一碟蓉蓉的蒜泥端上来。醋是酸的,蒜是辣的,几滴麻油是香的,佐以水饺,所有的辛酸与悲苦也便甜了、香了起来。
石蒜科的水仙不懂,那是另一种形式上的美好,相当于生活之外的童话。你入瑶台,我落民间,互不相干,各有各的生活秩序。
蒜是一味药
蒜,如今的名字叫大蒜,简单到让人忘记了蒜的身世。就像一个漂荡已久的浪子,流落他乡,时间长了故乡变得模糊起来。但性格不会变,火性子的北地人,到了南方,也化不成一汪水,也变不成绕指柔。
蒜亦是,蒜是异邦来的一位高士。两千多年前,由汉使张骞从西域带回。漠漠风沙,漫漫荒滩戈壁,想必蒜早已忘记归家的路。可腔子里的赤诚与豪爽仍在,火辣辣的性子表明,骨子里仍流动着一股猎猎胡风。胡,没错,加上草头成葫,也就是蒜的古称,亦称作葫蒜。
蒜是一味药。《新修本草》中记载:下气,消谷,化肉。由此看来,蒜不仅仅是一位异乡来的高士,更像一位怀揣千金方的妙手神医,惠及中土大地,勘察民生,了解民间疾苦。
儿时,常有腹痛,泻,绞痛,豆大的汗珠颗颗滚落,砸在母亲的心上,生疼。灶膛里的火光明明灭灭,晚炊过后的余烬尚未失去火的温度。母亲将几枚蒜,独头蒜,投入余烬,慢慢煨熟。独头蒜该是蒜中的长子,其味辛辣,甚于兄弟七八个的蒜头。大概张骞出使西域归来时,带回的也是这种,只不过经过漫长岁月的浸淫,性格渐变为温和。温度,通过草木之火传递,辛辣,渐变为一种药,在煨熟的蒜里生成。剥开,浓浓的蒜香直冲鼻子,几乎迫不及待把独头蒜塞进肚子,绞痛,随之烟消云散。
又有鼻衄,俗称鼻子流血不止。人一瞬间赤白了小脸,前院的二娘最知道治疗鼻衄的应验良方。取大蒜一头,却不让人看见,在蒜臼子里捣碎,在掌心摊成小饼,约一豆厚薄。左鼻出血贴在左脚心,右鼻出血贴在右脚心。两个鼻子都出血呢?对,你答对了,贴在两个脚的脚心,鼻血刹那止住。当年,很多人不解,问二娘到底施了什么妙方,黑乎乎的,蒜气冲天。二娘羞愧地笑笑,还不是当年日子穷,想让你们捐几粒米下锅。黑乎乎的是从灶坑抓了一把草木灰,而蒜气冲天本身就是捣碎的蒜头,两者搀和在一起,即是止血良方。
也难怪,难为了二娘将蒜当作一门营生。如此,是比伸手去要来得让人心安。
草木之间,蒜作为平民在乡间游走。草最是缠人,但能安抚牛羊,庄稼显得高格,茫茫人世哪一天离了粮食也不能存活。唯独,蒜是边缘人,作为边缘人的蒜,就不得不在风雨乡野练就了一身异能。
现代医学研究证实,大蒜集一百多种药用和保健成分于一身,其中含硫挥发物四十三种,硫化亚磺酸(如大蒜素)酯类十三种、氨基酸九种、肽类八种、甙类十二种、酶类十一种。另外,蒜氨酸是大蒜独具的成分,当它进入血液时便成为大蒜素,这种大蒜素即使稀释十万倍仍能在瞬间杀死伤寒杆菌、痢疾杆菌、流感病毒等。
此外,大蒜可断亚硝胺类致癌物在体内的合成。到当前为止,其防癌效果在四十多种蔬菜、水果中,按金字塔排列,大蒜位于塔顶。在一百多种成分中,其中几十种成分都有单独的抗癌作用。
原谅我,蒜,和你在一起生活了许多年,初识你的悲悯与良善。人世可谓繁华,庖厨一事几成为行为艺术,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水里游的,只要人想得到的,便能红光满面大快朵颐。而进食之时,还是忘不了喊上一嗓子:老板,来一头大蒜。心中暗笑,到底是不能免俗的皮囊啊。你看大街上衣着光鲜的摩登女,大概在听说大蒜吃了能减肥的话后,也是趋之若鹜,嗲嗲地叫:蒜,我的小亲亲,你是我此生永不分离的另一半。
蒜不管,蒜只是性格甘辛、温和地从草本纪走来,入脾、胃、肺经,像一位真正的寒儒、大隐,生活在乡间。
从魏晋遗风里走来
蒜,除了是一位高士,隐士,我想更是一位从魏晋走来的名士,叫作嵇康或向秀。皇朝易帜,并不能改变一些人骨子里的清高,他们心性里向往不羁与自由,更把活着当作一门艺术。有一天,大司马钟会打马从柳树下经过,燃烧的火焰,和叮当的打铁声吸引了他的视线。当时大司马肯定在想,这就是不潜心仕途的下场,只能夜以继日地劳作,或许,再过一会儿他们会问我,需不需要打一柄长剑或两副马掌,会不会低声下气向我打听司马府是否缺少一个雇佣的杂役?但是没有,只见嵇康捋了捋袖子,向秀朝手心里吐了一口唾沫,又继续他们的打铁歌。便怏怏而去。
那时,嵇康投之以魏晋风流的青眼说: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答: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蒜听见了,蒜知道这也许就是流传已久的魏晋风骨,由着性子,月白风清,不食嗟来之食,也不谄媚于封疆之王。
而真正的王一定不会忌讳。话说到了唐代,唐人食蒜之风大炽。《太平御览》有记:成都王颖奉惠帝还洛阳,道中于客舍作食……天子啖两盂。燥蒜数枚,盐豉而已。说来让人有些怀疑,或许成都王颖舟车劳顿,大概真的饿得不行了,这才要来一头大蒜,就着腌好的豆豉,狼吞虎咽,竟然一口气吃下两大碗米饭。
我也喜欢吃蒜,虽不如村里酒鬼王大眼子有道行,一个蒜瓣喝下两口烧酒(一口半斤),却也有段时间离了蒜口中无味。《本草纲目》上说的“下谷化肉”,大概因为生活水平日渐提高,需要蒜来清淡一下胃口。蒜,这时候是兄弟,两眼清澈地望向你,心胸坦荡如砥。每次回家,母亲做好饭总是忘不了告诉我,窗户上挂着蒜,好像在提醒别忘了这位乡间兄弟。
怎么会呢,人一旦和蒜结拜,必忠肝赤胆,哪怕眼前放着山珍海味也会食之寡淡。《广王行记》载:“唐咸亨四年,洛州司户唐望之冬集计至五品,进止间有僧来觅。”这位僧人来干什么呢?大约也是一位苦行僧,赶脚累了,来向司户讨要一盘鱼吃吃(多气派,要饭也要得高格),司户信然答应。可谁知家人把一盘制作精美的桂花鲈鱼端上来,僧人又说:看有蒜否?言辞间颇有得陇望蜀之意。家人说:蒜尽。得买。我想当时司户的家人肯定有一股子怨气,真是个不知好歹的穷和尚,要鱼给你,你摆哪门子鸟谱。
依我看,僧亦是蒜的知音。你退却民间,我舍弃浮华,为的都是一个缘字,缘分未灭,蒜依然是穿越汉唐遗风的白衣秀士。且吟风听月,仗剑天涯,我自悠游山水间。
蒜的吃法
人的皮肤有黑有白,黑者往往给人一种强悍的感觉;白者就显得油头粉面了一些,善交际,做事圆润利滑。蒜也是,分为紫皮蒜和白皮蒜。紫皮蒜像个北方汉子,偏辣,味辛,揪一只蒜瓣丢嘴里,辣得浑身通泰,面有红光。白皮蒜,如江南美人,或许有点儿小性情,却总还算是小鸟依人,味甘,明目利胆。
说起吃蒜并不复杂,祖母自得腌渍之法。拔过蒜苔的新蒜,像害了相思,丢了三魂七魄,倾倾欲倒。七八天最好,祖母一边说,一边挎上柳条篮,喊我去蒜地拔蒜。新蒜收回,剪去蒜株与蒜的胡须,在底部用小刀挖了一个锥形小洞,浸在盛有清水的陶罐里,密封,用塑料布系紧。三日后,祖母在塑料布上扎了许多小孔,将水滗出,辣,辛臭。大概祖母原是为了给蒜们洗洗胃。
三十年后,我才知道山东有个叫丁宜的人,早就掌握了此种腌蒜之法,记在《农圃便览》里:“拔苔后七八日刨蒜,去总皮,每斤用盐七钱拌匀,时常颠弄。腌四日,装磁罐内,按实令满。竹衣封口,上插数孔,倒控出臭水。四五日取起,泥封,数日可用。用时随开随闭,勿冒风。”祖母没上过学,却通晓各种蔬菜的腌渍,这多少让我有些惊奇。大概,连蒜也不知道,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某个黄昏,一位鲁西南的小脚老太太虔诚地将一只陶罐抱在怀里,取出腌好的糖蒜,通体如玉,入口酸脆,甘甜。
《齐民要术》里讲的是八合齑,我想该是江南的细腻吃法,将一头平常的大蒜吃出味觉艺术,吃出美感。我等北人,耐不住那样的精细功夫,鸡蛋蒜(鸡蛋与蒜同捣)尚是好的,常有人一口蒸馍一口大蒜,吃得津津有味。好不好吃?你问。他娘的,通泰。哈你一口气,喷出一股大蒜来自西域的仆仆风尘。
今世的江湖与魅影
蒜依旧在田野上生长,时间的季风掠过山川,高原与丘陵,亦拨动当代社会的神经。有时我想,一头小小的蒜为何独有如此大的魅力,集药用保健一身,心系民生社稷。
面对一头蒜,也许你已经无法言说它的身世与生地,风沙漫漫的胡地也好,还是遥远的中亚和地中海地区。总之,蒜在清清白白之外,又弥漫着一种巫蛊之气,以一种接近神灵的魅影,来到民间,进驻都市。于万千气味中调和世界,保持着严肃与深邃的面孔。
鲁西南大蒜,以金乡为例,从一九八九年的十六万亩发展到八十余万亩,始终位居全国和世界县市之首,并荣获二○○二年上海吉尼斯证书。由于当地的自然条件优越,并采取了科学方法种植,金乡大蒜平均亩产一千二百公斤,最高可达三千多公斤。由此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并带动了一系列大蒜深加工企业,大蒜以及大蒜制品出口总量的比重始终处于首位。
说来说去,其实大蒜的精华大多集中于大蒜素这样一种神秘的物质之中。大蒜素,是从大蒜中提取的挥发性油状物,其中的三硫化物对病原微生物有较强的抑制和杀灭作用,二硫化物也有一定的抑菌和杀菌作用。
我曾参观过大蒜素提取的工艺流程,看起来不算复杂,其实相当严谨。在当地一家极具规模的工厂,弥漫着一种浓郁的大蒜气息。忙碌的工人将成熟、干燥、无虫蛀、无霉烂的蒜头,去蒂分瓣,清水漂洗。第二步就是将筛选好的蒜粒加工成糊状,类似我们平常食用的蒜泥。将蒜泥放入烘箱,文火烘干。然后将烘干的蒜块用粉碎机研磨成粉,过筛。蒜粉浸泡的流程尤为重要,用三十至四十度的白酒密封浸泡除臭。抽滤法,澄清的溶液悬浮于上层,即为无臭蒜素原液。
大蒜素粉的精华萃取,有效保留了大蒜所有的天然成分,纯度高,无异味,食用方便。也可以进一步加工成糖浆、乳剂、注射剂和大蒜素片,在活化细胞、促进能量产生方面效果奇特,祛脂降压,降糖防癌,调节肠胃。
今世的江湖已非昨日,大蒜作为一种朴素的乡间植物,早已化身成魅。大蒜素也许可以说成是大蒜的灵魂,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商品行销世界各地,流进现代人的血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