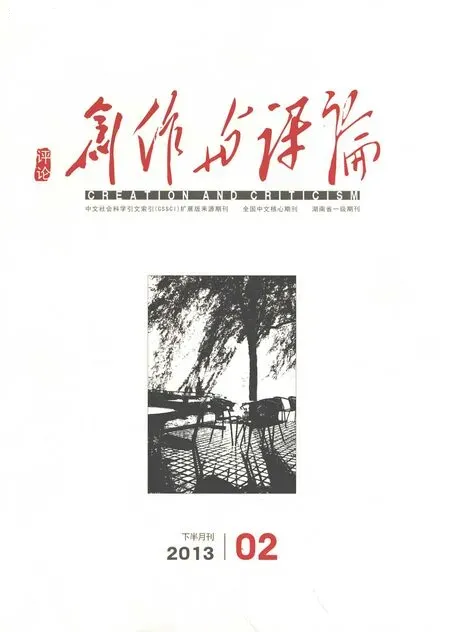一个村庄与一个文学空间的书写——龙红年诗歌论
2013-11-23苏文健
○ 苏文健
美国著名文学理论家哈罗德·布鲁姆认为:“诗比其他任何一种想象性的文学更能把它的过去鲜活地带进现在。”在某种意义上,文学创作是作家对自己过去记忆或者生存空间的重新书写与建构。我们知道,美国作家福克纳对“一张邮票大”的故乡的虚构书写,构筑了著名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大师加西亚·马尔克斯也因营构了文学史上有名的“马孔多”小镇而闻名于世。若以此观照龙红年诗歌,他则是以诗歌话语营构了文学空间审美意义上的“绕竹村”,它所彰显出的美学哲学意蕴,为我们思考“乡村内伤”与诗歌伦理提供了某种重要的启示。
一、走不出的绕竹村:那些人那些事
诗人龙红年在一次“创作感言”中曾这样道:“十六岁走出那个叫绕竹湾的村子,可我仍无法摆脱土地和乡村在灵魂里同我的纠缠……我决计在土地里扎下根来,让我的诗歌像家乡随处可见的水稻、麦子、蔬菜,或者是暮色里摇着尾巴回家的小狗……”土地与乡村是龙红年诗歌的底色,它要求创作贴近现实,展现人们处于逼仄的环境之下如何接受那些困惑、郁闷,它不仅表露了诗人的创作姿态,而且体现了诗人创作的美学追求。龙红年在《绕竹村》一诗中认为绕竹村是“大地上的一枚鞋印/土豆上的一粒斑点”,它甚至“小到虚无”,“小到心疼”,诗人在绕竹村发现了无限的诗意,在大地上平安牧放理想,从而构筑了别样的文学审美空间。在“绕竹村”这个特殊的空间中,那些人和事,在龙红年的诗歌话语中一一鲜活过来。乡村(文学空间)实际上是一个社会的缩影,乡村传奇人物与日常琐碎生活中的普通邻里的人物形象,质朴自然的亲情伦理关系等都在此空间中得到彰显,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切身体会。
第一,书写乡村的传奇人物或者日常生活中的普通邻里人物。穷乡僻野中的许多不起眼的底层人物都各具“传奇色彩”,且具有真实、富于人情味的品性。如《老家的一个邻居就要死了》写患肺癌的邻居,由于贫穷屡遭省、市医院拒绝,卖掉家里最后一只母鸡,只够到乡医院求医,结果可想而知。“为什么连一个肺结核也治不好呵”,邻居最普通的小事变成了一则“传奇”。又如《村庄的传奇》写一个八十岁老人的沧桑生命历程,“八十岁 你成了绕竹村/标志性建筑/八十年 你走过的桥/多过我走过的路/你和我父亲一样/用尽一生/仅从村西走到村东”,老人的一生经过多少“露水喂养饥饿的日子”,才会充满丰富的人生经验与难以言说的故事。八十岁的老人俨然是“村庄的传奇”,“村庄活着的典籍”。又如《一个铁匠的前世今生》,一个曾经的钢铁工人,无奈地放弃了绚烂的梦想,回到乡村自由的时光,逐渐地成为一个过期的铁匠,最终被命运冷却成一块生铁。铁匠过去是如何的绚烂与辉煌,如今却无意中成为世界之外的“一个标本”,“一张过期的票证”。底层乡村的人物如铁匠、邻居、老人、暮色里的赶路人等千姿百态,各具特色,虽然他们身上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但都是一部“乡村传奇”,诗人书写这些人情物理,自然地流露出悲天悯人的道德关怀。
第二,刻写乡村日常生活中质朴自然的家常伦理与亲情。“乡土中国”与传统宗法伦理密切相关,它们共同内化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人与人、家常之间最质朴纯真的亲情伦理。龙红年在《想起母亲》中写孤独的母亲,饱含深情,“而在乡村/母亲坚守空房/破旧老屋里打发生命/蛛网结在四周/自发生在贫寂的日子”。母亲靠对死去的父亲的怀念与灵魂对话来寻求精神的慰藉,寻求活下去的理由,诗人这样写道,母亲“不再斜倚木门眺望远方/母亲的远方在斑驳的墙上/透过粗糙的玻璃/父亲多年前的目光探来/眷意盎然 在内心深处”,母亲眺望的双眼与父亲多年前探来的目光互相交接,静静地对话,但是母亲的一双老眼“终陷落为一双空巢/没有一只鸟 来栖息……”,诗人还在《坐北朝南》 《收拾》等多首诗歌中书写自己对母亲的愧疚与感伤。这些诗歌,没有雕琢的词藻,也没有大起大落的事件转折,但是其诗歌话语在整体上酝酿着自然真挚的深情,流露着淡淡的哀伤,在内敛克制的语词中饱含巨大的情感张力。
以传统宗法伦理为扭结的乡村,日常生活的亲情往往呈现细腻或者难以言表的心照不宣,这种情感似乎一股潜流在他们身上流淌。《六叔》描写一个七十多岁跛着一条腿的打工仔六叔,因风雪无法赶回家过年,被困于广州郊区的一个石棉瓦盖的工棚里独自过年,被风雪虏获,和着雪花喝自酿的米酒,“正月十二终于回到家乡/正月十五查出结果/正月十六将两万存款交给儿子/鞭炮声在屋外噼噼啪啪响起/六叔,从此与世无争……”《姨妈突然走了》书写高血压突然带走了姨妈的生命,“一滴露水在风中/出人意料地干涸/高山之上的一个早晨/她为菜地锄草松土/来回百米提水浇灌/血压悄然攀上山顶/七十五年的一口井/不知不觉到了底”,一个人的死给生者留下了诸多的忧伤:喝酒成疯的姨父突然清醒,八十岁的母亲伤心哭泣地,其中的乡土亲情伦理关系,真挚、质朴动人。还如描写勇敢坚强的老嫂子(《老嫂子》)、朴素可亲的父亲(《寻人启事》)、出世几天即夭折的姐姐(《未曾谋面的姐姐》)、还有当村支书的兄长(《当村支书的兄长》)等等,这些诗作都抓住普通人物一生中最具有转折性的事件进行抒写,并以此勾连过去与将来,从而使得人与事更具立体感,诗歌更具感染力与穿透力。
简言之,龙红年对绕竹村日常生活中的人情物理的书写与刻画,没有波澜起伏的情节,也没有华丽的语言修辞,而是运用质朴自然、不假雕琢的平易语言娓娓道来,抒写乡村普通人的生命与悲欢离合,给人营造一种身临其境的氛围。这些诗作平实而质朴,坚韧而流动,细致而真切,看似失之技巧但得之真挚,看似无情却有情,充溢着人文关怀的光亮。诗人龙红年敏感细腻的情感触角与在平凡中发现诗意的才能在在可见。
二、乡村内伤:消逝的家园
现代工业文明高速发展,无可避免地给乡村带来颠覆性的变化。在理性主义至上的作用下,乡村一些古老文化传统习俗也会随之被消解。乡村的“祛魅”,美好家园的消逝,造成了“乡村内伤”。龙红年关于“绕竹村”“乡村内伤”的叙事与抒情,在文学空间意义上,不仅体现在自然物质家园上,而且反映在人与人之间亲情伦理的精神家园上。
首先,在大自然物质家园中,“乡村内伤”随处可见,它在“绕竹村”的文学审美空间中,形成一道道疤痕。家园的消逝或荒芜,使人对过去曾有的无限美好带来诸多的追忆与伤怀。如在《家园》中,诗人怀想土地的芬芳,“晚稻在秋光里摇曳/一粒大米的芬芳满含悲壮/一堆堆卵石裸露在风里”,诗人放飞遐想:“防洪林挂着兽啃的伤痕/夕晖里 炊烟缓缓升起/老牛和牧童从古诗中回家/穿过民谣的吉祥鸟/再度飞进 我的家园”,夕晖里炊烟缓缓升起,老牛和牧童在古诗中走向家园,穿过民谣的吉祥鸟,飞进诗人的家园,这幅诗意田园般的诗性构想图景令人神往。失落了的美好家园不仅是人类的栖居之所,更是人类精神的乐园,洋溢着宁静慈祥的氛围。在《扛起一肩暮色》中,诗人写道:“秋天的阳光/一点点减去/一块地被抛荒/是乡村一个崭新的窟窿”。田园荒芜、人员流失消减,都是“乡村内伤”的直接体现。而《野兽的叫声从冬夜的田野传来》则描写野兽在现代工业文明中逐渐地失去了藏身之所,曾有的乐园慢慢地被人类的机器吞噬着,野兽的叫声凄迷,落进忧伤,变成无家可归的野兽在流浪。诗人写道:“黑夜蔓延河水空响/它细长的腿/在田野上迟疑走过/收获后的土地/没有留下它 藏身之所”。人与自然的对抗,最终带来的是人自身的毁灭。在这些低回的诗歌话语中,诗人的忧愤之情不言自明。
诗人书写家园消逝的惆怅,也抒写人们对美好事物的无限向往。如在《从一条小河开始想念家乡》中,借镜小河上溯村庄的过去,打量它们的现在,想象它们的未来。小河隐藏着诗人与村庄丰厚的想象性记忆。还有,诗人看见麻雀的快乐与天真想起了多年前那个捣蛋的少年,现在想来充满悔恨,害怕麻雀认出“我”“心底的风雨和岁月中腐败的稻草人”,但是当“我”认识到麻雀们的目光坦然,身子纯洁透明的时候,尽管一颗粪便落在头顶,也感到格外温暖(《麻雀们》)。麻雀们的自由天真、纯洁透明更衬托出人的委琐与低矮,鸟犹如此,人何以堪?
其次,在人与人之间的亲情伦理上,精神家园上的“内伤”对于乡村而言更具有根性或颠覆性。在以传统宗法伦理为基础的乡村,亲情伦理在维系他们内在精神上有重要作用。一旦失去这种维系,他们便顿时陷入精神困境,甚至有被连根拔起的抽空感。如《乡间消逝》写日常生活中一个简简单单、普普通通、平平凡凡的“个人”,“一个简单的乡下人/稍不留神就消逝了”。乡村的一切都很不起眼,没有丰厚动人的故事情节,只有单薄粗糙的日常琐碎。而在《这些人,数着数着就少了》中,描写一种“老去的美丽”。强大的亲友团见证着“我”的成长,他们的包容与容忍铸就了“我”的品性,“在这世上 只有他们能将我的缺点包容/一如容忍 米饭里的谷子 菜叶上的虫/麦地里的青草和土豆上的那些斑点/如今 他们在我的指缝中消逝/在绕竹村 我再不可能遇见他们/偶尔想念 也只能在风中闻到/他们无比亲切的气息……”“我”走得再远也逃不出家乡的所有馈赠,乡村原初深处的记忆总是在缠绕着诗人的思想。《老树》则通过描写老树的扎根姿态。树上的鸟虽有过飞出去的心思,但最终还是飞了回来,诗人由此联想到人落叶归根、思念故土的情怀,诗的最后写道:“一棵树老了/会再长出些青翠的爱恋/一个人走了/影子 渐渐旧掉”。诗人从老树联想到树上的鸟,再联想到人自己,它们三者都具有落叶归根思念旧林的扎根姿态,但是人死了连影子也旧掉老去,一方面反映出时光岁月的冷酷与残忍,另一方面也体现生命个体的短暂与渺小。时间永恒流驶,一切都在老去,人的生死离别与物的新旧更替都会给乡村留下巨大的“内伤”。
总之,诗人通过对家园物质记忆的打捞与亲情伦理踪迹的追寻,着力书写一种老去的美丽,整体上充满想象与追思,呈现出一种感伤与惋惜的情调,透露出诗性或者哲性的美学思考。在某种意义上,诗人以“创伤叙事”为视角不断地修复改写个人的经验与记忆,使得对“乡村内伤”的书写裹挟着缕缕挽歌般的哀伤气息。
三、诗性正义:文学空间意义上的“绕竹村”
龙红年诗歌着力营构美学意义上“绕竹村”的文学空间,里面的一人一事、一景一物都染上了诗人真切的生命体验与乡土情怀,更融入了诗人对“乡村内伤”深刻的美学思考,尤其是其中彰显出来的人文关怀思想与悲悯哀伤话语,与诗歌写作伦理、诗性正义密切相关。
第一,“乡村内伤”的书写视角。以此视角对乡村人情物理的细致变化及其幽暗处,进行独特书写与忧思,透露出浓厚的人文关怀思想。如《一个农民工的遭遇》写被盘剥的农民工,在年关不但没有领到一分钱,还遭受包工头雇来打手的铁棒威吓,“没有工资我们怎么过年呵/十根铁棒/替包工头做了回答……”一个六十岁的人,“被人从长沙抬回来/在除夕夜 成了植物人”。去找包工头讨个说法却早已不见包工头的踪影,去报案派出所却说没有证据,再找民工作证却再也没有愿意开口的,“于是他只能像一株植物/眼睁睁地 看青天和白日/怎样将自己掩埋”。这种现象现在屡见不鲜,诗人的社会伦理关怀体现在他能如实地书写这些社会的“内伤”。又如《想念晓文》写小公务员晓文在残酷的现实中不断挣扎的命运。二十岁开始,晓文就努力摆脱乡村的贫困向往繁华的都市,并在城市中连滚带爬一路挣扎着:“晓文在银行工作 办公室秘书/为比自己年龄更小的领导服务/写材料 出通知 上蹿下跳 安排吃喝/弄些成果辉煌之类的新闻上日报”。诗人继续写道:“晓文有着相当经典的微笑/只有到深夜 瘦到百来斤的晓文/脱掉尘世的外衣 露出几根硬骨头/露出他仅有的几颗铁钉/在黑夜里发光”。现代社会犹如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牢笼”,我们身处其中,只能绝望地瞎折腾与无奈地挣扎,恰如西西弗斯一样,不是英雄,一直在做着徒劳的虚妄举动。诗最后以一个生动的比喻作结:“人到中年 依旧保持冲锋的姿态/晓文使我想起深桶里的一只青蛙/在命运的合围中 不停地蹦达”。在此,只有现实生活的巨大荒诞与生命的坚韧,诗人生动地刻写了我们当下人们生存的境况。还有如《背着一场雨奔跑》、《鲜花屋》、《一个人白天躺在大桥底下酣睡》、《我牵挂的人又少了一个》等都着力对底层民众的日常生活暗处的描写,都表现大致相同的情感与悲愤,寄寓着诗人深深的忧思与伤怀,体现着诗人的人文关怀与诗性正义。
第二,反讽修辞的巧妙运用。龙红年以“一种暗含嘲讽、否定意味和揭蔽性质的委婉幽隐的修辞”,回避直陈的程式,含蓄地揭穿假相,更为睿智地表达了诗人的“诗性正义”。《当村支书的兄长》一诗就有很出色的体现。诗人描写“意外”地选上村支书的兄长。“纯属意外事件/八十岁的老娘/都把选票投了别人/结果 兄长还是选上了/村支书”。兄长从此不能再到外面打工闯荡而是开始纠缠在村中鸡毛蒜皮的琐碎,“一辆二手摩托在村道上穿梭/好多矛盾和纠纷/都熄了火”,“拿钱救济了孤儿寡母/拿钱修了村道水渠/拿钱补了漏雨的村小”。不愿当但还是选上了村支书的兄长把自己豁出去了,不存一丝私心,纯朴得透明。结果如何?诗人接着写道:“并不富裕的兄长/每月就领着一百元的补贴/一下子瘦得/跟他家下过崽的/母狗似的”。诚然,村支书也是一个“干部”,也是一个“官”,它因了权力与金钱的巨大诱惑而吸引着人。但在人人都为权力与金钱而不择手段的时候,不愿当村支书的兄长,纯朴、怀着“理想”的兄长却“不幸地”又一次充当了一次“纯属意外事件”的主角,滑稽可笑的同时又透出几分酸楚与讽刺意味。“意外事件”背后的假相在此暴露无遗,此诗貌似对当村支书的兄长表示赞叹,实则表示了一种无奈和对社会恶劣丑行冷静的鞭笞与批判。《井下遇难的四个女工》写“从未想过要出名”的四个普通农村妇女在一次矿井透水灾难中“一夜成名”的“神话”。“矿井透水的一刻/她们败给了暗处的汹涌”,“一个紧挨一个/一副生死不分的模样”出现“在党报三百字的新闻里”,以生命换来“一夜成名”。但是“矿主在省城的赌桌上/一掷百万 然后/仅用八十万赔偿金/买断她们生命”。此诗在言与意的错位与悖反的话语张力中,蕴含着诗人激烈的反讽与忿恨。而《没有厕所的村小》则写乡村小学厕所的三个精彩场面,运用“戏拟”具体手法达到反讽的效果,乡村的美丽与简陋清晰可见。再如《2009:湘江断流》描写湘江的前世今生,流露出无限的悲愤之情。湘江北去,百舸争流,洋溢着八十年前“诗人”的激情壮志。而八十年后的湘江,只见“厂子里的污水还在排放/中计的鱼亮出腹部/水位仍在回落 湘江/如一个败走麦城者/想刻舟求剑的人 十秒钟/成了市场的干鱼”。诗人在对比映衬中营造了诗歌话语的修辞效果。
在反讽的修辞中,透过龙红年诗歌深层精神纹理,我们可以窥听到一些苦涩无奈的轻叹,但其中的温暖言述同样值得注意。如《与擦鞋女桂花的浪漫》,通过写“我”与擦鞋女桂花的一次“浪漫”来描写底层劳动人民的艰辛与欢乐。“我在她眼里看到桂花的香”,桂花的落落大方与“令人有些醉意”的美丽不免让人“想入非非”,“有一次擦完鞋我逗她/今天没带钱 怎么办哩/她低着眉 说:/让你欠我一辈子才好哩”。这首诗俏皮精巧,读来忍俊不禁。还有《在清晨 在寒风中》等多首诗歌也是如此,生活在底层的人们努力地活得有尊严,找回个体自我身份认同的存在依据。总之,龙红年运用言在此而意在彼、正话反说、戏拟、对比等造成反讽修辞,加深了诗歌话语对社会批判的力度与深度。
第三,“低处”姿态的自觉诉求与营构。“低处”是一种姿态,更是一种立场,因为只有以“低处”的姿态才可以发现更多的美丽,才能感受到生命中更多精彩的瞬间。诗人在《低处》中如是唱道:“孕雨云在低处/稻子在低处/绕竹村 在低处//低处看见土豆的心思/一垄水稻/五月铺一匹绿绸/七月取回遍地黄金/乡道旁 蚂蚁迎宾/听得见鼓乐齐鸣”。在此,“低处”姿态或者“低处哲学”不是标榜,而是乡村“土地伦理”立场的本真呈现,人在世界之中存在,需要一种谦卑的态度,以此态度观照世界的万事万物,那么它们都会带上盎然的气息。现代社会中一切的主宰立场与主体万能的心态都被视为病态,它的根源在于大写的“人”的无限膨胀。在诗人看来,返回“低处”,贴着地面前行,正可以克服这样的恶陋与异化,使人返回天真谦逊的天性,返回自然纯朴的美好家园。此外,“低处”立场它本身也要求张扬一种“慢的姿态”,“低处哲学”与“慢的姿态”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在《摩的》中,诗人描写城市人的芜杂生活,一个老人,一个孩子和一个扒手,他们的关系简单得只需两块钱,这难道是城市破败的风景?这是诗人的疑问,也是我们的疑问。城管与扒手,偷袭与被监看,犹如穿梭的老鼠或者摩的,其中的角逐充满抵抗与越界的纠结。城市“人群中的人”构成一张无形错综的权力之网。诗人最后感叹道:“看到你们/在城市的喉管心脏或胃边飞奔/我只能在心底为你们祈祷:/兄弟在祖国的大街小巷/你莫惊慌 速度要慢些/——请再慢些”。摩的象征速度,而生活的快速度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与冷漠,进而使得“城市破败的风景”随处上演。因此,诗人提倡一种“慢”的姿态,“慢下来的时钟 就是一个慢下来的童年/月光下 他用倒影牵我回家”(《慢下来的时钟》)。在整个社会都追求“快”的时候,诗人能够静心地营构一种“慢的哲学”,这本身就是一种对抗,一种关怀,更是一种勇气,它也是诗人对土地和乡村的内在情感的最自然最直接的流露。总而言之,乡村内伤的视角、反讽修辞的运用与“低处”姿态的立场,在诗性正义的维度上,它们一起丰富了“绕竹村”文学空间的审美意义。
龙红年在他的“绕竹村”系列书写中流露着浓厚的人文关怀思想,试图通过反讽、隐喻等修辞来修复或改写曾经存在的美好记忆,构筑了“绕竹村”这一个独特的文学空间,以乡村的人与事的书写把握着“乡村内伤”的内在张力。
龙红年的诗歌话语融入了自己丰富多重的个人记忆、经验,纠结着乡村传统习俗文明在现代社会失效的诗性或哲性思考,在质朴的诗歌话语修辞中寄寓了诗人对乡村秩序与文明的追思与忧伤,这种“诗性正义”为“乡村内伤”与诗歌写作伦理提供了重要的诗学启示。虽然在词与物的对话关系上,在诗歌意象的营构上,诗歌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但无论是从个人诗歌创作史来说,还是将其置于中国诗坛的当下背景,龙红年的诗歌都实现了新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