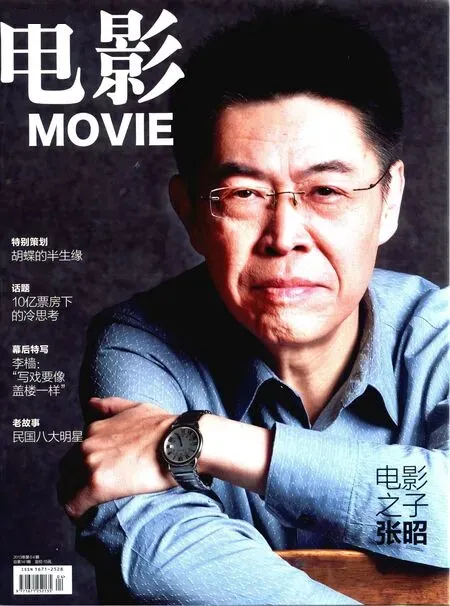电影,是一时一地的一个我
2013-11-21木夕
文/木夕
32年前,我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小县城。县城里全部的文化设施就是一个电影院+一个剧院。
小时候,看电影和去公园一样是一种福利。那时候爸爸单位偶尔会发票,每个大人可以带一个小孩儿,我就坐在爸爸的腿上,抱着妈妈给我准备的红黑格子小包吃零食。后来,妈妈调动工作,新单位就在电影院对面。妈妈偶尔带我一起上班,跟电影院看门的叔叔打个招呼,我就能在里面看一下午。今天回想起来,演员、故事、情节都不记得了,只记得有一次电影院画海报的那个叔叔指着满地的油彩问我画的像不像?我摇摇头说不像不像。
后来上小学,看电影变成一种集体活动,出发前老师会反复强调纪律:走路要手拉手、队形不能乱、看电影不许说话、回来要交观后感……我天生好动,这些都是挑战。那时候我总是很羡慕五年级的姐姐,因为她看完电影还能记住董存瑞炸的是哪一场战役、哪个中学、哪一个碉堡,写的作文也总能得奖。
初中、高中,班主任把体育课都换成了数学课,看电影成了一种奢侈。终于上了大学,我看的第一场电影是在学校后面小街上的一个地下录像厅。录像厅门外有一块黑板,上面写着每天要放的片子,每天下午四点是一元钱一场的精品场,回放一些经典的外国电影。那时候文科班的哲学课安排在周一下午一点,我总是坐在教室最后一排。夏天,风吹着窗帘盖在身上,一觉醒来,正好能赶上小电影院的精品场。《罗马假日》《金色的池塘》《廊桥遗梦》《克莱默夫妇》《魂断蓝桥》……都是从那里开始的。也算是做产业链吧,录像厅旁边有一个简易的报刊厅,里面常常有各种各样撕去版权页的便宜电影杂志,买回来一起翻,茱莉亚·罗伯茨的嘴、凯瑟琳·泽塔琼斯的婚姻、黛米·摩尔是否吸毒都是女生宿舍的热门话题。那时候,骨子里有一点小叛逆,最喜欢的明星是苏菲·玛索。那时候宿舍还没有电视,周末回家会追电影频道的佳片有约。
后来学校的新图书馆竣工,增加了多媒体厅,门口一本厚厚的目录本,办张卡就可以点播自己想看的片子。一个学期,我从《西雅图不眠夜》看到《两个人的车站》,还记得我说要看《周渔的火车》的时候,看机房的老师上下打量一番,然后义正词严地说:“这个片子刚来,我还没审过,你们不能看!”
当时,系里有一个女孩儿看片海量,有一次在多媒体室遇到,她给我推荐了《蓝色大门》。初见,以为是一个闹闹的偶像剧,于是放下。朋友再三催促,才交差式地拣起,谁知一发而不可收拾。那一年,也是在一个有海的城市里,我看完了张世豪和孟克柔的故事:没有结局,但是有一个秘密、一个约定。渐渐地,电影对我而言成为一种除文字之外全新的语言,每秒24格,迎面而来,拂袖而去。帧与帧的排列组合让我想起《红楼梦》里的“丁香结子芙蓉绦、不系明珠系宝刀”,干净利落。
毕业、求职、辗转、无果。几经反复,心头那点关于电影的念想再次浮出水面——要一个跟电影有关的身份。碰过壁,梦想这个词便不再轻易提起,但心里会偷偷憧憬,憧憬有一个机会像《蓝色大门》一样错而不过、失而复得。偶尔也会学孟克柔,把心愿写在纸上,一遍一遍,想着墨水用完它就能实现。之后有将近大半年的时间不再看电影,朋友问起我会开玩笑,“今天不看,为了将来每天都能看。”
2005年,我如愿来到北京。北师大艺术楼101、北国剧场、敬文讲坛、艺术影院……劲头足的时候一天能看四、五个片子,晚上一群人天南地北、指点江山。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年多。慢慢地,初到北京的新鲜感逐渐淡去。生活像一部事先没有走场、事后来不及剪辑的电影,现实、琐碎,甚至是沮丧。人也会本能地懒惰、倦怠、健忘,不再想将来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大人。一天收拾DVD,重新翻出《蓝色大门》。再看已然不是当年的心境,但是台北的阳光、海滩让我瞬间回到了曾经的大连,瞬间,呼吸里也有了海水的味道。
工作四年,做着跟电影有关的工作,有一个跟电影多少有点关系的身份。把喜好变成工作,常常也会厌倦、沮丧、挫败。这时候,偶尔会再翻出《蓝色大门》,对着电脑屏幕吹吹海风。
2012年参加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报道,传媒大奖的颁奖典礼上主持人问每个评委电影是什么?每个人,每时每刻总有不同的答案。在我,电影是一种可能,它意味着千千万万我不曾、不能经历的角色、人生;电影,也是一时一地的一个我,时而在路上,时而已经抵达。它提醒我,低谷时自信,膨胀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