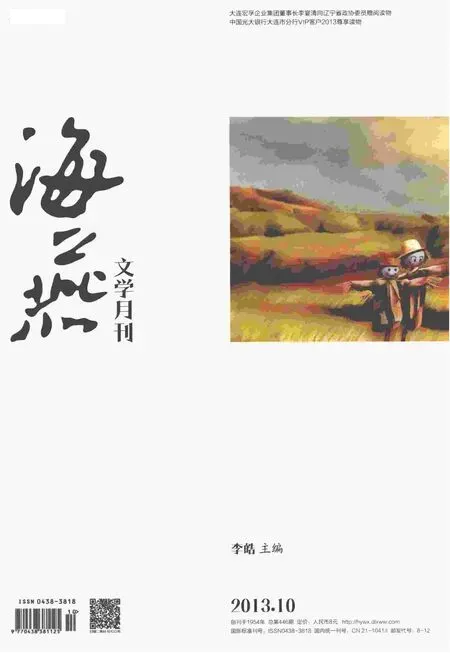拉拉嘴子•轻腚啷当
2013-11-16董晓葵
□董晓葵
在一商务酒店吃饭,见菜牌上有一行黑字:啖蟹热线。作为品读大连话的作者,我极为惊喜,遂向服务生建议写成“歹蟹热线”,大连话的“歹”由“啖”而来。服务生说:“歹”太难听了,你们大连话太土了!土气是各地方言的共同气质,没有哪座城市的方言是高雅的,方言土语素来土得扎实、亲切,土得趣味纵生,魅力四射。当然,如果只是一味地土气,那也低估了方言的特殊魅力。土得掉渣的方言,有着令人叫绝的摹情状物的功夫,那浑然天成的贴切简直令普通话失去作为。
曾记否,20世纪90年代,常见甘井子一带的饭馆在窗上贴一行红色草书:杀猪菜,血受!血受,即纵任奔逸、血脉不断的草书心情。“歹蟹热线”也可以用嘛,南方人吃蟹子摆一套精细工具,细细地啖,而北方人吃蟹子,一掰两半,左一口,右一口,完事了,“歹”最能体现这种粗犷与蛮气。
在各地方言库里,含贬义色彩的方言占比不小,它们趣味强,传播广。品读大连话你会发现,对于举止失宜、才疏学浅的形容比比皆是,若从中拽出两个代表,应是“拉拉嘴子”和“轻腚啷当”两例。
拉拉嘴子
拉拉嘴子,是指班级里的后进生,同义词是“拉巴丢”。
大连作家陈昌平在长篇小说《国家机密》里描写了一个擅长做梦、预言现实的男孩儿,他名叫小六子。他做的梦分为大梦和小梦,大梦是梦见毛主席的梦,小梦就是大梦之外的所有梦。小六子和伙伴们在老街上茁壮成长,滚铁环、抽陀螺、打弹弓、跳房子、骑马打仗、警察抓特务……他们不仅会玩游戏,更会发明游戏。“那时候,只要有一个人要撒尿,其他人马上传染一样地都要撒尿。于是大斌就把撒尿提拔成一项赛事——第一看谁滋得高,第二看谁时间长。大斌嘴含铁哨,‘嘟’地一声令下,每个人都腆起肚子,使劲儿往墙上吱吱吱地射尿。墙上顿时涌现出一波一波的湿线,脚下生成一条条生动活泼的蛇流……这是几乎每天都有的一项比赛,只是小六子的战绩一向不太好。因为小伙伴们的个头比他高、小鸡鸡比他大,所以即使小六子每一次比赛都使出改天换地的劲儿,也从来就是一个拉巴丢儿。”
论大连足球,有人说“阿尔滨没有乌塔卡就是个拉拉嘴子”、“我赞成两队合并,那些靠钱和关系踢上比赛的家伙赶紧消失,留在大连的必须是人才,拉拉嘴子请走人!”、“国内门将除了王大雷,其余都是些拉拉嘴子。”
关于“嘴子”的方言不少,天津方言“卫嘴子”,是指天津人能说会道,口才非凡;武汉方言“火嘴子”是指在嘴周生发的脓血小包;河南方言“扁嘴子”是指鸭子。这些“嘴子”都没有“拉拉嘴子”生动形象,“拉拉嘴子”是什么样子呢?衣衫不整,蓬头垢面,歪眉斜溜嘴,嘴角流涎,做什么都不敢趟儿,提溜着裤子鞋还掉了,要么是精疲力竭的休克状态,要么是疲沓慵懒的麻木状态。从上到下,由内而外,都是一副“脏乱差”。
林语堂在《北方与南方》一文中对南北两地人有生动描绘。“习惯于简单质朴的思维和艰苦的生活,身材高大健壮,性格热情幽默,吃大葱,爱开玩笑。”这说的不就是咱大连爷们吗?关于南方人,“在东南边疆,长江以南,人们会看到另一种人。他们习惯于安逸,勤于修养,老于世故,头脑发达,身体退化,喜欢诗歌,喜欢舒适。他们是圆滑但发育不全的男人,苗条但神经衰弱的女人。他们喝燕窝汤,吃莲子。”大葱与莲子,以这两样物质来区分南北两地人,简直令人倾倒。
对于南北语言上的差别,林语堂讲了一段小故事:一位北方军官检阅一队苏州籍士兵,他用洪亮的声音喊:“开步——走!”士兵们都纹丝不动,北方军官蒙了。一位苏州籍连长知道其中奥秘,请求用他的办法来下命令。长官允许了。他没有用洪亮清晰的声音喊:“开步——走!”而是用婉转诱人的苏州腔喊道:开——步——走——嗳——结果,苏州连乖乖前进了。
回头说大连话。以三、四声为基本调,一水儿洪亮脆生,铿锵有力,大连话是“开步——走”,绝不拖泥带水,绝不拖腔拉韵,缠绵不休。
“拉拉嘴子”多用来形容孩子。“老张的大孙子在班里是个拉拉嘴子,老张的儿子儿媳妇都是人精,这孩子没一丁点像父母。”“俺班那个拉拉嘴子,在操场上抓了条泥蚯夹在我书里,吓死我了!”成人世界里也有一些“拉拉嘴子”,才学浅薄,品德欠佳,大连人不说“拉拉嘴子”,说一声“哈啦”——“那是个哈啦!”方言的语焉不详,令人百思不解欲罢不能。
轻腚啷当
以“轻腚啷当”为首、形容一个人性格过度外向、言谈举止夸张轻浮、做事不稳不靠谱的大连话有一小撮儿,比如:小腚飘轻、得瑟腚、蹀躞、得瑟等。
某人没什么真才实学,却一心想当官,有人私下嘲讽:“得瑟着二两腚削脑袋尖往上爬,浑身没有二两重。”某村有一个小媳妇,不爱干农活儿,就爱抱着洗衣盆去村头小河边洗衣服,小河水清亮亮,映着小媳妇美丽的脸庞,边洗衣边与其他小媳妇八卦人间。小媳妇们抱着洗衣盆向小河边走去的样子就是“小腚飘轻”。在此处,“小腚飘轻”是中性词。在职场,“小腚飘轻”却是贬义词。某员工能力不咋地,还爱偷懒耍滑,成天“小腚飘轻”往领导屋里钻。到此处,戛然而止,没有下回分解。
城市不大,你转身碰见了我二大爷,我一回头遇见了你三舅母,人,原来是不经打听的。“那是个得瑟腚,你有话可不能跟他讲,没啥真玩意儿。”分明说的是下半身,怎么与上半身联系上了呢?方言的土气与粗俗就来源于此。武汉有一条方言叫“撇胯子”,是指水平很差的人。
从字面上看,蹀躞(dié xiè)有些生僻,有些古雅却是大连人的口头语。青春期的女孩子爱交朋轧友,爱游山玩水,难免遭遇父母的数落指责,“屁股上安锥子了?成天蹀躞蹀躞往外跑,哪有女孩儿样!”
《现代汉语词典》对“蹀躞”的诠释是“小步走路”、“往来徘徊”。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长亭》:“女郎急以椀水付之,蹀躞之间,意动神流。”蔡东藩的《清史演义》第一回:“三人欢喜非常,便从山下蹀躞前行,约里许,但见一泓清水,澄碧如镜,两岸芳草茸茸,铺地成茵,真是一副好床褥。就假此小坐。”冰心在《寄小读者》里也用过“蹀躞”:“当她在屋里蹀躞之顷,无端有‘身长玉立’四字浮上脑海。”其实,“蹀躞”是先秦汉语在现代语中的活化石。屈原那句“众蹀而日进兮”(见《哀郢》),翻译成今天的大连话就是“那些小人们蹀躞着二两腚削尖了脑袋往上爬!”
在方言中,“蹀躞”由动词转化为形容词,意指浮漫轻率、庸俗低劣的谄媚行为。山东方言体系比较庞杂,同一条方言在不同地区,其含义具有细微差别。济南人所说的“蹀躞”是指盲目积极和无效劳动,含“失败”之意,或形容一个人脸色很难看。潍坊人所说的“蹀躞”是指一个人穷显摆。“蹀躞”在青岛地区音转为“踮涎”,从字面所表达的形象看,那种踮起脚跟、涎着脸儿看别人眼色行事、小腚飘轻地献殷勤,确是令人生厌的行径。
与山东作者交流,得知诸城正流行一条很有喜感的贬义方言——扶摇。“扶摇”本意指飙风、腾飞。腾飞是好事啊,一个人在仕途上扶摇直上,地位、名声、财富也一路攀升。然而,在老百姓眼里,官员的职业风险系数太高,是高危职业。那种漂浮在空中、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姿态悬念重重。“看这家伙整天扶扶摇摇的,早晚得卡跌(摔跟头)”。“扶摇”又逐渐动词化,成为都市里的流行词。“今晚又准备上哪儿去扶摇啊?”与大连人常说的“今晚又准备去哪儿潇洒啊”是一个意思。针对男人频繁应酬经常迟归,女人半揶揄半恐吓:“最近扶摇得不轻啊?”那斯文含蓄的女人,对男人的叮嘱却格外温柔:“悠着点啊,轻轻地扶摇就行了……”这七分恩爱,三分情色,令人为之倾倒。
在中国近代史上,发生过三次大的移民潮,分别是走西口、下南洋、闯关东。走西口的主体是经济实力雄厚的商民;下南洋的主体是难民,他们是中原王朝改朝换代弃下的皇亲贵族;闯关东的主体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灾民,他们的文化素质在三大移民主体中是最低的。移民潮必然会带来文化冲突之痛,文化嬗变、交融的标志是方言的诞生。大连话很土气,较直白,缺文化内涵,与先辈们的文化素质有关。
有人说,大连话太难听了,太丑了。从艺术角度看,方言的“丑”折射出了一种朴拙奇异的美感,予以人一种情感的慰藉。当我们畅快淋漓地说着家乡话,灵魂是撒欢儿,我们是自然之子,没有一丝虚伪。土里土气的方言诉说着我们内心的喜怒哀乐,而这一方水土的历史、文化也都蕴藏在这一剂土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