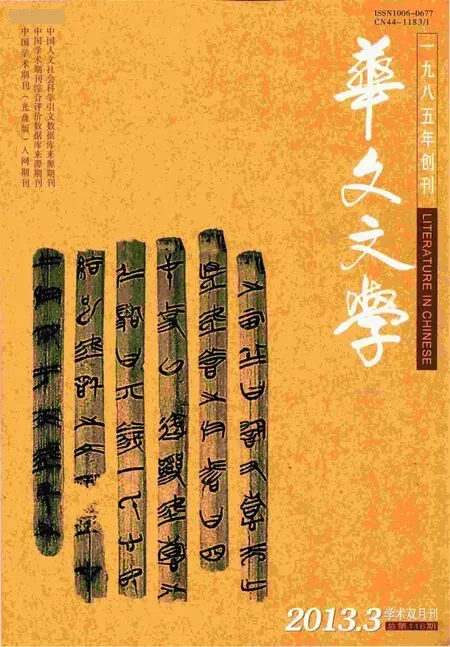薪传渡海:齐邦媛《巨流河》中的历史书写与文化想象
2013-11-16杨君宁
杨君宁
(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北京100732)
《巨流河》面世之前,齐邦媛留诸世人的形象是学人、教师,谦畏礼义之长者。即使在评论集《千年之泪》和其编纂的台湾文学选集中,隐隐透露出其去国怀乡的幽微情思,仍并无任何预兆日后会有这样一册“本命书写”的自传出现。“六十年来,我沉迷于读书,教书,写评论文章为他人作品鼓掌打气,却几乎无一字一句写我心中念念不忘的当年事——它们是比个人生命更庞大的存在,我不能也不愿将它们切割成零星片段,挂在必朽的枯枝上。我必须倾全心之虔诚才配作此大叙述。”①世悠悠适足问,书写和涂销的行为都系乎历史与记忆。在后现代语境中“作者已死”,取消著者的权威,且将历史文本化,认为其既可虚构复可消解的汹汹之论下,年迈之人对其生途的自我撰述,更像是小说中的场景,不免成为文学隐喻式的存在。便如苏伟贞短篇《日历日历挂在墙壁》里的冯老太太每天在日历背面记录下似真亦幻的家族秘史,仍然能保持自外的旁观者角度,意外地以未必自觉的超然达到了与时间的对抗和反讽。然而齐邦媛这本记忆文学的书写方式却显得古典而温谨,文字并无藻饰,修辞亦不繁复,整体上采取了纵笔直书,实录其事的写法。向历史求证的赤诚之心固然充分自觉,于抒情上则隐忍克制,不因感慨激奋而大肆渲染,论及世变情迁都以平和叙述出之,使其得到熨帖的安置。于是这种书写的姿态本身就与当下一些近似题材的表达形式构成了颇大的反差和对话的张力。大抵未亲历其事,依凭间接经验和二手材料重新营构昔时历史情境者,易有夸张之联想,虚浮之情感,往往择善固执,对其题材过分着力,反而无法还原真实感,失却可信度而沦为演义传奇故事。
《巨流河》的缘起与前身是单德兴为考察英美文学与比较文学在台湾的发展而对齐先生做的一系列访谈,后来随着访问的推进,其议题又增加了谈女性处境等内容。这部分访谈因而兼具口述史的性质。其时齐先生因病住院,所以访谈的结果并不理想:“由于思绪涣散,我已无法做访谈所需之资料准备,也无暇思考大纲与内容。所谈多是临时记忆,主题不断随记忆而转移,口语也嫌散漫,常不知所云。”②对于当时“惨不忍睹”的几百页访谈稿,齐先生无时以忘,“试着将它改成通顺可读的文字”,然效果不佳,屡战屡败后一度产生了抵触和逃避的情绪。
“当我下定决心重写,拿出纸和笔时,一生思考的方式又回来了。”③从无法整理的口述史记录稿到另起炉灶的自传书写,文体形式和写作目的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我手难以改我口,然我手力图写我心。原先的访谈已不足以容纳和承载作者想要表达的内容,需要寻找新的形式。口述与书写之间亦有断裂,于是唯有重新开始叙述,且是经由更为独立的书面写作来完成这种叙述。毕竟访谈这一形式中,受访者的思维会受提问者的暗示和牵引,也会被提问者的认知水平、设问角度等种种因素限制,难免被动。由毕生职志思及自身的性别处境,进而回溯更为完整的人生经历与其背后依傍的庞大历史背景,大抵就是《巨流河》的成书因由和展开思路。所谓“本命书写”,是因就叙述者的身份及经历而论,颇多可与近代以来女性知识分子的奋斗历程两相接续和对比参看之处,其书写过程中由学养识见所熔铸成的视角情怀历历可见。若非此,应也不会有对历史的追问与自觉承担。文学因应历史,以新的文本形式对呈已不可全然信靠的,同样被文本化的历史,并试图从自身出发与之进行对话,这一过程就此具有了互文的性质,而所要处理的中心正是“记忆”问题。纪实与虚构,记忆与遗忘的机制如何实践和延展,亦是文学和历史交互之间连带到的问题。一切的回忆都是重构,而在记忆畛域之外要凭借史料构筑的不在场情境,以及重新发掘已习焉不察的某些经验更为艰难。“我记得”的宣示之后,只有赋予记忆充分的证据和意义方能将其落实。
本文考察《巨流河》的历史书写与文化想象,主要从东北与台湾的经验接驳,对父亲平生的记叙与大历史的连带关系,以及作者当时所涉的知识分子群体交往和所承教养这几方面入手试做描述和阐释。
一、区域观念下东北与台湾经验的接驳可能
此处特地拈出“区域”这一观念来用于论述东北与台湾,是为了对惯性认识有所匡正和突破。如今的文化文学语境中,城市书写和与之相关的城市研究大行其道。这是因为进入社会生活的现代情境以后,我们理所当然将“城市”作为一个现代人文地理单位来量度和观看当下我们所活动于其中的时空,且发展成精细完备的成套书写谱系与论述系统。城市之间的对照式城记也陆续出现,譬如上海——台北双城记、沪港双城记,亦有沪港台的三城鼎立对比。它们因是具有发达资本主义特征的国际化大都市,在发展阶段和形态上甚多可比之处,而又兼有传奇的历史和繁华的现在。
特别是1949年前后,从对岸的角度回望此岸,平行的怀旧场景会发生投射作用,上海或南京经常变成台北的“影都”,尤以上海为甚。毕竟民国以来至今的文学中,南京的存在较之上海,还是更加低频隐秘的。此中除了经济状况、历史文化沿革等因素造成这样的对照思路,不可忽略的重要线索还有此前在大陆中断的现代主义文学脉络,由纪弦等人在台湾“纵的继承”式延续下去,六十年代有了文学艺术领域全面的现代主义发展兴盛时期。上海和台北作为这一文学场域的前后两座中心城市,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新感觉小说、象征主义诗歌及新电影被奉为圭臬,成为彼时台湾初兴的现代主义者们用以学习模仿的范例。新电影先驱如刘呐鸥,其台湾本省身份加之上海经历,更是以传奇人物的样貌串连起两座城市的联系。即使时移事往,六七十年代的台北在实际景观与文化生态上都与三十年代的上海大相径庭,这种勾连和汇通的努力却一直都不曾消歇。林文月《江湾路忆往》中回忆的幼时虹口居住经验,白先勇《台北人》里今不如昔的慨叹,之于旧时上海精致繁华场景的温情再现,皆已成为可供参考的经典文本。作为同样具有上海记忆的台湾作家,张系国则对当代台湾的“上海热”显得颇不以为然:“基本上我从幼年起,对海派并不认同,所以就会觉得上海热很奇怪,尤其所有的人都在迷上海,而这些人就不见得很懂上海”,“不一样,这完全不一样,当然,海派最主要的一个特征,为什么说一个人很海派,就是说一个人的手气很大,……(台湾人)跟上海人的表现完全不一样,没有相似的地方”。
在更大地域范围内进行城市对照书写的范例应是朱天心的《古都》,在小说中将台北和京都并举,写成了如影随形的姊妹城市。川端康成原作与此同名作之间扑朔迷离的互文关系亦多为评论者所称道。《古都》的写法更接近于萨义德帝国“对位书写”意义下的,带有殖民色彩的城市互看。我们若再放眼外观,在整个华文世界的城市文学中,书写者的知识构成、身份视角的影响对其书写形态弥足轻重。
譬如董启章比较文学出身,其城市题材的小说所涉及的内容,与城市研究理论就吻合度很高,虽然可能是反向的解构式的呼应,但学院教养(此处并非要贴“学院派”之标签)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不可小觑。但城市的概念过分被凸显,无形中亦对研究视野构成了限制。以至于当代的人类学研究也受其影响往往窄化为社区研究,缩减到城市内部更微观的度量单位。城市书写与城市研究皆已因其略显泛滥,而在研讨的有效性和新意上大打折扣。
故而“区域作为方法”的引入,在对城市已成的叙述和研究惯性上有望进行突破。此处所使用的“区域”,随语境流转见义,故当是多重含义的概念。甚至也不能完全脱离与原本城市研究中的部分相关概念。在这里的讨论中,它至少包括了侧重行政区划意义的区域(area),重在强调所坐落之地和相对位置关系的地点(location)以及兼有人文自然双重意蕴的地景(landscape)。后两个概念仍是从城市研究中对空间的指称延伸而出的。
固然上海、台北、香港这些城市屡屡被相提并论,关于它们的论述亦大有陈陈相因之势,在其真实的联结关系上未必情理熨帖,毕竟从地理亲缘上说,尚都隶属于泛化意义上的“南方中国”这样的地域区块。而东北和台湾看来因地缘上的相隔甚远,要放在一起似乎张力更大。然而意义的产生也常在于彼此的落差和异质性,在《巨流河》文本的具体语境中,这两地之所以会有关联,乃由于它们分别属于作者身经的这场大离散所造成的起/止之地,在时间的序列和站位上各据一端,成为需要两边参照借鉴的经验来源。
以区域面貌出现的东北,无论对于其参照地台湾,还是书写者齐邦媛,都不是某种单一意义上的所在。区域更有其丰富面向及其内部复杂性:相对台湾而言,东北不止于是与之有过深厚纠葛的殖民地;亦非作者“原省籍”或生身之地意义上的单纯故乡。东北在近现代史上的名声与重要性大半来自其战争边关的位置,历经伪满洲国、东北易帜、抗战中首先沦陷的重重浩劫之地,因而其在政经事功方面的形象鲜明,其他方面的特色往往被遮蔽隐没。《巨流河》中至少为我们揭示了两方面不囿于此前单一固化印象的东北:“文教东北”与“自然东北”。前者的命名来源于书中对于东北流亡学生的战时流徙生涯和《时与潮》杂志创办的若干事宜等之叙述;后者则基于对风光景物的描绘,都发掘了东北在惯常印象之外包蕴的其他因素。前者或许可以与大陆文学史常载的三十年代东北流亡作家群的创作活动联合起来观照。后者则具体表现为以一种物质性的、日常生活的景观书写来呈现奇丽的风光,猝然展示了东北白山黑水的冷峻印象之外妩媚的特质,揭开女性视角所带出的更温情的浪漫化想象,也是与生命息息相关的议题。“铁石芍药的故乡”之印象绵延良久:“我记得祖母把我采回的一大把花,插在大花瓶里,放在大饭桌上,整个屋子都好像亮起来了。祖坟松柏随着故园摧毁,那瓣瓣晶莹的芍药花却永远是我故乡之花。”
在关于东北论述的部分中,东北中山中学作为流亡学生群体的主要来源应该也是值得提及的一笔。《巨流河》本文中与此相关的人物张大飞,是在战乱年代中失去家庭和亲人,几度易名、命运多舛的学生代表之一。《巨流河》成书后,很多“读者反应批评”将其看作是战火中难得的浪漫爱情传奇,但作者本人其实无意渲染于此。张以生命的代价给少女时代和后来的作者兄长式的关爱、伴护与交流。作者重访南京故都恰逢张的悼念仪式,几成近似宗教经验的启悟,而与张大飞的情谊和他带来的影响也是引导作者走向基督信仰的起始。
如果以区域的概念重新审视东北经验与台湾经验的接驳过程和方式,当可使度量单位扩大,着眼于更为宏观的状况。离散经验中的流寓和迁移也与作为区域形成动力的流动性彼此呼应,甚至是将两种论述叠加运用来看区域与离散之间的关系。虽然区域形成动力的流动性更倾向于其内部的因素变动,与外在其他地方的区隔含义大于交融;而离散则是异地之间发生的变迁移动,实际涉及的场所会比区域更为开阔。但两者有重合亦有交集。恰如夏多布里昂《意大利之旅》所言:“每一个人身上都拖着一个世界,由他所见过、爱过的一切所组成的世界,即使他看起来是在另外一个不同的世界里旅行、生活,他仍然不停地回到他身上所拖带着的那个世界去。”东北和台湾就是齐先生和那一代有过两地流离经验之人的两个世界。
二、从“迷宫中的将军”到“没人写信给上校”——父亲的憾恨
《巨流河》的一个潜在文本是作者父亲齐世英将军的戎马平生。如前文所提及的,齐世英将军创办的《时与潮杂志》及其相关的副刊、月刊乃至后来增设《时与潮文艺杂志》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刊物系统,是抗战当时难得的坚持己见,而又卓有风格的刊物,在及时报道时局政事和推进文艺方面都颇有成绩。然而关于这个刊物的研究成果至今寥寥,基本还只是停留在最基本的刊物研究做法对其分解式的描述,尚未与其他问题发生勾连。在《巨流河》中它则意外成为当时身为中学女生的齐邦媛参加学校的知识竞赛时的阅读宝库和后备资源。在国民政府的有紧有收的文艺政策和禁书制度下,后期的《时与潮》并未如《自由中国》那般贾祸至牵连主要人员遭受牢狱之灾,但其中的主创者也确是多与蒋有异见者。齐世英、王镜仁、梁肃戎等人作为昔日高级将领、国大代表等军政要员,随国府迁台之后多半是挂闲职,不再掌握实权,但他们摒除与蒋的私怨,仍然坚持自己的政治信仰和为历史作证的决心值得钦敬。从他们的晚年回忆和前半生的重要经历观之,其观点和经验都提供了对于抗战、内战中若干关键的历史时刻的再认识,也是对民国史的重新考察。
“渡不过的巨流河”,尚在郭松龄麾下时,此一役功败垂成,成为齐世英将军无时以忘的深心隐痛。这种创伤体验亦重现于去台之后的日子。精诚忠义之人的结局是被革除党籍,晚景凄凉。这般遭际几乎复写于白先勇之父白崇禧将军身上。因而,当两位多年交好的文坛前辈,于现实中再现白氏名篇《冬夜》场景,对坐谈文学、话人生之际,都不由得思及两位父亲来台后,一起在田埂上漫步谈心的情景。东北四平街战役之失守,是他们共同的憾恨。白先勇近年来致力于《仰不愧天——白崇禧将军传》的写作,用意也在于藉父亲的传记为落点,书写相对客观的民国信史。史料浩繁,爬梳不易,遂五、六年来仅写得1/3,已在两岸同时刊行的章节之一《广西精神》,惊人地揭示给我们当年秘而不宣的“斯巴达式”训练制度下,军民合一,练兵与生产并重的“广西新政”。使人不禁揣想这套方法若得以扩大且持续执行,会否给其时制造意外变局。
历史的草灰蛇线伏笔千里,不就一时一地而论,重被发掘的某些电光石火般的潜在因素,也可为后人开启新视景。白先勇曾说:“我父亲去台湾不带一兵一卒,他去是为了对历史有个交待”,又说:“来台湾后,齐世英先生在办当时言论最自由的《时与潮》杂志”⑧。父辈的悲愿和未竟之业,传到齐先生和白先生手上,换了以字立骨,求信于史的方式去承续。《巨流河》是“忧患之书”,沿袭了现代知识分子感时忧国之传统。而其情切切,又以忍情出之,温柔敦厚,实乃合乎儒家情教的“惆怅之书”。这亦是一本“偿还之书”:作为女儿还诸父亲(齐先生自己也讶异说,她本想这样的著述之事应由其兄长来完成);作为写作者还诸世界(以自身经验建构纸上城国);作为属灵者还诸信仰(那是生命中至关重要之人的遗泽馈赠)。
因之齐邦媛和白先勇以传记为民国史之书写实践,同质异构。齐先生谈到白先勇早慧杰作《台北人》时说,这本书“五十岁、六十岁、八十岁时看,都不一样”⑨。扉页上引用的《乌衣巷》并那句题词:“纪念先父母以及他们那个忧患重重的时代”深意恒在。张大春曾在《小说稗类》里提点:“白先勇在张爱玲‘竟以小道而不语’的‘乡愁中国’这题目上既不‘荒诞’,也不‘滑稽’,反倒‘精巧’地点染出感时怀旧的温情。”
在这一角度的观看下,齐先生很似是《台北人》谱系中缺位的人物。内中人物“罔不因势象形,各具情态”,却唯独没有如齐先生这般身家历练的,新旧过渡,两岸流离的知识女性。到了《纽约客》中Tea For Two 安弟的妈妈叶吟秋(Yvonne)女士似是个最有可能发展成这一类型人物的影子角色,其人落墨不多,其开明同理之态度(对其子的同性爱人理解包容,且将儿子像托付给兄长般交托其手),优雅淡然之气质,却暗示读者她必是有故事之人,惜乎未再多写。
幸好为小说所“不容”的齐先生日后现身说法,写下《巨流河》,除了向历史求证,亦要替女性求学、治学之不易做一可贵的笔录。古典女性向外寻求自身价值意义,惯常以“情”为重要驱力,那还是略浅的层次。身为现代知识女性,齐先生求索的动力来源于广博的中西文化传统,更可能是中国古典抒情言志的文人传统。超越政治的文学书写,来对抗时代暴虐与历史无常。只有在君父城邦訇然坍塌,倾情以之的爱人殉国永诀之后,文脉薪传方成了惟一可堪寄身的所在。无论是父亲那一诺千金的烽火家书“……吾儿随学校行动可保安全,无论战局如何变化,我在有生之年必能找到你”,还是张大飞哀婉沉郁的绝笔信:“这八年来,我写的信是唯一可以寄的家书,她的信是我最大的安慰。……以我这必死之身,我怎能对她说‘我爱你’呢?……请你委婉劝邦媛忘了我罢,我生前死后只盼望她一生幸福”都已灰飞烟灭,留在记忆中成为时代劫毁之见证。然而武大外文系时期,朱光潜先生英诗课上的随堂笔记,却伴随齐先生一直穿行半个多世纪,仍完好无损,得以同后人分享克难岁月中的不灭诗魂。那是“三大本最好的嘉乐纸笔记本,从里到外都是梦幻般的浅蓝,在昏暗灯光下抄得满满的诗句和老师的指引。一年欣喜学习的笔迹仍在一触即碎的纸上,随我至今。”此处除了对知识的渴求以外,关于物质本身的喜悦也是令人颇为神往的,事实上这也正是壮烈凄怆的行文中,偶尔闪过的轻巧灵光。从父亲年少时以长衫衣襟兜回的一抱樱桃,到大西洋彼岸一间宽敞明亮的“自己的书房”,齐先生落笔触物尽皆有情,将“花果飘零”重新翻转出离乱之中更为宝贵的正面意义:纵使身若浮萍,亦不忘对受用的好物好景时时发出热情的咏叹,并以文字持之永恒。飘零之中,依然花灿花色,果溢果香。许是出于女性天生对物的敏感爱惜,更是好奇顽强,对生命的热爱和不弃。
三、交往与教养:姊妹星团中知识女性的情谊和师承
由殷张兰熙、林海音、林文月和齐邦媛所组成的女性知识分子团体。如以五四以来的知识女性成长史观之,或许可称之为近似卢隐《海滨故人》版的情谊再现。当然齐邦媛等人所形成的这个小团体从成熟度和内聚力上都比卢小说中的文艺少女集合要高明得多,或许更接近苏雪林和袁昌英式强强联合的阵型。四人在创作、教学、研究、翻译方面各有所长,皆成名家。其可贵之处也在于才女之间往往以才相嫉为多,鲜有如她们般彼此讨论学问,互益互助而又形成规模且具有很长的持久性。虽然林海音和林文月并未直接介入《季刊》的编辑工作,但在交流和友情上都支持甚多。英文版季刊创刊时,殷张兰熙为主编,后交棒给齐邦媛,得以延续进行。其间辛苦为继的历程,可谓友谊与道义互见。在这些成绩斐然的文情文谊背后,包蕴的竟是无穷渡海怅望的家国心事。彼一代优异的知识女性,休戚与共、得以结盟的潜在因素,恐怕同其相似的记忆和经历难脱干系,由此才能维系这一小规模的文化共同体,于教书、创作之外,林文月撰述《青山青史——连雅堂传》,林海音纯稚低婉的北平城南旧事书写(台湾女孩成长于北平后又返岛的弹力球人生),殷张兰熙筚路蓝缕创办《笔会季刊》推手台湾文学外译各自有其值得圈点称奇之处,并昭示了“过去”与“未来”在她们腕底经营出的当下印痕,烙于文学活动之上的历史感。当然林文月的日本文学翻译,林海音创制《纯文学杂志》及纯文学出版社之功,早就世所公认的。
齐先生曾在《联合报》访问中如是说:“1972年很有意思,笔会英文季刊开始,我编《中国现代文学选集》、《书评书目》创刊、林文月翻译《源氏物语》都在那年。”
《巨流河》将四人的交谊职志,头一次认真付诸书写,也正在此书中。“科学是我,艺术是我们”。齐先生如此追忆这段珍稀友谊的缘起:“出版期刊是个日催月迫的事,那二十多年间,兰熙和我这顾问之间的热线电话从来没有停过……1978年底,林文月和我参加教授访韩团期间,结成谈心的朋友,回台后也常参加我和兰熙的小聚,不久林海音也常来。”因缘际会,遂成惯例:“十余年间,每月或隔月聚会,每聚都兴高采烈地说最近写了什么,译了什么,颇有各言尔志的舒坦和快乐。”
后来“文月离开台北后,海音也卧病,客厅的灯也熄了。”淡笔带过,却是“人散后,一钩新月天似水”的凄清,好友终至星散。未几,殷张兰熙失忆,无法再从事她钟爱多年的翻译工作,齐先生接棒,临危受命主持《笔会季刊》的编务,《笔会季刊》在推动台湾文学外译方面,功莫大焉。由翻译所呈现出来的台湾文学面貌,推及国际也是台湾形象的塑造。考察季刊所选译的台湾文学作品,也可看出编译者当时的心思与用意,在试图展现怎样的台湾文学景观。而这又恰可与大陆的《中国文学》刊物形成对比,梳理两岸当时在文学文化领域中外现的形象和分殊。
及至《巨流河》初刊,林文月在美国“花了一个礼拜读完,书里夹满各种颜色的条子,非常感动”,她笑说:“一般人以为女人聚在一起,就是唱高调、女性主义什么的,但回头看殷张兰熙、齐邦媛,为台湾文学界做了许多有意义的事,但都是默默地做,从不标榜什么。”


台大自1949以后由傅斯年校长始,所形成的优秀文教传统自不待言,齐邦媛先生赴台后在外文系任教,延续和光大了这一传统,由此遂有“永远的齐老师”之美誉。她在大陆之时已受教于朱光潜等名师,到台之后又有四位与之有过交集的老一辈著名学人。对于形成一个学者、作家的知识体系、阅读眼光和文化教养至关重要的师承在此得以彰显。而大陆赴台的老一辈学人应对世变之心史及其在岛上的薪传沿革,大可考究。他们的存在具体证之不同的记忆个体,大致都是一种松散、似有关联而不成聚落的存在。每一位后辈与他们的接触方式亦多非传统之有系统的师承,而是零星缘分。
在之后“外省第二代”作家的小说书写中,对于这种流亡知识人团体的描述不约而同地聚合为一种集中的关注,而且绝大部分都是近年的长篇新作:苏伟贞的《时光队伍》写到以庄严为首护送故宫文物去台的“国宝流浪队伍”,张大春的《城邦暴力团》开篇所写台静农、欧阳中石、贾似曾等七位在成长过程中谊兼师友的前辈,朱天文的《巫言》对乃师胡兰成、乃父朱西宁致以极高的礼敬与回忆。及至再下一世代的创作者,对师辈的敬仰怀念已转变为对经验匮乏和教养缺失的焦虑。骆以军《西夏旅馆》之副册《经验匮乏者笔记》的标题鲜明地点破了新一代写作者在失去庞大家族背景和系统的知识教养以后,对于书写如何继续的困惑。而在香港,董启章的《学习年代》则采取了“教育成长小说”的形式,加入大量对经典作品和理论的直接研讨学习,也寄托了作者兴灭继绝的苦心。纵观这几代人之于其身受的教养不同的处理方式,可以见出由尊师重道、尚得亲炙到渐去渐远,乃至自己要代身为师的艰辛。在旧有一代知识群体的由兴而衰,师承与道统逐渐解体的过程中,愈发显得薪传之可贵。
结语
适逢辛亥百年,回顾历史的传记和回忆录性质的书籍纷纷涌现,而民国史的相关资料也再度成为研究热点。综观《巨流河》,基本思路是以人带事法,举凡抗战、内战、国府四九之后渡海迁台,作者赴台以后在台大和其他文教领域所从事的工作都有所叙述,既串联了现代史上的重要关节点,也将1949年之后台湾文学的发展建设与外译介绍的情况讲述得较为完足。由此可见,《巨流河》的历史书写不是单一脉络的。由于1949这一年份所做的切割,以时间划分空间,大陆时段和台湾时段两部分各自偏重了不同的区域特征,从篇幅上几乎均等。究其笔法,并未因书写历史而过分历史化和国族寓言化,历史作为背景出现,在处理上仍以个体经验和直接感受为本,用温和从容的文学笔触描摹出人对大时代大环境具体而微的反应。作者感时忧国,回应历史的姿态含蓄蕴藉,是兴发感动式的传统抒情。而作者从流亡学生成长为一代学人的历程中,近取诸身的熏陶教养和知识经验时时在侧,都为其后的文化实践作了先在的准备与铺垫。无论是历史书写抑或是文化想象,其根源性的实现可能其实都是作者的身份所致,既体现其知识分子的关怀,又有出自女性视角的温婉细腻,历史意识的传达亦是渗透性的。生命本身的律动实比任何大哉斯言的企图和论述都来得更真实有质感。作者以其知识女性的本分与持守,对历史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并凭借其在文化事业上的作为曲折幽微地与其互动,在当代华文文学史与学术史上都创造了独异的价值。
一、报刊杂志
《时与潮》(1938年创刊于上海)
《时与潮文艺》(1943年创刊于重庆)
《印刻文学生活志》2009年7月号,印刻出版社。
二、作品论著
齐邦媛
《巨流河》,天下远见出版公司,2009年7月版。
《千年之泪》,尔雅出版社,1990年7月版。
《最后的黄埔》(与王德威合编),麦田出版社,2004年2月版。
王德威
《台湾:从历史看文学》,麦田出版社,2005年9月版。
《后遗民写作》,麦田出版社,2007年11月版。
《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中研院近史所,1984年5月初版。
《齐世英先生访问记录》,中研院近史所,1990年8月初版。
《姜允中女士访问记录》,中研院近史所,2005年版。
《从东北到台湾:万国道德会相关人物访问记录》,中研院近史所,2006年版。
张大春:《小说稗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版。
许秦蓁:《战后台北的上海经验和上海记忆》,大安出版社,2005年9月版。
赵林涛、顾之京编:《顾随与叶嘉莹》,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11月版。

④⑤许秦蓁:《战后台北的上海记忆与上海经验》中之附录(一)《张系国访谈录》,台北:大安出版社2005年9月版,第272页。
⑦⑧《联合报》2007年8月7日《名人相对论》之白先勇VS齐邦媛:《没守住东北,两家父亲的大憾》。
⑨⑭《联合报》2007年8月7日《名人相对论》之白先勇VS齐邦媛:《知交35年:白先勇齐邦媛文学不了情》。
⑩张大春:《小说稗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版,第103页。
⑱⑲林欣谊:《林文月典雅如昔,新书谈文说艺》,台北:《中国时报》2009年10月24日。
⑳赵林涛、顾之京编:《顾随与叶嘉莹》,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11月版,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