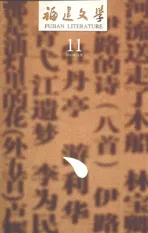大地的礼赞
2013-11-16黄加芳
□黄加芳
一
人们通常很难用一个量化的标准来界定所谓的“诗意”。尽管我们不能否认春天的鲜花夏日的小溪秋夜的月亮和冬季的太阳是“富有诗意”的,而这仍然很有限,固有的惰性迫使人们在对待“诗意”时,总是后知后觉,我们的预见性在此时常派不上用场,而想象多数时候也跟不上我们双眼所见到的。这就是说,我们很难凭空猜想某种场景是“富有诗意”的,我们更愿意在亲眼见识到那些确实打动了我们的景象之后证实:这实在是“极富诗意”的。这时候,艺术家禀赋的职责和荣耀凸显出来。在看起来平凡无奇的生活中间,艺术家敏锐地撷取那些被造化赋予了特别光晕的、足以使人们或欣喜或哀伤的东西。哀伤也并不总是多余的,因哀伤与欣喜一样,多少在为麻木于沉沦、沉沦于麻木的庸常生活带去一股清新的空气,使众生不至于绝望得彻底。
安德鲁·怀斯的画就是这样。在阅读怀斯的画作之前,我们对于“诗意”的概念是模糊的,至少是不成系统的。怀斯好比一个神通广大的炼金术士,那些俯拾即是的、毫不起眼的原材料,只要一经他的双手,便变成了光辉熠熠的金子。于是我们茅塞顿开、恍然大悟:没错,这就是我头脑中蛰伏多时的诗意了!
怀斯的诗意不是那种故弄玄虚的、高高在上的诗意,而是相反,他笔下的题材总是再俗常不过的,他画老屋、草坡,画邻居、动物……,一句话,他只忠实地描绘大地上的事情。所有这些人、事、物,全令观者感到犹如身体发肤一般的切近,但这些对象又不是毫无选择的,事实上怀斯是借这种种完全形而下的东西来寄托自己形而上的情怀。而这有如移步换景的扬弃正体现了艺术家匠心独运的天才。很显然,这一点与同时代的诸多热衷抽象、表现的画家大相径庭。在诸如德·库宁、阿佩尔这样的画家那里,绘画原始的抒情特质被肆无忌惮歇斯底里的疯狂叫嚣取代了,我们从画面上看不到哪怕一点平静完整的形象,有的只是张牙舞爪的失态和粗重急促的喘息。而在另一类以米罗、康定斯基为代表的画家笔下,符号永远扮演着主要角色,它们从一面世就注定承载过多沉甸甸的隐喻与象征。似乎,画面上的东西只是一种单纯的工具,它们好似一束束强光,一旦将作者那沉思的哲人似的脸庞照耀得亮堂,便别无其他功能了。这样,当观众直面作品的时候,一场漫长而莫衷一是的脑力角逐也同时展开了——这样的画作,从来就是颇费思量的。其画外的意旨,也许就是画家本人也难以言明。艺评家就更不用说,他们除了过度阐释就无事可干了。怀斯却从不这样。所有他画布上展示的,都是触手可及的活生生的生活本身。通过这些零零碎碎的场景,建构的却不是照相写实主义所孜孜以求的繁琐与赤裸——相反,怀斯的作品堪称是照相术大发展时代的新浪漫。这样的浪漫表现常常能收到与那些抽象画同样的效果,有时甚至更加直截了当、深入人心。这不由得引人想起一句古话:“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
也因此,一个悬置已久的问题重新凸显出来,那就是究竟何谓现代性?难道只有那些莫名其妙的涂抹、不顾一切的解构才足够“现代”么?若是如此,艺术将不免沦为一场无聊的狂欢。固然,逸笔草草是允许的,抽象表现也是必需的,然而怀斯却分明向我们证明除此以外的第三条道路的存在。怀斯所赓续的是纯粹写实的传统,在众声喧哗的“现代”、“后现代”的热潮中,他看来始终不为所动,如同一位闭目塞听的中世纪隐修士,或者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斯多噶主义者,一意孤行地埋头耕耘着。在这近乎固执的、旁若无人的努力之外,“现代性”的真面目也渐渐清晰起来:“现代性”从来就不是那种空洞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标榜,也不仅只是形式的徒然比拼,说到底,它是一种态度,一种精神,一种悲天悯人的现世激情,一种借助画布和油彩得以表达的终极关怀。
二
怀斯和他笔底的世界容易使人想起另一位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他们就像《百年孤独》中吉普赛人拜访以前的马贡多村民,任自己的一生默默流失在故乡的土地上。后者一生只游走于自己的故乡——美国南部的小镇奥克斯福。在人们印象中,似乎这位没出过远门的作家就那样游手好闲玩世不恭地赤足逛荡于奥克斯福乡间,然后轻而易举地创造了包括《喧哗与骚动》在内的十八部长篇小说和一大堆中短篇小说,接着又轻松摘取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无疑地,这就像一个传奇。同样,这一传奇也发生在安德鲁·怀斯的身上。怀斯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查兹佛德生活了一辈子,同时也画了一辈子。与福克纳一样,怀斯从不表现褊狭的故乡以外的任何事物。这固然限制了他的视野,却也决定了他的深刻。乡村的版图何其有限,那么,就让这有限的版图尽情讲述她无尽的忧伤吧。
在这里,怀斯以他的始终只耽于对故乡风物的表现,向人们提示了一种严谨而诚实的艺术创作道路的存在。当艰苦卓绝的前创造阶段过去以后,真正伟大的艺术家无不重返自己的内心,忠实地摸索属己的心跳,这时候他将发现自己的悲悯,这悲悯必是大的,而他的表现手段恰恰忌讳大而无当,他只有通过具体而微的絮语才有望将这悲悯传达,以抚慰芸芸众生那疲惫的心灵。在这个意义上,查兹佛德的草木鸟兽,及其生活着的人们,单凭其担负着的沉甸甸的使命,难道不可以说是有福的吗?故乡虽则小矣,但实在是丰富宽广,乃至浩瀚无边的,因故乡于每一个鲜活的生命,都是那样暧昧而难以割舍的所在。
所以,站在怀斯的作品面前,每个人都必染上忧郁的怀乡病。确切地说,是他的画唤醒了我们心中一直沉睡着的怀乡病。本来,这怀乡病作为一种与生俱来的绝对的能量潜伏在每个人的骨子里面,概莫能外。它们大部分在玩一种捉迷藏的伎俩,始终以隐蔽的状态伴随人的终身,只有极少许有幸等待外力的刺激,才活跃起来。而这外力是十分丰富的,或者是色彩、画面;或者是声音、气味,只要一触动那道隐秘的开关,那一连串远年的尘封的怅惘就被唤起。很经常,当我们凝视着怀斯的作品,我们就无端记起多年以前的一幕熟悉的场景——对了,“多年以前”,是在哪里呢?在童年的竹篱笆前?在家后门的黄土坡上?抑或仅仅是在遥远的梦里?在灵魂深处?其实,它或许就隐藏在心魂的故乡中,不生不灭,称职地暗示你生而为人的悲伤和美好。真的,怀斯总好似一位神秘的通灵者,一次又一次地使观众恍兮惚兮,如游旧径,如见故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怀斯的伟大是堪与那位敏感的天才马塞尔·普鲁斯特相提并论的:那些亲切的蛋彩画就像曾使普鲁斯特浮想联翩的玛德琳娜小蛋糕,使每一个人惆怅不已,继而做起《追忆逝水年华》那冗长而温馨的迷梦。这时候,长久迷失的人就走在“归家”的路上了。这幻梦非但不使我们感觉不适,反而激发了我们生存的快感。因为,人们大抵更情愿悲壮地忧伤着,而不愿平庸地快乐着。在悲壮的忧伤中人们饶有兴味地把玩生活,自身那渺小的背影会变得空前高大起来;而沉醉于平庸的快乐的人,一旦清醒,将不免惶惶不可终日的。这正如穆勒所说,“人们应该宁可做一个痛苦的苏格拉底,也不做一只快乐的小猪。”
三
怀斯无疑是禀有魔力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一度为他那一股莫名的魔力所深深着迷,看着黄昏里一匹埋头吃草的灰牝马,屋外对着大海狂吠的猎犬,或者仅是一片融雪的草坡,一面斑驳的墙体,我便顾自神往心驰,摇撼无主。我在心里揣想,都说怀斯是“怀乡写实主义大师”,是的,“怀乡”是不错的——怀斯不总在描绘他生于斯长于斯的查兹佛德吗?“写实”也确乎如此,怀斯从不玩儿故作高深的把戏;但无论“怀乡”也好,“写实”也罢,都片面得可怜,也难免干瘪苍白。乡村抒情歌手可谓多矣,而写实高手也有如恒河沙数,却无不同怀斯隔着深不可测的巨沟大堑。说到底,怀斯不是轻易能够概括清楚的,如同一条源远流长的河川,生生不息地流淌,对于两岸生物的滋养却是悄无声息的,也是不可穷尽的。
怀斯的笔触从不多余,接近吝啬,这使得画面中的每一个细节都严丝合缝、脉脉含情。他画中的人物从来不矫揉造作地摆姿势,而是保留他们原有的神态,或沉吟,或远眺,或行色匆匆,或气定神闲,一点儿也不迎合将他们摄入画中的艺术家。事实上,他们已经与传统意义上的模特儿相差得极远了,他们像是被画家扛着相机抓拍到的,却于那瞬间的镜头语言中传达一些与“永恒”这一概念息息相关的信息。倘若我们足够细心,我们将不难发现,怀斯笔下的人物始终没有剑拔弩张的神气,而总像是在安静地等待什么。我们不必再怀疑,其实不单是画家在心平气和地记录,被记录的人们不也自始至终毫不矜持地等在那里吗?恍惚间,那些人们早已脱略了高高在上的为人的自负,隐匿在草木中,同周身卑微的草木毫无二致了。
——而这,就是生活。怀斯不厌其烦地提醒我们的,就是关于本真的生活本身。
是的,生活是琐碎而具体的,怀斯也丝毫不否定这一点。非但不否定,还径直将生活的细枝末节披露得干干净净——怀斯是不惮细腻的,但于这细腻中不动声色地叩问生存本质的,除怀斯外,怕没有别人吧?
很可能,怀斯是不屑成为一个吟风弄月的乡村抒情诗人的,如果一定要给他非凡的心灵加上一个冠冕,那么怀斯就是思想者,一个凭借画笔思索的哲学家。怀斯笔下没有饶舌费解的哲学术语,但他一而再、再而三传达的,却是最为根本的哲学命题。热闹的事物是为怀斯所摒弃的,相反,他在乎宁静,而他竭力呼唤的,是孤独。怀斯深知孤独是人最大的生存处境,人生而孤独,这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摆脱的。在怀斯那里,再灿烂的阳光也令观者倍增迟暮之感。阳光奢侈地泼洒在草地上、树丛中,或者索性慷慨地倾注在人类和禽兽的脸上、身上,只因其无私的温暖而予人以“人生忽如寄”的慨叹。
诗人里尔克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里曾这样发愿:“我们的使命就是把这个羸弱、短暂的大地深深地、痛苦地、充满激情地铭记在心,使它的本质在我们心中再一次‘不可见地’苏生。”——我们惊奇地发现,终其一生,怀斯在画布上一以贯之灌注的,不就是这种心思吗?作为故乡大地高明的记录者和虔诚的歌颂者,怀斯巧妙地运用毫厘不爽的精细刻画来传递最为高蹈的情思,面对他创造的画面,我们常常有太多话要说,却又总是不知从何说起。怀斯有一幅《漂流》,描绘一个老人平躺于小舟中间,任凭海水无目的地将他带走。逼视着它,我们不禁满腹狐疑:这是一种怎样的仪式?老人最终又将归宿何方?我们无法得到乐观的解释,只能放任不着边际的联想。画面的平静肃穆和悲壮决绝总使我们想起巴西作家若昂·吉马朗埃斯·罗萨震撼人心的《第三条河流》,仿佛那位自我放逐的面目模糊的父亲来到了怀斯笔下;同样,我们也可以引用波兰天才的布鲁诺·舒尔茨在《父亲的最后一次逃走》结尾的话来形容它:“他靠着剩下的精力,拖着他自己到某个地方去,去开始一种没有家的流浪生活;从此以后,我们没有再见到他。”——无论怎样解释,都一样使我们绝望而痛苦。而怀斯最著名的《克里斯蒂娜的世界》在给予我们遐想和猜测的自由的同时,也将深邃的孤寂与隐约的不安一并抛给了我们。怀斯的色彩总是柔和的,笔触也细腻到完美,但柔和中全是悲伤,完美的同时也不乏凄凉。望着克里斯蒂娜那娇弱的背影和山坡上的小屋,我们仿佛感到这中间横亘着些许被称之为“宿命”的东西,挥之不去。秋日的草坡枯黄得令人心碎,它们仍旧像在践行一个承诺,年年岁岁荣了又枯,枯了又荣。而拖着病体匍匐在这草坡上的人,将不免终于照不见那暖和的秋阳。“去者日已疏,来者日以亲”,这对于无缘无故被抛在世上的孤独的人来说,是何等残酷呢!怀斯在这里要讲的,是一个关于命运的故事。他深知,单个的人的命运同其他生灵生息的节律本来就没有两样,这不代表它们是微不足道的,恰相反,这才是自然的“天道”。在这“天道”中,人不仅与自己的祖先亲密对话,还同天地万物声息相通,个体有限生命超时间的可能性就达成了。
怀斯就是这样,作为故乡大地忠诚的儿子,冷静地目击着,温情地记录着,一方面将流逝的时光安静地画在布面上,一方面又对着宽厚的大地悄声耳语:可爱的大地,请你开口……
大地就开始倾诉。要知道,大地从不自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