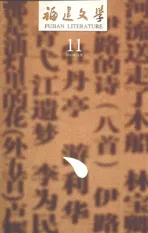寻找梦境按钮的诗人(评论)——《伊路的诗》读后
2013-11-16□游刃
□游 刃
对伊路诗歌的特点,有许多她的长期读者甚至是一些专业读者,都会以“单纯”、“透明”、“沉静”、“纯粹”这类语词论之,然而,我们知道,仅仅停留在单纯透明的层面,内部缺乏足够的复杂性与丰富性的诗是不值一写的,也不值一读。那么,引发读者长期关注的伊路诗歌的深邃之处与核心到底是什么?推动伊路诗歌写作持续进行并随着时间推移愈加精粹深邃的内在动因到底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可以从她的诗里找到回答这些问题的有效切入点?
关于诗,伊路有一段自我表白:“那参杂着诗分子的生命,一遇到外界的可感信息,就在我的体内闹情绪,终于有一天,我憋不住了,就生出一首小诗来,那可真是脆弱的小东西,但就如同生了一个孩子似的怎么也离不开了。就这样不知不觉地对它负起了责任,就像不知在何时欠了一笔还不完的债一样。我必须把它带大,带强壮,带高阔,带得情感丰富,带得生机勃勃。这谈何容易,我得把自己弄成一座能适合它生长发育的屋宇才行啊!”(伊路《看见》“与诗有关的一段话”,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
相对于诗,伊路却不是以诗人的身份进行自我定位,而活脱脱是一个对自己的诗心怀深沉大爱的母亲!
伊路这种对自己诗歌母性柔情的呵护,体现在方方面面,她写作态度的敬畏感、诗歌语言的精准、诗歌意识的清明,以及她对世界认知的透彻、对自我书写的真诚上,就像她自己说的,通过这些努力,构建一个适合诗歌不断生长的精美屋宇。
一般而言,我们读诗都是由语言之表及诗歌之里,得出对这个诗人或诗歌的总体判断。伊路的诗歌语言总是平静、节制的,她去除掉形成诗歌语言的芜杂路径,不蔓不枝,以清晰自然的表达方式,很准确地把每个句子甚至是每个词语,安放在这首诗来临之前就已经为它预留的那个恰当位置上。
“这话我也是忘不了的/还有多少忘不了呢/世界不会因此重一毫/因为它实在无法轻一点了”(《忘不了》),“世界不会因此重一毫”,这是在世界轻重之间复杂判断面前,最极精微故而也最准确的总结陈述,这种性质的陈述,在伊路的诗歌中比较普遍,作为诗人的她,向来总喜欢把眼前发生的一切重新透彻地思考一遍。存在之思即是语言之思。正因诗人卸去了挡在读者面前的语言屏障,才会让人直接感知她诗歌的表达,仿佛从语言表层就可以直击诗人之所思,这也正是她给人以一种单纯透明印象的原因。其实,这种单纯透明,远非一些人所想的那样简单表面,伊路是想要表现一种她所状写的事物的“客观性”,即它的本然状态,它既是世界真实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世界秘密的构成,它与世界背后不可言说的大道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关联。我想,这才是伊路诗歌的单纯透明却能获得隽永而悠远的诗思的关键所在。
《在黄洋界看见一只鹰》,我相信,这是一次真正的“神遇”,目击道存,这是一种真正将体验赋予生命力的表达,世界就在诗人目击鹰存在的那一刻开始,也是在目击鹰存在的那一刻结束。我想,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语言风格意义上的单纯与洁净了,而是一种将混乱、芜杂、盲目的现实存在净化成只剩下这首诗的一种顶级形态。正是这些存在之思,使伊路的诗歌获得不凡的深度。
诗人并不知道自己是诗人,诗人也不知道诗歌是什么,甚至不知道诗歌是否存在。只有当她与诗相遇时,诗才会发生,诗才会成全她为一个诗人。伊路也在多个地方提到她与诗的这种神遇。所以,她说:“诗人得把那些跨越得比较远或掩埋比较深的、幽微不易觉察、一闪即逝、最新鲜的妙境展现出来。而只要诗人有心有意,似也无需辛苦地寻找,会自发地互相感应、吸引,像火苗一样亮进生命里来。我常常会自言自语地说,谢谢!谢谢先赏赐于我!这种感动同时激发了语言的觉醒和表达要求,因此我觉得语言也几乎是它们给的,没有它们就没有如此的语言。是它们调动了我身心的全部,千路万径一起响应,一个个涌动的小盒子在打开,促使我把它们整体——像一座屋宇般捧移出来。我的每一首诗都不是没来由的,所以每一首都珍贵,不能丢掉。”(伊路《永远意犹未尽》“后记”,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
如果对伊路诗歌价值的分析到此为止,显然尚未更多地揭示出其诗歌的复杂与丰富,尚未对这样一个影响颇广的女诗人说出属于她本人的内在特征来。以上对其诗歌语言的简单分析,几乎是将她作为一个诗人进行的一次抽象。因此,要看到其诗的复杂与丰富,如果我们将她还原为一个女人,也许会有更多属于她本人的深层发现。
拉康令人眼花缭乱的女性主义理论中有一个概念,叫性身份定位,大意是说女人都会在潜意识里“选择”自我,决定自我采取男性的或是女性的生存方式。在当下,随着性自由度的不断扩大,原来看似不是问题的性身份定位如今确实变得是个问题了,这样,我们不能不预设人都是雌雄同体的。有些女人的女性性格只不过是一种伪装而已,这一派的理论家认为,我们所有人都是说话的存在物,即我说故我在,而每个人的存在都要受到整个社会规则支配下的语言或言语的阉割,当我们言说时,我们就已戴上面具。看来,一个言说的女人,自是不可避免地在自我定位与自我伪装间矛盾地游走着。
显然,当伊路作为诗人以发现世界秘密的思者现身时,便超越了性别概念,她从不以自己的性别身份参与到自己诗中的言说,虽然诗中的一切都是她发现、设计、制造组装的,是她对现实经验的提炼,但她努力在诗中保持事物的本来面貌,并努力将她诗中的“我”与现实真身的女性的“我”区别开来,以确保诗中发生的是作为现实真身的“我”身上的客观事实,而并不是仅仅从作为一个女性角度看到的事物。女性视角确实有时候会造成一种偏狭,一叶障目,无法看清诗的全貌,这是她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作为这些诗歌的母亲,她一直不能确定她生下的孩子到底是女孩还是男孩,或者说她从来就不想去确定在她看来毫无意义的性别断定,而这恰恰是伊路作为女性诗人试图让诗歌呈现原状的努力。她的诗是如此客观、精确,像在还原事物的本来面目,截取现场鲜活的切片,我们几乎看不到作者是以女性的身份、视角来言说的性别倾向,很少看到伊路在诗歌中展示女性主义思想、女性身体、女性身份甚至女性主题,也就是说,伊路不把自己的女性身份带进她这些诗的语言表达中。作为女诗人的伊路,只想给自己进行定位:我是她(他)们的母亲!仅此而已,却也足够。
这显然是一种很奇异的悖谬,就是作为女性诗人,与诗中的“我”保持碰上一种性别上的距离,却又在写诗的动因上深具母性意识。如果我们把伊路诗中的那个“我”看作是作来摆脱自我的一个幻象,那么,许多源于现实中的“我”的真切深刻的感受却是通过诗中的“我”表达出来的,有些诗明显清晰的个人经历甚至如《忘不了》这样的诗还带有强烈的个人传记色彩,我们强硬地将现实与诗中的两个“我”严格区分开来,就显得不切实际。但如果我们将这个两个“我”混为一谈,那就无法解释为什么诗中的“我”却极少表露自己的女性性别。
我以为,在这两个“我”之间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悖谬,其实两者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种辩证的关系,一方面,现实中诗人的自我需要通过诗中的另一个自我来实现,这样,诗中的自我与现实中的自我必须具有差异和个性。另一方面,这种差异与对立,又必须是现实的一方统摄诗中的另一方,这样,两个“我”才能在诗人身上得到协调。这就是我前引的:我说故我在,每个人的存在都要受到语言或言语的阉割。我们的言说即是戴上面具的言说。所以,作为一个言说的女人,总是在自我定位与自我伪装间矛盾地游走着。我想,这也正是伊路诗歌的深层心理动因。
在《无数炉子烧出的灰》里,诗中的“我”显然是现实中的我进行一次自我实现的尝试意念:像鸟一样飞远,像云一样上升,但“我升得再高也要落回来”,两个自我相互纠缠也相互牵制。所以,伊路诗中“我”的性别缺失,与其说是她对性别角色定位的疏离与反感,不如说是对一个假想中的那个完美自我的肯定。只有在自己的诗中,现实的“我”才能找到存在感,才能使真实的自我在诗中不断持续地进行。在伊路看来,每一首偶然产生的诗又都是必然现象,因为它深深地植根在“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这个系统“包括诗人的过去、现状、家庭、学养、个性……”,是“一首诗的渊源、根系”。这个渊源与根系,就是制约自我实现的“现实原则”,因而,我们要说,任何一首诗里的“我”都是戴着面具的那个“本我”。
如此,一首诗就是一个我为另一个我而营造的梦境,在这样的梦境里,他(她)们在梦境相遇,超越时空,获取灵魂重生的自由。
我们都得格外小心,“就那么一丝缝隙/就会使石头裂开”,“那么一小片波浪的转身/整座海就改变了秩序”。现实在历史的维度上是环环相扣的。每一首的到来有其因果链上的必然,而这种必然往往又是极其脆弱的,一片雪花终会引发一次雪崩,一次错失将是永远的错失。
为了两个自我在诗的照面,所谓诗人,就是那个不断寻找梦境按钮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