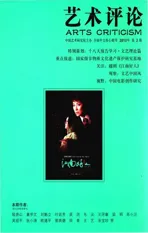茅威涛:越剧是我的宗教,舞台是我的佛门
2013-11-15唐凌
唐 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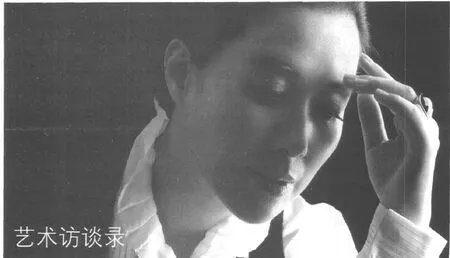
《艺术评论》:沿着您多年的艺术创作轨迹,从《寒情》、《孔乙已》到 《藏书之家》、新版《梁祝》等,能够看到其中明晰的方向和追求。我想知道您如何看待《江南好人》在这个轨迹中的位置?
茅威涛:《江南好人》的创作,相当于《西厢记》之后创作的《寒情》和《孔乙己》等作品,是在追求越剧唯美、诗化的纯度和高度之后的思变,是逐步沉淀下来的某种思考:怎样避免复制那种众所周知、业已习惯了的唯美风格。我是一个不太安分守己的人,愿意做一些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或者说艺术本身就应该具有更多的独特性,给观众更多的审美期待值。
郭导说我们这个戏相当于越剧再次闯荡上海。实际上百年前农耕时代诞生的越剧,从浙江嵊州的乡间田头走进大都市,并在新中国得以繁盛发展,以及后来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间我们所做的这些探索之后,重新面临了一个信息、传媒,高科技急速发展的崭新时代。我们怎样才能够让越剧生存得更好?或者说在当下的时代我们还有没有生存的可能性?我们的空间还有多大?通过这个戏我们尝试着解答这些疑问。
《艺术评论》:郭导所说的这部戏的意义如同当年越剧进上海,您是否认同?
茅威涛:我认同。他说的所谓“进上海”,是一个文化上的维度和高度,并不指具体的地理空间。实际上他是说越剧已然处在了这样一个信息科技的时代,我们应该考虑如何生存如何发展的问题了。
这些年我们的戏曲艺术创作有些固步不前,缺少一些突破和跨越。为什么?我们业内的演员、专家、学者有没有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们的文化官员们有没有在思考这个问题?我相信都在想,都在思考。于是我愿意自身先做一些尝试和努力,以我既是一个表演者,又是一个艺术管理者的双重身份和双重责任,凭着那份文化良知,那份艺术理想。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越剧“芥子园”的梦。
这次创作上的难度很大,但这次合作却是我和导演争执最少的一次。这可能是因为理念上的高度统一,我们明白是在做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茅威涛和郭小男在对戏剧的认知上,对人文的认知和对艺术的追求上,我们是凭着良知在做事情。让我违背这些去懵里懵懂、一知半解地去创作,我是难以接受的。
《艺术评论》:选择《四川好人》的缘由?
茅威涛:选择布莱希特的《四川好人》,最初只是停留在我个人的层面上。就是看茅威涛是否可以再演演时装民国戏。看茅威涛是不是可以演演男人再演演女人,给自己的表演做一些挑战和突破。但是没想到排下来之后,出现了很多新的课题,产生了许多新的思考,思考的同时也寻找到了某种价值。
布莱希特七十多年前写的戏,戏里写的所涉及到的社会问题今天依然无处不在。也就是说,人类为了生存可能发生或已经发生了的关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由此产生的关于剥削、贫富、道德、善恶等等现象,仍然强烈地发生在我们身边,作用着我们的生活,侵蚀着我们的灵魂,伤害着人类自身!比如,“小悦悦事件”、食品安全、贩卖儿童等等,所有的一切都好像正当防卫、理所当然,为了生存么。就像布莱希特笔下这些赖着沈黛去救济的人,他们都觉得我没有办法,我只能这样去生活。布莱希特对底层民众是非常关注的,这个跟现实社会也是有紧密相关的。这个剧能跟当下如此切合,所具有的深刻的现实意义,反映出社会发展的诸多问题。之前,我们只是觉得它是有现实意义的,但是越排越觉得这个价值太强烈了。而我们的选择,正是我们对社会、对人类文明进程的关怀和参与、希望与诉求。
《艺术评论》:除却剧作本身具备的社会意义,从艺术的层面来看,越剧排《四川好人》的价值何在?
茅威涛:它作为一个舞台艺术形态,可能会带给今天的人更多剧场艺术的真谛和本质的东西。剧场艺术从古希腊以来就是带有一点宗教信仰色彩的,在一种“游戏”精神中叩问人的灵魂、启迪人的灵魂。我一直觉得,我做剧场艺术一定要带给观众两个方面的满足,一是欣赏的愉悦,二是思考的愉悦。我觉得这个剧好看、好玩,带点儿游戏精神,同时又很唯美,越剧的载体之外还有思考的愉悦在里面。看完这个戏,每个人都会叩问自己。陶斯亮大姐看完演出后发来信息说,“戏的主题很深刻,切中时弊。对‘做好人难’我一直有切身体会,不过正如戏中神仙所言:必须做个好人,这也是我终身的信仰”。
这个戏的社会价值比我的预想要超出得多,这种思考的逾越几乎是过去的越剧不可承载的。第二个方面我觉得就是技术层面上的,就是布莱希特和中国戏曲的渊源关系。布莱希特在莫斯科看过梅兰芳先生的表演,我也查了一些史料,他看过戏后发表了自己的一些感想,他隐隐约约感到自己戏剧的体系和风格在梅兰芳身上找到了。同时他也在某种程度上批判了梅兰芳的体系。他批判梅兰芳什么东西呢?他觉得他想追求的思辨、间离、陌生化,在梅先生那里只是建立在个人身上,而在文本和演剧风格上并没有建立起来。他希望把剧场永远当做足球场一样,让观众始终带着一种审视的眼光来看。他的《四川好人》剧本前言有一句话,说此剧泛指人类存有剥削的地方。所以,其意义指向是宏大的,由此,也衍生出了我们的改编剧名《江南好人》。而就艺术层面上的价值,就是布莱希特遭遇了中国戏曲,遭遇了梅兰芳。只不过梅兰芳是男旦,而我是女小生罢了。


《艺术评论》:作为表演艺术家,您的表演可能已经到了一种“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因此可以带领剧种去探索它多样的可能性,去拓展它的边界,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但这样是否会对您本人,包括“小百花”的优秀演员造成一种伤害,因为许多时候不是在扬长避短,而几乎是相反,演员们的接受度怎样?
茅威涛:我觉得这次排练给“小百花”全体是一个提升,一些八零后、九零后演员突然发觉原来演戏是可以这样子的,他们会很有创作欲望,也会发现自己的底子还很弱,缺少基本功。他们知道了必须要加强基本功的训练才能够在随心所欲的境界中达到创新。郭导会说,为什么茅老师能够很快地进去你们就进不去,为什么茅老师能够找到手段你们就找不到手段呢?就因为积累得不够。所以创新是需要积累,需要资本,需要勇气的。首场演出结束,我的一位资深媒体人朋友送我宋代黄庭坚写水仙花的两句词,叫做“坐对真成被花恼,出门一笑大江横”。什么意思呢?你比如说唯美的,才子佳人的,整天是这些,最后就像你一直对着水仙花,你自己都会恼了。但是你出门一看“出门一笑大江横”,这个世界原来这么开阔,还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我想这是特别有意思的,而且对于剧团和我个人不具备伤害,只是又一次豁然开朗了起来。
《艺术评论》:我知道《江南好人》的整个创排过程中难度和付出都是极大的,然而并没有任何要求你们必须要这样做,完全可以延续以往。
茅威涛:延续原来的风格,这对我们来说太驾轻就熟了。就是把戏排好,把唱腔设计好,把身段设计好,把人物理顺。而我们现在是在寻找一种在世界戏剧的语境中对话的可能性。十八大之后,当我们整个社会经济都在寻找转型升级,寻找中国梦的时候,我们戏剧人如果没有一点转型升级的理念,怎么办啊?我们不想唱高调,我们是有这个心理准备的,所以我开玩笑说这次是穿着防弹衣来北京的。我也知道这一次的批判声一定会超过《孔乙己》,但《孔乙己》十多年后大家都觉得好。我相信时间会给出一个正确的答案来的。
《艺术评论》:目前观众们对这个戏的反馈是什么样呢?是不是专业人士反而没有声音?
茅威涛:对的。以前我每一次演出,都会在演出后的第一时间接到朋友们的意见,这一次演完《江南好人》,我没有在第一时间听到专家们的意见—-我想是不是我们这次步伐走得太快,这种跨越超出了戏曲业内的承受能力?但也有许多观众立刻就有了很好的反应。业内老师的“失声”,这一点我是有准备的。我觉得他们还在思考,真正的知己好友他们会想好,再来给出一个中肯的评价。其实我已经听到一些比较难听的声音,没关系,中肯的意见再难听我也会接受。我这个人既骄傲也平实,我必须要把自己的心性养护得很高洁,要不然我没这个底气和能量。
中国美术学院许江院长的一个观点我非常同意,就是凡有技术,一定是先有学术的。这个戏之后我更坚定了这样的理念。之前我年少无知,对阿甲先生的“戏曲是技术先行”的理论很不以为然。当时觉得要演戏就是体验先行嘛,一定是先体验再表现。但通过排这个戏才知道阿甲先生的了不起,戏曲真的就是“技术先行”。演了三十三年小生,在剧团、学校坐科经过了那么多的训练,当我演沈黛的时候,我想把之前学习的“昆舞”用到她的身上。但是说说容易,当我真正要这样做的时候,我竟然没有支点,手脚都不知道怎么放,真的是手足无措啊!而有了一些姿态后,气息又不知道怎么走。陈辉玲(剧中饰杨森)也一样,她所有的准备都是旦角的,所以对我们来说真是乾坤大挪移,这个挑战太大了。目前隋达这个人物我还可以驾驭,但是这个旦角(指沈黛)我只能说还在素描、临摹,我觉得还有上升的空间,请大家给我更多的时间。还有就是声腔,越剧最体现艺术特质的就是流派唱腔。隋达我可以唱我师从的尹(桂芳)派唱腔,我想沈黛可以找一个花旦的流派来唱。后来觉得一定唱不好,我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掌握,最多就是模仿,而且也没有江南那个年代的风情。当时就想到了用一点评弹,因为沈黛本来就是个歌伎。同时,我还用了一些江南小调,让它有一点那个年代的味道。表演上用爵士舞、RAP之类不是噱头,也不是为了搞笑,纯粹是在追求达到“间离”的效果。
《艺术评论》:但是比照而言,这样做会不会使得越剧的成分相对有点儿弱?
茅威涛:我目前感到此剧多一点则多,少一点则少。就是你再多加一点唱腔,会不会削弱布莱希特本身的思辨意味?现在的“嫁接”,它一定要有一个度,我个人觉得现在还挺恰到好处的。不过现在戏有点长,这需要在演出中不断修正和改进。
《艺术评论》:由于布莱希特剧作本身的“硬”,使得融合难度很大,但有些地方把越剧和布莱希特融合处理得特别好,比如最后审判时您跪下来陈说心曲“我不是个好人,也不是个坏人”的那一段,真是情理俱佳,令人动容。
茅威涛:是的,你刚刚说的那一段真正是理性的思辨达到一定高度的感动。德国汉学家,原歌德学院院长阿克曼先生也认为此段最为出彩。记得第一天演出到这里时,我唱着念着眼泪就下来了。西方叫“原罪”,我们儒家叫“人之初,性本善”。到那个时候,真的是到了雌雄莫辨、善恶不分的境界。这时的善恶同体,就像刮骨疗伤,是痛在心里的。但是,布莱希特的那种“硬”和越剧本身的“软”确实是两种相抵消的气质,我们也还在调适、寻找更适合的手段和形式。这个“度”的把握,导演真是下了功夫。我觉得郭导的了不起之处,是他把布莱希特的西方政论文用东方的散文和诗歌的形式来表述,这是最难做到的!我们这次每场戏排练的时候都录下来,然后大家看、谈,联排之后继续看,检查自己的问题。
《艺术评论》:郭小男导演与您有过多部作品的合作与共同探寻,您认为郭导对这部戏的贡献何在?
茅威涛:这次非常有意思,以前的作品中我可能会提很多意见,但是这次我觉得郭导有他的看家本领,有他的所谓学院派艺术理念的秘笈。他所坚持的艺术纯粹性,以及他游学日本学习到的黑泽明的导演意识,很多之前积累的东西全部调用到这个戏里面了。而且他最大的功力就是在布莱希特和越剧的契合上找到了很好的一个点。既是布莱希特的,又是越剧的,这个分寸很难拿捏。所以濮哥(濮存昕)看完演出说:“小男、茅茅,你们不得了,你们就像李安做《少年pi的奇幻漂流》一样,大家都以为做不了,结果就真的做成了。”当然我们的青年演员依然还需要“描红”,依然要像我当年做传统戏一样,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来,然后才可能做这样的作品。
《艺术评论》:以您的理解,这么多年,郭小男导演在您的越剧生涯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而他为“小百花”创作的诸多作品在他本人的导演生涯中又占据什么样的位置,您觉得这些创作有没有很好地实现他自身的艺术理想和他的艺术潜质?
茅威涛:我曾说没有郭小男就没有茅威涛。真的,每个演员都有改变他命运的导演。如果说我的艺术生涯是分两个阶段的话,第一个是杨小青导演,第二个就是郭小男。他真的懂得我,他知道我想要什么,他在帮助我实现自己的艺术理想,他为“小百花”打造了极高的艺术品质,同时也实现了他自己的诸多艺术理想。他现在依然不喜欢越剧,常常开玩笑说,他是一个打铁匠,却让他来绣花。但是我相信他所追求的写意和诗化,越剧给了他文化上、美学上的很多认识和支持,我觉得也是在成全他。我觉得我们就像萨特和波伏娃,是双方互相影响的。但是确实因为给我排戏,他也回绝了一些自己很想完成的邀约。我跟他开玩笑说,导演和演员不同嘛,我也就这么几年了,而导演如同中医,老了更吃香啊,你先给我排,等我演不动了你随便!我觉得我们比较契合的就是对艺术的纯粹性的追求。

《艺术评论》:这种纯粹,是最不易也最可珍贵的。
茅威涛:我去高校讲座,有人问我:茅老师,你的信仰是什么?我就说,越剧是我的宗教,舞台是我的佛门。我常说,人这一生做好一件事就非常好了。一位英国评论家评论梵高,说他一生用全部精力追求了一件世界上最简单、最普通的东西,这就是太阳。我欣赏这样的生命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