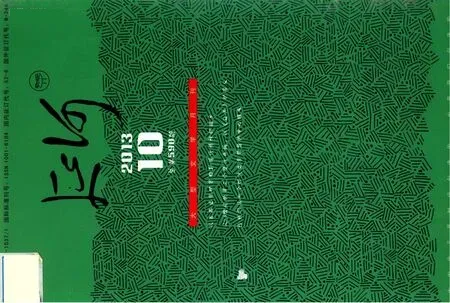镇 物
2013-11-15张秀峰
张秀峰
自打入伏以来,太平家就没有真正地太平过一天,总出事,接二连三地,先是死鸡,一只一只地死,十天不到,一十几只鸡就全都死了。然后呢,就开始死羊,连当年的羊羔子都没能幸免,全死绝了。没过几天,喂了半年的克朗猪也死了,时隔不长,他家的那头老灰叫驴也悄没声儿地死在了圈里。又是请兽医,又是按土方子灌药,一点作用也没有。看着这些原本上窜下跳、欢实可爱的牲灵们一个个地变成了僵硬冰冷的尸体,太平这心里是百爪挠心。可是呢,还没等太平缓过劲儿来,家里的人又开始害病,先是老婆,下来是大儿子、小儿子、女儿,这个刚爬蜒起来,那个又睡倒了,轮班换岗地,没消停过一天,独独他没害。八九月天,庄稼都熟了,正催人呢。太平一天忙完家里的,又忙山里的,跑断骨头累断筋,脚后跟打着后脑勺地两头奔。半个月下来,七千多块就全赔了进去,精精壮壮的一个后生,愣是操磨得变了样子走了形。
“日他先人的,今年一满里不顺头。”太平说,狠命地抽着烟。
“狗日的。”太平说。
“要我说,这怕就是命,是命!”太平说,睁着通红的眼睛。
“你说是命吗?净胡球说。”胡子爷挪开了嘴上的旱烟锅,看着太平,说。
“那可不,不是命还是个甚,你倒说说看,那么多的麻烦事咋就都让我给摊上了呢?这叫个甚事。”
“吃了驴肉嚷鬼话,大路上的狗屎咋就净让你一个踩了呢?放屁拉了一裤裆,哪有这么背运的?我估摸着,得是你那地方有问题,要我说,还是请个阴阳先生来看看吧,不碍事的。”
村里的人都这么劝他。
“球,我才不信那号东西,鬼谷乱谈的,两句鬼话就把你们哄得五迷三道的,哼,我才不相信呢。”太平倔倔地说,脖子一梗一梗地。
“你看你看,狗吃粉子糨(犟)×嘴,糊脑孙了不是?”
“这鬼孙,真是犟板筋,不识人心好坏。”人们说,悻悻然中透着惋惜。
“球样。”胡子爷说。
“我才不信呢。”太平说,“我上过小学五年级的,学过文化,你们说的那是迷信,是假的。”
老镢头一上一下地翻飞,很实在,也很沉实。太平觉得这才是真正的生活。
亮红晌午的,罗阴阳就来了。
罗阴阳是在背庄埋完人后被太平他大背锅老汉叫过来的。背锅老汉知道和太平说这事肯定不行,就先斩后奏。先请来再说。没想到太平正在家,老汉就有些尴尬。
“我让他来看看。”背锅老汉说。
太平就站在太阳地里看着罗阴阳,眼睛亮亮的。
“就是看看嘛,碍不着甚事的,咱家今年不顺头。”背锅老汉看着太平,说。
“是这,我就是来看看,我不来,是你大硬拉我来的。”罗阴阳说。
太平看着罗阴阳,不说话。
“知道吧,背庄的木狗老汉今早上才发丧出去,一上午都没消闲,把他家的,这不,刚从山上下来嘛,你大就叫我过来了。”罗阴阳说。
“你要是不让我看,那我就不看,我还要坐席去。”罗阴阳说,看着太平。
“噢,那就看看”。太平说。
罗阴阳斜歪着脑袋端详了老半天,眉头就皱了起来,脸上一忽儿晴一忽儿阴的,然后拿出罗盘,放在地上,站远了,走近,然后又蹲下,站起,很认真地端祥着,突然像火烧了屁股似地跳了起来。
“啊噢,啊噢,了不得了不得。”说完后,还牙疼似地抽了抽嘴。
太平看着他,觉得这家伙做什么总是神神道道的,很招人厌。
太平一向对这个家伙没有好感,总觉得他不顺眼,削瘦寡白的脸上总带着些败败的灰色,小眼珠子闪烁不定,东瞅西睃的,一点都不正相。特别是说话,总是偷声缓气的,好像随时都在密谋着什么,最不顺眼的是那几根稀稀疏疏的黄胡子,就那么胡乱地支乍着,还总爱穿些个灰不叽叽的衣服,松松垮垮的,长袍不像长袍,短褂不像短褂。不知怎么地,太平一下子就联想到了老鼠,所以一看到他就不由得想笑,现在,他又想笑了。
“什么?”太平问。拼命地忍住笑。
“你这窑址是谁定的?咋连个规矩都不懂。”罗阴阳说,语气很严肃。
“我这地方向阳背风,吃水又方便,还不好吗?”太平问。
“啊呀呀,你这人真是的。”罗阴阳瞅着太平,有些不耐烦。
太平不说话,只是眨巴着眼睛看他。
斜眼瞅着太平,看他像真是不懂,就有些恨铁不成钢的意思:“是这,你这地方坐字儿不对,晓得不?你看看你看看,啊哟哟,这叫什么话?啊,怕连姜太公、徐荗公也不敢坐这样的字儿呢,咱算什么?平顶子老百姓一个,这么价胡来,能服得住?”
“要改,一定要改,要不就麻烦可就大了。”罗阴阳说。
“嘿嘿,我不信,”太平终于憋不住,笑出声来,“打小我就不相信那号事。”
“什么,你再说一遍。”
“三个阴阳定不下了拴驴的橛子。”
“你呀,真是头驴,一头倔驴。”罗阴阳说。
“这号人,说不成个球事。”罗阴阳说,跺跺脚,走了,肚子一鼓一鼓地,活像只蛤蟆。
“哎,我说你个鬼子孙罗阴阳,咋不吃饭就走啦?”
太平来找罗阴阳的时候是一个有霜的早晨,罗阴阳正在拉屎,脸憋得红红的,像个正在下蛋的小母鸡。太平就站在茅房外短短的土坯墙边跟他说话。
“消停了,总算是消停了。”太平说。
“噢。”
“鸡死了,猪死了,老叫驴也死了,”太平说。
“噢。”
“你不晓得,我那是半大的克郎猪呢,骨架可真不小,就是还没长膘,说好了今年十月出栏,卖个好价钱,咋说死就死了呢,好可惜。”
“噢。”
“那是我开春时在集上买的,出了二百块钱,我能看出那是个好胚子。”
“噢。”
“还有,我家的那头驴,你见过,是头叫驴,顶好使唤的。一点也不欺生。那年满顺用骡子和我换我都没答应,我那驴真真儿个好,口轻,又肯下死力,猛格拉乍地,就死了,”太平说,“日他先人的,这叫什么话。”
“我大也殁了,今儿个是头七,”太平说,声音颤颤地,顿了顿,又开始说,“安塞、延安,几个大医院都去过了,查来查去,愣是查不出个什么,眼见着肚子一天比一天大,那么刚强的个人,竟然疼得嚎哇哭叫,实在没法子了,请后阳沟的王巫神来跳过一回大神,好了几天,就殁了,唉。”
“噢。”
“谁不晓得王巫神顶着黑虎灵官呢,听有万老汉说,很灵的,拉板她妈的心口疼就是他给看好的,咋就偏偏治不好我大的病呢?你说,这是不是命啊?”
“噢。”
“唉,我看就是命,老辈人常说……”
“胡球说甚哩,这咋是命哩嘛?我说啦,是你那地方有问题,”罗阴阳一边说,一边系着裤带,语气十二分地肯定。“早就给你提了醒,你个狗日的就是不听,看看,看看,这不有事了吗?哼。”
“咋会有问题呢,我不信,”太平说,语气软软的,明显的底气不足。
“你那地方坐字不对,”罗阴阳加重了语气,说,他左右看了看,忽然压低声音,将嘴凑近太平的耳畔,“而且还被人下了镇物。”
他一惊:“什么?镇、镇──物?”
“对喽,就是镇物。”
“怎么可能呢,绝对不可能。”
罗阴阳看着他,笑了笑,背抄着手,雄赳赳地回家去了。
他马上意识到:事态严重了!脊背上一阵发凉。这下可不得了了,他知道,若真如罗阴阳所说,那他家发生的一切不幸就全都会有了一个合理的解释——以前他只是听说过,并没有亲见,石匠给人家箍窑洞时,若有主家怠慢于他,他便会给这家人下镇物── 一把泥刀、一个钢钎甚至是一双破手套、一块石头,只要一沾人血,然后封进窑里,就会变成一个十分灵异和可怕的东西,然后这家人就别想有安生的日子过,轻则多病多灾,重则死人断后。
太平脸色通红,愤怒使得五官都挪了位。
“狗日的。”他咬着牙,狠狠地骂。
“是金锁,肯定是他,这个狗日的,我箍窑时这小子才是个学手,合龙口那天我发烟时忘记给那狗日的发了,他当时就恼了,口口声声说我没把他当人看,”
“肯定是那小子。”太平说。
“你得禳解。”米阴阳说,“要不还得出事。”
果然,经过一番搜腾,在第三个窑腿下找到了一些物件:一把泥刀,几根铁钉,都已经锈得不成样子。
米阴阳说,按行规要收二百元钱的,但这是行善事,就不能要钱了,可又不能坏了规矩,就拉走了太平家的一只黑头山羊。
“这是行善事。”罗阴阳说。
年底刚过,太平就被枪毙了,犯的是故意杀人罪。
村里人说,太平也真是的,金锁给你家下了镇物,那是你怠慢人家在先,别忘了,那可是匠人呀,就他那驴脾气,换了金锁,别的匠人也会这么做的,及古以来,没听说过谁还敢得罪匠人的。再说了,你把金锁杀了,那是他的报应,一对一扯平,告到法院也有理,你杀人家的老婆娃娃做甚?不死才怪呢!
太平的婆姨自太平抓走后就疯了,整日价坐在门口哭一气,又笑一气,晚上就在对面的山畔畔上孤魂野鬼似地游荡,发出一阵又一阵的长长的嗥叫,像狼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