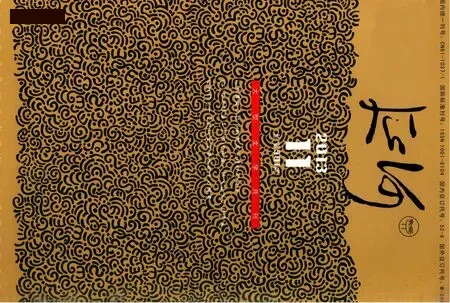陈年的惊问
2013-11-15一果
一 果
那年夏天,高考失利的哥哥重操旧业,他重新拿起了画笔。那天我们家的院子里聚拢了许多人。人们的表情复杂诡秘,说不上来路。他们寓动于静,以一种安全的静态表情表达内心的心照不宣。父亲不说话,一张脸在烟雾缭绕中时明时暗,阴晴不定,同样说不清来路。母亲提着一空水桶从厨房走出来,说,散了吧,大伙都散了吧。红玉娘压附在母亲耳边偷偷说,新鲜几天就锁起来吧,你忘了水莲的相好被砍掉的手指头了?母亲一哆嗦。她花了好大力气才稳住身体。可那极其隐晦的不祥预感却怎么也赶不走。红玉爹在走出我们家门槛后给了他婆娘一个白眼,就你话稠。虽这么说,可他迈出的脚步却是怵然戒惕的。
人们对待陈年旧事的态度,要么津津乐道,要么闪烁其词。亘古不变。对待陌生事物,则一律采取批判的眼光。这是体面的人们总结出的狡黠的智慧。无师自通,心照不宣。有一年春天,一个名叫戴静书的年轻人来到了我们镇。他带来了一样陌生的东西:油画。他画的油画光怪陆离,每一笔都充满了魔幻的神秘色彩。镇上的人看不懂,都说,哪里是什么画,分明就是油彩开会。不着调,胡乱拧巴的屁。更有人说,什么狗屁画家,弄些油彩和画布,老子都是艺术家了。同样遭受质疑和嘲讽的,是年轻画家的过肩纷乱的头发。用镇上男人的话说“是不男不女的狗屁玩意儿。”
年轻女子可不这么看,虽然她们同样也看不懂,她们恨自己看不懂。知音相遇永远是别人的故事。画家的每一笔都长了指头,在她们内心深处无声撩拨。喜爱在内心以隐秘的方式滋长。这种情感既润物细无声,又葳蕤四溢,同镇上的植物一样痴长妩媚。每天清晨,戴静书站在那副画布前,小凳子上是摊开的油画色板。油彩斑斓绚烂,每一个色彩都眉清目秀媚艳撩人。年轻的画家眯着眼睛,修长的手指捏住画笔,画布上的色彩随姑娘们的心事流转。水莲也是这群看客中的一员。
两种迥异的审美情趣不久就水火不容。它们针锋相对,它们唇枪舌剑。说到底,两种交锋,其实是女人和男人的交锋,也是新和旧的交锋。女人们忘记了一个颠扑不破的规则:世界是男人的,也是女人的,但归根结底还是男人的。
一种隐晦的杀机悄悄滋长。年轻的画家很难再置身事外。
哥哥作画时的神态,和戴静书有着惊人的相似,镇上上了年纪的人私下里都这么讲。人们一向喜欢总结经验教训,总是善于在两段不同的历史里寻找某种相似的联系,尔后据此推断。既定推断使人们未卜先知,他们恍若看到了哥哥未来的命运,和遥远的戴静书紧密相连。在哥哥如痴如醉地勾勒他的画中世界时,一种关涉他的预言在镇上悄然流传。灾难向来是预言的中心内容,忧戚和戒惕使充满智慧的双桥镇人看上去忧心忡忡。
先验的暗示和灾难的昭然若揭,勾搭出明确的不祥气味,在我们家狐狸尾巴一样神出鬼没。父亲噤闭不语,母亲却按捺不住。她惊悸于每一个眼神,每一个眼神都意味深长,都长出尖利狰狞的指甲。女人表达某种激烈情绪的智慧,向来都是出其不意,让人措手不及。那个夏日的夜晚,母亲突然大哭起来,毫无来由。母亲的哭号愈发加重了父亲的心烦意乱。父亲一张黧黑的脸变了色,冷气嗖嗖。父亲捻灭烟头,大声说,深更半夜的你他娘的哭个球!母亲的哭声依然我行我素,愈发恣意嚣张,似乎等待着某种炸裂,抑或是某种承诺。终于,父亲一巴掌打在那张破旧的桌子上。别哭了!父亲说,你他娘的别哭了!我明天一早就把那龟儿子的东西锁起来!
父亲说做就做。翌日,黑着脸的父亲走向他的儿子。这注定是一场司空见惯的不平等交锋。不待父亲发布他的命令,哥哥就说,不。父亲说,给我!哥哥依然说,不!父亲看着他的大儿子抱着作画的工具,脸上决绝的神态分明是鱼死网破的前奏。父亲缓和了口气,声音里堆满语重心长和推心置腹。父亲说,等这段风声过了,你再拿出来画,到时我绝不拦你。哥哥大声说,你怎么也相信那些鬼话?那些话都是流言蜚语,都是谣传!你怎么也会相信!父亲一怔。给我!今天你必须给我!父亲的声音不容置疑,粗暴无礼。哥哥的脸上卷起刀刃一样的笑意,就是死,我也不会给你!在这一触即发的攸关当口,躲在屋外窥伺的母亲冲了进来。说什么死,你要是死了,娘我也不活了!母亲哭泣着拉着哥哥的手,儿啊,娘求你啦。
双桥镇人发现哥哥不作画了。在流言长了翅膀蝙蝠一样四处瞎飞的时候,哥哥竟然不作画了。哥哥的浪子回头,斩断了双桥镇人对预言嗜血般的热情,同时也葬送了他们对事物引发和怀旧的津津乐道。他不画了,双桥镇人叹口气说。叹息里暗藏着一种怅然若失的隐隐不快。好多日子过后心头还难以释怀。
不作画的哥哥又重新拾起了课本,哥哥捧着课本时常常若有所思。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哥哥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哥哥还惦记着他的画。在每天捧读课本的这段时间,哥哥心不在焉,显得孤独寂寥。不久之后哥哥开始鼓捣收音机、收录机等微电器。哥哥的聪明才智,使这些几乎被主人遗弃丢掷的物什起死回生,重新发挥它们的作用。哥哥的身影开始频频出现在双桥镇上大街小巷。哥哥不接受任何报酬,只是间或有意无意地打探戴静书的过去。双桥镇人向来喜欢总结经验教训,他们为此展开了诸多细微的联想,每一个联想自然都是有关之前那个不祥预言的派生部分。这样多好,双桥镇人说,他要是继续画画,一条路走到黑,说不定就——话语戛然而止。犹如作画时的留白。留白的部分寓意无限,任人遐想。对于戴静书的过去,双桥镇人也采取了留白的手法,在最关键的部分闪烁其词欲言又止。双桥镇人暧昧而又隐晦的态度,只能激起哥哥更加疯狂的好奇。
终于有一天,红玉的娘向哥哥追忆了戴静书的过去。红玉娘对双桥镇人留白的部分展开了补续。探询者对于过去的专注和好奇,无疑让被讲述者感到无限快慰。红玉娘故意使自己缺失水分的嗓音置身在神秘诡谲的故弄玄虚之中。“他的画镇上的人都看不懂,偏偏大姑娘小媳妇们都喜欢他。看不懂也喜欢,你说这是什么道理?”
不知道。哥哥说。
那还不是贪念他人长得好看。红玉娘说,自古红颜多祸水,说得是女人。可是这男人长得好看也是祸水。
不明白,哥哥说,好看的男人怎么会是祸水?
这有什么不明白的。哥哥的不解其意使红玉娘顿生对牛弹琴的憾意。这有什么不明白的?长得好看自然遭人嫉恨呗。红玉娘说,你知道他怎会被人剁掉一根手指头?他勾引人家寡妇水莲,他把脱得一丝不挂的水莲画成了画,画成了画啊。全镇的男人们都看到了。水莲的大伯子小叔子能饶得了他才怪,这不,就砍掉了他一根手指头。
水莲既是寡妇,哥哥说,既是寡妇就有追求幸福的权利。
你怎么能这么说?红玉娘瞪大眼睛,名声可是女人的命根子,女人要是不爱惜名声,那还怎么有脸在世上存活?哎呀,我怎会给你这个学生娃说这些,真是昏了头了。
一种隐晦的冲突笼罩在这个夏日的午后,讲述者和探询者迥异的立场愈发加重了夏日的燥热。知了声在午后恪守自私,聒噪声扩散着一种前所未有的艰涩。收音机在哥哥的摆弄中,终于发出了声响。只是不甚清晰的电台波段声斑斑驳驳,仿佛诉说着一个遥远的陈年旧事。在强劲有力的知了声中,显得孤寂难支又不合时宜。冗长的沉默是红玉娘打破的。红玉娘说,要说这也不能全怪她,哪个女人不愿找个依靠。可这女人一动情,就矮了几分,就不值钱了,脸面不管不顾了。不过,找个画画的男人靠得住吗?红玉娘这样说。不知是出于对哥哥的让步,还是对水莲的同情。哥哥不置可否地一笑,算是对红玉娘一个回应。哥哥临走时抛下的一句话,让红玉娘过了好多天后还只想抽自己一嘴巴。哥哥说,谁说画画的男人靠不住?
不久之后,双桥镇人很快就发现哥哥开始反复听一首歌曲。确切地说,是一首没有乐器伴奏的清唱,是一名女性嗓音。嗓音苍凉空茫,自吟自唱,嗓音时断时续,支离破碎,充满了陈旧,让人们联想起在风雨中浸淫多年长满苔藓的旧墙。纵然人们支起耳朵,也无法完整清晰地听清她在唱些什么。人们的面部表情支离破碎、四分五裂。攒足好大劲儿五官才总算各就各位、各司其职。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嗓音浅吟低唱,无限哀愁,无限寂寞。就如同哥哥和他的画一样知音难觅。双桥镇迎来了绵绵细雨,密密匝匝的雨帘挂在屋檐下,合着来路不明的女性嗓音,映衬出哥哥迷蒙的身影和失神的眼神。哥哥的行为,在双桥镇人的眼里,自然背上了悖谬的色彩,难逃双桥镇人如炬的慧眼和意义不祥的非议。本已逐渐土崩瓦解的流言,此刻卷土重来。有悖常理自然是灾难的前奏,依照常理生活的双桥镇人仿佛一下子把握住了真理。这孩子怕是魔怔了,有人这么说。一个女人道出她的疑惑,不是不画画了吗?言外之意很明显了。那东西透着邪性,另一个人看上去成竹在胸,说,八成是让邪性缠上,甩也甩不掉了。女人就睁大她惊恐的眼睛,贼一样向四周窥探,仿佛真的看到了妖魔鬼怪。父母继承了上次流言入侵时的态度,父亲的脸终日硬绷,母亲的愁容放大了又缩小,缩小了又放大,完全是察言观色后不得已的进退两难。连日雨水过后,太阳终于露出了头,患病了一样,在双桥镇的上空垂头丧气,每一根光线上都涂满铁锈。
哥哥的录放机没有挺过中秋节。中秋节的月亮一反常日的萎靡困顿,月亮在中秋节的夜空不同寻常,安详从容,一副母仪天下的富态相,每一个家庭都沐浴在月光下话团圆,搜肠刮肚地说一些吉祥话。那个夜晚,除了哥哥,我和妹妹都围拢在院子里的石桌前,吸溜着口水,等待母亲拿出月饼。哥哥不知道灾难即将来临,他躲在屋里,兀自听着那段含混不清的唱腔。哥哥的缺席,使这个本该热闹又温馨的场景蒙上了一层勉强色彩。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母亲使唤妹妹叫哥哥。妹妹贪婪的眼珠子遽然就黯然神伤了。妹妹撅着嘴巴,在哥哥的窗前敷衍地叫了两声。今宵离别后……回答她的依然是那个神秘的女性嗓音。妈,哥都不搭理我,他还在——猛一抬头,妹妹无意间撞见父亲黑着的脸,未说完的话生生给吓进了肚子。你去,你去叫你哥出来吃月饼,母亲说,同时慌乱地扫一眼缄默不语的父亲。母亲的声音小心翼翼,我也小心翼翼地站起身。都坐下!谁也别去搭理那个龟儿子!父亲的声音炸雷般爆裂。月光长出了指甲,月光抓挠着大地,长久的阒然无声预示着灾难的无可规避。父亲闯进去,随即,我们听到啪的一声,这一声响惊心动魄。月光长出了牙,铺天盖地。我们冲进哥哥的房间,哥哥的神态僵死在脸上,一副毫无戒备的愤怒模样。父亲用脚碾灭烟头,一扭头出了哥哥的房间。哥哥的收录机躺倒在地,四分五裂,在月光的照射下奄奄一息。一切都恍若视觉的,一切又如同非视觉。
母亲颤着声安慰哥哥,坏了再买新的。哥哥不做声,母亲的安慰犹如隔靴搔痒。不做声的哥哥脸上顿现一种鱼死网破样,胶合着月光,面目可怖。有话你不会好好说,母亲冲着消逝的父亲背影大声吆喝,过节也不让人安稳。咣当。这一声听上去丧心病狂,哥哥操起窗台的玻璃花瓶,晶莹剔透的玻璃碎片拼了命飞迸,整个静谧的夜空都被这种危险的炸裂声弄得无处遁形。
哥哥和父亲的战争,看起来在所难免,我们家的每一寸空气都揣摩到了这种预示性的蕴含,我们脚下的每一块砖都不踏实了,走快半拍或者慢了半拍随时都有天塌地陷的危险。事实上,战争没有爆发,愈来愈清晰的事实和我们与日俱增的戒惕心态背道而驰,说不清原因,仿佛是生活的一次睒眼。
中秋节过后双桥镇迎来了秋收。那个秋季我们镇的收成不错,玉米堆满了家家户户的平台,玉米成了双桥镇人眼中心照不宣的风景,所有的预设都毫无悬念,果然是一个丰收年。人们丰满的笑容里堆满了沾沾自喜和欣欣向荣。那年秋季,双桥镇似乎只有哥哥愁眉不展。他一张脸透着疲惫怅惘,散发着地窖般的幽远气息,同双桥镇人铺张的喜悦格格不入。
哥哥不久之后再次成为双桥镇人关注的焦点,被关注的源头是哥哥怪诞的行为。在双桥镇人逐渐忘却两次荒谬透顶的预言的时刻,哥哥带着他的收录机挨家串户。收录机里,那个不详的女性嗓音吐字清晰,在每一户人家荡漾。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愁堆解笑眉,泪洒相思带。人们这次都听清楚了。你们听听这是谁唱的,哥哥说,你们都认识她的,哥哥说这话时的表情怪异。人们答不上来,你们都认识她的,哥哥说,怎么连她的声音也听不出来了?哥哥的声音大摇大摆,人们都闻出了哥哥声音里嘲弄戏谑的味道。
哥哥的怪诞行为,给双桥镇人带来了无穷无尽的想象。想象沿着灾难的尽头顺流而下,戛然而止。人们原谅了哥哥的无礼,人们开始变得忧心忡忡,几乎所有的人都看到灾难吐着毒辣的蛇信子。这孩子这次真的是魔怔了,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妇人很不放心地问,不会出什么事吧?人们一起沉默。这都是命啊。一位已近耄耋之年的老者捋着白花花的胡须,一开口就是谚语。老者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这就是命啊,人的命天注定,又有谁能拗得过命呢。面对这些模棱两可遮遮掩掩的说辞,红玉娘的声音可谓振聋发聩,怕是水莲当年死得不甘,她的魂附了这娃子的身。人们都噤了声,担心都是象征性的,互怀鬼胎的目光撞上彼此,又闪开。心有灵犀,心照不宣。
死亡对水莲来说是最后一次体面。贞节是女人的生命,女人的全部价值和意义,都不过是这两个字。水莲的身体漂浮在双桥镇的河水中,恍若是河水的疤。水莲过腰长发同河水缠绕纠缠,如同河水中长出了黑色水草。即使死亡也不能葬送她的娇艳。那副水莲的裸体油画在人们的目光中栩栩如生,活灵活现。水莲的身体后来被摆在河滩上面,法医操持凛冽的手术刀在她身上游刃有余。有好事者偷偷爬上河滩的树,偷窥解剖过程。自此,这个好事者后悔迭迭。水莲在油画中饱满的玉体,再也无法支撑他的想象了。他的想象此后黏满触目惊心的血腥色彩,丧失了温度,唯一堆破烂器官在心中繁殖。
公安机关出具了这样的尸检结论:溺水窒息而亡。可能是自杀或者意外溺水,但也不排除他杀的可能。双桥镇人在水莲死亡的方式上达成了惊人的默契,他们认定是自杀。水莲生前有辱风化的个人史,唯有通过自杀,才能保全最后的体面。
红玉家是哥哥最后光顾的。红玉娘很庄重地缄默不语,如同忌讳一样隐晦。哥哥依照惯例,向她展示了那个神秘的女性嗓音。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请进些小菜。谁!谁!清唱猝然中断,随即是一声惊问,声腔竟是再熟悉不过的双桥镇口音。哥哥什么都没说。红玉娘终是没有抵挡住那无法破译的神秘嗓音的吸引。
你还是走吧。我也听不出是谁在唱歌。
你再认真听听。你认识她。
我认识她?
她当年就住在你家隔壁。
你是说金宝家的?她可是个结巴。
不是金宝家的。是另一个人,据说她是淹死的。
你是说——
老天爷啊。红玉娘瞪大惊骇的眼睛,屋外的太阳犹如瞳孔一样漆黑。
夜晚的阒寂满足了叙述者的心理需要。晚上熄灭灯后红玉娘说,你知道收录机里唱歌的是谁?管他是谁,红玉爹说,你往后少管闲事。你也认识她,红玉娘说。我认识的人多了,管他娘的是谁!她当年就住在咱家隔壁。金宝家的说个话都结结巴巴,还能唱歌?不是金宝家的。她已经不在了,是淹死的。你是说——你别瞎说!我没瞎说。我仔细听了,是她的嗓音。歌还没唱完她还问了声谁,八成是有人到她家串门去了。
红玉娘看到自家的男人惊恐地弹跳起来,由于用力过猛,他的头撞上了墙壁。咚的一声,合着床板的嘎吱声犬牙交错,水莲死后的双眼在黑夜中炯炯有神。红玉娘慌乱之中拉开灯绳,自家男人惊恐的面部和水莲死而复生的眼睛一齐向她汹涌过来,裹挟住她。一大堆似是而非的疑问顷刻间昭然若揭。
当晚,哥哥亲手毁掉了那盒磁带。哥哥的这个举动,使我们的猜度瞬间跌入了俗套,失却了意义。哥哥把磁带放在地上,取出铁锤,“咔嚓”的一声,磁带的塑料碎块迅疾向夜的四周飞溅,夜晚被这声响撕开了一道口子。“咔嚓。”随后又是几声咔嚓,声音战栗、揪心,整个夜空千疮百孔。
那晚哥哥回溯了一个梦,那个梦旷日日久。那年他九岁,正是好奇心鸡飞狗跳的年龄。水莲家的那台录音机占据了哥哥的全部憧憬。那晚,他偷偷潜入水莲家的院子。水莲的房门虚掩,哥哥乘虚而入。水莲不在,静谧的夜晚无限扩大了哥哥做贼心虚的脚步声,同样做贼心虚的还有心跳。借助手电筒,哥哥轻而易举地就捕捉到了他心仪已久的宝贝。录音机置身在褐色的条几之上,对着闯入的陌生人虎视眈眈。他听到了录音机里传出的奇怪声响,他不知道那是磁带在转。确切地说,是磁带在记录,记录它的主人在人生弥留之际的遗言。哥哥在那一瞬间犹豫了,他无法为这个庞大的物什觅得藏身之所。尽管录音机在他心中风情无限魔力无边,他只偷走了磁带。当次日水莲溺水的噩耗传来,她最后的只言片语笼罩了哥哥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