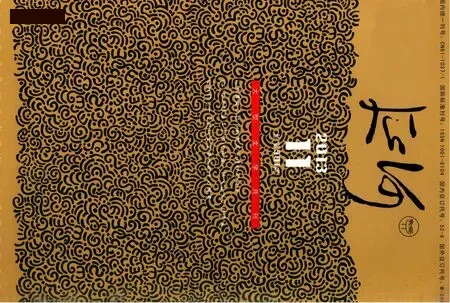身体地图
2013-11-15须弥
须 弥
“我们全身都是性器官。”
——刻在石头上的话
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在光的指引下,人应时而生,行于苍野之地。身体与大地相互感应,相互成为对方。它思考着世界,也表达着自己。同时,它也作为一个对象,不断地被研究、被探索。人类之初,它是一个神奇的宇宙,迷雾笼罩,但又诡秘撩人。后来,在科学的手术刀之下,它从一个混沌之圆逐渐变成一张类似于地理学上的地图,摊开在众人的眼皮底下。不过,手术刀越是精密,雾也就越迷幻,二者作为两个投射轴端同时汇聚于身体之上。同时,进入这个混沌之圆的路径在时间的催迫之下不断增多,呈现出异质而多元的身体书写面貌。它吸引着有身体癖的漫游者。它在身体地图上的行走不像军事战略家那样逻辑鲜明,也不像普通读者那样目标明确,而是像个迷路人,在喝了迷离散的邻近原则、类同原则、关联原则之中穿行,跌跌撞撞地踏入身体的万千密室。身体的每一间密室、每一块开裂处、每一种表达都是一道光,照亮着人被遮蔽的精神因子。而漫游者就像被一种来自大地深处的莫名力量牵引着,在身体上不断地擦拭和重写着他的地图。它,既是“一”,也是“多”。
耳朵的旅行学
耳的地貌较为复杂,笼统地说,即外似山丘,内有深谷。山丘状的耳廓,乃耳之表象,就像一座远山,极易给人一种并不过如此的虚假印象。一旦穿行于山间,就会发现它的惊险之势;若是一不小心闯至洞口,这种无知将会随着一阵冷汗而消失殆尽。充满迷雾的耳洞,深不可测,令人望而却步。然而正是这种未知之状,暗示着洞内可能出现的神秘风光。对身体漫游者来说,这是一个致命的耳诱惑。当你鼓起勇气进入那些复杂而曲折的丘陵小道,小心地跋涉前行时,就会忍不住大呼惊叹,那些崎岖、回旋的耳道、耳蜗,真是神秘物体的绝佳藏身所啊。某一瞬间,自己也变成了一个出没其中的小东西。坐在耳中稍作歇息,聆听着谷底传来的吟鸣之音。
洞口作为一处地界,将高山与深谷联系在一起,这是表里的界限,明暗的界限,白黑的界限,甚至是平淡与神奇的界限。在白昼,这个洞口总是处于一种严防的状态,守卫者运用各种招式,使用各种解药,小心翼翼地应对着外界的攻击。大地发出的轰鸣变化莫测,千奇百怪,但总是无法攻入耳营。因为它们在洞口的防卫者面前,毫无优势可言,它们被各种招式所排解、转化,抵达耳营时已被转为安全的声讯。到了午夜,大地沉寂,它也卸掉了一身的重担,浑身放松,进入一个近乎零度的状态。这个时候,耳朵才抖掉“尘埃”,恢复它的本色,像一个纯粹的结晶体,敞开自身隐秘的孔洞,接纳夜之万物。
夜与耳朵
“终于有两条腿穿过黑夜。两条女人的腿发出的脚步声,还有耳朵:我不想去看。我的耳朵像一个入口停在街道上……她的脚步此刻越来越深地消失在我的耳朵里。”(罗伯特•穆齐尔)耳朵在黑夜中如惊弓之鸟,极为敏感。它的自我意识强若划过渊谷的一道光芒,不受人的意志控制。耳朵是属于黑夜的,它只有在黑夜才显露出它的本质。反过来,黑夜也是属于耳朵的,它在耳朵中找到了真正的自己,惟有耳朵能体会它的精妙之处。耳朵之中藏着黑夜的现象学。在不知不觉中,夜拉下了它的帷幕。循着时间在沙漏中的轨迹,它先后关掉了太阳、云彩、大街、人群和眼珠,呈现出世界的混沌本相。在漫长的岁月中,一切都已沉睡,只有耳朵清醒着,它在丈量着夜的长度、宽度和高度,丈量着历史的深渊和表层;它在感受着大地的呼吸,响应着万物的蠕动。也许,这已成了现代人脑海中的一个记忆断层。也许,我们只有依靠伟大的心灵创造出的诗意形象,才得以返回这个梦境。但我们确切地知道:耳朵才是世界上最原初的深夜勘探者。
迷人的嗓音
嗓音,往往是一个人智慧的化身,灵魂的居所。而耳朵则是上帝为这些经由口腔呼出,在空气中游荡的灵魂所配置的接收器。它在人间驻扎,像天使一样敏感,寻觅着姿态万千的迷人嗓音。
“他的嗓音勾画出他的嘴巴、他的眼睛、他的面孔,向我描绘他的整个肖像,外部和内部的肖像,比他本人站在我面前还逼真。仅仅通过耳朵就能获得的最佳解码。”在罗伯特•布列松看来,嗓音即是肖像。其实,嗓音也即是灵魂,惟有耳朵能直接地接通灵魂的信号。
将一个人的嗓音视为他的整个身体,就好像认为将一个人的衣服焚毁或对一个人的头发施虐会祸及其身一样,是远古时期人类换喻思维的一个变种。如今,它却成为了现代诗意书写的一种典范。
卷舌音与连笔字
“耳”,在一种自上而下的权力规训中,往往念[er],是个卷舌音。它对我来说是一个噩梦般的读音。产自南方蛮荒大地的舌头,遗传了祖辈的习惯,依赖于“前后”伸缩,而忽略了“上下”和“平卷”之摆动。因此,长期自由、安宁的舌头突然进入一种“卷舌”的教育建构中,就像野猪闯入了繁华大街,难免要经历一场漫长的屈辱历程。如今,虽然舌头已被规范化,但在“耳”字的念法上仍有“口音记忆”的残余。不过,“耳”的字形却是如此漂亮,如此连贯,它这种易于连笔的品质所带来的愉悦感抵消了它的口音屈辱。与其“难以发音”不同,它易于书写这一特点我很早就已发现。小学二年级,我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下临摹正楷字帖,但因年少反叛,总是故意将一些字改以行草的方式而完成。其中,“耳”字就是“潦草大军”的一员。因此,在意识到它语音上的拗口之前,它书写上的飘逸形象已整个地占据了我的脑海。后来当它的卷舌音开始困扰我之时,它的形象甚至可以无损地游移于此之外。当然,这或许还要加上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即它作为一个敏感的器官,接通着大地万物的声音。这使我对它更充满敬意和好感。因此,耳——在我脑海中呈现的依然是一个美妙的意境。
舌头的快感
舌头是获取身心快感的最佳媒介,正如牙齿是获取哲学知识的最佳工具一样。在咬字方面,舌头要么极为狂放,要么极其节制。前者所产生的快感,可达心醉神迷之境,主要依附于一种非理性的口腔快感;后者则呈现一种接近于沉默的寡言,这种寡言散发出一种面纱般的诱惑。不过,舌头的真正快感来自于食、色方面。性感的味蕾藏在舌头的背面,随时准备着迎接“美味”的来临。这种快感的声望在当下的物质消费时代更是如日中天。而在食物的享受之外,性的享受则有另一番滋味。这时候的它,要么令人销魂,要么令人厌恶。在性方面,它尚未完全走向公众,它的销魂只属于少数人。它更多地扮演着被压抑的角色。
大喉咙
“喝呀!喝呀!喝呀!”高康大初到人世时所发出的叫喊,像幽灵一样在我们时代的上空回荡。与其他婴儿发出的“呱!呱!呱!”的叫声相比,高康大的叫声显得很奇怪。“高康大”这个名字是由他那正在喝酒的父亲随口所取,意思是“好大的喉咙”。一万七千九百零三头奶牛同时产奶,才能满足他的大喉咙,真是一个饕餮之王啊!“喝呀!喝呀!喝呀!”虽然我们出生时不会这么喊,但我们很快就会无师自通。虽然我们在吃喝的总量上没有这么多,但在吃喝的种类上我们却是更胜一筹。这种欲望就像日常生活中的病菌一样,无所不在,无孔不入。在这个饕餮的时代,张开的巨嘴已成为我们的代言形象。我们都是高康大,我们都有大喉咙。
嘴之渊
与耳洞相比,嘴洞显得更大,而它所通往的深谷也更为深远,更为浩瀚。但在旅行学的意义层面,或存在学的精神层面,嘴洞却大大不如耳洞。
在我幼小无知之时,曾以为嘴巴这个大洞,必会途经喉咙,进入肠子,一直通向一个深不见底的潭渊,直抵神秘之腹地。多年后,在科学文明的教益之下,我才终于懂得:嘴巴是与肛门连在一起的。它通向的是肛门,而不是什么神秘的地方。
嘴巴与肛门,一个是入口,另一个是出口。反过来亦然。不论是在现实层面,还是在象征层面,它们都是作为“进”与“出”之辩证而存在的。
口腔与肛门
在精神分析学家看来,口腔期与肛门期乃人类性发展的最初两个阶段,在婴儿时期就已经存在。嘴唇,是婴儿用以吮吸母亲的乳房的工具,是获得第一快感的器官。这也成了人一生中一种戒不掉的瘾。而肛门,则靠排泄的刺激来获得满足,属于第二快感。这两个阶段所激发的身体本能一直延伸到后来的性生活中,即口交与肛交。不过,这两种性交方式在历史上往往是一种禁忌,尽管在不同地域、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规定。与阴道性交相比,它们更加不道德,更加“见不得人”。但正是因为这样,它们却更添增了一种附加其上的“反禁忌”的特别快感。
阴道的叙说
阴道,“维纳斯的圣殿”,是通往子宫的幽径。它看上去神圣庄严,透出一种令人敬畏、不可侵犯的气息。但却又有一种压抑不住的放纵、疯狂的欲望。“美女们……舒展身姿,紧包住阴茎,叙说着交合的快乐……血管的使用是为了把生命液输给阴蒂的实体中,而神经的使用是为了给它灌注一种溶入兽类灵气的精汁良液(其中充满富于弹性的颗粒,使之生气勃勃,绷得紧紧)……阴道的腺在交欢中受热,使精炼发酵的严肃液体通过许多管道射入阴道的空穴中,使其通道十分潮润而黏滑,这在交合中是很舒服的。下腹动脉以数不清的分支在阴道的侧边和其他部分活跃跳动,它有那样多的血的通路,遂使阴道在交欢的动作中变得温暖而饱满。”在科林斯的精彩描述中,阴道并不像传统观念所说的那样“被动”、“无助”、“仓皇失措”,而是充满了饱满的激情,积极主动地向阴茎发起进攻,释放它的欲望。它站在山巅之上,欢乐地叙说着它的快感。
嘴唇之电
这是一种神赐的行动:一朵花瓣在寻找另一朵花瓣。他的嘴唇在渴望中缓慢启动,带着一种妙不可言的脉脉温情,找到了她的嘴唇。在那一瞬间,就像闪电划过屋顶一样,它们迅速地抵达眩晕的中心。它们在纠舔与轻咬之中,渐渐合为一体,直抵天堂的芳香之地。“他的嘴再一次寻找着她的,那情景就好像整个世界从他们身边扫荡开去,他俩单独地处在云巅之上,太阳的灿烂光辉之中,周围有一种神圣的东西。”更有甚者,情欲是如此的强大,如此的迫切,以至牙舌无法停止撕咬,擦出一根根导火线,一次次引爆自身,在身体之中掀起欲望的滔天海浪。
“咬”的哲学
牙齿是一门“咬”的哲学。名词向动词转化,是窥探语词的原初意义的一条捷径。咬脖子、咬嘴唇、咬舌头、咬手指头(更多的是吮)、咬树皮、咬面包、咬鲜肉、咬根茎、咬绳子、咬牙切齿。它是我们人体最初与外界进行斗争的基本武器。
正是在自身的这种基本经验之上,人开始并完成了对世界中所发生的万千斗争的感知。换句话说,通过牙齿,身体获得了一种可贵的知觉能力,并在这种感知基础上,达到了对斗争的真正认识和深刻理解。牙齿,是人领悟世界万物之斗争的一个基本工具和基本经验来源。
颈脖
作为头颅与躯干之间的桥梁,颈脖在身体的地图上属于战略要地,是“粮草”输送的交通枢纽。维护枢纽的安全,保持交通的顺畅,是身体的要务之一。它若被切断,氧气就无法输送到大本营,而以氧气为生的躯体将会变成尸体。从书本或屏幕上,我们可以看到众多杀人的镜头都是凶手切断(吸血鬼用“咬”的方式)对方的颈脖,使之走气而亡。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破坏交通顺畅的方法,那就是勒脖(被动),或上吊(主动)。与切割颈脖的“走气”不一样,勒脖、上吊是堵塞住气的流通,使身体被活活憋死,两者的结局皆为“断气”。由此我们可以得知,颈脖乃“活命气”的重要命脉。
卑微的膝盖
与颈项一样,膝盖也是人体极富有弹性的部位。这也使得它成为人体最软弱、最卑微的东西。与颈脖的容易低头一样,膝盖也很容易下跪。
人类历史中的跪拜现象,无论是跪拜上帝、天神,还是跪拜皇帝、领导,或是跪拜长辈,都是膝盖的卑微性的佳好证词。
正是富有弹性的这个特点使膝盖成了跪拜之礼的承担者,也因此使它背负了这个罪名。它成了一种伦理的身体替罪羊。
脚的伦理学
如果说我们身上有什么部位可以算得上任劳任怨的话,那么必属我们的双脚无疑。就像其在生物学上位于人体的最底端一样,它们的身份也是处于最底层的劳苦人民。我们亏欠它们太多了。它们像牛马一样,默默地为我们服务,毫无怨言。我们不仅忘记了感恩,反而变本加厉,不断地对它们施加各种压力。除了让它们在世界各地不停地跑动,丈量上帝的疆域之外,我们甚至对之用刑:缠足以及新式“缠足”——女人给它们套上高跟鞋。
缠足,一种多么残忍的手法,多么畸形的习俗!现在看来,这段漫长的历史,简直就是一场漫长的酷刑史!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金莲小脚在当时却又是性感的。在男人的眼里,金莲小脚魅力无限。对女人来说,也是如此,不管这种审美是出自本能,还是被建构,小脚都是她们眼中的时尚和魅力。旧时的“缠足”与现在的“隆胸”如出一辙。因此,这就出现了一个悖论:不管是旧时的缠足,还是现代的高跟鞋,既是对脚的一种残忍侵害,又是对脚(身体)的一种苦心美化。
臀部之梦
它做梦都想与椅子连在一起。这是它的原始欲望。但它从一开始就被引诱、胁迫,以至偏离了原初的人生轨道。它无时不在逃离椅子,逃离固定的姿态。它追随着精力旺盛的动力源,活泼乱跳、四处奔走,感受着世界的活力。然而,它总会在某个时刻,产生一种“回原”的意识,渴望重返原初,返回一种椅子的状态。而且,就像是上帝的安排一样,那天迟早会到来的,它将以固定的姿势,变身为椅子,或椅子的一部分。
作为诱惑物的胸脯
“……丰满的胸脯实际上是套在女人脖子上的一块磨石:它使那些想把她变成玩偶的男人觉得她可爱,但却从不许她思考一下,他们突暴的眼睛是否的确看见了她。她们的乳房只有在不显示其功能之时才为人倾慕:一旦变暗发黑,耷拉萎缩,它们就成了令人嫌恶的对象。它们不是肉体的一部分,而是挂在脖子上的诱惑物,像魔力油泥一样供人搓揉摆弄,又如冰棍一样让人咀嚼吮吸。”(杰梅茵•格里尔:《女太监》)
女人之肩
在我的个人阅读经验中,一直觉得东、西方作家在关于女人身体的现象学体验上存在着不同的趣味偏向。像肩、颈、背等部位的细腻书写大多见于东方文学之中,而像嘴唇、乳房、阴部则是西方作家更为偏爱的表达部位。这种比较虽略显粗糙,但其所对应的美学传统则可从中窥得一二:西方人推崇直接有力的美学,而东方人更注重委婉含蓄的美学。
比如肩,其精致而细腻的描写在中国古典诗词中极为普遍,但在西方的文学传统中则较为罕见。试举一例。清朝代词人朱彝尊在其《沁园春•肩》中将肩的形态与风情描写得微妙无比:“纨质停匀,比似陆郎,何曾暂离。被词人赋就,望中疑削;画工减尽,染处恒垂。篱弱才过,墙低乍及,结伴还从影后窥。缘红索,上秋千小立,恰并花枝……吟飞雪,怕玉楼生粟,拂袖遮伊。”最初将肩称为玉楼的是宋人苏东坡,朱彝尊此处的“玉楼”,正是发挥自苏东坡的词句:“冻合玉楼寒起粟”。肩之意象,在中国古典诗词中有着丰富的面貌:传承有之,新意有之。
上述关于肩在东西方文学的比较中,当然也会有例外。比如西方现代作家巴尔扎克,对肩就有着一种罕见的激情。他在《幽谷百合》中对女人之肩的描写虽不如“东方之肩”那样细腻、精微,但却更添有一层情感的深意:“我的目光一下被雪白丰腴的双肩吸引住,真想伏在上面翻滚;这副肩膀白里微微透红,仿佛因为初次袒露而羞赧似的,它也有一颗灵魂;在灯光下,它的皮肤有如锦缎一般流光溢彩,中间分出一道线……我看准周围无人注意,便像孩子投进母亲怀抱一样,头埋在她的后背上,连连吻她的双肩。”
头发诗学
从诗学上来讲,长发就是女人的化身,凝结着大地的香气和人间的芳香,汇聚着人类的原初梦想。“哦,浓密的头发直滚到脖子上!/哦,发卷,哦,充满慵懒的香气!/销魂!为了今晚使阴暗的卧房/让沉睡在头发中的回忆往上,/我把它像手帕般在空中摇曳……在你那头发的岸边绒毛细细/它们发自椰子油、柏油和麝香。”(波德莱尔)在诗人波德莱尔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头发情结。不过,他在诗中所展现的“头发”意象主要是来自作为伴侣的女人,而另一种女人尚未涉及,即作为母亲的女人。“在昏黄的灯光下/时间在流淌/母亲的头发像记忆一般散开,我躺在其中/子宫般的温暖。”(无名氏)在这首佚名之作中,头发作为植物的海洋,也是生命诞生之环境。这让人想起未来世界中母体的管道,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就是人的头发,人从中而生。头发,聚集着我们的记忆与想象。
胡须的表达
它不能感知,也不能发声,更不能做出有价值的动作。它深深知道自己的无用。每天清晨它都会被刮平,但它并不气馁,次日清晨又会以一种积极的姿态提醒我们,告知我们它的存在。在它的字典里,清晨与早春是同一个意思。它以一种春草的方式生长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懂得清晨与早春的同位性,并提醒我们:时间的流逝,不可阻挡。
但它又与春草不一样,它无法连根拔起,它锲而不舍地生长。晨风一吹,它又会手舞足蹈地冒了出来,就像一个被奖予糖果的小孩。
皱纹
“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叶芝)我们都希望有一个像叶芝这样的爱人,但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年代,它只能是一个梦。没有人爱你的衰老。皱纹就像一个诅咒,总是伴随着烦恼、悲哀与恐惧。
我们的鼻梁上开始出现“烦恼的沟槽”。我们开始抬头现纹,笑对鱼尾。我们双唇萎缩、舌头瘪陷。我们颚部低垂,脖子皱裂。我们开始满脸皱纹,胡须四处蔓延。我们全身披着树皮。皱纹,就像一个瘟神一样,让大家都惟恐不能避而远之。但它是生命的痕迹,是自然法则留在我们身上的烙印。也许我们应该坦然一些。就让我们像叶芝一样,在这个年代,唱一首献给皱纹的歌谣吧。
掌纹
“上帝把每个人的命运都写在了他的掌上。”手相学家就像是上帝派到人间来解读凡人命运的使者。他们说,我们手掌上这些错综复杂的褶皱和纹路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地图,摊开了我们独一无二、错综复杂的一生。我们身上的树叶真有这么神奇吗?但凡谁仔细观察过这些复杂的纹线,并对之有所沉思,就不会不产生一些好奇之心。
手上的掌纹,承载着一种恐惧,一种关于未来的恐惧。我从不向其他人展示自己的掌纹,不管是算命先生,还是懂手相的朋友。但这并不代表我不相信自己的命运就写在上面,恰恰相反,我非常相信这些神秘的粗线细纹。我知道它们掌控着自己的命运,所以害怕将它展示出来,害怕在这个过程中,它们所烙印的奥秘,会遭到外来之力的破坏,从而导致失序。
手的诺言
手的家族虽然不是十分庞大,但它们很机灵,充满智慧,在人类进程中,不断开山辟路,积极开拓新的疆域。作为人体的先锋兵,它们打进了世界的各个关口。
它们无所不能。它们无怨无悔。它们牢牢地紧记着,它们的祖先在历史进化过程中所许下的诺言和奋斗的事业:争取更大的自由,勇当人体的先卒,捍卫家园的存在。
双臂
它们已忘记了原来的梦想。那是个羡慕飞鸟的时代。双臂是为了奋飞而生长着,为了振翅而梦想着。然而,它们也与臀部一样,偏离了原初的人生轨道。它们在现实生活中,不断遭到挫败,不断失去信心。对于它们来说,曾经的飞翔之梦已越来越稀薄,越来越遥不可及。它们在现实的捆绑下,日复一日地完成着一些拎、提、举、扛、挥、转等安分守己的动作。当然,这个遥远的梦想并没有销声匿迹,偶尔还是会发来一声轻微的召唤。但这种召唤并不在其本身起作用,而是将其投射于另一种事物的构想及其实现之中。风筝的发明以及飞机的发明就是人类双臂这种欲望的替代性实现。
脚
脚,手的兄弟。它们源于一脉,它们的先祖拥有同样的面貌。“哦,我们的祖先……”
手早已“进化”,逃离了先祖的规则;而脚却安分守己,坚守着先祖的岗位。它贴靠着大地,支撑着全身的重量。这需要一种奉献精神。在外表上,它显得比较憨厚、老实,让人想到牛一类的事物。它默默地在大地上行走着。
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只有这种憨笨的禀赋。它同样可以是出色的能手,表现出超越的一面。它是运动员,像马一样,快速地奔跑;像豹子一样,迅猛地跳跃。它甚至会功夫,像猴一样,做出复杂多变的动作,机灵而有力。
此乃“真人不露相”,也是其牺牲精神所致。在大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它呈现出的只是那副憨厚老实的表情。任由使唤,默默无闻。
鼻子中的女妖
相传,美丽的女人鼻子中都住着一个美丽的女妖。历史上众多史学家、思想家都深谙此理,虽然没有明说,但其言说中皆有蛛丝马迹可寻。比如,帕斯卡尔说:“克娄巴特拉的鼻子要是长得矮一点儿,整个世界的面貌就会大不一样。”看上去,帕斯卡尔所要表达的意思是:女人美貌的核心在于她的鼻子;完美的鼻子掳获了那些王者的心,使得他们不断发生冲突,不断改变着世界的版图。而克娄巴特拉就是这样的一个女人。实际上,这话还有另一层意思:克娄巴特拉的鼻子长得恰到好处,刚好容得下女妖巴斯拉斯。巴斯拉斯是世界上最有魔力的女妖,她的居所都是那些在世界历史中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女人的鼻子,如海伦之、克娄巴特拉等。正是鼻子中的巴斯拉斯的魔力使得世界历史在女人的面前发生了变化。
耳中人
在我小时候的耳朵里,住满了飞翔的蝙蝠。天一黑,蝙蝠们就从大地的深处哗啦哗啦地飞了出来,绕着梁柱不断地来回盘旋,发出叽叽叽的声音。我躺在木床上,数着屋顶的梁柱,总十一根,最中间那根是红色的,它的两边各五根,都是黑色的。蝙蝠们时而飞入我的耳朵,进入我的眼中,时而又飞了出去,一直飞到蓝色的天空之中。这个世界充满了蝙蝠的翅膀。
关于童年的蝙蝠之夜,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耿耿于怀,但却无法对这个场景进行描述。直到后来我读到《聊斋》中的“耳中人”以及《耳证人》中写到的从耳朵中跑出来的各色人等,才感觉到一种释然。这些隐约的对应表达间接地解开了我的心结。我们知道,耳朵乃世界上最原初的深夜勘探者,而耳朵中的蝙蝠与耳中人则都是深夜之物,它们具有同一个结构。
游荡的眼睛
眼睛总是在游荡。从一棵树到另一棵树,从一张皮肤到另一张皮肤,从一个口子到一个深穴,眼睛被诱惑,被牵引,在事物之间来回游荡。游荡是眼睛的本质之一,它作为观看的现象学前提,赋予了眼睛以真正的价值。
然而,这种游荡并不是特别自由,它戴着枷锁。但“它自以为发明了白昼和唤醒了风。”因此,它总是试图摆脱所有束缚,克服所有困难,而争取最大的游荡自由。我宁愿相信确实是它书写了白昼。那么我们就应该让它尽情地游荡,直到它再也提不起兴致,再也无法享受它的这一本质。
瞳人语
“忽闻左目中小语如蝇,曰:‘黑漆似,叵耐杀人!’右目中应曰:‘可同小遨游,出此闷气。’渐觉两鼻中,蠕蠕作痒,似有物出,离孔而去。久之乃返,复自鼻入框中。”(《聊斋•瞳人语》)诗人勃莱说,当一个人注意物体时,他就存在于目光之中。事实上,并不仅仅如此,即使一个人没有在注视什么,他也存在于他的眼睛之中,他的心常驻于眼睛之中。这是一种更加本体的观念。正如蒲松龄的这篇神怪小说所揭示的,眼睛中住着一个人的人性,以及人性的因果。眼睛就是人本身。
肚脐
“人体中自然的中心点是肚脐。因为如果人把手脚张开,作仰卧姿势,然后以他的肚脐为中心用圆规画出一个圆,那么他的手指和脚趾就会与圆周接触。不仅可以在人体中这样地画出圆形,而且可以在人体中画出方形。即如果由脚底量到头顶,并把这一量度移到张开的两手,那么就会发现高和宽相等,恰似平面上用直尺确定方形一样。”当读到维特鲁威关于肚脐乃是人体中自然的中心点之论时,我走了神,想起自己小时候对肚脐的印象:这个与母亲相连的中心点怎么竟是一个藏污纳垢的地方呢?虽然当时并没有任何的几何知识,但却凭着它与母体相连这一点,我一直都断定肚脐就是身上最核心的部位。如今,它就更是如此了。在想象力的推波助澜之下,它甚至成了世界的中心。躺在草地上,掀开衣服,迷人的风吹动着整个身体,它在晃动之中与天空的中心点遥相呼应,竟是如此的耀眼。
睾丸上升
它们像刚孵出来的两颗鸟蛋一样,在寒冷中不停发颤。我们的睾丸害怕寒冷,像冷血动物一样,在寒冷的面前总是恐慌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同时,它们也害怕愤怒,害怕刺激,害怕心跳的加速。坏情绪是它们的敌人。为了应对这些敌人,它们会收缩、上升到贴近身体的地方,寻找温暖。
我曾将睾丸上升视为它的“魔术”,但一直以来都无法破解它“为什么会变魔术”的这个秘密,就像不知道世界上最可怕的动物——蛇为什么要冬眠一样。
生殖器的美妙想象
在遥远的岁月中,人们并没有男女之间的身体差异的概念。他们认为,女人的生殖器官与男人的生殖器官是一样的,只不过是以相反的方向而生长,一个朝内,一个朝外。“阴道被想象成朝体内长的阴茎,阴唇就是包皮,子宫就是阴囊,而卵巢则被看成是长在体内的睾丸。”这是一个多么美妙的想象啊!生活在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世界之中,我却宁愿相信这样一个如此美丽的“愚昧之言”。
作为文化史符号的脚踝
脚踝,一个极为普通的人体部位,却因为阿喀琉斯,在西方历史文化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除了在性挑逗的描写中偶尔被提及,这个字眼基本不会出现,它完全被淹没在“脚”的这个统称之下。我们习以为常地使用“脚”这个词来指代所有与脚有关的部位。但在阿喀琉斯的事迹中,它被突了出来:阿喀琉斯的母亲是不死之神,也希望自己的孩子不死,在阿喀琉斯出生后,她捏着他的脚踝将他浸泡在天火中,使他全身刀枪不入,除了被她捏着的脚踝。后来阿喀琉斯正是因为被射中脚踝而死。这也使得脚踝成为了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符号。而阿喀琉斯的事迹提示我们:脚踝是一个脆弱的东西。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脚踝,就像有眼睛,有鼻子,有耳朵一样。在这个意义上,脚踝可以是阿喀琉斯的任何部位。
脂肪
它的常居之处,是臀部与胸部。以前它十分安分守己,尽可能做到不匮乏、不泛滥。但如今,它紧随现代生活的节奏,越来越放纵,毫不节制。它在人体中变得越来越膨胀,也越来越多余。甚至激起了一种过度的反弹:某些人甚至恨不得将它剔除得一干二净。如今它已像过街老鼠一样,成为人见人憎的事物。人们将多种罪名归结于它:肝硬化、高血压、糖尿病等多种疾病的罪魁祸首,友谊、爱情、甚至包括日常交往的障碍物。在这个物质过度膨胀的时代,它面临着多重危机:极度饥渴、强制萎缩(各大减肥妙法:节食、运动、药物);被机器强制抽除(真空吸脂手术);脂心惶惶(综上所述)……
胃的社会学
胃,是人体极其受罪的一个器官:要么是极度放纵,数不清的美味佳肴,道不尽的疯狂刺激,经由大吃大喝,直灌而入;要么是极度饥饿,百日无肉,油米难见,挨着饿过着干瘪的日子。它的处境,也是社会的处境。它呼应着这个社会,作为社会的镜像而存在。
它既讨厌生存在富人子弟家中,又讨厌生存于穷苦人家之处。普通市民家庭曾经是它最好的归宿,但如今这种情况也已不复存在。在当下这个物质膨胀的消费时代——既是饕餮时代,又是瘦身时代,胃无论置身何处,都扮演着首当其冲的角色。
打嗝
这是人体的一个玩笑。不知从何时开始,体内有一股气情不自禁地从胃中往上跑。它迅速流经喉咙,发出一种急而短促的呃声。它在刹那间就完成整个流程,一气呵成。它夹杂着胃的跳动。就像从鼻孔中溅出的哈欠一样,这种冒失的呃气,常会使人感到十分痛苦。
为解决这个玩笑所导致的困扰,我们找到的方法更多是民间相传的江湖方子,比如喝碳酸饮料,或受惊吓,或背上挂钥匙。每一种我小时候都尝试过。其中最无厘头的一个方子是,由别人竖大拇指,问:这是什么?自己答:手指头。现在想来都忍不住大笑。
但在福楼拜的《庸见词典》中,却出现了同样的治打嗝的方法:在背上挂一把钥匙,或受惊吓。也许,玩笑因,玩笑法,相生相成。
鼻孔
鼻孔并不仅仅是鼻孔。从解剖学的角度来看,它逊色于耳孔的复杂度;而从功能方面来看,它也不及耳孔的洞察力。但有一点,它打败了耳孔。它除了作为呼吸的通道以外,还是妄想的场所。也许是因为它的形貌,也许是因为它在生物学上的功能,它被赋予了具有精神分析意义的形象。诗人狄兰•托马斯在诗中写下“装满蟾蜍的鼻孔”,这是一个怪异的意象,成为诗人关于“疯了”的世界的注脚。而精神分析家所面对的意象,是精神病人说的“射精的鼻孔”,一个精神分析的好文本。作为形象或符号的鼻孔,好像只是为精神分析家而存在的。像世界的其他孔洞一样,鼻孔在精神分析家那里刻下了无法消除的烙印,它无法形成一个美好的意象,无法进入巴什拉式现象学的视线之中。它已被建构成一种深渊。
与毛孔有关
“在我的每个毛孔之中都生长着婴孩。”这种小与大的辩证论述,是弗洛伊德式的精神病患者的呓语,还是巴什拉式的诗人的笔下意象?也许,“婴孩”的意象更具有精神分析的意味。它让我联想到另外一句出自精神病患者的话:如果不这样,我的每个毛孔都会长满乳房。它们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这里,倘若是出自巴什拉所赞赏的诗人的笔下,这句话将会是:“迷路之人在毛孔中发现了迷你火车,于是跃上开始启动的车厢,消失在毛孔的幽暗隧道之中。”
青筋
某个夏日的早晨,我突然发现自己的手臂上也出现了微微凸起的青筋。它们是如此的熟悉,又是如此的陌生,望着它们,我久久没有回过神来。
父亲身上的青筋长到我身上来了。小时候曾摸着父亲手臂上凸起的青筋,问:这是什么?为什么我没有,是不是它们藏起来了?父亲笑着看着我:等你长大了,它们就会偷偷爬出来。已经多年没看到父亲的青筋了。不知道它们现在长成什么样子了?
胡须的意义
从生物学上来看,胡须对我们来说毫无意义,它既不能帮我们摄入营养或保存能量,也不能帮我们排泄废物或抵挡病菌。但从象征意义上来看,它却是一种极具美学价值和政治意味的事物。古往今来,胡须往往是男子气概、刚性威严的标志之一。在当下消费社会中,流行审美中男子气概的普遍削弱使得它不再享有曾经的“荣耀”,转而成为小资时尚的一部分。胡须在政治学上的意义也很明显,老左派领袖们都曾以彪悍的胡须作为反抗的标志。当然,如今这种盛况已然不再。胡须的意义总在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
对我来说,它只在感知现象学的意义上才有效。与头发一样,它作为长在我们身体上的植物,看上去可有可无,但却成了身体可触性的一种特殊承载物。留起一小撮山羊胡,最初只是为体验身体突然多出一种“衍生物”的感觉。后来却渐渐地喜欢上这种不断生长的植物,通过手的抚摸、顺捻、拉扯,它甚至使我对自己身体的感知多了一条路径。若从审美意义上来看,胡须在我身上则是一场失败的出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