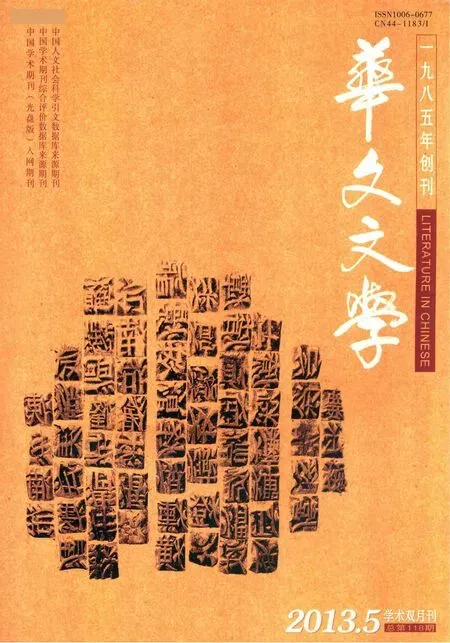跨国的文学研究:林英敏的《两个世界之间》
2013-11-15潘雯
潘 雯
(浙江行政学院,浙江杭州311121)
在诸多的美国华裔文学的研究文本里,美国华裔学者林英敏(1939—1999)的《两个世界之间:华裔女作家研究》(Amy Ling,Between Worlds:Women Writers of Chinese Ancestry,1990)是一部重要的作品。林英敏是最早以华裔文学命题,并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之一。虽然英年早逝,她却为华裔文学批评留下了珍贵的学术遗产和不同寻常的学术锋芒。她的《两个世界间》循着时间的序列,分析了伊顿姐妹(the Eaton sisters)、韩素音、林太乙、汤亭亭、谭恩美等华裔女作家,从她们的写作内容到文体特色,从文本内的虚构到文本外的政治。本文将以文本细读的方式进入林英敏的批评话语空间,以她的研究做案例分析,去具体而感性地体验并思考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的学科意义。
一、边缘化了的学科
在解读林英敏的《两个世界之间》之前,我们不妨先试图追寻一下,林英敏是在什么样的语境里选择成为最早进行华裔文学研究的学者。林英敏曾发表过一篇笔调动人、鞭辟入里的学术杂文《这是谁的美国?》(1995),在文中她回忆了自己从求学到出书立言的成长历程。林英敏作为第一代移民家庭里的孩子,二战刚结束时进入了象征着自由、平等、进步与美丽的“美”国,但是,她在美国的梦想实践之路绝非坦途。尽管1980到1990年代,美国已经开始了全面的多元文化运动,可横亘在亚裔学者和国家的文化上层建筑之间的障碍并没有历史性地清除。林英敏的亚裔研究一度四处碰壁,因此她在文章中叩问学术界:
为什么我,一个华裔美国女性学者,研究乔叟、莎士比亚和弥尔顿是“正常的”,而如果我说阅读汤亭亭会令我们获益匪浅,那就是一种颠覆性的、“政治的”行为?如果我们整个国家奉行的是民主,为什么有些声音比较主流,而有些声音就该被忽视?难道不是所有人的故事都同样可能令人激动、给人启迪、感人肺腑吗?民权运动和女性主义运动留给我们的遗产很简单,就是要承认没有哪个单一的视角可以完全表达“人类的境遇”,或代表“普世”的立场;我们每一部分人都有我们每一部分人的独特历史,都有我们具有个性的视角,而所有这些视角,以它们千差万别的复杂性共同表达着“人类的境遇”。
林英敏在这篇杂文的最后坚信,只有不同类别下的人群彼此尊重的视角,并真正认识到“我”脚下的大地既属于“我”,也属于别人,这个被称作“地球村”的星球才可能安然太平。
从治学姿态上说,林英敏与《东方主义》的作者赛义德相似,也是从自身成长历程中的感性认识出发,将自身的体验与政治批判和学术理想结合起来。同样在《这是谁的美国?》里,林英敏回忆起在1980年代选择自己的学术道路时的挑战。当时她受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影响,决定致力于华裔英语文学研究。但她的导师与同事向她提出一个很尖锐的问题:有没有可能,在华裔,乃至整个有色人种的英语文学积淀里,根本就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成果?因为,假如有成果,那它岂不应该像奶油一样浮在牛奶的表面,世人理应已经看到了?对于这个问题,林英敏没有在文章中陈述她当时的回答,但是在她走过这段人生历程后,她的体悟是这样的:
今天,我已经渐渐懂得,价值能否在当世浮现出来取决于谁在端动文学。书不像奶油一样会自动上浮,有些书被摊放在众人面前,有些书从一开始就被冷待。
问题不是某一少数族群里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写出任何好的作品,而是没有学者关注过“那些”族群写过什么,因为学者几乎全部是白人男性;又或许是,既然这些作品被看作是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文本,它们被自然地归类为“民族志”或“人类学”,而未被视作“文学”。
林英敏1939年出生于北京,6岁随父母入美,获纽约州立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曾任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美国亚裔研究中心主任(Director of the Asian American Studies Program at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1999年因病离世。早在1990年,她发表了具有学科开拓意义的研究专著《两个世界之间:华裔女作家研究》,此后主持或参与了6本文学选集的编辑,包括《想象美国:来自上帝期许之地的故事》(Imagining America:Stories from the Promised Land,NY:Persea,1991),《美国亚裔文学阅读》(Reading the Literatures of Asian America,Philadelphia:Temple UP,1993)和《希斯美国文学史》(Heath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Lexington Massachusetts:Heath,1990)。
林英敏的博士论文与亚裔或华裔文学并不相干,相反,它研究的是西方正典里的作家——威廉姆·萨克雷、埃米勒·左拉和亨利·詹姆斯,以及他们的作品与绘画艺术之间的关系。进入大学教学后,在1980年代,林英敏带着“寻找母亲的花园”的浪漫理想,和捕捉并铭刻前人的声音的学术使命感,开始她多少有些孤军奋战色彩的华裔女作家研究之旅。1990年,《两个世界之间:华裔女作家研究》一书出版,这本书的意义,也许并不在于它的研究深度,而在于它的学术突破性和文化传承性。它突破了当时还是非常顽固的西方学术的分层机制,那种机制长期以客观的学术面目对某些人文领域进行无意识的边缘化;同时,它还钩沉并重组了某些即将逝去的文学记录,那些文学记录在弱者史料匮乏的情况下无疑可补历史之不足。正如英籍华裔作家韩素音为该书撰写的前言(foreword)里所言:“我预见,在未来,这本书会成为漫漫征途上的第一座里程碑,指引着人们去理解我们——欧亚人或欧非人等——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文化不再是恃强凌弱者的武器。”
林英敏把《两个世界之间》的研究对象设定为有华裔血统的、用英语在欧美西方世界写作的女作家。当然,从晚清开始到她写作时的1980年代,符合这两层条件的华裔女作家人数不少,而林英敏并不是要做全面的记录与分类,事实上,她有更具体明确的学术定位与选材标准。她对《两个世界之间》的学术定位是“文学考古学”,即挖掘并呈现给世人曾经的华裔“文字英雄们”。她们有勇气,也有能力,抵住那试图阻止她们说话的力量,以落于纸面的文字、以小说等文体形式,在英语的世界里表达自我。林英敏说:
我把她们挖掘出来,并聚拢到一起,这样她们的光芒就会有史以来第一次地集体绽放。我这样做有三重目的:一是打破旧的刻板形象——柔弱的“莲花”和邪恶的“龙女”;二是为年青的美国亚裔女性树立她们极为需要的偶像形象,并为她们开辟出一方亚裔女性文学传统的沃土,令她们能扎根于兹;三是通过对女性作品的挖掘工作,为女性主义的学术发展作出贡献。
从结构上说,《两个世界之间》除“序言”外共有五章。第一章和第五章是对华裔女性文学整体性的论述,而中间三章是具体的作家及文学现象分析。第一章《写作是一种叛逆:华裔女作家历史及文化背景》,以简促的笔调勾画出20世纪华裔女性英语文学的跨国的历史和文化背景。简单地说,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东西方移民浪潮促生了华裔文学,所以20世纪的华裔女作家们往往以第一代或第二代移民的身份书写于中国和欧美两个世界之间,并以她们的思考和文字呈现这两个世界之间的张力。林英敏认为有四种文化或政治语境,共同构成了华裔女作家的写作背景。首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林英敏泛泛罗列了重男轻女和“三从四德”等封建时代父系社会的典型思想,同时,她特意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也曾出现班昭、花木兰、武则天和李清照等具有叛逆色彩的女性形象。其次是19世纪中期开始的风云变幻的近代中国,革命与爱国是这个时代的主题词,也为中国女性的解放提供了历史机遇。与封建传统的中国相比,近代由封建走向共和的中国往往是被欧美学术忽视的华裔女性文学的阐释语境;但是,正是从这个语境中走出了早期的华裔女性作家。第三种社会语境是美国语境,其特点是对中国的东方主义话语,包括种族刻板形象和底层的经济分配。第四种语境是中美外交关系的亲疏变幻和两国政治气候的冷暖。林英敏受美国学者哈罗德·伊萨克斯的《心影录——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和印度形象》(Scratches on our Mind:American Images of China and India,1958)的启发,指出华人在美国的处境如何,与某一具体历史阶段里美国与中国的政治关系密切相关。“他者”往往体现着“我”的意志,无论18世纪欧洲启蒙主义者对礼仪之邦的“中国”的尊奉,还是紧接着启蒙之后的社会进步论对“文明停滞”的中国的鄙视,都符合西方现代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同样,美国在二战时对中国的友好,冷战时对中国的敌视,不同时期钟摆式的态度变化更应该从美国民族心理的内因中寻找答案。另外,钟摆式的变化也决定着大众层面对中国和华人的阅读、想象与理解。“哪些被写下了,哪些被出版了,哪些被阅读了,哪些上了畅销榜单了,哪些被遗忘了,哪些又被重新挖掘出来了,这一切都极大地取决于当时的政治气候和社会情绪。”从政治气候和外交关系的考量出发,林英敏说,现在,即她编写此书的1980年代末,也许是重新查考华裔文学的良好时机,因为,美国,以及一般意义上的西方,已经打算“听听中国的”(have the ears to hear)了。
二、跨国的文学谱系
必须指出的是,《两个世界之间》具有学科标志意义,它标志着华裔文学研究的真正开启。并不是说林英敏在这本书里所关注的已经脱离了亚裔文学族裔研究的范式,恰相反,族裔研究的问题意识和关切主题依然是此书的核心内容,只是,当“亚裔”还是理所当然的学科分类标签时,林英敏率先以“华裔”标示她的研究领域,同时也率先踏上了亚裔研究体系里跨国研究的路径。很有可能,她对“华裔”研究领地的青睐出自她的华人文化理想——一种无意识的学术自觉,而非对十来年后亚裔跨国研究倾向的敏锐捕捉。
通览全书,林英敏最为重要的文学贡献在于她独到的谱系建构,她建构出一条在当时可谓别开生面的、“跨国”的华裔文学研究谱系。当学界普遍习惯于以“外交官文学”作为亚裔文学的开端,以刘裔昌和黄玉雪作为真正的亚裔文学创作的启动时,林英敏将她的华裔文学的谱系追溯到两位欧亚混血女作家身上:伊迪丝·莫德·伊顿(Edith Maud Eaton,1865—1914),笔名“水仙花”(Sui Sin Far)和威妮弗雷德·伊顿(Winifred Eaton,1875—1954),笔名“夫野渡名”(Onoto Watanna)。当然,这样的谱系追溯和她的研究框架有关,她明言研究的是华裔女性作家的写作,因此,“外交官文学”虽然出现很早(比如曾经是最早一批留美幼童的李恩富的自传《我在中国的童年时代》出版于1887年),但很自然地被林英敏规避掉了。而一旦以伊顿姐妹,确切地说,以“义不忘华”的“水仙花”作为她的文学谱系的开端,林英敏其实已经为这个文学谱系注入了斗争的力量与传统。《两个世界之间》第二章《先锋与范式:伊顿姐妹》从两位作家的生平入手,夹叙夹议,以感性的笔调刻画出在华人被西方全面鄙视和妖魔化的时代里,两位具有华人血统的作家的不同的写作姿态与文学价值。接着,在第三章《关注中国:爱国、批判与思乡》中,林英敏把从中国革命和抗战背景下走出来,并进入英语文学世界的女作家纳入了她的华裔女性文学的谱系,韩素音、谢冰莹、施美美、郭镜秋和林太乙等的家国记忆和烽火岁月构成了属于华裔的、别样的女性主义传统。这种承载着英雄气息的女性传统,在美国悄然生根,虽然在民权运动中它不像黑人女性主义那般响亮,但在后来的多元文化运动的机遇下,它还是绽放出鲜艳的文学之花。在第四章《聚焦美国:自我的寻求与定位》里,林英敏认为黄玉雪和汤亭亭在种族、民族和性别政治纠缠的社会里继续着华裔气质的女英雄传统。
从“排华”时期的“水仙花”,到烽火中走出来的中国新女性,再到多元文化中的女勇士,这是林英敏比较集中笔力刻画的华裔文学谱系。当然,还有许多华裔女作家并不能很合适地进入这条中心线索中,林英敏在沿着这条主线论述的同时也加入了其他一些文学现象的分析。
从华人话语建构的角度上说,林英敏相对于她写此书的1980年代,至少在三个方面做出了开拓性的努力:她丰富了华人的斗争话语;她引入了新鲜的华人女性传统;她强调了华人的“跨国性”所蕴含的美国教育意义。
首先,林英敏丰富了华人的反种族主义的斗争话语。正如作家以人物作为自己思想的传声筒,文学批评家也往往以对作家的评判来传递自己的观念。伊迪丝·伊顿是林英敏浓墨推介的作家,因为伊迪丝做出了与其同时代人迥异的身份和文学道路抉择。虽然林英敏把伊顿姐妹定为华裔女性写作的开端,但她对这两位伊顿的文学价值的判断明显高下有异。
伊顿姐妹的父亲是英国商人,母亲是被一对在华的英国传教士夫妇收养的华人弃儿,他们的跨种族婚姻遭到男方家庭的反对,因而离开英国移民美洲。在伊顿姐妹写作的时代,美国“排华”呼声甚嚣尘上,华人在西方社会遭受着生理和文化上的贬损与苛待,而伊迪丝·伊顿并没有因自己更接近白人的外表而隐瞒其华人的血统,反而以广东话发音的“水仙花”(一种英语中又称作“中国百合”Chinese Lily的花)为笔名,以写作再现华人的真实性情与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伊迪丝的妹妹威妮弗雷德则回避了自己的中国背景,转而选择“日裔”的作者身份,她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以貌似日语音译的Onoto Watanna作为自己的笔名,而且她的作品的背景设计和她个人的服饰穿戴都令读者以为她是日裔作家。由于当时日本与中国在西方世界里的民族形象截然不同,威妮弗雷德的“日裔”角色扮演其实是更复杂的身份现象,既可以被理解为自轻自贱的心理弃却,可以被诠释为趋利投机的商业行为,当然也可以是作者文学想象的自由。林英敏没有断然批判威妮弗雷德的身份选择,她甚至将其视为一种讽刺性的身份幽默:“威妮弗雷德意识到,尽管他们贬损一个,佩服另一个,他们其实并不能把中国人和日本人区分出来,既然姐姐已经选择了‘华人’的身份,她决定去做那个被欣赏的‘东方人’。”
但变通的身份策略显然缺乏人性的感染力,投射于创作中,伊迪丝的一些情节设计至今读来都令人心潮澎湃,而威妮弗雷德的许多作品都流于“低层次的通俗套路”,不过是“16年来养活她和她四个孩子的生产方式”。林英敏一方面认可身份弹性也是一种生存的需要,另一方面还是以明确的对比来烘托伊迪丝的精神境界:“伊迪丝选择傲然挺立,抵抗肃杀的西风,像坚实的橡树呈现出无畏与正直的气概。”“威妮弗雷德的选择是顺风而弯……伏倒于地的姿态可能有些屈辱……”更有说服力的比较还是来自于威妮弗雷德自我的反思,林英敏发现并撷取了威妮弗雷德本人对自己的文学“面具”的反省:
我曾经以为乍现的灵感是神圣的文学天赋,但现在我觉察它们不过是平庸的才能,并不会引领我走得更远。我的成功建立在低层次的通俗套路之上,我那堆被称作感伤的月色的作品,现在看来,印证着我的软弱与无所作为。哦,我出卖了我的出生,换回一锅乱炖的粥。
我想起了我的姐妹。我的大姐,其实天赋远胜于我,虽则她一生都不幸残疾。她现在已然过世,但在她的墓边树立着一块纪念碑,铭记着她为母亲的国家所做过的一切。
似乎,我们所继承的遗产就是斗争。我们都还没有取得世人所说的成功……
似乎,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我没有成为拯救家庭的人。我曾经梦想名望与财富,认为它们足以提高我的、以及我所属于的人群的地位,但这样的梦想,实在是流沙般易逝,雾气般渺然。
林英敏认为伊迪丝最重要的文学贡献是在华人几乎不能发出任何自己的声音时,在华人只能任凭白人主流文化对其进行“非人类”的描述与定性时——如吸大烟者、妓女、骗子和黑社会,她以文字记下了华人以及混血华人的生活与体验,以种种艺术的手法刻画了华人的人性与情怀。“在伊迪丝·伊顿的时代,种族主义远比汤亭亭的时代更明目张胆,更粗暴广泛。从国家元首到各级议员,再到普通百姓,男男女女,对华人压倒一切的看法就是华人是不可同化的异教徒。‘习惯恶心,道德低下’……”林英敏还引用1873年蒙大拿报纸上的一段言论,这段言论的大致意思是华人的生死本无足轻重,但是现在国家需要华人的廉价劳力,所以不宜对华人太严逼。林英敏感叹,在这样的“保护”华人的言论背后,是冷血的经济动机。就在这种语境下,伊迪丝不断地创作,写出华人的可爱、善良、勇敢和坚韧,当然也会写到华人的狡猾或愚蠢,但不管褒贬,她所展现的是华人的“人性”。“水仙花,她的小说描写了华人家庭生活,讲述了爱怎样战胜困难或者被困难摧毁,刻画了立体的、有深度的人,这些确实大大地填补了华人和白人之间的沟壑。”
三、别样的华裔女性主义传统
《两个世界之间》的第二重意义在于,林英敏引给美国学界别样的华人女性主义传统。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宣布对日作战,加入了世界范围内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国和美国成为战争盟友,而日本却由西方的“同路人”的角色转化为恶敌。“二战”新的政治气候推出新的中国话语,在1940年代的美国,许多关于中国和华人的书籍面世,最早的美生华人的文学创作也是出现在这个时候,如刘裔昌的《父亲和裔昌》(1943)和黄玉雪的《华女阿五》(1945)。在中国,日本在华多年的侵略激发了火山般的民族怒火,国恨家仇推动着大量爱国救亡的作品出现,而其中大多是由能够进入英语世界的,来自中国的记者、学者和外交官所写。在《两个世界之间》的第三章,林英敏刻画了一组比较特别的华人女作家群像,包括韩素音、少女时代的林如斯和林太乙、翻译家兼作家郭镜秋、艺术家兼作家施美美。
这五位作家中,韩素音和林太乙比较广为人知,在此不多作介绍,另外三位作家的创作和生平则几乎随历史的流沙而去,笔者以为在此需要赘述几笔。林如斯(Adet Lin,1923~1971)和林太乙是文学大师林语堂的女儿。1939年,年少的林如斯、林太乙和她们的妹妹将日记合集出版,英文书名Our Family(中文版书名为《吾家》)。1941年,姐妹俩合写的杂文集《重庆的黎明》(Dawn Over Chungking)出版,记录了她们在中国六个月的生活经历,以及日军的空袭带给中国百姓的恐惧与灾难。此外,1940年,林如斯和林太乙还共同翻译了谢冰莹的作品《一个女性的奋斗:谢冰莹自传及〈女兵日记〉节选》(Girl Rebel:the Autobiography of Hsieh Pingying with Extracts from Her New War Diaries)。1943年,林如斯以“Tan Yun”的笔名出版小说《岩石上的火焰》(Flame from the Rock),该小说以战乱中的中国为背景。1970年,她翻译的唐诗集Flower Shadows(中文名《唐诗选译》)出版。
郭镜秋(Helena Kuo),1911年出生于澳门的上流社会家庭,曾就读上海大学,1930年代在中国做记者。郭镜秋自认“既是女性主义者又有女性气质”,年青时游历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道理。1939年,受罗斯福总统夫人的亲自邀请入美,以女性主义者的身份讲演,随后定居纽约。1940年,她发表散文集《桃花路》(Peach Path),表达了她的女性主义观念;1942年,自传体《漫漫离乡路》(I’ve Come a Long Way)出版;1944年,人物传记《中国巨人》(Giants of China)出版;同样在1944年,小说《向西,去重庆》(Go West to Chongqing)出版。她还翻译了两本老舍的小说:《离婚》(The Quest for Love of Lao Lee,1948)和《鼓书艺人》(The Drum Singer,1952)。
施美美(Mai-mai Sze),原名施蕴珍,是民初著名外交家施肇基的女儿。1927至1931年,就读于美国麻省威尔斯利学院,曾在巴黎学过油画。她的画作中,为美国剧作家尤金·奥尼尔所绘的肖像画最为知名,曾用作美国1957年一期《新闻周刊》的封面。1945年,施美美出版了一部自传体小说《哭泣之回响》(Echo of a Cry);1948年,她又推出第二部小说《沉默的孩子》(Silent Children)。1956年她发表的美术论著《绘画之道》(The Tao of Painting)产生巨大社会反响,该书上下两卷,上卷介绍了中国画的美学原则,下卷用地道的英文翻译了中国画经典的技法入门书《芥子园画传》。
实际上,林英敏把她们纳入华裔文学的谱系,是带着经典重组的勇气的。她是依据“文本原则”,而不是“作者原则”来选择她的谱系构成。如果以职业作家的标准去看,少女时期的林如斯和林太乙怎能步入文学殿堂?但林英敏认为她们的作品具有和《安妮日记》同样性质的价值,都是智慧而敏感的女孩在极端的年代和恶梦般的现实里的感受和思考。
林英敏具体分析了五位华裔女作家在1940年代发表的英文作品,包括韩素音的《目的地重庆》(Destination Chungking)、林如斯的《岩石上的火焰》、林太乙的《战潮》(War Tide)和《金币》(The Golden Coin)、郭镜秋的《向西,去重庆》和《漫漫离乡路》,以及施美美的《沉默的孩子》。这些创作并发表在美国的、关于战时中国的作品,在1990年代之前一向处于文学研究的边缘地带:因为不带有“美国感性”,它们没有自然地进入亚裔文学的研究范畴;同时,由于创作语言非华语,它们也游离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或“港澳台文学”的领地之外。林英敏对它们的钩沉,适时地挽留了华人曾经的历史记忆和文学体验。林英敏在对这些作品的分析中多处强调,这些作品体现了中国人即使在战争的恐怖与流离的困苦中,也依然保有的勇气、机智和幽默。
在1940年代,这些作家或以英语写作,或译介中国的作品,不仅向西方传递了中国人的抗战故事与爱国精神,同时也展现了中国女性的革命气质。山河破碎的时代,民族存亡的关头,当国家需要动员一切可能的力量去抵御外敌时,其国内的民族主义和女性主义之间更易于形成历史的默契。勇于战斗的女性在西方社会的文化里是欠缺的,“在西方‘女勇士’是如此罕见,以致只有圣女贞德独树一帜。”林英敏认为在中国女性的解放进程里孕育着西方所没有意识到的进步性。和她的这种见地与思路相似,美国华裔学者林涧在《语言的铁幕:汤亭亭与美国的东方主义》(Jennie Wang,The Iron Curtain of Language:Maxine Hong Kingston and American Orientalism,2007)里也确立华人的“巾帼英雄传统”(the heroic tradition of Chinese women)。林涧认为长期以来美国文学批评界对美国华裔作家汤亭亭的代表作《女勇士》(Maxine Hong Kingston,The Woman Warrior,1976)的解读和编辑表明,在西方的东方主义的话语机制里,即使女性主义批评论者也难以诠释出汤亭亭笔下的华裔女性的英雄精神,那是由汤亭亭、汤亭亭的母亲勇兰、汤亭亭的精神先祖花木兰和蔡文姬等一系列华人女性形象所构成的精神世界。
四、来自“间际”的教育意义
林英敏强调了美国文化研究的“跨国”视域,并断言在不刻意割断过去的情况下,“华人”可以成为教育美国的正面力量。
二战后的华裔女作家离战争记忆越来越远,对于她们来说,所谓的“两个世界”并不是她们的身体亲历的中国和美国,而是在她们心理上互为纠结的两处归属:她们应该属于父辈、属于中国,还是属于当下、属于美国?以今天的身份政治来看,林英敏研究华人的这种心理纠结似乎毫无新意,因为显然这种两难的身份选择是建立在“中国性”和“美国性”先验的对立之上,而对先验的二元对立的解构在当今文化研究领域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批评路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多样性、杂糅性和异质性成为亚裔流通的批评话语是在1990年代末,在林英敏写作此书的1980年代,东西方二元对立的意识仍然在左右着人们的判断。
林英敏首先透过文学作品来体味新一代华人在身份认同上的两难处境。在《两个世界之间》里,林英敏以相当的笔力和篇幅分析了两位影响最广的华裔作家:汤亭亭和谭恩美。她注意到《女勇士》里有这样一处情节:隔壁的药店把别人家的药错送到了“我”家,妈妈勇兰认为这很晦气,就使唤“我”去药店要一颗糖回来,以纠正之前不好的暗示;可女儿觉得这简直是丢人的讨要,只能犹犹豫豫地看着人家店里的糖。店主给了她糖,是搁在柜台很久都没人吃的糖。勇兰一点儿也没看出这糖果里的尴尬,还很高兴女儿给开药店的白佬上了一课,殊不知药店主心里想这些华人洗衣店里的孩子真可怜,一点零食都吃不到。对于这个情节,林英敏认为它明确反映了美生华人在两个世界之间的纠结。两个世界里的人都不能读懂对方,而生活在两个世界之间的“我”虽然明白,却还没有能力和资历去跟他们解释清楚。
汤亭亭和谭恩美的作品有很多类似的身份纠结,林英敏通过一系列的文本细读,指出对“不同世界”之“间际”的价值认定是解决现实中的困惑的出路。华人并不需要以牺牲过去的方式去换取其在美国的未来,恰恰相反,那些由父辈记忆和族裔经验构成的过去是他们的人生资源,而且,他们可以用这“中国”的一半去影响、教育那“美国”的一半。“无论是黄玉雪,还是汤亭亭,还是谭恩美,这些华人女儿们,如果她们想真正地成熟,并且在两个世界的状态之间找到平衡,她们都不能只抓住新的、美国的生活方式,而放弃旧的、中国的方式,那样不过是孩子式的简单想法。”
比如,当代华裔作家笔下最典型的情节设计是“母女叙事”,即华人母亲如何系统地作用于她们的女儿的成长。不管这个发生作用的过程多么曲折和痛苦,其结果总会包括女儿对自身存在的更深刻和清醒的认识。华裔作家对母女关系的母题的一再造访,本身就是投放于现实的价值传承和文化建设行为,因为华人的价值观在新一代作家写作之前几乎未被认真对待过,而母女叙事提供了一种自然而适宜的铺陈华人价值观的方式。林英敏提请批评界看到华人的话语里蕴含的力量,她说:“很显然,母女关系的延展是一场痛苦的历程,是两种同样强大的力量之间的拉锯战;在这场较量中母亲动用起她曾经的痛苦回忆,在‘动摇’了女儿的叛逆精神的同时,把自己已有的精神注入了女儿的血液。”
如果说华人的价值观仅仅实现了对华人子女的教育功能,那么它依然只是属于族裔内部的文化行为,华人的文化价值依然游离在美国的民族文化构建之外。在《两个世界之间》的最后一章综述里,林英敏将华人话语的教育功能扩展到美国社会和中国社会,提出“以‘错’纠错”(righting wrongs by writing wrongs),即华裔文学的社会价值之一在于写下种族主义的、性别歧视的和殖民主义的历史错误,以揭示即使在现代文明社会里也依然存在的强权政治和人类倾轧。
林英敏在其学术杂文里曾这样写道:“我今天所做的亚裔美国文学研究,其实是要努力营造自己的家园,为自己在这个直到今天依然充满敌视的土地上寻找一个舒适的所在。”在1980年代林英敏开始华裔文学谱系的编写时,朋友善意地提醒她,说她的确是开路者,但是她开辟的小路无人想去。情况确实一度令林英敏沮丧,她的科研领域之“边缘”曾使她难以得到固定教职。直到1995年,林英敏在将她的大半生治学抱负浓缩为一篇散文时,她在文章里说情况现在好转了:
我依然是我,我的工作依然如故,但是,似乎某种奇妙的魔法施过,我周围的世界现在变得比较友好了。突然间,似乎很多人对我曾开辟的“小路”意欲一探。我每天都收到来信和电话:出版商想要多元文化的素材编入他们的课本里;百科全书和参考书的编辑者要我推荐我所挖掘出的作家的作品;还有种族关系研究学院和两性研究中心邀请我去学校讲演,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生申请我来指导他们的博士论文;还有更荣耀的事情,一位中国学者最近征求我的同意,希望能将我的书翻译成中文。啊,他的翻译将使我再次登上“回家”的路程。
①②③⑳这里引用的林英敏的杂文来自Weber-The Contemporary West学术期刊网站。[美]林英敏:《这是谁的美国?》(Amy Ling,Whose America Is It?,1995,Winter.)。http://weberstudies.weber.edu/archive/archive%20B%20Vol.%2011-16.1/Vol.%2012.1/12.1Ling.htm
④“寻找母亲的花园”出自黑人女作家、评论家艾利斯·沃克的杂文合集《寻找母亲的花园》(Alice Walker,In Search of Our Mothers’Gardens,1967),其书名生动勾勒出一种重返母亲的故事现场、寻找母亲的精神花园的文化和身份的建构途径。虽然这本论文、演讲和访谈的合集内容杂陈,且大多是篇幅短小的个人感怀,远非厚重而系统的学术批评,但它的书名和书里提出的“Womanist”的身份概念却立刻流转为富有活力的批评话语。“Womanist”因无天然对应的汉语词条,经常被表述为“黑人女性主义者”,大致说来,Womanist是这样一种黑人或其他有色人种的女性主义者的自我身份定位:她首先是成熟女性气质的——敢作敢为、乐观勇敢、意志坚定,是矫饰、轻佻而不负责任的“女孩气”的反面;其次,她认定并追随女性文化,她不仅懂得并欣赏女性灵动的情感和力量,而且以和谐统一的态度对待男性;另外,最重要的一点,她不是作为男性的附庸与陪衬而出现在历史或生活里的。[美]艾利斯·沃克:《寻找母亲的花园》(Alice Walker,In Search of Our Mothers’Gardens,Orlando:A Harvest Book,1983,p.xi.)。
⑤⑥⑧⑨⑩⑪⑫⑭⑯⑱⑲[美]林英敏:《两个世界之间:华裔女作家研究》(Amy Ling,Between Worlds:Women Writers of Chinese Ancestry,New York:Pergamon Press,1990,p.x,p.17,p.19,p.20,p.25,p.49,p.26,p.49,p.59,p.139.)。
⑦关于东汉女史学家班昭的叛逆性,林英敏认为在班昭身上有个悖论:班昭一方面写下了《女诫》一书,指引女孩的教育,另一方面她本人并没有完全按照“三从四德”去生活,比如她“有才”而博学,比如她没有在丈夫死后殉夫。显然,林英敏所看到的班昭的叛逆性更是出自一个美国华裔学者的问题意识,同时也体现出即使像她这样的华裔文化学者,对中国历史的认知也不免简单而有限。
⑬这两段引文原本是威妮弗雷德的文字,出自她的半自传作品《我:一部回忆录》,此处转引自《两个世界之间》。[美]林英敏:《两个世界之间:华裔女作家研究》(Amy Ling,Between Worlds:Women Writers of Chinese Ancestry,New York:Pergamon Press,1990,p.31.)。
⑮[美]林英敏:《两个世界之间:华裔女作家研究》(Amy Ling,Between Worlds:Women Writers of Chinese Ancestry.New York:Pergamon Press,1990,p.60.)。林英敏这里所说的《安妮日记》,是13岁的德国犹太女孩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的日记。1942年至1944年间,她和家人为躲避德国纳粹的搜查而藏身于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一个密室里,她和家人后被发现,1945年她病死于集中营,但她在密室里所写的日记战后出版,并成为珍贵的关于战争记忆的第一手资料。
⑰[美]林涧:《语言的铁幕:汤亭亭与美国的东方主义》(Jennie Wang,The Iron Curtain of Language:Maxine Hong Kingston and American Orientalism,Shanghai:Fudan University Press,2007,“Chapter 3:Translating a Heroic Tradition of Chinese Women”,pp.74-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