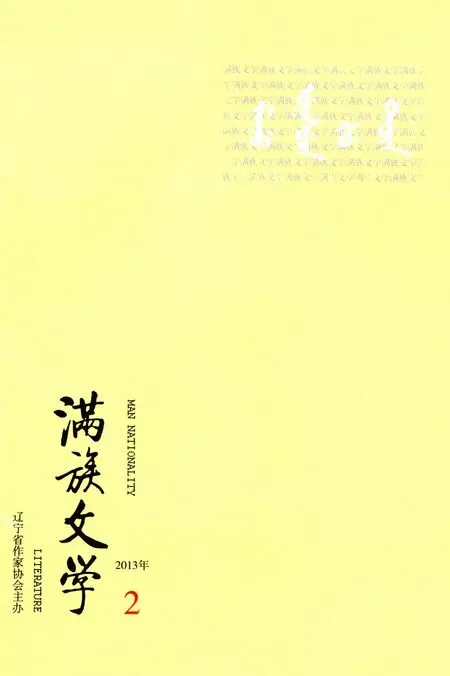另一种爱
2013-11-15向迅
向 迅
那个夏季的雨水特别多,村子里湿热难挨,很容易让人想起一九八四年那场持续多日的大雨。那一年恰逢我出生,猛兽般的山洪将山崖下起伏的坡地冲刷撞击得惊心动魄。潺潺溪流在一夜间变成了深沟巨壑。埋伏在泥土里的桌子般大小的石头遍布山野。屋子里灌满了水,浑黄的泛着泡沫的水还在汩汩不停地从火坑里涌出来。一个夏天的雨水改变了整个盆地的形态。都以为世界末日来了。大家心中充满了愤怒,积满了怨恨,憋足了诅咒,在泥泞里苦苦挣扎,求尽八方菩萨赐一碗饭吃。那异常灰暗的一页,虽给所有人都留下了无比深刻的印记,但最终还是被一双双生满老茧的手给从日历上硬翻了过去。
难得的一个多云日子,阳光扑朔迷离。拄着双拐的父亲,在我的协助下,吃力地操刀破开母亲刚刚从竹园砍回的两根水竹。两年前编织的撮箕、筛子等家用工具早已有了败坏的迹象,几经修补终于决定废弃。不能忍受终日闲着的父亲,要试一试身手。他右脚上打着的那一大截石膏,老在我眼前晃来晃去。这半年来,它试图让我们习惯它的存在。可如何能够做到呢?就是它,让父亲的步伐变得异常沉重,让父亲必须依靠拐杖才能勉强在院子里挪动。母亲为此一定是落过不少泪的。父亲的技艺还算娴熟,削开的篾条依然像模像样,游蛇一样在父亲手中灵活游走。我在旁边打下手,可实在帮不上忙,只好傻傻地站着。我习惯性地站在他的右侧。虽然父亲不能像以往那样健步如飞,而且右腿恢复的前景也比较暗淡,但我依然依赖他。
我正看得眼花,院子西边的路上响起了重重的跺鞋泥的声音。原来是穿着靴子从坡上下来的一位伯父。父亲的堂兄。村民组长。他在例行咳嗽了两声后,径直来到院子。像个真正的国家干部。父亲坐着,站不起来。寒暄了一番,接着稀稀拉拉地扯着闲白。父亲没有停住手中的活路,听伯父说话,偶尔插一嘴。伯父比父亲年长两岁,这几年因儿子在外打工挣了不少钱修建了新房子而显得有些志得意满,看起来倒比父亲年轻好几岁。父亲原来是极看不起他这位堂兄的。在父亲眼里,伯父就是一个不务正业的人,做事情没有规划,以至于把日子过得那么不像样,到他家里烟抽不到一根,茶也喝不上一口。有一年,伯父得了阑尾炎,动了手术,切除了阑尾,从来不问医药的父亲与邻人都以为他再也站不直腰了,这一辈子再也翻不了身了。他哪里料得到,那个被他经常嘲讽为“日古子”的伯父,现在就挺直了腰杆坐在对面与他谈天呢。父亲心底定然是有所惆怅和感喟的吧。
我虽已满十八岁,却仍不是十分关心大人之间的事情。我听着吩咐,在一旁候着为伯父装烟递茶。他们的谈话,我并未全部听进去,却也记住一些。略略记得伯父谈起了村里村外一些人事,提及谁谁家的孩子没念几年书,在外面挣了大钱,而谁谁家的孩子好不容易念完了大学,却一直窠在家里,那书算是白念了。木讷迟钝的我,并未听出伯父一席谈话的弦外之音。姜到底是老的辣,听话听音,父亲将伯父客客气气地送走后,立刻倒出了不满:自己的儿子没本事考上大学,也不让别人的儿子念书呢!他这一番阴阳怪气的话,不知是替谁来游说呢!父亲颇有一些动气,一直在堂屋里忙活着的母亲也前来将伯父数落了一番。我虽对乡下这种类似于长舌妇的议论很有一些深恶痛绝,却究竟是将伯父的话回味了一遍,明显觉察到了他的不善意图。我分明记得刚考取县城高中的那一年,他在我家炉火边信誓旦旦地对我说过,要是三年后你考取了大学,伯父奖励你一千块钱,伯父说话算数,决不食言!
这是异常艰难的一年,而我却极不合时宜地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自从知道高考成绩后,我就已自断了念大学的妄想。高考前,我曾一度吹嘘,倘若考不上重点,这书我就不念了。父亲也在与我的谈话里表达了这层意思,并用非常严厉的方式警告过我,要是你考上重点了,老子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你读书,但若只考个普通大学,那就不要怪我们了。我对父亲这一番苛责的话生不起丝毫怨恨。他在前一年意外出事,整个家庭陷入从未有过的困境。大有家道中落之感。这个时候,急切需要一件事情来扭转一下这种异常颓唐的气氛。他们都将这一点希望全部压在了我的身上。而我自负得过了头,以为考个重点大学跟到菜园子里掐一根葱那样简单,却不曾预料到那么快就要自食其果——高考发挥失常,我只考上了一所二本院校。也就是我们通常上所说的二流大学。连我自己都看不起自己。出门总觉得脸上有苍蝇在爬,跟干了亏心事一样。
我的确心怀愧疚。在父亲受难的情况下,他们仍然咬着牙关把我送上了高考这个战场。他们愁眉苦脸地等着我金榜题名,结果也跟我一样大失所望。我没有争气地考上足以让他们扬眉吐气的重点大学。然而我究竟是向家那块巴掌大的地方上名正言顺考取的第一个大学生。那些在我之前曾经以读书著称的堂哥堂姐们,最终都名落孙山。父母终究还是在暗淡的叹息声里拾起了那么一点喜色。那算得上是这一段堪称漫长的愁眉紧锁的日子里,唯一的一片亮光。作为主要当事人的我,到底没有勇气兑现曾经的承诺。只要一想起不能再继续读书,从此也将像父母一样,在这无尽的山野里挣扎一生,就不免黯然神伤。每天都有那么几个时刻,我茫然地站在阶檐下,望着无尽的蓝天与飘渺的远方踌躇不决。若不去念大学,我到底是心有不甘的;但是眼下的情境,不叫人死心也难。小我五岁的妹妹,见证了我全部的忧戚。我觉得同样念书的她,可以理解我的心境。我不曾向父母痛下不再读书的决定。这是一个让他们骑虎难下的问题。
考上大学的消息,一夜之间传遍村子。虽无人登门道贺,但我还是闻见了一种莫以名状的气息。那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气息呢?我至今仍无力陈述清楚。我在村子里走路,总会有暗器一般的包含了很多内容的眼光在我身上游走。这其中包括十多年不曾与我家来往的仇家。生活在同一个院子里的叔叔婶婶,见到我也闭口不提考大学的事,即便提及,也是一句话带过。然而等我刚一转身,她们就关起门教育自己的孩子,也就是我的堂弟堂妹们,一定要服恨读书。那恨从何而来?我不得而知。只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多少有一点眼红的意思吧。大抵是母亲对我说的吧,自从你去县城念高中的那天起,就有许多人等着看你的笑话。他们要看的笑话,就是等着我在高考后背着铺盖卷灰溜溜地滚回村子躲进院落,三月不敢出门,一辈子抬不起头。他们为此准备了足够多的嘲讽和唾沫。然而,我令他们失望了。特别是那些仇家,压根就不想听见我们家有人出人头地的消息。用父亲的话讲,他们恨不得把我们家一辈子踩在脚下。
父亲虽终日呆在家里,却洞察所有的变化。一个雨天,他拄着拐杖站在阶檐下,望了一眼惆怅的雨帘,很有一些愤然地对我们说,人家现在都躲着我们呢!我考上大学,虽没有将他们的颜面丢尽,却让他们陷入了一个比先前更为愁苦的深渊。他和母亲终日里愁肠百结,茶饭不香,夜不能寐。他们和所有乡下夫妻一样,时而为一些鸡皮蒜毛的事而大打嘴巴仗,甚至恶语相向。那个夏天,父亲因脚伤赋闲在家不能做事,对母亲的态度和外人的说辞格外敏感,用他的坏脾气维护着一个男人的自尊。沉默坚韧的母亲,在照料父亲的饮食起居的同时,用她的柔弱之躯挑起了家中里里外外的大小事情。虽然他们都尽量谦让和理解对方,在说话上十分考究,却还是因无数琐事和沉重负担积郁了太多的情绪,需要爆发。一个太阳天,我和母亲在院子里晒玉米,父亲坐在堂屋里乘凉。他们聊着聊着不知什么原因就吵了起来。我一向看不惯父亲的坏脾气,便对母亲说,不要理他,等他一个人说去。父亲听见了,脸豁地一下煞白得不成样子,紧紧地抽搐了一阵,一团话久久哽在喉咙里,随之将拐杖哗地一声甩在地上,一声不吭地躺到床上去了。父亲一气三四天,情绪极为低落。母亲后来才告诉我,父亲是为此事掉过泪的。我对不起他。可以说,他的意外出事,都是因我而起。而我的话,却像一颗杀伤力极强的子弹,像是在他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伤害了他。之后不久,他们终于在我的事情上起了争执。母亲撒气般地对父亲说,这书大不了不读了。父亲对此火冒三丈,却是自嘲道,不读了,说得好,不让别人笑死才怪,人家现在巴不得我们供不起他,巴不得我爬不起来!我听着心酸,但不敢插嘴,坐在一旁,手脚不知往何处放。那已是到学校报到的前夕。父亲终于决定厚着脸皮去求他的那几个与他深有罅隙的弟弟了。一向脸皮甚薄的母亲,也往返于亲戚邻人之间。几日下来,那看起来遥不可及的一笔学费已差不多凑齐。这很让父亲惊异,觉得自己的脸面摆在那里还管用。但几位同门之辈的做法让父亲憎恶不已,他曾这样慨叹,那些人啊,现在见我的脚一时半会儿好不了,生怕我们借钱了还不起!说这话时的父亲,确实对自己能否再次站立起来,没有抱多少希望。
母亲提起过一件事,说是我的一位叔伯表叔愿意借给我三千块,将来读完大学了再还不迟。但希望我们把家中的那只小狗送给他们家。那只小狗是在镇上念书的妹妹,与同学在街上玩耍时收养的一条流浪狗。妹妹周末回家时,不顾路途遥远把它带回家里。那是一只刚满月不久的小狗,却极为听话。到我们家后不久,就已经学着吠叫咬人了。父亲说这是一条好狗。我们都很喜欢它。生得虎头虎脑,长得结结实实。只是母亲不喜欢它,虽然它天天跟着母亲去地里巡逻,回家时还装模作样地衔一根木柴。母亲说,它身上长着那么多“漩涡”,不吉祥,送人算了。我们都没有把母亲的题外话当成一回事,以为就是那表叔顺口说说的。我私下跟妹妹分析,表叔大概不会以借钱为借口而白白地换我们家一条看家狗吧。如果真是那样,那就太卑鄙太无耻了。妹妹虽与表叔家的姑娘玩得烂熟,也知道实质上是那表妹喜欢上了那条狗,却对我的话深以为然。她对那条狗的感情,比我们任何人都深厚。
离上学的日子已经不远了,父亲还是对我第一次出门远行放心不下。也不放心母亲去送我,因她也从未出过远门。他决定亲自送我。当所有人知道他的这个决定后,都提出了反对意见。我一再表态,我已成年,完全可以独自去学校。母亲对他说,你自己连路都走不稳,怎么去送啊!这个时候的父亲,行走完全不便,倘若离开了那一对拐杖,那是寸步都不能走动的。这一年多来,他已先后做过几次大手术,一次次伤筋动骨。由于是粉碎性骨折,手术后因条件限制又没有得到很好地休养,加之他年龄也不小了,伤口愈合得极其缓慢。医生反复交代,千万不要碰着伤口,如果让植入骨头里的螺丝和夹板松动了,后果不堪设想。可是父亲一意孤行。他执意让母亲请来在镇上诊所里的一位医生,在家里的椅子上,为他卸除了那一截起着固定作用的石膏,用酒精简单地处理了一下右脚踝处那一道豁然醒目的伤口,硬生生地拆了线。我在一旁看得头晕目眩,浑身发凉打颤。父亲显然也是紧张的。他抓着椅子把柄的手上青筋暴露,干裂的嘴唇被咬出了两道牙印,额头上布满了豆大的汗珠,用毛巾揩了又揩。这一场景让我想起大哥给我讲过的一件事。父亲为了节省钱,在一次需要用器械打开他脚踝的大手术时,竟然要求医生不要打麻醉药!父亲的倔强与蛮勇,让我不禁想起刮骨去毒的关羽。我无意夸大父亲的坚强,但他的所做作为的确让我望到了一些罕见的英雄气!
此后的父亲,天天拄着拐杖在院子里练习走路。他每走一步,都让人感觉到世事的艰难。
父亲和母亲没有准备整学酒。他们觉得我的成绩还不足以撑起那个场面,同时也担心没有多少人来捧场,那个脸丢不起。自父亲出事后,家里一直是门前冷落鞍马稀。可就是在他们准备悄无声息地送我去上学那天的前夜,家里来了好几桌客人,都是向家院子里同门同姓的族人和远远近近的邻人。好面子的父亲,再次认为尽管他的脚受了重创,但面子还摆在那里。我和妹妹忙着招呼客人,装烟倒茶,端菜斟酒。那是父亲出事后,家里第一次来了那么多客人,好好热闹了一番。愁眉苦脸的父亲,终于在桌子上露出了难得的苦笑。前来道贺的表叔提起了那条狗的事。父亲当仁不让地爽快答应了。他吩咐我去找一根绳子,将那条狗拴来交予表叔。我一脸不快,半天不应,把表叔冷在那里。父亲一下子火了,叫你去找根绳子没听见啊,怎么这么不懂事。表叔站起来打圆场,要是娃娃们舍不得就算了。父亲说,哪能连一只狗都舍不得呢!在他的一再催促下,我终于报复似的找来一根绳子,将那条狗狠狠地拴了起来交予了表叔。做完这一切,我跑到了屋子西边的菜园子,眼泪扑簌扑簌地落了下来。脑海里全是那条狗活蹦乱跳的影子。妹妹不知什么时候也蹲在黑暗中,嘤嘤地抽搐着。然而,最终是她过来安慰我,送人就送人了。不一会儿,院子里狗声四溅,大狗小狗的叫声缠作一团。我赶到院子,才知道是表叔牵着小狗要回家去,被我家的那条大狗给缠上了。不知大狗怎么那么凶,任凭你拿棍棒怎么打都打不开,它不去咬人,却只管咆哮着扑上前去咬小狗。那架势,是要把小狗置于死地的。记得小狗没来多久,它们就已经混得烂熟,形同母子了,终日形影不离。天气暖的日子,小狗时常把头趴在大狗身上晒太阳。在大狗的眼里,看得见暖暖的母爱。可永远无法解释,在这个晚上,它竟疯狂到要将朝夕相处的亲如爱子的小狗亲口撕咬。我们终将大狗强行赶开,小狗尖利的叫声撒了一路。母亲说,它确实是将它当成自己的孩子了。
那个不眠之夜,大狗与小狗的叫声在月色下彼此呼应着。
那个夏天,刻在了我的记忆里,挥之不去,翻越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