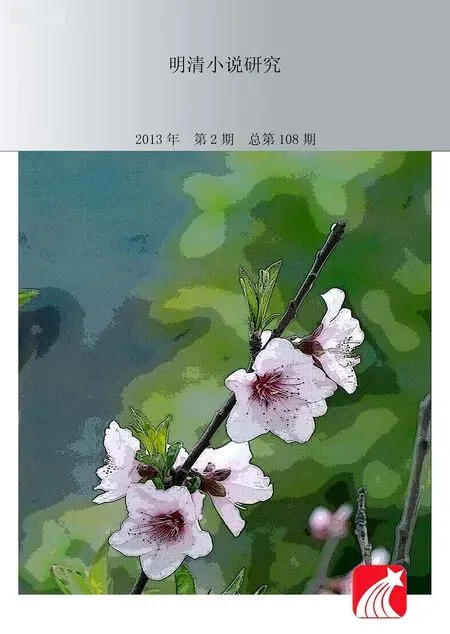论林纾情爱观对译文的操纵
2013-11-15··
· ·
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提出,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Creative Treason)。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渗入个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认知方式及生活体验等,从而影响对原文文化意蕴的认知和阐释,产生改写现象。译者的情爱观是其价值观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翻译过程中介入了对原文的重构。林纾翻译的几部重要言情小说——《迦茵小传》(Joan Haste)、《红礁画浆录》(Beatrice)、《巴黎茶花女遗事》(La Dame aux Camelias)、《剑底鸳鸯》(The Betrothed)、《玑司刺虎记》(Jess)、《橡湖仙影》(Dawn),充分反映了其情爱观对译文的操纵。
一、林纾的情爱观
晚清时期随着外国言情小说的引介,欧美社会的婚恋观被引进,使中国社会的婚恋观呈现多样化,保守与激进并存。中国传统礼教制度没有为爱情留下多少自由空间,视情欲为洪水猛兽。吴趼人对“情”字的申发代表了当时保守者的观点,他认为“情”一经施展,可发展为忠孝大义,而儿女私情是“痴”。把男女私情从“情”中排除出去,与私情相联系的“欲”更没有存在的理由。与保守者相比,林纾的情感观具有先进性,他重情、专情、肯定情爱的价值。
林纾是个重情的文人,自传《冷红生传》呈现了他的内心世界。这篇文字篇幅很短,通篇陈述自己的情感观。先形容自己“貌寝”,“木强多怒”,再述少时“力拒奔女”,年长又拒绝“色技绝一时”的妓女的爱慕之情,对此林纾的解释是自己太专情:“吾非反情为仇也!顾吾褊狭善妒,一有所狎,至死不易志,人又未必能谅之,故宁早自脱也。”结尾称自己所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凄惋有情致”,“吾能状物态至此,宁谓木强之人,果与情为仇耶?”林纾作自传,仅强调重情的个性,理想抱负、功名成就等大主题不着一字。而且,表现重情有诸多形式,最常见的是与妻妾之间的深情,可林纾独独选择“奔女”和“妓女”这两类游离于儒家正统观之外的女性角色。他拒绝妓女与奔女的辩词,透露了他不但重情、专情,还要“得情之正”的感情观。
林纾不仅重情,还主张情感专一,这与西方恋爱观念对他的影响不无关系。西方言情小说表现的爱情观综合了爱情至上的观念与基督教的牺牲精神,一方面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另一方面崇尚无私奉献精神。奉献精神在中国并不少见,也一直被正统观念所肯定、赞扬,但是排他性的情感在中国男权社会却一直遭到批判,传统社会对妒妇基本持否定态度。林纾对这种排他性的、专一的爱情却持肯定态度。他的自撰小说《何靉娘》、《胡燕玉》、《洪石英》,写的都是既专情又严厉的悍妇,在《洪石英》中借女主人公之口表达作者对情感专一的理解:“西人之求偶,偶其终身也。西俗之不置妾媵,即恐移其终身之爱,分诸他人。须知两心之沉结,合卺之期,即悠悠接于同穴。”
林纾情感丰富,翻译时投入强烈的情感,“余既译《茶花女遗事》,掷笔哭者三数”,为马克的痴情与悲剧命运悲伤。林纾作词《买陂塘》,悲叹迦茵的遭遇,在小说的《序》中称该书“以美人碧血,沁为词华。余虽二十年庵主,几被婆子烧却,而亦不能无感矣”。林纾还在正文中表达自己对迦茵的同情,如第13章评述迦茵对亨利的情感,添加“顾情不自禁,非即亨利,不能自聊”,以用情之深不能自拔为迦茵日后逾越礼法的行为作情感铺垫。小说《脂粉议员》末尾有评语:“天下人无情爱者,百事均无成功。世界中但有此著为真力量。”林纾以圈点的方式着重标出以示赞同,充分肯定爱情对人生的意义。
林纾虽然重情、专情,但他对情的肯定是在“礼”的规范之内,“发乎情,止乎礼义”是他始终恪守的原则。因此,他一再强调“得情之正”:“小说一道,不述男女之情,人亦弃置不观,今亦仅能于叙情处,得情之正,稍稍涉于自由,狥时尚也。然其间动有礼防,虽微近秾纎,或且非导淫之具,识者或能谅之。”
在晚清的时代背景下,林纾的爱情观处于保守和激进之间,他理解“情”,消解“欲”,注重“礼”。一方面,中国传统的伦理价值观在林纾的思想中根深蒂固;另一方面,受西方现代爱情观的影响,林纾认同西方某些先进的观念,如婚姻自由、爱情专一。林纾在翻译时不断调适中西两种不同情感价值观产生的矛盾冲突,以求找到一个平衡点。
二、情爱与礼防
“情爱”与“礼防”两无所失是林纾希望的理想状态,为此林纾对原文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写,一再强调“礼防”,以中国传统道德规范——“礼”约束西方小说中的浪漫爱情,调和“情”与“礼”的关系,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三、欲望的消解
中国古代小说有描写情欲的,但都是以情欲的危险性警戒世人,如白话小说《周胜仙》、《崔待诏》等。尽管冯梦龙在《情史类略》把“情”提到一个高度,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的色彩,试图调和情欲与儒家道德相冲突的一面,但在中国传统观念里,情与欲是分离的。而西方的情感价值取向是灵与肉并提,感情与欲望相联,两者既对立又统一,因此西方小说中有不少关于情欲的描写。林纾又是如何处理西方言情小说中的欲望表述的呢?


林纾是性情中人,也许并不反对恋人之间私底下的亲昵,但却不能诉诸文字。他不能接受关于情欲的直白描写,尽量用含蓄的言辞来代替,或者删去。《巴黎茶花女遗事》马克与亚猛曾经在乡下度过一段静谧的隐居生活,小说中有几段描述他们在一起的情景以及亚猛的感受:

林译:


以上分析可见,林纾的情爱观直接影响甚至操纵了他对原文内容的处理,传统的价值观使他不能接受西方小说中有关情欲的描述,因而采取漏译或改译的方式消解欲望。林纾重情又专情的性格使他能够理解并同情小说人物的爱情,但恪守礼法的儒家正统观念使他不能完全接受小说人物的一些言行,因而在译文中作了不同程度的改动。

注
:① [法]罗贝尔·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王美华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37页。
② [清]吴趼人《恨海》,豫章书社1981年版,第1页。
③ 林纾《冷红生传》,《畏庐文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25页。
④⑨ 林纾《畏庐漫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第328、189页。
⑤ 林纾《露濑格兰小传·序》,见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98页。
⑥ 林纾《迦茵小传·序》,上海商务印书馆1905年版。

⑧ [英]司丢阿忒《脂粉议员》,林纾、魏易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09年版,第150页。
⑩ H. Rider Haggard. Jess. Fairfield: 1st World Library, 2006, pp.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