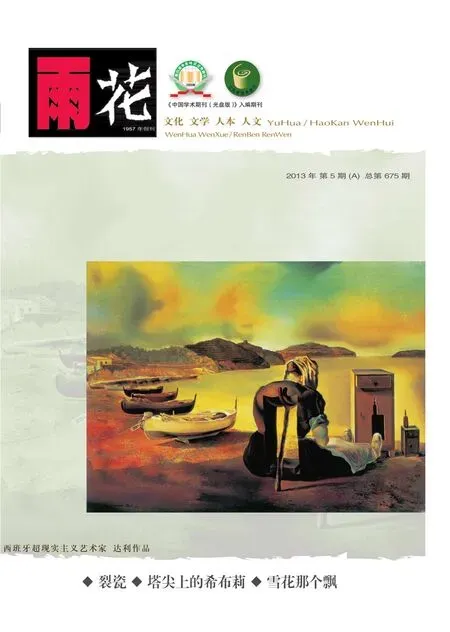我的父亲,我的土豆
2013-11-15王茵芬
● 王茵芬
土豆不只是用来吃的。
我把父亲给我的一袋土豆搁放在一个墙角落里。当我往它们身上看的时间长了之后,会觉得像我的父亲坐在那里,体形敦实,沉默无言。到后来,总会留下吃不完的那几颗土豆,它们像冬日里的一个个老人,在时间中打盹,等待春天的来临。
我的视线延伸进这几颗土豆的内里,那细细的芽儿探头探脑地向外张望,一缕阳光照射过来,它们的眼睛眯成一道线。这让我想起了我父亲的眼睛。父亲在小时候因罹患天花,造成左眼几乎失明,原本的双眼皮萎缩耷拉,整只左眼变成一条可怕的细缝。父亲几十年来竭力让这道缝闪着光亮,他一直认为,这只眼并不妨碍他的生活和工作,一样能看见世上所有事物,包括每一颗土豆的微小变化。比如他总会眯起左眼观察土豆细细的芽,并小心地将土豆一个个平放在干净的地上,使细芽向上。
就这样,我分不清是土豆的眼还是父亲的那只眼,让我寻回岁月深处的一些片断。多年前的一个春日,太阳很暖,照得人们的脸膛流光溢彩,大家心里盘算着该在自留田里下种哪些瓜果蔬菜。我父亲额头的两道皱纹舒展开来,头发理得光滑黑亮。他来到柴屋后墙,蹲下身,满目温情,那只左眼发出柔软的光线,落在躺满一地的土豆上面,看到豆芽长得很快,有一根手指那么高,他便吩咐母亲和我把土豆搬到篮子里,并特别关照不能碰坏一根土豆芽,然后一个人去地里翻土施肥。
父亲脱了棉袄,只穿一件薄毛衣,卷起袖子,不停地上下抡着铁耙,致使小臂上青筋直暴。这一刻,这三分僵硬的土地在慢慢醒来,变得松松垮垮的。父亲像春天水塘里的一条鱼,欢快而迅捷地来回游动着。他的左眼在放光,浑身散发出一股强烈的热量,和地表下面的热气交融,瓦解了冬季的残寒。
早春的旷野上,草和树都干枯着,在冷风里瑟瑟发抖。父亲却干得热火朝天,翻完地,挖好一行行垄沟,它们像用梳子梳理过一般,整齐规范。他又去粪坑挑大粪,按他的说法,要让荒地变肥,多浇几担大粪。记得我头一回跟着母亲去种土豆,踏进这粪便狼藉的地里,就捂着鼻子逃回家。后来,父亲在饭桌上问我,这些饭菜好吃吗?我点点头。他就说,你吃进去的东西都是地里种出来的,你不吃它们,行吗?我摇摇头。我只看到父亲的左眼用力挤了一下,并听到他的喉咙内发出一声重音。他接着说,那以后不许再逃避劳动。自此,我对父亲心生畏惧,也很少正视过他的眼睛。
村野的田埂很窄,父亲挑着沉重的大粪,嘴里有节奏地喊着号子,脚步稳健,精神抖擞。母亲帮父亲将大粪浇在垄沟里,他们还欢快地谈论着这块名叫“河上丘”田地的种种好处。我在这样的场景当中,被父母的劳动热情所感染,也动作麻利地把一个个发芽的土豆种到地里。我的内心像有一条小溪在流淌,我肉眼所看到的事物变得干净起来,而父亲劳作时的身影烙在了我的心中。后来,当我看到土豆,这样的情景就会重现。我想到我来到人世,和父亲种土豆没有两样。是他让我来到世上,他一定是满怀希望的,就像他坚信自己的左眼也能和土豆的细芽亲密接触交流一样。
父亲种出的土豆可以让我们吃很久。土豆有多种吃法,而我最喜欢吃那些煮熟后剥了皮再红烧的土豆。其实也不是纯粹为了吃,而是喜欢静静地坐在板凳上剥土豆。我抚摸着那些干净嫩滑的土豆,我会觉得很满足。拿起一颗和我拳头一般大的土豆放在掌心细看,发现它就像我的家一样,结实温暖。我再翻出一颗稍小一点的土豆,那形状如同一个枕头,它应该是我的父亲了。我继续翻看着每一颗土豆,偷偷乐了,原来不光是我们一家人在里面,还有村上的一些人和物都可以从中找到。
在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吃着土豆长大的同时,对父亲的情感越来越深切,他成为我成长过程中必要的依赖,就像我对土豆的期待,一到夏天便去土豆地张望,看那些碧绿的藤蔓是否粗壮得可以让一个个土豆从地里蹦出来,滚满我家。如此的感受,一直延续了多年。慢慢地,我能正视父亲的双眼,尤其是他的左眼。
记不清是哪一年,我发现自己被土豆喂养成人,并离开了我的村庄,父亲叮嘱我一定要记得回家,记得这片土地。
后来几年,每到六月,我就会匆匆忙忙地赶回家,和父亲一起去地里收获土豆。父亲举起铁耙,角度精准地刨开隆起的地垄,三下两下扒拉开松散的泥土,土豆便骨碌碌滚了一地。我弯下腰,一边捡拾一边惊喜地赞叹土豆的大,土豆的多。父亲不停地刨着,我来不及看他的表情,但我可以感受到父亲的左眼一定明亮如镜,每一颗土豆都在他温情的眼里,在他本真的生命里。
那些带着细泥颗粒的土豆,在我父亲的眼里就像小小的生命一样,清新动人。同样,它们不只在我的手里,也住进了我的心里,生动而鲜活,让我感到踏实和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