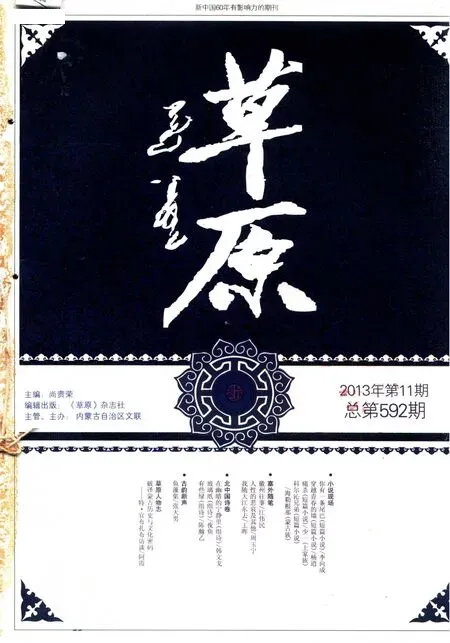《随心所语》序及后记
2013-11-14流沙河蒙古族张阿泉巴特尔蒙古族
□ 流沙河(蒙古族) 张阿泉 巴特尔(蒙古族)
序一巴特尔,一个早起采蘑人
内蒙古电视台记者张阿泉君转来蒙古族作家巴特尔先生的短语集《随心所语》书稿,嘱我写几句话缀在书前。 我与巴特尔先生的相识,也是几年前由张阿泉君所介绍。 二○○九年九月,我去内蒙古草原参加第七届全国民间读书年会,还与巴特尔先生在呼和浩特有过一次短暂而愉快的晤面。他的新书不久将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精编出版,我在此首先向他表达祝贺!
作为蒙古族后裔,我对来自草原的风物感到格外亲切,对来自草原的作品也是如此。巴特尔先生的《随心所语》由数百条信手而写、惊鸿一瞥的短语所构成,范围涉及人生的许多侧面, 语言朴质而观察精微,角度寻常而境界高远,流露着一种开阔舒展、旁逸斜出、草漫天涯的“蒙古人智慧”,我品读一过,领略到别样的机智、顿悟之美。 “巴特尔”在蒙古语中本是“英雄”之意,而我眼中的这一个“巴特尔”实在是像巴拉根仓一样的“智者”。
巴特尔先生出生于内蒙古土默川, 早年从教,后转而从政,虽宦海浮游,始终不废读写与独立思考,尤惯以短语方式阐述对世界的看法。 离职归养以后,他更彻底回归作家本行,潜心笔耕,坚持过秋收冬藏的“书生活”。 《随心所语》即是他长期从事短语写作的精华与智果, 世事与人情洞明,诗意与哲理兼备,虽云“随心所语”,其实每一条文字都颇费周折, 用心思虑凝练而成。 这般从丰厚生命中提纯出来的“箭镞一样”的短语,其价值要远胜那些空话连篇、 无病呻吟和泛滥抒情的长文。
同样的尘世生命,同样的眼睛、耳朵和心,有人对生活感悟无限,有人对生活却熟视无睹, 生命的馈赠多寡取决于每个人对生活的不同态度。 记不清是哪一个国家的一句谚语,说“只有早起的人才能采到蘑菇, 晚起的人只能采到荨麻”,我想, 勤于思辨的巴特尔先生正是一个早起采蘑人。
是为短序。
序二短语寥寥胜过大论喧喧
在蒙古族诗人巴特尔所著短语集《随想录》出版时,我曾写过一篇序二《随想体文字的生动之处,一在于“随”,一在于“想”》。 现值《随心所语——巴特尔随想精选集》集萃付梓之际,我再次应邀缀文于此,前文中没有说尽的感受,正好拾掇整理,衍成这篇新序。
巴特尔先生的随想文字, 已坚持写作多年,逐渐形成了一种简洁明快、诗理相融、直击事物内质的典型美学特征。
譬如:
拥有很多时间的人自在, 不需要很多钱的人自由。
多么简洁明快! 毫不玄虚的点石成金中,已经清晰攫住了“自在”和“自由”的哲学逻辑关系。
再譬如:
钱多的人比钱少的人吃得好, 钱少的人比钱多的人睡得香。
多么诗理相融! 只从习以为常的饮食睡眠升发,将物质与精神诗意对比,理性升华, 豁然中见出得失自在天理的顿悟,让人抚节叹赏。 这句随想,使我想到另一句含有悖论智慧的格言:“皇宫里也有哭声,茅屋里也有歌声。 ”
还譬如:
一个高度,一个境界;一个角度,一个世界。
多么言虽简而意赅! 四个“一个”,两个排比,没有一丝晦涩和迟疑,却明明白白告诉你世界的丰富、 宽广、 多元和变幻,正所谓“认知之妙,存乎一心”。 这句随想,透着水净沙明、拈花一笑的禅意。
仔细体味,上面三个短句,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出语非常简淡,青菜萝卜,竹头木屑,不经意写来,却出奇制胜,从“生活现象的海” 里网住一两条浮游而出、极易脱手、活泼跃动的“思想小鱼”。纵观诗人的整体随想写作, 也都遵循着这一“不花俏,重内涵,传奇思”的话语格调,这是更高难、更考验作家捕捉能力和思维深度的写作挑战。 俗语云“一粒沙里见世界,半片花上说人情”,此之谓也。
在短语集《随想录》跋语《“随想”的随想》中,诗人曾说:“随想写到最后,拼的不是语言,而是思想:思想的诚实,思想的深刻,思想的智慧。 我写随笔,总想简约一点、美丽一点、意外一点。 ”这段话,正是诗人追求“不花俏,重内涵,传奇思” 写作理念的脚注。 在这种理念贯注下,哪怕是随手写下的一个短语,都仿佛成了“指明问题所在的神奇魔杖”,能够简捷、有力、精确、概括地评点生活,评析人生,评价生命,达到反观审省、启迪心智的功效。
人的思想没有长度, 人生随想却可短可长。 巴特尔的随想求短弃长,短中见长,以短胜长。 不过,把文字写短,不仅要有提纯的能力,更要有高度的修养。 人们大多不愿写短文章, 所以长文章才泛滥成灾,以冗言耗时。 寒斋插架藏有几本倡导“减法主义”的书,譬如法国彼埃蕾特·弗勒蒂奥著《要短句,亲爱的》、钟叔河著《学其短》、英国E·F·舒马赫著《小的是美好的》、 美国里奥·巴伯塔著 《少的力量》,传达的都是“减法思维”——这些大家们倡导的“短”、“小”、“少”说的都是一种 “自我设限”、“去粗存精”、“化繁为简”、“全神贯注”的力量,因为“越简单越厉害”是工作和生活的双赢法则,没有限制就永远不可能强大。
随想短语写作看似容易实而艰辛,恰似“冰山露在水面上的八分之一”,而另“八分之七” 都藏在了水下。 这里的“短”,以“长”为前提和铺垫。 有时候,“短”即“长”,“长”即“短”,所以不能轻易从字面上论“短长”。 列夫·托尔斯泰晚年的著名短语集《智慧历书》,写作过程超过十五年,动笔时已接近八十岁高龄,并先后修改增删三次,出版过三个修订版;拉罗什福科的代表作 《道德箴言录》,则是根据他近五十年的人生驳杂体验而“榨取”出的一本人生断想,尖锐、深刻而透辟, 书中每一个短语都渗透着谋生和与人周旋的机智。 同样,读者手中赏读的这卷《随心所语》,其写作时间跨度虽只在一二十年间, 但其素材积累和心智积淀的跨度则至少在四五十年间,是“厚积薄发”、“春蚕吐丝”、“燕啄春泥” 的心血沉淀,是光阴与生命的双重缔造。
为什么巴特尔先生会如此痴迷和擅长精短写作? 我想,能将生命要义提纯悟化是一个原因, 有长期的人生历练和心智修持是一个原因, 惯于用精短语句表达深刻思考还是一个原因。 他把平日的思绪、观感、即兴文字、片段灵感等等都随想随记下来,落叶一样积累成“脱口而出”的札记,正像他自己所说“……我写随笔,是无意插柳,因为它是半路起家,只是一发而不可收。 ” “一发而不可收”,这最是理想和谐的“失控态势”,凡事能达到这种欲罢不能、 水满自溢的 “下意识”、“宿命”境界,把文章做好就是顺理成章的了,但这种状态难遇,其常态便更难求了。 想来这个世界的格言箴语已足够多,中外古今触目皆是,甚至早已濒于俗滥,而吸收领会的分寸,则全在我们自身——几乎所有的格言箴语或有历史局限、或有具体语境、或有一定指向,甚至有的彼此矛盾。 格言箴语本是对生活的“沙里淘金”,但其中仍多有“沙与沫”,因此我们对格言箴语的认知同样需要 “沙里淘金”;格言箴语内涵浓缩,类似“语言中的盐巴”,摄入量不可超标,需不断佐以社会实践的“主餐”方可正常消化;格言箴语会激活我们的思维和见识, 但不会轻易“改变一个人的一生”,因为它只是前人留下的路标, 脚下的路还得靠自己“一步一个脚印”地走。 阅读格言箴语,就像与许多伟人奇士一路同行,但“尾随其后”总非长计,要彻悟人生的趣味、诡谲与奥秘,必须同时学会“一个人背着行囊勇敢远行”。 我与巴特尔先生以书为媒,由此而相识,以文为友,由此而相知。我知他从不强加于人, 更不会以布道者自居,让人全盘接受他的所思所想所悟。但是,手捧《随心所语》一书,或随手翻阅,或掩卷沉思,你会渐渐感受和领略到巴特尔心灵中的五味杂陈和生命里的七彩斑斓。 当然,读者自会见仁见智,各有各解,也自是入情入理之事。
在《随想录》一书的序二中,我曾把巴特尔先生的短语文字比拟为 “巴特尔式随想”。 因为它独特、融化了个人哀乐与体悟、富于北方草原粗犷风貌、原创、草根,不是“随团旅游”而是“独自探访”,不属于“名人名言”,但绝对像毡房早晨刚挤出的鲜牛奶一样清香而饱含营养。现在,面对《随心所语》一书,我进一步想到的是,随想短语写作类似“电报体”,其效果是“短语寥寥胜过大论喧喧”,意思完整而深永,弥漫着无穷魅力。 所以,有人评价说精彩的随想短语,或“读之如饮甘露,如啜醴泉”,或“读之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都说得情真意切,令人悦服。
人生摇曳多姿, 奥秘无穷, 关乎学问、存养、持躬、养生、敦品、处事、接物、齐家、从政、惠吉、悖凶等方面的格言也累牍联璧,不断谆谆诲教于人,但往往亲切的朋友比严肃的导师更有亲和力,更实际和更有作用。 而这本三联版《随心所语》,正属于这样一个“亲切的朋友”,有时“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有时“相见亦无事,不来常思君”,一如巴特尔先生本人一样坦诚、率真和朴茂。
后记 我与随想
梦,是一种渴求,是人生追求最初的渊薮。 梦,温暖心灵,点燃生命,引渡苍生。
文学是我人生最初的梦,它美丽、漫长而平实。 我的文学梦,是从学诗开始;之后, 随想使这一美梦变得更加绚丽多彩。 如今,诗与随想便成为我文学之梦的双翼。 它们的不同在于:我写诗是有心栽花,它既是我最初的兴趣,也是至今的爱好;我写随想是无意插柳,虽半路起家,却一发而不可收, 竟成了我生命的难舍和不弃。
先从文学的创作历程来看。 从一九八五年以来,至今先后出版不同体裁的作品共二十部。 其中,从一九八七年至二○一○年先后出版有关随想的书共七本。 它们是:《沉思与随想》,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一九九○年获全国第三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优秀作品奖;《教育随想录》,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中国卓越出版公司出版,一九九一年获全国中华教育艺术研究会第三届年会优秀论文奖;《人生随想》,一九九八年六月作家出版社出版;《自选集·随想卷》,二○○三年四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随想录——一个思想者的远行》,二○○八年八月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戊子年随想》,二○○九年十一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游思录》,二○一○年八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再从创作的心路历程看: 一是我把诗与随想总是交织在一起思考, 二是我把自己的随想定位为“诗意随想”和“哲理随想”。 正像我曾经说过的那样:“我的随想,是文字的舞蹈,更是灵魂的呼吸。我喜欢把散文当诗写, 有时也喜欢把诗写成散文的样子——这就是我赋予我的随想的风格。 ”“我还认为,诗人的灵感,艺术家的敏感,作为一个思想家,这些也是少不得的。 我虽然与‘家’无缘,但却竭力想探求和寻找一种属于我的独特的表现形式,即一种诗与艺术的哲学思辨,或一种哲学思辨的诗与艺术。 ”“诗意随想,是我的天堂, 它演绎我的灵魂; 哲理随想,是我的宗教,它诠释我的人生。 ”所以, 我不懈追求的是:“哲学是理性的诗与随想,诗与随想是抒情的哲学。 ”
另外,我曾在《随想录》一书的“跋语”中还写道:“人生就是一次寻找,寻找当然离不开思考, 而随想便是我的生命轨迹和精神家园。 ”“生活教会了我沉默,沉默又教会了我沉思, 我又在沉思中学会了用随想表达对生活、对生命、对人生的感恩。 ”“我的随想,是我生活的况味、人生的感悟和生命的体验, 也是我生命独具的形式和人生沉思的独语。 ”“人,可以延续和演绎生命的不是名位, 更不是权势和财富,而只有文字和思想。 ”总之,我的随想,是我心灵和思想的“传记”。
现在呈现给读者的 《随心所语——巴特尔随想精选集》一书,是我以往先后结集出版的七本有关随想书中内容的精选, 这是一个思想者远行途中人生五味和生命七彩的浓缩和聚焦。 当然,出版这样一本书,是我文学夙愿中的梦中之梦,现在终于实现了,我只想说:圆梦的感觉真好! 与此同时,我要真诚地感谢:感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偏爱, 力荐并把它推向社会; 感谢责任编辑关丽峡的垂青和倾情付出;感谢著名诗人、学者流沙河和流沙河先生的忘年交、 书爱家张阿泉分别为书写序, 以及给予我的真诚鼓励和鞭策; 感谢广大读者一直以来的喜爱、关注和支持。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但畅游的思想永远不会老去。 所以,梦还在梦中,路仍在路上。 我将续写我喜欢的文字,让思想沐浴日月,穿越四季,一路远行。 远方,有梦光明的际遇;远方的远方,有梦灿烂的期许。 我希望自己是一个清醒的梦游者,而且只要梦在路上, 就一定会见山外青山,会有景中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