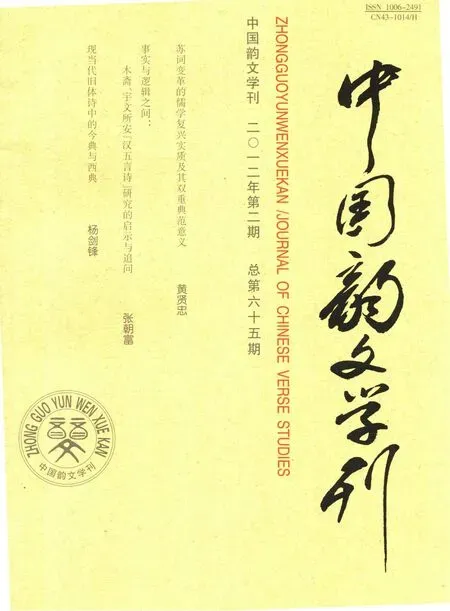事实与逻辑之间:木斋、宇文所安“汉五言诗”研究的启示与追问
2013-11-14张朝富
张朝富
( 四川大学 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四川 成都 610064)
关于汉魏五言古诗的研究,最近颇不平静,因为两部著作的出现,一是木斋的《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一是宇文所安的《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按照他们的说法,署名班婕妤的《团扇诗》、苏武、李陵的“苏李诗”、秦嘉、徐淑的赠答诗、《白头吟》、《陌上桑》、古诗十九首等等,均非汉人作品。关于汉魏古诗作者及时代问题,传统认识一直也不统一,即使进行否定的一派,也往往是个案型的、对若干首的翻案,虽时有新意,但终未影响汉魏古诗研究的大势,传统以来的文学史编排、讲授和研究,基本都把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古诗、乐府一类,纳入到汉代的文化背景中进行考量,而按照木斋和宇文所安的认识,大家兀兀所营之汉魏古诗版图,不仅虚空,原为徒劳,更折射出我们一直的思考和做派出了大问题,想来心惊。
结论依然可以商榷,这也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我们尤为关注的是,他们的进路与一般有何不同?对传统认识的否定性思考有何超越?它们能否担待起这种天崩地裂式的解构?与之映照,传统的认识和处理原则有何不足?试述之。
他们首先都清理了“汉诗”生成的历史,不过针对性不同。木斋虽然对“古说”进行清理,但更多聚焦于古诗十九首“东汉发生说”的近现代强化史,并以之为突破口渐次解决“汉诗”的整个问题。宇文所安则着眼于古典诗歌起源的古代生成史(当然,五言诗是其中的本质问题,其著述也围绕着五言诗展开),故关于古代经典中的相关论述梳理得更为细致,从檀道鸾的《续晋阳秋》、谢灵运和江淹的拟作、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到《文心雕龙·明诗》、锺嵘《诗品》序、萧统《文选》及徐陵《玉台新咏》,看出“汉诗”史是从无到有渐渐开始出现的。
汉诗的来历和史的构成是有问题的,乃众所悉知情况,关键是能从中看出什么问题并怎样解决。处理原则在这里至关重要,信而好古尽力弥合纵使迷雾重重却逐渐形成条分缕析眉目清晰之文学史脉络固然有问题,但原则不当逻辑不清纵使有疑也是徒增纷扰。关于汉魏古诗研究的纷争起合,并非某方发现新材料引起,大家所见同一,差异多由于切入角度所用原则不同造成。体现思考力之处理原则实在大有不同,这直接决定了结论的有效程度,就思考和处理材料之原则而言,木斋和宇文所安确有不同寻常处。
木斋的逻辑针对了一个强大的认识传统:
我有相当长的时间沉潜于汉魏五言诗和唐宋词体演变这两大课题的同时研究之中,……两者之最后的研究结果,竟然是不约而同地证明了胡适、梁启超以来流行的民间说的不能成立。我所看到的一部中国诗歌史、文化史,在盛唐之前,基本上都是以宫廷为中心的向外、向下的辐射历史,……盛唐之前形成的五言诗、近体诗、唐五代声诗曲词体制,此三者皆为第一个文化类型——宫廷文化的产物,哪里轮得到民间创造这两大文化体裁呢?
大论议往往出于对坚硬传统的颠覆或反思,这种攻坚需要特别的战力,木斋的战鼓有发蒙启滞之效。传统认知如诗词曲赋等文体无不发于民间成于精英,已成常识,于习以为常处起疑难,非有相当的警觉和思考力不成(有趣的是,宇文所安也恰有相关的反思)。即使论断依然可以探讨,单就其方式和效果而言,已殊可观。以此视角来检讨传统以来关于五言诗的思考和做派,其不足和问题显而易见。
宇文所安的逻辑也是从怀疑一个根深蒂固习以为常的传统开始,传统以来一直按时代顺序给诗歌排序,他以遵照了这一传统的逯钦立编著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为例,该著一方面把一首团扇诗系于汉成帝时的班婕妤名下,一方面指出此诗盖魏代伶人所作,疑问就此展开:如果不这样团扇诗该安放在哪儿?当然宇文所安不是想探讨诗歌如何排列的问题,他的指向是大量不确定作者、以手抄本为主要存在形式因而一直变动着的早期诗文本,如何就逐渐变成了“汉诗”?当四五六世纪,五言诗渐渐地被精英选家和批评者所重视,从檀道鸾、沈约到刘勰、锺嵘和徐陵,“汉诗”开始从无到有地渐渐多起来了,时代要为这地位已得到极大提升的诗歌形式匹配相应的价值并安放于特定的文化时空,以呈现五言诗渐变渐长的发展逻辑。诗歌从开始时的简单、直接、来自民间,到东汉晚期不知名文人创作更为规整的作品——古诗,再接到建安时期,现代文化史的这一标准叙事,即为齐梁批评家的重新表述。
只破不立的批评家是好做的,只需指出人家的不是就可以了,只到这一层面无以为继匆忙收束算不得好的思考,好的论难让人有更大的期待:那么,如何更为合理地推动问题的解决?这才是真正体现功力的地方。木斋和宇文所安都系统地提供了自己的解决方案。
木斋采用的是围城打援、各个击破最后攻坚的方法。对于五言诗发生于东汉说的一些重要依据,如证秦嘉五言诗为伪作,从故事流传到文本成熟的角度证明《陌上桑》与曹植或傅玄有更为密切的关联。一步一步清理下来,到曹魏时期作者考察指出:“这种(抒情的)五言诗,在整个三国时期,只有曹魏有三曹六子会写,吴蜀两国,均无人问津。”就可见作者而言,整个三国时期,确实只有建安诸子能做五言诗,且整齐地发生于归曹之后,五言诗的水准不具备整个时代的普及性,从这个层面看,说之前就已形成了如现在所认定的汉诗水准,的确难以让人相信。接下来从清商乐、游宴诗、女性题材等多方面论述了曹魏五言诗成立和兴盛的条件、原因。作者认为只有到了这一时期,高水准之古诗十九首才可能具备了出现的条件。如何给古诗十九首进行历史定位?作者从语汇语句的角度考察十九首与其他诗歌群的关系,十九首和苏李诗的基本句式及主要词汇与汉诗几无交集,与建安七子有数句相似,与曹丕开始十余句,而与曹植则达到三才能大致较好地为之定位,这体现出比传统视之为十余句,作者认定十九首基本可以确定作于曹植时期,并进一步论证曹植就是十九首的主要作者,甚至给出了十九首为曹植所作却逸名的原因,乃至于为十九首一一系年。
就审查办法而言,宇文所安与木斋有相似性,他把现存的早期材料放到社会文化系统中进行同步检视,不过他的考察对象不是诗的语汇语句,而是“主题、话题、描写的顺序和一系列语言习惯”。因为我们所面对的是手抄本系统,不能把它想象成完整未曾变动的“定本”,其在传抄流布择取应用的旅程中变动不拘,其规模也迥异于我们现在所见的数量,在这里判定谁先谁后哪个借鉴了哪个,基本不大可靠,如果视之为共享资料库的一部分,来探讨它们表达的主题、采用的话题、如何展开一些共同的故事或情节、体现了怎样的语言习惯,进而观察这些共通要素的进程及时代特点,独立创作、为之强行划定作者、执意探究文体差异等做法更为妥当。
根据上述原则,作者检视通常所谓汉诗,多不符合实际情形,十九首不是汉代作品,苏李诗不是,《孔雀东南飞》不是,《白头吟》不是,秦嘉诗不是,连班固的《咏史》都成了问题。
殊途同归,木斋和宇文所安视角不同,但结论几近整齐一致,连对学界若干观念或做法的检讨与反思都多类通之处,感叹妙思可通时地之隔。可喜者固然是二者之精思妙论,尤可说者为二者集中联袂而出的预示。翻开关于早期五言诗研究的史册,你会很惊异于一种状况,很长时间以来,关于早期五言诗研究的路径、原则乃至相关结论,基本都是由较早的老一辈学者提出的,这些说法久得都凝固成一种坚硬的传统了,固然说明前辈了不起的水准,但显然还反映后续研究者的创造力不济,成说演绎得太久思考力会钝化。也许正有感于此,当傅璇琮看到木斋的相关研究后毫不吝惜赞美之词:“《古诗十九首》研究的首次系统梳理和突破”。当有针对性之佳作连出,显然显示了相关思考领域发生了变化。两者的集中出现给了我们不少信心,引起我们对某些研究现状进行思考,学界曾经有论议曰论题难寻,亦有创造热点追随热点者,其中是隐含了怠惰和投机倾向的,不是没有问题,其实越基础的问题就越连带大问题,只是发现难清理尤难而已。
历史渺远,学问不衰,关于那一曾经的“唯一史”,怕已不可能完全恢复了,关于“史”的追问目的当也不在于此,史事间蕴含的历史演绎,结合于事实与逻辑之间,拷问着当下对历史的感悟。在这一视角下回看两者的追问,显然是有超越性的。
相对而言,宇文所安的方式容易接受一些,虽然他普遍地检讨了传统认识体系中的诸多问题,但他的结论也还是趋向宽口径的,他经常性的表述是:可能是那样的,也(更)可能是这样的,突出逻辑的更为可能性。木斋的表述就激切了一些,他似乎根本不考虑余地的问题,直接奔问题的解决而去,在迷雾重重中,他寻求彻底突围,把十九首一一指向了曹植,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但在壁垒纷纷中疾进,不周全的环节当是有的,在他的一些论据和论证依然可以有“非如此”的指向时,商议和探讨肯定还要持续下去。
读木斋、宇文所安著述,启发良多,学步于其善问之道,以愚钝难以一时开悟乃至回护传统之心,起一二追问,不揣浅漏,为学也。
建安时期,早期五言诗发展起大变化,动力问题显然至为关键,如传统认定之汉代作品,多归于此时及此后,则此动力之促成实有古来少见之大效力,那么其为何?又怎样开辟此前几无之独造局面?而促成曹魏时期文化发生大变化的政治文化变局,在东汉桓灵时期以“党锢之祸”、“鸿都门学”为显现,及其类通地发生过,所引起的文人格局变化与曹魏时期几无二致,那么是否也可以追想它带动汉末的五言诗发展呢?
关于汉代五言诗史的建构,基本来自齐梁及其以后,其间的长时段空白确令人生疑,但存不存在一种逻辑可能:某一时期的某些文化现象,隔代乃至隔几代在另一时期出现呢?如同一条河流有效部分之暗流,于另外的时地升入人们的视野?历史记录所扫向广阔社会空间的角度和宽窄,尤其在历史的早期,不但是有限的而且还是受限的。这一现象有类于敦煌,其中的太多现象不曾被记录史所言说,敦煌是特例,“敦煌现象”在传统文化发展史上倒不是特例,文化现象不但常常存在空间错位,也时常发生着时间错位,当某一文化类别未曾进入精英记录者法眼或不符合时代文化检查者的标准,蛰伏就成为一种可能,当其在另外一个时期开始受到重视,那么重新得到挖掘整理,逻辑依然可通。无论是组合型乐府,还是某一材料或主题、话题在不同文本中的应用,都可能反映着早期演出痕迹的遗留,也都可能透露着文人普遍介入之前无论是创作还是演出应用地位都不那么高端的事实。这让我们想起了刘勰和锺嵘论诗对象的身份问题,二者不约而同地把论述者的身份确定在了精英文人层,也都明显整齐地对其他社会文化空间的现象不予置评(除非为了溯源需要述及前代的谣讴,在正式梳理某朝的诗歌承续上,均明确地指向精英文人),这在别雅郑建道统意识非常明确的古代,是可以理解的,无论是梳理文学统序还是“品诗”都遵循着类似的逻辑,即使在今天,现当代的文学史序列,也都还是精英文人的天空,那么另外的社会文化空间,是什么样子?让人充满想象。比如汉文人感叹“类同俳优”的俳优之唱作,风行的赵代秦楚之歌辞,的确存在乃至风行,但记录史并不予呈现,类比或批评之需要,是它们被提及的理由。其中的谣词歌讴形式,为楚歌、四言、五言还是杂言?难说。因为材料缺乏,批评于此环节往往并不置评,但那个文化空间的确存在,其中可能就有五言的信息。可以明确的是,南朝描述建构的汉诗史,一定是依了某种意图顺道进行了改造和添加,问题是完全为独造,还是对作品进行部分改编、完善或是模写?手抄本的流传史是否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共同创造史?其中主题或话题较为集中地出现,固然反映了较后或更高端的发展阶段,但那中间是否包含着重要的汉代成分呢,即使它的历史不会像后世描绘的那样成熟高端,但基本形势或许是存在的。
联系曹氏父子全面网罗音乐人才和整日倡优在侧的沉浸,可知演唱场合的文学因素是如何繁复地呈现于三曹诸子之前,诸子归曹后三曹诸子开始一致地创作五言且基本都与音乐场合相关的现象,提示我们想起五言与音乐的特殊关系。在此挚虞的一段话不能不引起重视,其《文章流别论》云:
古诗率以四言为体,而时有一句二句杂在四言之间,后世演之,遂以为篇。古诗之三言者,“振振鹭,鹭于飞”之属是也,汉郊庙歌多用之; 五言者,“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之属是也,于俳谐倡乐多用之;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之属是也,乐府亦用之;七言者,“交交黄鸟止于桑”之属是也,于俳谐倡乐亦多用之……
可知五言与“俳谐倡乐”的特定关系。遗憾的是挚虞没有提及“何时”俳谐倡乐多用五言,这中间有多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是曹魏时“俳谐倡乐多用五言”,这一现象只从曹魏时候开始;另一种可能是挚虞指的是一个一贯的传统,至少延及到曹魏之前的汉代。从上下文的逻辑来看,专指曹魏时期状况的可能性远小于其为从汉延续而来的一贯传统的可能性。我们再来看这一材料的另一个版本,《太平御览》卷五百八十六为“五言者,……乐府亦用之”,无论这里的“乐府”是一个音乐机构还是一种诗体,它指向汉代的可能性都要更明确些。从现在的可见材料看,五言诗在曹魏这里大兴,借鉴比独造说似乎更为可能些。这能提供曹魏五言诗的借鉴背景,解决曹魏五言诗高水准集团性突现所引起的质疑。当诗主要为演唱演出所需之故事脚本,那么诗叙述故事的特点及主题、话题和若干片段乃至套语在不同文本中出现交互,应是一种习见现象。五言诗的这一特点,在精英文人介入的初期,尚以一种“传统”的面目在诗里得到反映,但这预示着“诗”的功能已发生了变化,由演出的脚本性质向文人创作和阅读的文本样态转化。五言诗从曹魏这里转关,是否就包含了前后状态的转变?早期五言的演出痕迹,真的就是曹魏文人肇始的?同样令人怀疑。
但无论怎样,题目中的“两汉诗”都要打上引号了,因为看了木斋和宇文所安的相关研究之后,我已不大敢确定,传统以来一直归属汉代并以汉代为背景来研究和教授的“汉代诗歌”,是不是还能一如既往理所当然地列于汉代文学的版图。已积久成习的传统被解构掉,不安和抵触几乎是本能的,而理性地对待他们的质疑和论证,你已不得不承认,眼前的汉代文学史诗歌框架已变得有些模糊,至少不再显得那么顺理成章不可更移。
此时想到的,不是部分“汉诗”在以后的教学和研究中如何对待的问题,而是既有的文学史思考和做派,是否还存在着类似的问题。
[1]木斋.《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反思[J]. 社会科学研究,2010(2).
[2]木斋.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3]宇文所安.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M].三联书店,2012.
[4]傅璇琮.《古诗十九首》研究的首次系统梳理和突破——评木斋的汉魏五言诗研究[J].山西大学学报,2009(2).
[5]挚虞.挚太常集[M]. (明)张溥辑. 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第二册)[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