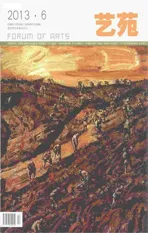《剧评家》:18世纪爱尔兰剧场穿越之旅
2013-11-13文‖冯伟
文‖冯 伟

如何了解18世纪爱尔兰戏剧行业的人情世态?读历史书。不,最好的方法莫过于去当时的戏剧圈里体验。穿越?对了一半,穿越至关于戏剧的戏中。2013年都柏林戏剧节上演了本国剧作家理查德·谢礼丹(Richard Sheridan,1751-1816)的《剧评家》(The Critic,1779),巧妙地将环境剧场(environmental theatre)和步行剧场(promenadet heatre)融为一体,让观众走进戏剧史,亲身体验。理查德·谢克纳最早在1968年提出“环境剧场”这一概念,意指将观众容纳到演出空间的表演方式,如此一来,表演环境和观众的切换都会给每一次的演出带来新的变化,从而增加演出的同时性和代入感。而中途剧场更换,观众跟着演员跑到另一个剧场,又显然是步行剧场。Promenade的意思是“散步”,而这个术语的内涵,便是观众一直在随着演出而流动。虽说此剧并未时时刻刻与观众发生互动,但观众的身份,却从头到尾都是见证者。
演出地点是都柏林市中心坦普尔酒吧区(Temple Bar,又译圣殿酒吧区)附近的文化之屋(Culture Box)和方舟剧院(The Ark)。坦普尔酒吧区历史悠久,位于都柏林丽妃河南岸,沿河往西去,便是乔伊斯《都柏林人》的主要场景。由于该区域是娱乐和餐饮中心,而尚存的建筑本身就是历史遗迹,也就终年游客不绝。对于嗜酒如命的爱尔兰人,与朋友聚会的最佳场所莫过于酒吧。每到周末,这里就会变得熙熙攘攘,而与之对应的是——街头老歌手的蓝调、年轻人的说唱、风笛和手风琴演奏、摇滚乐队,当然,还有每一家酒吧里的各种现场音乐,以及各种小剧场的活动。所以,历史和表演是该区域的关键词。而将此剧置于这样的环境,显然是导演有意为之。
原剧背景设在英国,但该剧导演将其挪到了谢礼丹的故乡都柏林。因为该戏的场地分别在客厅和剧院,故演出地点也在中途改变。文化之屋其实就是一个起居室大小的展厅,第一场荡格先生(Mr.Dangle)之家便设在此处。一进剧场,便看见放在屋正中的18世纪欧式圆桌和椅子,一位奥斯丁小说里走出来的妇人坐在桌旁,翻着一份报纸,并不时抬头打量入场的观众。墙角坐着荡格先生,正在温习该剧剧本。屋子四周靠墙放着两三排椅子,观众沿墙而坐,仿佛是等待主人开口的客人。所以,这是要观众从360度全方位身临其境。演出开始,一位叙事者从观众席中走出,讲述谢礼丹写作的时代背景,比如,坦普尔酒吧区是当时都柏林的戏剧中心。他告诉观众,这个剧的内容就是当时戏剧界的各种乱象。彼时的谢礼丹已是伦敦的皇家特鲁里街剧院(Theatre Royal,Dr ury Lane)经理,与该行业形形色色人群的来往自然也令其满腔怨愤——否则为何需要写一出讽刺喜剧来排遣?在本剧中,他调侃了百无一用却还颇为自矜的批评家,自命不凡却不停落入窠臼的剧作家,以及同行之间的抄袭现象。当然,按照爱尔兰所有剧院的惯例,叙事者也不忘提醒观众关闭手机,而这时,荡格太太举起了餐刀,目光巡视全屋,众人会心一笑。——但是,这到底是表演还是现实?演出过程中,叙事者不时的插话让观众明确了自己的身份:保持一定距离的参与者。换言之,他好比时空旅行的导游,带领游客返回古代,同时不忘在关键时刻补充一点背景知识。如果没有背景知识,其具体的讽刺内涵就难以捕捉;而如果不推倒第四堵墙,喜剧何以成为喜剧?观看喜剧最好的方式并非正襟危坐,而是进入越界的欢乐情境,让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去享受越界的快感。
演出以夫妻斗嘴开场,主题自然是争论剧评家究竟有没有存在的必要。老两口相互抬杠,却又一本正经,不由让人想起《傲慢与偏见》开场中聒噪的本内特太太和冷淡的本内特先生,只不过在本剧中,冷漠的是太太,聒噪的是先生。荡格先生会拿着桌上的报纸,念一两句剧评,可是他手上拿的明明是今天的《爱尔兰时报》,时间的幻觉也被打破了。屋里随后来了两位客人,一位目空一切的剧评家,奚睨尔(Mr.Sneer)先生,一位热衷于抄袭别人的剧作家,胡来疯·剽狼藉(Sir Fretful Plagiary)爵士。谢礼丹的命名中已经暗含了二位的性格:一位自控而尖刻,一位暴躁而蠢笨。室内风俗喜剧的氛围不难想象:几位戴着假发,穿着当时流行于上流社会的男式裙裤、吊带袜和高跟鞋的男性,说起话来用词考究、装腔作势、含沙射影,不时夹杂王尔德和萧伯纳式的爱尔兰幽默,配以奥斯丁小说人物的神经质色彩,最后闹得洋相不断——难道这不很具时代风貌?剽狼藉先生代表当时抄遍天下书且抄袭品位极差的平庸剧作家,奚睨尔则是拐弯抹角、故作矜持其实却尖酸刻薄的剧评家。油滑的荡格先生自然是晃荡于二者之间,尽量谁也不得罪。后来,曾以拍马屁为业的主角捧夫(Mr. Puff)先生登场。这是一位自恋而躁动的剧作家,明明浑身散发着丑角的喜剧劲,却非要去写悲剧——毕竟,喜剧太低级太廉价了,只有悲剧才能彰显人的崇高和伟大,尤其是其创作者的崇高和伟大。为了和观众打成一片,这位让人联想到哈巴狗的捧夫先生在屋内夸夸其谈,搔首弄姿,四处晃荡,并不停地抚摸四周女观众的金发,以及男观众的秃头。为了解除他们的尴尬,所有观众都会哈哈大笑。当然,经理偶尔也会与之互动。观众没有直接参与,但却偷窥了当时剧评家和剧作家们不堪的一面。
第一幕结束前,捧夫先生邀请奚睨尔先生和荡格先生去剧院指导其剧作的彩排。可是哪里有剧院?这时屋里款款走进三位年轻女郎,说着盖尔语,请观众离席去另一个剧院。于是我们跟着人群走了,两分钟的路上还遇到三个抗议者,举着牌子喊叫,牌子上的口号内容分别代表不同年代的爱尔兰历史事件。有趣的是,这一幕在酒吧区的老屋和老街中显得尤其自然。要是放到充满现代气息的艾贝剧院(Abbey Theatre),或许更会让人哭笑不得。

走进方舟剧场,坐下一看,也是一个能容一二百人的半环形剧场——类似于古希腊剧场的室内缩小版,观众席上方是导演调度的空间,剧场中间坐着十几个身着演员训练紧身衣的学生——是都柏林这边戏剧系的学生。中间一位身着现代装的光头老师,正是之前那位叙事者。他手捧彼得·布鲁克的《空的空间》,跟学生讲席勒、布莱希特和布鲁克的戏剧理念。舞台右后方搁着大提琴、钢琴、吉他、竖琴和鼓,左后方是挂着演出服的衣架。一个实时拍摄的镜头对准了舞台上方围观的三位先生,其影像又被同步在了舞台的幕布上,这样观众就能看见戏内戏外全部的演出。喜欢在台下说三道四的剧评家们被前置到了舞台上:恐怕这是他们始料未及的吧?是捧夫先生的悲剧好看呢,还是他们几个人好看?没错,这是戏中戏,而且戏中戏里面还有戏,导演真是要把幻觉和现实的吊诡关系玩个酣畅淋漓。而这种玩法,便是对书本教条中陌生化或第四堵墙的游戏,导演穿梭于其间,观众入戏出戏,却丝毫不影响看戏的兴致。而这种效果的实现,也有赖于现代舞台媒体技术的加入。
《西班牙舰队》彩排开始,三位剧中人在舞台之外观看,因此这部分演出主体是这些学生——学生的身份让人联想到演员的业余,不过除了业余演员蹩脚的演技,还能有什么配得上陈腐的剧情?捧夫先生的悲剧自然杂糅了悲剧这一题材的所有陈词滥调:雄壮的音乐、诗体的语言、一见钟情、相思、骑士、拯救、瘟疫、决斗、吻别、誓言,不一而足。因为他反复强调:这些都是成为悲剧的必要条件!两位见多识广的剧评家连连点头附和。排练期间,捧夫先生不停地向两位剧评家解释每一场的“良苦用心”以及“创作理念”,而作为剧评家的荡格先生和奚睨尔先生也会不断地吹毛求疵,毕竟这是他们的专职:这一段不是出自《奥赛罗》嘛?怎么到你这里了?或者,这些人不是应该睡着了么,怎么又跑出来了?这好像不合逻辑。不拘小节的捧夫先生只得耐心解释,但他越解释,其才能的不堪、创意的陈腐、构思的粗陋越是一露无遗,而相对应的是,剧评家自以为是的优越感也越发荒诞不经。通过目睹戏剧诞生过程,观众明白了陈腐而荒谬的观念和烂戏的亲缘关系,同时,也能围观当时所谓的剧评家们到底有什么“本事”。这些煞有介事的切磋令观众忍俊不禁,但反讽的是,最具喜剧性的恰恰还是悲剧的排演。


为了表现业余水平,学生们带着不知由来的道具——举起破伞就是剑,裤腰塞上雨衣就成了翅膀。需要制造阴森气氛时,就有学生乱拨竖琴、吹哨笛、配合人声,效果一团糟,这就是恐怖效果?作为学员,他们自然而然理所应当该以造作和夸张的方式去表演。因此,其道具的恶搞、剧情的陈腐和荒谬、表演的拙劣和僵硬,与投影中三位莅临指导的专家的一本正经构成强烈反差。悲剧也因此成了闹剧。后来捧夫先生被演员们打出去了,奚睨尔和荡格先生从上面走了下来,叹道:哎呀,真是一出精彩的喜剧!谢礼丹所嘲讽的正是当时戏剧界的种种怪象:剧评家的自作聪明、剧作家的随波逐流和无耻抄袭。随后,荡格先生拾起地上的《空的空间》,念了开头,然后二人会心地相视一笑:什么狗屁玩意!历史和现实又被混在一起开玩笑,而这背后是对两个时代剧评家的辛辣嘲讽。如果二位先生走进后现代剧场,肯定会骂道什么乱七八糟,而如果布鲁克去了18世纪,又会嘲笑他们观念的陈旧。二者孰是孰非?
演员上台谢幕时,作为背景的幕布起了,整面后墙被打开,室外的冷风吹了进来,外面的椅子上,坐着一个人,拉着大提琴。演员朝着墙外的“观众”谢幕,然后墙又合上。原来方舟剧院的观众席室内室外均可用。伴随演出空间延伸的也是主题的深化。该剧最大的特点就是有意将不同的时间维度置于同样的空间维度中,这种叠加也让本剧沾上了批判色彩:剧评家嘲笑同时代的剧作家,也嘲笑后来的剧评家,而如今的观众又按照当今的戏剧美学理论,嘲笑当时的剧评家及剧作家,到底谁在戏外谁在戏中,谁在观看谁在被观看?或者,作为评价依据的,是受制于历史的狭隘视界,还是撇开偏见之后看见的戏剧本体?答案恐怕是后者。而最后舞台打开其真正的幕布,恐怕是在提醒观众:你坐在舞台上看戏,看戏的人在舞台下看你。你的客观发现和主观体验,你的真实和幻觉,可能都不是绝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