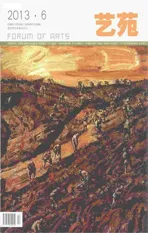具象与变形——谈生活动作与舞蹈动作的辩证关系
2013-11-13陈玲玲
文‖陈玲玲

《踏歌》北京舞蹈学院演出
若论生活动作与舞蹈动作的辩证关系,音乐是其中必须触及的一个关键因素。因为舞蹈是由一连串有节律的肢体动作所组成的,这个节律就来自音乐的节奏与旋律。在舞蹈艺术中音乐与肢体动作是水乳交融的,音乐起着贯穿的作用,它的节奏与旋律决定着肢体动作的变化起伏、舒缓快慢,将无序的肢体动作组合成有机的一个整体运动过程,音乐就像丝线,肢体动作就像散置的珍珠,丝线将珍珠贯穿起来,成了一件赏心悦目的艺术品。但肢体动作又不是被动的,它在随着音乐的节律不断运动的过程中又常常表现出有独立价值的艺术个性,它是演绎音乐精神的外在形式,同时自身又能动地参与并丰富着音乐精神内涵的阐释。
由此可见,音乐与肢体动作的和谐展示是舞蹈成为一门艺术的本质要素,更是舞蹈动作区别于生活动作的重要方面。但凡动作,都有肢体语汇的表现,但是动物原始的本能的肢体动作,却很少能称得上是舞蹈动作的。猿猴的手舞足蹈,烈马的奔驰,金蛇的狂舞,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舞蹈,因为其间缺乏自觉的音乐节律,肢体动作有规律的运动只是一种生存的本能反映,不是在阐释有丰富意蕴的音乐精神。真正掌握了肢体动作语汇与音乐精神间的微妙关系,并将其提升到舞蹈艺术层面的只有人,而不是别的动物。
一、舞蹈动作脱胎于生活动作
任何一种艺术都是源于生活,却又高于生活,舞蹈也不例外。原始的舞蹈动作与生活动作有着难以分离的密切关系,原始的舞蹈动作几乎都是直接脱胎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生产劳动中的动作。人们在生活和生产劳动中抑或有喜怒哀乐,难免拍手顿足,情感溢于外表,但此时也只是作为表情达意的一种手段,是语言交流的补充和具象化;人们对生活有所感悟,要抒发胸臆,语言的表达不能尽其意,不觉“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这里有了舞蹈的原素——有意味的肢体动作,但还构不成舞蹈,因为缺乏内在的音乐节律,动作并未依着节律而运行。最早为肢体动作与音乐节律提供了沟通结合的平台的是原始的祭祀活动和庆祝活动。在这些活动中,人们徒手或借助道具模仿日常的生活和生产劳动,以肢体的语言总结回顾生产或狩猎的收获,以自己的记忆用肢体语汇重温生产或狩猎的过程。于是原始的舞蹈就生产了,肢体动作上升为舞蹈语汇。此时的肢体动作多是对生活和生产劳动动作的模仿,有时甚至可以称作对生产(或狩猎)过程的重演,但是它却已经是舞蹈了。因为已经有了音乐原素的介入,并与那些模仿性的动作糅合在一起,肢体动作是按音乐的节律来运动的。一般情况下祭祀的场合都有音乐作为引导,可以是丝竹,也可以是打击乐,哪怕粗粝原始,节奏旋律仍在。其实,即使没有音响式的音乐存在,那些原始的舞蹈也仍然按照既定的节律来运行,音乐可以是有声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声无形的,音乐在舞者的心中。内心按着某种音乐节律在念想,手足肢体便有了有规律的运动,舞蹈便也随之产生,更何况口中的号子,击节的节奏,都可以外化音乐的节律。虽然原始舞蹈动作是模仿生活动作,但它不是当场的模拟,而是事后的回顾。这就意味着,这些模仿的动作都已经过了心灵的加工,已经或多或少地被提纯升华了。也正因为此,它可以不追求与生活动作的酷似,而更多地追求与内在音乐节律的合拍。于是生活的意蕴就有可能被演绎,人们的情感就有可能通过肢体的语汇被抒发。在这一过程中也就产生了原始舞蹈的艺术氛围,产生了自觉或不自觉地追求艺术欣赏的要求。在中国古代,诗、乐、舞是三位一体的,因为它们有着共同的内核,那就是音乐的精神。诗、舞的本质就是音乐,有韵律的诗,有节奏变化的诗才有可能是好诗;没有韵律的肢体动作,只能是杂乱的指手划脚、搔首弄姿,也就没有舞蹈可言。
二、舞蹈动作是对生活动作的升华与变形
原始舞蹈只是舞蹈的初级阶段,那些粗粝的动作,因为未经锤炼雕琢,显得简单而率意,与生活动作过于相似的肢体动作还不能给人充分的审美愉悦。人类在不断进步的过程中,也不断地将舞蹈艺术一步一步地提升、发展。人们已经越来越谙熟生活动作与舞蹈动作之间的关系,并在具体实践中自如地应用。将生活的动作艺术性地化为舞蹈的动作,实际上需要创作者具备审美的眼光。舞蹈动作当然来源于生活动作,是对生活动作的艺术性模仿,但不是所有生活动作都可以随意地化为舞蹈动作的,必须经过艺术家心灵的筛选、过滤、加工,并找到动作的韵律要素和作为表达某种情感的可能性。就单个动作而言,生活中的一举手一投足,不可能是刻意去做的,它仅是心情的外化,或者劳作的需要,目的仅是表达一种心境,也可能是劳作中的一个必须动作。这样的举手投足不关乎审美,只关乎实用。而艺术家在设计舞蹈动作时,都要依据所要表现的情感意蕴来选择生活中的某一举手、某一投足来加以模仿并加以提炼。所以艺术家在选择动作时是将目的指向美的,是寻求能够表达艺术境界的动作。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则是寻找出动作内部的韵律感,只有具备韵律感的动作才有可能成为舞蹈动作,才有可能成为一种表情达意的艺术语汇,才有可能成为阐释音乐精神的一个单元,并能动地参与音乐精神的创造。这其中的原因就是前面所说的舞蹈与音乐的密切关系。于是艺术家就要动用各种手法,强化动作的韵律感。夸张、变形、延伸、重复等等都是常用的艺术手法。例如,闽南民间的“拍胸舞”动作,源于旧时人们自我驱寒取暖的生活动作原型。生活中的拍胸、跺脚、击节,目的只是御寒,当然并不在乎美观与否,也没有特意地去设计这些动作的节奏和韵律。在生活动作升华为舞蹈动作的过程中,这些生活中的动作就被改造了,增加进了音乐的要素。拍胸、跺脚、击节的动作或加以伸延,或加以夸张,或加以变形,并将这些单个的动作加以组合,按一定节律做有规律的运动。这样,生活的动作就上升为舞蹈的动作了,动作的实用性隐退,动作的艺术性随之浮现,“拍胸舞”也随之产生了。就一个完整的表达创作者思想情感的舞蹈节目而言,情形就略为复杂一些。生活中很难找到一个有一定时间长度的动作段落恰好与创作者的情思相吻合,创作者必须构思一个情节的框架,并将音乐的节律一并融合在其中,而后寻找一个主体舞蹈动作,加以变化、拓展。这个主体舞蹈动作又必须具有可塑性,能衍化出许多不游离主干动作的支干动作,它们之间既神似又富于变化。这个主干动作仍然要从生活动作中去筛选,去提纯。这一原则在创作情绪舞蹈节目时尤其要加以重视。例如,在表现西藏翻身农奴得解放时,艺术家就选择了一个主干舞蹈动作:主人公一臂平伸,一掌附耳,双足交叉跳跃。这一动作,总是在奔跑中进行,双手可交替换位,总体形象不变,可以是呼喊的肢体表达,也可以是倾听的肢体表达。以这一主干动作为支点,又变幻出许多神似的意味相同的支干动作,很好地表现了农奴翻身得解放的难以言说的狂喜之情。
三、生活动作与舞蹈动作的互补现象
另有一种情形,那就是舞蹈动作又可以借鉴准舞蹈动作(如民俗活动中的肢体语汇)和其它艺术门类的肢体动作来丰富自己,创造新的意味。这其中便有了一个中介,是间接地艺术化地模拟生活动作。例如,高甲戏丑角舞蹈中的木偶丑动作。木偶丑的舞蹈动作来之于艺术化地模仿木偶(或提线或掌中)的表演动作,而木偶的动作又来之于模仿人生活中的动作。由于木偶表演的特殊性和局限性,木偶的动作呈现出了自己别具一格的风采,形成了一种“偶趣”。丑角舞蹈也由于寻求趣味的需要,在“偶趣”中找到了与自己表演风格的契合点,于是巧妙地通过人仿偶的过程将“偶趣”进行二次的创造,最终成为丑角的“人趣”。借鉴准舞蹈动作也是如此,都是一种二次的再加工。民俗活动中有一些约定俗成或简单模仿生活的动作,它不是生活动作的原样,但又不具备舞蹈动作的基本要素(如音乐要素等),是舞蹈动作的半成品。艺术家以自己的审美眼光将这些半成品再加工为成品,并为自己的舞蹈理念所用,这种情形也是常见的。
生活动作是舞蹈动作的原型,舞蹈动作是生活动作的升华;生活动作为舞蹈动作提供了意念的基础,舞蹈动作反过来表达更深刻的生活意蕴。其间的结合点是音乐的原素。这就是生活动作与舞蹈动作的辩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