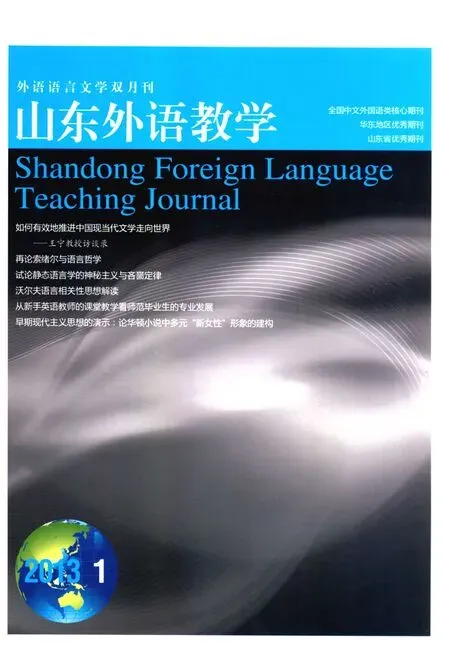试论静态语言学的神秘主义与吝啬定律
2013-10-24李葆嘉
李葆嘉
(南京师范大学语言科技研究所,南京 210023)
关于静态语言学的“神秘主义”与“吝啬定律/懒汉哲学”,2000年以来,除了在讲课时说过若干次,在阐述索绪尔(F.de.Saussure,1857-1913)学说时也多有触及,但在付梓时又都删除了,以免对“既有看法”刺激太大。
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约前530-470)说过:“一个人不能先后两次跳进同一条河流”。在语言的长河中,不存在所谓“静态”。当然不排除把“静态”看作一种虚拟态,一种暂时的定格。在《中国语言文化史》(李葆嘉,2003)的“作者手记”中,我曾写道:
浩瀚碧空,群星璀璨……
何曾想到:此时映入我们眼帘的闪闪星光,却是从宇宙的不同地方分别出发的光粒子,经过长短不同光年的长途跋涉而同时到达的壮丽一幕……一个历时的动态过程展示为一个共时的静态存现——我们面对的世界现存诸语言的状况如此,我们面对的诸方言的关系如此,我们面对的某一语种内部的若干要素同样如此。
作为人类的创造物和使用物,语言符号自然有集体无意识的一面,但一旦背离符号的认知本质,势必滑向神秘主义。语言研究自然需要做出必要限制,但一旦背离实体而标榜形式为唯一对象,势必陷入吝啬定律。语言符号首先基于语主(社会文化主体)的存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语言符号的本质属性首先是语义性,实体不存,形式安在?静态语言学的流弊,可能导致信奉者流于形式、困惑于形式。因此,有必要重新认知索绪尔的静态语言学理论。
1.0 索绪尔的叛逆个性与恃才自傲
2003年6月在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论坛上,我发过一个帖子:
不同的遗传和早期教养导致不同的兴趣,不同的兴趣和机遇导致不同的知识结构,不同的知识结构导致不同的语言观,不同的语言观导致不同的学术视野,不同的学术视野导致不同的研究理论、方法和目标,不同的研究理论、方法和目标导致不同的研究结果。学术研究的旨趣不在于寻求公认,而在于坚持独立思考。
要了解索绪尔的语言学思想,仅靠《普通语言学教程》文本显然不够,就是这一文本要认真看懂也并非轻而易举。我们需要《普通语言学教程》的语境,即索绪尔时代的学术思潮,索绪尔的学术经历、学术个性及其驱动力。
1.1 源自家族的科学思维与叛逆个性
索绪尔出生在日内瓦的一个法裔家庭,这个家族出过生物学家、博物学家、物理学家和地质学家。少年索绪尔便受到科学思想的熏陶,学会了法、德、英、拉丁和希腊语等。作为其祖父的挚友,语言古生物学家皮克戴(A.Pictet,1799-1875)无疑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15岁的索绪尔就写出了《论诸语言》(Essai Sur Les Langues),试图证明希腊语、拉丁语和德语的词,可以归结为有限的“C+V+C”词根。这表明少年索绪尔就具备了对语言现象的抽象思维能力,而这正植根于其家族的科学思维传统和皮克戴的影响。
1870年,索绪尔在马迪纳专科学校学习期间,发现了希腊语的响鼻音N在两个辅音之间可变成α。1873年,索绪尔进入日内瓦公立高中。在皮克戴的建议下自学梵语,阅读了葆朴(F.Bopp,1791-1867)的《梵语语法》和古尔替乌斯(G.Curtius,1820-1885)的《希腊语词源学基础》。1875年,18岁的索绪尔进入日内瓦大学,遵从家族传统主修化学和物理学,同时选修了语言学、哲学等课程。1876年5月,索绪尔加入巴黎语言学会。同年10月,转入莱比锡大学文学系。尽管一开始遵从家族传统,但最终还是转向了自己热衷的语言学领域。毛罗(T.de Mauro)(1983)认为,他对家庭传统的叛逆只涉及研究的内容,至于其科学思维方式,那是经由他父亲的直接教育继承下来的。这构成了索绪尔一生治学和著述的最典型特征。
据上述材料,已经可以看出:1.索绪尔具有学术研究的天赋和超人的思辨想象力(隐含着恃才自傲、冥思苦想的倾向);2.索绪尔对语言历史比较的兴趣受到皮克戴的影响(隐含着兴趣至上、难免钻牛角尖的倾向);3.索绪尔具有叛逆天性(隐含着偏执一端、离群索居的倾向)。
1.2 对新语法学派的出言不逊与叛逆心理
当时的莱比锡大学是新语法学派的中心。进校不久的索绪尔,就去拜访了胡布施曼(H.Hübschmann,1848-1908)教授。交谈中,胡布施曼提到布鲁格曼(Karl Brugman,1849-1919)在《论印度日尔曼始源语中的响鼻音》中,对希腊语的某些α由N演变而来的新发现。索绪尔说:“这一发现并没有特别价值,也算不上是新发现。”(转引自 戚雨村,1997:42)一个入学不久的新生,何以出言不逊?因为索绪尔自认为早在3年前已经发现了这一现象,只是没有成文。
索绪尔感到,他对原始印欧语元音系统的构想比布鲁格曼的假说毫不逊色,这可能就是促使他急于研究的直接动机。在《论印欧语的原始元音系统》(1878)中,他未提自己早前的发现,而是写上了“多亏布鲁格曼和奥斯托霍夫的研究成果,使我们知道了响音N和r”。文章发表以后,布鲁格曼写了一篇礼节性的短评。但是随后就有人,尤其是奥斯托霍夫(H.Osthoff,1847-1907)教授提出指责,这一篇没有任何教师指导完成的论文,显然抄袭了别人的成果。然而,引起新语法学派教授们反感的原因,并不在于某一具体发现,而在于作为学生的索绪尔的恃才自傲:
我不是在空想费解的理论问题,而是在寻求这一学科的真正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任何研究都是没有根据的、武断的、不确定的。(《论印欧语的原始元音系统·序》)(转引自卡勒,1989:11)
如此雄心勃勃的出言不逊,无疑触动了新语法学派头面人物的某根神经。
与之类似的论述,在《普通语言学教程》(索绪尔,1980)中同样可以看到。索绪尔认为:
(由于新语法学派的努力)人们已经不再把语言看做一种自我发展的有机体,而是语言集团集体精神的产物。……然而这一学派的贡献虽然很大,却不能说它对于全部问题都已阐述得很清楚。直到今天,普通语言学的基本问题还有待解决。(索绪尔,1980:25)①
来自新语法学派师辈的流言蜚语,无疑使21岁血气方刚的索绪尔感到苦恼和失望。20多年过去了,当斯特莱特贝格(W.Streiberg,1846-1925)来信中提及《论印欧系语言的原始元音系统》时,尽管事隔多年,索绪尔仍难释怀。为了澄清与新语法学派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洗刷“剽窃”之冤,还是写下了《关于青少年时期和求学年代的回忆》(约1903年,索绪尔时年46岁),但是当时没有寄出(索绪尔去世后,其夫人寄给斯特莱特贝格)。在该文中,尽管索绪尔一再表明他对“首创权”并不介意,但是,恰恰流露出索绪尔对不白之冤耿耿于怀。正是这一青年时代的事件,在索绪尔心灵深处形成了“首创权情结”(剽窃恐惧纠结)以及“憎恶新语法学派情结”。以至于他几十年不写或极少写,更谈不上发表任何重要论著,惟恐因为观点的“不谋而合”,成为师辈指控他的“新证据”。
新语法学派的保罗(H.Paul,1846-1921)把语言学的普通原理学科分为描写语法和历史语法,与之类似,索绪尔把普通语言学分为静态语言学和演化语言学。作为历史比较语言学家,保罗主张优先考虑历史研究,认为只有历时研究才能把握语言的生命及其变化,揭示语言活动的因果关系。如果仅仅停留在“状态(相当于静态)”描写上,那就称不上科学的研究。然而,作为新语法学派的叛逆,索绪尔则反其道而行之,标举静态研究应优先于历时研究,甚至把二者完全割裂开来。索绪尔在札记中写道:
语言学家要研究的是语言态(作者注:静态),他不需要理会导致目前语言态的历史事实,他应该把历时研究置于不顾。……历史的干预只能歪曲他的判断。(转引自 许国璋,1991:151)
甚至措辞激烈地呐喊:
我们必须做出反应,抵制老学派的邪道,而这种反应的恰当口号是:观察在今天的语言和日常的语言活动中所发生的情况……(同上:105)
一方面他力图冲破“老学派的邪道”,试图创立新的语言学,以证明自己的独创才能;另一方面,当他了解到博杜恩(J.N.Baudouin de Courtenay,1845-1929)的理论时,也许在赞赏之余不免顾影自怜。证明独创性的热望,燃起了他寻找突破口的熊熊之火,而永无休止的探索和接踵而来的困惑,又使他陷入了深深的焦虑。
长期离群索居的索绪尔,“他关起门来研究,只是间或向他的朋友传递片言只语;但在国际学术交流方面,几乎一言不发。”(毛罗,1983:11)他的学生和朋友都曾提到他在学术界长期沉默,提到他私生活上的某些特点,以及他与学生在最后几次见面和通信时所掩盖的忧愁,无一不是索绪尔孤独的表现。
1.3 对辉特尼的恃才自傲与任意性偏执化
美国语言学先驱辉特尼(W.D.Whitney,1827-1894)强调语言的社会因素,他认为:“我们把语言看成一种制度,正是许多这样类似的制度构成了一个社团的文化”;“动物的交流手段是本能的,而人的交际手段是完全约定的、惯例性的。”(转引自 刘润清,1995:80-81)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语言符号的“任意性-约定性”、“不变性-可变性”等。
索绪尔与年长30岁的辉特尼有过交往,甚至还见过一面。起初,索绪尔试图用辉特尼的“约定论”来解释语言符号,但是后来认为声音与意义结合之前都是不定形的。索绪尔认为:
为了使人感到语言是一种纯粹的制度,辉特尼曾很正确地强调符号具有任意性,从而把语言学置于它的真正轴线上。但是他没有贯彻到底,没有看到这种任意性才可以把语言同其他一切制度从根本上分开。(P113)
因此,索绪尔最终选取“任意性”作为语言符号的基本原则。索绪尔断言:
符号的任意性原则没有人反对,但是发现真理往往比为这真理派定一个适当的地位来得容易。(P103)
言下之意,虽然辉特尼发现了符号的任意性,但是给任意性“派定”适当地位的艰难任务却是由“我”来完成的。索绪尔的恃才自傲,由此略见一斑。
对自己的研究总是充满自信,是索绪尔的一贯风格。比如,他是这样评价自己的语音研究的:
说到我个人在语言学方面的进展,就其对语言学的重大部分而言,必定是令人震惊的,……不是这就类比的事实,而是指对语音的事实。(1960:25)(转引自屠友祥,2011:93)
实际上,符号任意性原则是把辉特尼的“约定性-任意性”的绝对化或者偏执化。不过,如果要建构静态语言学,首先就必须否决语言符号的可论证性,因为可论证性必然把人们引向符号实体或历史演化研究。
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多次出现了辉特尼的名字,然而始终没有出现博杜恩及其学生克鲁舍夫斯基(Н.В.Крущевский,1851-1887)的名字。索绪尔与博杜恩见过面,听过博杜恩的演讲,相互有书信往来;博杜恩与克鲁舍夫斯基给索绪尔邮寄过论著,在论著中引用过《论印欧语的原始元音系统》。尽管索绪尔在札记(1908)中也曾写下:“博杜恩和克鲁舍夫斯基比其他任何人更逼近于从理论上理解语言的意义,他们没有溢出纯粹语言学的范围”(转引自戚雨村,1997:23),但是《教程》中始终没有提及他们。因此只能推定,索绪尔在讲课中只字未提。早在索绪尔之前,博杜恩已经提出《教程》中的主要概念及基本理论。《教程》的某些段落,几乎一字不差地重复了博杜恩的表述。(转引自屠友祥,2011:3)有人推测,《教程》中采用“静态-动态”这对术语,是为了与博杜恩的“共时-历时”相区别,以避开“蹈袭”。善意的学生担心老师讲授的内容失传,而根据课堂笔记整理出版的《教程》,致使生前将讲义扔进字纸篓的索绪尔又陷入了“蹈袭门”。作为博杜恩的学生,苏俄语言学家谢尔巴(L.V.Sherba,1880-1944)在《博杜恩·德·库尔内特及其在语言科学中的重要地位》(1929)中写道:“1923年,当我们在列宁格勒收到索绪尔的《教程》原版时,使我们感到惊讶的是,索绪尔与我们所熟悉的原理在许多地方是相同的。”(转引自 戚雨村,1997:55)
2.0 符号任意性原则与神秘主义
1986年10月,我提交给“全国首届青年语法学学术研讨会”(华中师范大学主办)的论文是“论语言符号的可论证性”。这篇长文后来分为两篇发表:一篇题为“论索绪尔符号任意性原则的失误和复归”(1994)②;一篇题为“论语言符号的可论证性、论证模式及其价值”(1994)③。1998年12月,另一篇论文“论索绪尔静态语言学的三个直接来源”,提交给“方光焘百年诞辰纪念暨学术研讨会”(南京大学中文系主办)。
作为中国20世纪第一篇以专文形式批评索绪尔的文章,《论索绪尔符号任意性原则的失误和复归》认为:索绪尔对所指和能指不加历史性探讨,而以“任意性”一言蔽之,是任意性原则论证中的第一个失误。以不同语言系统之间能指和所指结合关系的差别,来证明同一语言系统之内能指和所指的结合关系是任意性,是任意性原则论证中的第二个失误。用共时的比例掩盖历史的溯源,在模仿的近似性和任意性之间划等号,把符号的历史演变性和不可论证性混为一谈,是任意性原则论证中的第三个失误。接下来,索绪尔把任意性一分为二:相对任意性和绝对任意性。把相对任意性定义为符号相对地可论证,是任意性原则向可论证性原则复归的第一步。把绝对任意性解释为“可论证性的转移或丧失”,是任意性原则向可论证性原则复归的第二步。把语言内部的演化运动阐述为不断地由论证性过渡到任意性和由任意性过渡到论证性,则是向可论证性原则的全面复归。由此可见,任意性原则的展开论述反证了语言符号的可论证性,符号任意性原则实际上是个虚构的原则。该文的发表,不期引发了20世纪90年代语言观的大讨论。
在以上几篇论文中,我都提到索绪尔语言研究观的神秘主义:
索绪尔说:“我们对符号的任意性有一种非常敏锐的感觉,认为事情可能是这样。”(索绪尔,1980:102)这种“敏锐”的“可能”不是神秘主义,又是什么呢?因此,索绪尔的符号任意性原则实际上是个虚构性原则,除了给人们造成语言符号的形成过程不可捉摸的错觉,只有舍弃对语言符号的历时系统性研究之外,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命题在实践上没有任何价值。
由于索绪尔立足任意性,因此他对整个语言系统的概貌只能作如下描述:整个语言系统都是以符号任意性的不合理原则为基础的。这个原则漫无限制地加以应用,结果将会弄得非常复杂;但是人们的心理给一大堆符号的某些部分带来一种秩序和规律性的原则,这就是相对论证性的作用。“语言机构”只是一个本来就很混乱的系统作局部的纠正的研究对象。(同上:184)果真如此,人们的心理只能给某些部分带来规律性的原则,而另一部分中的不合理原则是什么东西带来的呢?是谁在冥冥之中制造系统的混乱,而与人们的局部纠正抗衡呢?
索绪尔的描述会不会把人们导向神秘主义呢?可论证性抹去了命名方式或音义结合关系上的神秘主义色彩。
初民们在自己的历史活动和认知过程中,绝不会对自己的认知对象的命名漠不关心,他们具有认识的能动性,符号具有内在的系统性。命名就是认知和抽象,名称牢牢烙下了认知的痕迹。当代人给新事物的命名过程可以看作是初民命名的模拟实验,新词的产生总是不断地向任意性原则提出挑战。(李葆嘉,1994a;1994b)
索绪尔的神秘主义,与当时欧洲学界关注的“无意识”有关。辉特尼曾提出“语言系统是人类心智的无意识产物”。索绪尔则认为,语言符号价值(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的转移,纯粹出于无意识。在第一次讲授普通语言学时,索绪尔谈到语言创新的类比模式其心理过程是无意识的。索绪尔把这种无意识称为“某种神秘的本质”,它缘于对先前语言的继承、转移或暂时遗忘,以及内隐的语言机制。(转引自屠友祥,2011:93)
自1894年起,索绪尔的同事、心理学家弗洛诺乙(T.Flournoy,1854-1920)连续6 年对通灵者“丝迷黛”(H.Simth,1861-1929)的表演进行观察和破译,写成了《从印度到火星》(1900)一书。其中收录了多封索绪尔与弗洛诺乙讨论丝迷黛梦游状态下说写“梵文”的书信。这些讨论反映了索绪尔对语言符号的无意识运作或“某种神秘的本质”的看法。(屠友祥,2011)晚年索绪尔还对古印度的灵智学感兴趣,为欧特兰玛利德(P.Oltramarede)的《印度灵智学思想史:婆罗门灵智学》写过一篇书评(《日内瓦日报》1907年7月29日)。(转引自 屠友祥,2011:269)
晚年索绪尔还沉湎于研究拉丁诗人怎样在诗中隐藏专有名词的“词谜”之中,并且留下了大量的笔记。这种词谜把字母分散在文章里,有时按原词的字母顺序出现,有时不按原词的字母顺序出现。索绪尔曾说:“在最重要的问题上我仍然迷惑不解,也就是说,对词谜这种现象或假设,应该如何解释呢?”(卡勒,1989:146)词谜的成因可能是:因为有一个关键词在诗人的潜意识中徘徊,以语音联系而影响到对其他词语的选择。
语言是人类心智与认知对象活动的产物,人类心智自然有无意识的一面。语言学家能够直接研究的只能是有意识的心智,即表现为语言符号的一面。专注于无意识的一面而冥思苦想,势必把语言研究引向神秘主义或者玄学。实际上,许多人津津乐道的符号任意性原则,在索绪尔学说中只是一个对原初符号的假设,对语言研究毫无实际价值。屠友祥是这样评价的:
语言符号的任意性这一首要真理,只在符号创制出来,以之与概念相对应的一刹那,确是首要真理;但一旦成为社会事实,任意性就无足轻重了。因为它与符号学系统攸关的社会事实不相干,那社会事实的核心就是对社会事物的被动接受。可见索绪尔一方面奉任意性为第一原则,另一方面又以为它并不真正存在,只是一个想象而已,因为语言永远是一种既存、已在的状态,我们面对或者身处的是社会事实。因此,符号对其所表示的概念而言是任意的,对使用符号的语言社会而言却是强制的,两者都是由集体决定的,这充分说明语言符号的本质是社会性。(屠友祥,2011:251)
以上论述揭示了任意性“只是一个想象”、“语言符号的本质是社会性”,但是,正如辉特尼强调语言是一种社会制度、交流工具一样,因为特别关注语言符号的社会性,却遗忘了语言符号的认知性。语言符号的本质首先是认知行为及其成果,然后才是交际工具和语言系统。无论是原初语符,还是次生语符,都是人类认知的表现及产物。原初语符的这种认知痕迹,尽管可能磨灭殆尽,但是不等于在原初语符的产生过程中没有存在过。
与符号任意性原则相关的一个命题是“符号是空洞的”,即:
符号的本质就是不出现符号内在的固有价值,而是抽空它,人们以集体约定的方式拿空洞化了的符号任意地表示事物及其意义。(屠友祥,2011:254)
任何符号都是能指与所指结合的一体两面。没有内在固有价值的,根本就不是符号;既然要“抽空它”,符号就不可能是空洞的。这一命题的缺失在于,好像我们预先准备了一批空箱子,留着放东西。而这批空箱子,从何而来的呢?必然诉诸神秘主义。其实,从远祖那里,一开始制作出来的就是实箱子。
衡量一个观点是否有价值,其标准是看它推动还是限制(甚至阻碍)学术研究的进展。接受了任意性原则,也关上了语言符号可论证性的大门。接受了任意性原则,我们只能在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面前无所事事,束手就擒。因此,任意性原则不仅是一个“并不真正存在的想象”,而且是对语言符号拒绝深入研究的“懒汉哲学”。
3.0 静态语言学框架与吝啬定律
关于静态语言学,在《中国转型语法学》(李葆嘉,2008)的第三章中,我进行过如下论述。
虽然索绪尔提出“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P37)但是只有在区分语言和言语的前提下,才可能排除“乱七八糟的研究对象”(P29),以建构对象具有同质性的静态语言学。在这方面,索绪尔借用了瑞士正统经济学派的“一切研究价值的科学具有内在二重性”的观点。《教程》提出:“语言和言语互相依存,语言既是言语的工具,又是言语的产物,但是这一切并不妨碍它们是两种绝对不同的东西”。(P102)
依据“两种绝对不同”的偏执,索绪尔提出了四个PK:(1)语言的语言学PK言语的语言学;(2)内部语言学PK外部语言学;(3)静态语言学PK动态语言学;(4)语言形式PK语言实体。索绪尔的层层二项对立和仅选其一,可以图示如下:

根据层层分叉和选择,索绪尔的所谓“现代语言学”,其定义是:以语言符号形式为对象的、内部的、静态的、形式的语言学。用“现代语言学”作为名称含混不清,“结构主义”又不是索绪尔使用的。因此,合适术语应当是《教程》中的术语,比如:
1.与历时语言学相区别的“共时语言学”(P143)
2.与演化语言学相区别的“静态语言学”(P119)
很多人以为历时语言学中的任何一段都可视为“共时”,从而误解了“共时”就是“现时态”这一概念。作为科学思维的一种假设,“静态”代表着该理论的核心,而索绪尔本人也习惯于这么称呼。④
索绪尔的四层二项对立和逐层仅选其一,尽管早已被语言与言语的结合、内部与外部的结合、静态与动态的结合、形式与实体的结合所代替。关键在于,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需要相互观照、融会贯通,为什么索绪尔要偏执一端呢?也许,这还是对新语法学派的逆反所导致的结果。
静态语言学建构的层层分叉和仅选其一,将一个复杂系统硬要“纯洁”为一个单纯系统,将一个充满活力的语言生命硬要静态化为一个毫无生气的“僵尸”,将基于认知的语言机制硬要与世界知识切割开来,仿佛少研究一点好一点,更深层的是“绝对不同”的偏执观。后来者还搞出一个“本体语言学”的名目,其描写仅限于分布分析与层次分析(后来增加了转化分析),而将其他研究打入“非本体语言学”或“边缘语言学”的另册。毫无疑问,语言研究的视野应当是语言系统和言语行为的体用合一、内部结构与外部功能的耗散状态,以及虚拟静态与实际动态、语言形式和语言实体的融会贯通。⑤
马尔丁内(A.Martinet)曾经一针见血地揭出静态语言学的要害:“科学研究首先的要求,就是不能因为方法上的苛求而牺牲研究对象的完整性”,“功能语言学获得的任何进展,不论在过去还是将来一个时期内,都是逆着潮流的”。(冯志伟,1987:132)20世纪下半叶,以乔姆斯基革命为导火线,当代语言学理论才突破了《教程》的束缚,最终导致了对静态语言学的全面超越。
在《理论语言学:人文与科学的双重精神》(李葆嘉,2001)的第四章中,我写道:
实际上,静态语言学、任意性原则、强调形式而排斥意义,都隐含着语言研究中的“吝啬定律”或“懒汉哲学”,以及“语义恐惧”。所谓“懒汉哲学”就是避繁就简,多提理论框架而少做具体研究,少研究一点好一点。具体表现为——执意于“语言学家要研究的是语言态,他不需要理会导致目前语言态的历史事实,他应该把历时研究置于不顾”,舍弃具有静态与动态的贯通研究;所谓“语义恐惧”,就是拘泥于“语言是形式(forme)而不是实体(substance)”(P169),以“语言学家没有能力确定意义,只好求助于其他科学的学者或一般常识”(布龙菲尔德,1980:174)为借口,把语义研究推给其他学科。⑥
四层二项对立和逐层仅选其一,采取的是“排除”方法。毋庸置疑,在事实上的复杂性质与理论上的力求简约之间长期徘徊的索绪尔,其语言理论的研究目标是尽量简约。在一张破损的信纸上,索绪尔留下了这样的字句:
一种语言学理论越趋于精炼,要简明地表达出来也就越困难。这一问题使我感到痛苦倍增。我实际上是在表明,在这门独特的学科内,没有哪一个术语曾简明定义过。以至于一句话,我要反复修改五六次……
然而在第三次讲授普通语言学教程时,索绪尔踌躇满志地说,根据内部语言学的几条一般原理,成功地阐述了语言静态的规律。(转引自卡勒,1989:12-13)
此前,这种探索的思虑之苦,索绪尔在给梅耶(A.Meille,1866-1936)的信(1894年1月1日)中已经完全流露:
……可是我对这一切都厌倦了。在语言学问题上,即使仅仅写上十行言之成理的文句也感到困难。长期以来,我一直在思考:如何把语言现象加以逻辑分类,又如何把语言研究的各种观点加以分类。我越来越认识到,要阐明语言学家所研究的对象是什么,工作量太大了……当前流行的术语极不妥当,有必要加以改进。为了改进术语以及阐明语言的性质,我对语文学的兴趣越来越小,尽管我希望不去概括语言的本质,这会使我违心地著书立说。毫无兴趣和热忱去解释语言学术语,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转引自屠友祥,2011:139-140)
此时的索绪尔38岁,而正当盛年的他竟陷入了“失写”和“失思”。可以推定,索绪尔陷入了长期的焦虑与忧郁。后来,当雷德林格(Riedlinger)问他:为什么不把普通语言学课程讲授的内容写出来时,索绪尔微露笑容说:“我没有给自己规定要写出静态语言学”,并且反复重申这一工作的困难。(转引自 许国璋,1991:106)
英国逻辑学家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cam,1285-1349)提出的“奥卡姆剃刀”认为:如果有两个能得出同样结论的竞争性理论,那么简单的更好。奥地利哲学家马赫(E.Mach,1838-1916)提倡的是“吝啬定律”是“奥卡姆剃刀”的另一版本,即“科学家应该使用最简单的手段得到研究结论,并排除一切不能被认识到的事物”,然而由此可能得出“某物存在但无法观测=某物不存在”的谬论。这就提醒人们不能盲目使用“奥卡姆剃刀”。保留简单的理论并不意味:对于现象的最简解释往往比复杂解释更正确,因为现象并不可能那样简单。吝啬定律不能取代洞察力、逻辑和科学方法,永远也不能希望依靠“简单化”去创造一个理论。语言系统是一个历史性的复杂系统,可以进行不同程度的抽象。尽管抽象度越高可能概括力越强,但是控制能则越弱,因此我们需要的适度抽象。尽管结构主义促进了对语言系统的了解,特别是美国描写主义,揭示了语言结构的层次性,但结构主义无疑具有其先天缺陷。基于“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体”这种狭窄的语言观,结构的形式描写可能相对细致些,但是难免失之肤浅和单调。
4.0 系统整合:索绪尔对自己的定位
尽管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学术界通常称索绪尔为“现代语言学的开创者/奠基人”,⑦然而在《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问世后的3年内,巴黎语言学会约请了15位专家撰写书评,大多持审慎态度,有的甚至否定多于肯定。由于静态语言学片面突出语言的静态同质性,梅耶指出:“(《教程》)太强调语言的系统性,以致于忘却了语言中人的存在”(转引自戚雨村,1997:53),一语道破了静态语言学的要害。1931年,波利万诺夫(E.D.Poliyanov,1891-1938)在《论马克思主义语义学》(1931:3)认为:“许多人将《教程》视为一本启示录,但与博杜恩及其学派很早以前就取得的成果相比,它在普通语言学的提出并解决问题方面没有一点新东西。”(转引自 屠友祥,2011:1)1932年,特鲁别茨柯依(N.S.Trubetskoy,1890-1938)在给雅可布逊(R.Jakobson,1896-1982)的信中说到:“为了获得灵感,我重读了索绪尔,但这第二次阅读没有给我留下什么深刻印象。书中有价值之处相当少,大多是旧垃圾。而有价值之处则太抽象,没有细节阐释。”(转引自 屠友祥,2011:1)
倾向于把语言学作为哲学,还是倾向于把语言学作为科学,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倾向于把语言学作为哲学,则基于心灵主义,势必产生一系列的宏观构想以及思辨抽象,所提出的观点可能只言片语,既不加严密论证(由后人去揣度、去争论),也不一定付诸操作。而倾向于把语言学作为科学,则基于经验主义,注重语言事实的描写、分析和阐释,其理论无疑要具有操作性。根据这一分野,索绪尔本质上是一位基于心灵主义的语言哲学家。
对于索绪尔的学术定位,我曾经提出:
索绪尔曾对他的学生说:“语言是一个严密的系统,而语言理论也应是一个与语言一样严密的系统。难就难在这里,因为对语言提出这样或那样的见解并不稀奇,关键在于把各种观点整合成一个系统”(转引自 胡明扬,1999:79)正是在德克海姆的社会学理论、博杜恩的语言学理论和辉特尼的语言符号学说的基础之上,索绪尔基于各种观点的哲学整合而建构了静态语言学。确实,这一“如何整合”,不但需要哲人的智慧,而且不失理论创造的一种奥秘。(李葆嘉,2008:236)
给任意性“派定”一个绝对的位置,把言语的、外部的、动态的、实体的部分全部“排除”,把语言的、内部的、静态的、形式的部分凸显出来,这就“整合”成了索绪尔不留讲稿、而其学生依据课堂笔记整理出版的《教程》中的“静态语言学理论”。
“索绪尔的新发现者”忽视了一个事实: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索绪尔札记中是否存在肯定言语的语言学、外部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的论述,而在于不排除这些索绪尔批评的“乱七八糟的一堆离奇古怪、彼此毫无联系的东西”(P29-39),静态语言学也就无从建立。“索绪尔的重新发现”不过表明,批评、修正和企图突破静态语言学束缚的那些“异端邪说”,在“手稿索绪尔”中也同样存在。但是,在语言学界产生影响的是“《教程》索绪尔”,而与“手稿索绪尔”无涉。
人们通常认为研究某阶段的语言现象就是“共时语言学”,其实这种断代并非索绪尔的“静态”。索绪尔所要求的不仅是“现时态”,而且必须研究这一“状态”的基于无意识的形式,而并非描写实体、行为或功能。有趣的是,不仅索绪尔本人没有进行过某种语言的静态系统研究,而且听过他普通语言学课程的学生,似乎也无人做过此类研究。这使我们不得不认为,所谓“静态语言学”只是一个理论框架。“语言是形式”这一提法,在理论上,显示出集体无意识或“神秘主义”色彩,很容易把人们引向虚无缥缈;在实践上,不仅束缚了语言视野,甚至成为研究语言能力、行为和功能的某种阻力,涉嫌把复杂现象一味简单化的“吝啬定律/懒汉哲学”。与棋赛规则的人工性和封闭性相比,语言符号系统是个自然形成的耗散性复杂系统。索绪尔的“棋赛规则”类比(P46、128、155)将语言符号系统过于简单化,由此导致了理论的简约性与实际研究的复杂性之间的强烈反差。
总之,不必将索绪尔捧上“现代语言学的创始人/奠基者”的宝座,索绪尔是以系统整合为主的“静态语言学的倡导者”或精于思辨的“语言哲学家”。不可否认,正是这种超乎同时代语言学家的系统整合和哲学思辨,索绪尔方能自恃才高地坦言“对语言提出这样或那样的见解并不稀奇,关键在于把各种观点整合成一个系统”——这也就是索绪尔对自己的准确定位。
正常的学术生态应是多元状态,我们无权指责任何学术背景或理论方法下的语言研究。回到文章开头的发帖:“学术研究的旨趣不在于寻求公认,而在于坚持独立思考。”索绪尔的探索精神,应为后来者所景仰——唯此,才是对这位逝世100周年哲人的最好纪念。
注释:
①《普通语言学教程》,以下简称《教程》。本文所引《教程》页码均为中译本的页码。
②刊于《语言文字应用》1994年第3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1994年第11期转载)
③刊于《江苏教育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1994年第6期转载)
④一些学者却忽视了这一核心概念。《教程》中译本(高名凯1980、裴文2001)的“索引”中都没有“静态”、“静态语言学”这一术语。
⑤《中国转型语法学:基于欧美模板与汉语类型的沉思》一书印行时,此节删除。
⑥《理论语言学:人文与科学的双重精神》一书印行时,此节删除。
⑦ 罗宾斯(R.H.Robins)《语言学简史》(1967):“索绪尔对20世纪语言学的影响却是无与伦比的,可以说是他开创了20世纪的语言学。”莱昂斯(J.Lyons)《理论语言学导论》(1968):“如果有谁称得上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那么他就是伟大的瑞士学者索绪尔。”皆未深入研究过索绪尔。
[1]布龙菲尔德.语言论[M].袁家骅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2]冯志伟.现代语言学流派[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3]胡明扬.西方语言学名著选读[Z](第2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4]卡勒.索绪尔[M].张景智译,刘润清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5]李葆嘉.论索绪尔符号任意性原则的失误和复归[J].语言文字应用,1994a,(3):22-28.
[6]李葆嘉.论语言符号的可论证性、论证模式及其价值[J].江苏教育学院学报,1994b,(2):15-19.
[7]李葆嘉.理论语言学:人文与科学的双重精神[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8]李葆嘉.中国语言文化史[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
[9]李葆嘉.中国转型语法学:基于欧美模板与汉语类型的沉思[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10]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
[11]毛罗.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评注本序言[J].陈振尧译.国外语言学,1983,(4):8-12.
[12]戚雨村.现代语言学的特点和发展趋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13]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岑麒祥,叶蜚声校注.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14]屠友祥,索绪尔手稿初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15]许国璋.许国璋论语言[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