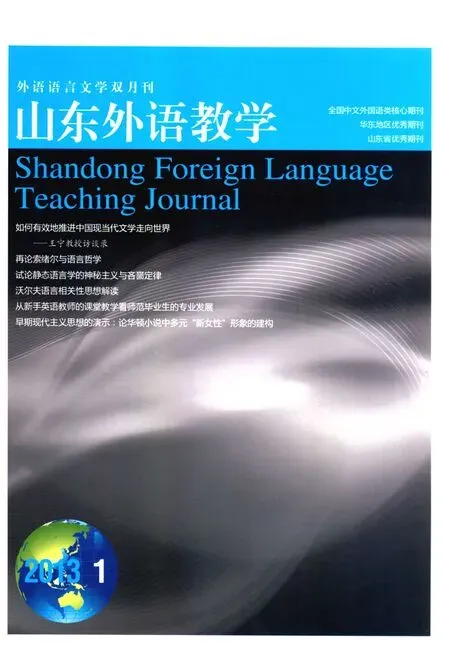典籍翻译研究的译者话语视角
——以辜鸿铭《中庸》英译文为例
2013-06-05丁大刚李照国
丁大刚,李照国
(上海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234)
典籍翻译研究的译者话语视角
——以辜鸿铭《中庸》英译文为例
丁大刚,李照国
(上海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234)
本文以傅柯与费尔克拉夫的话语理论和热内特的副文本概念为框架,建立了一个译者话语系统,并以辜鸿铭《中庸》英译文为例,阐释了译者话语的功能,以及如何通过译者话语解读翻译文本,旨在为国学典籍翻译研究提供一个理论框架。结果发现,译者话语不仅为典籍翻译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直接的线索,也使我们得以窥见译者在“中学西传”的过程中是如何理解和传播中国文化,从而形成真正的思想对话。
典籍翻译;译者话语;辜鸿铭;《中庸》英译
1.0 引言
潘文国教授(2007:1)在“新时期中国经籍英译事业的机遇和对策”一文中呼吁:“从事中译英研究的学者要在翻译实践中发展中译英的理论。”中国典籍的翻译与一般汉语文本的翻译在实践上存在很大不同,因其广涉中国传统文化的精气神韵,且与诸子之学密切相关,所以中国典籍翻译研究应在研究典籍翻译文本的基础上,总结译者的话语,并且用历史和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些话语,从而发展出中国典籍翻译的理论。
从译者话语的角度研究典籍翻译,就是将译者和译文置于翻译研究的中心,要求研究者完全浸入文本,深入文本的内在逻辑,让译者说话,让译者自我表述和再现,将译者话语置于译者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下,从而揭示译者的翻译思想,及其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文本的操纵和于翻译之外对翻译文本的阐释。
2.0 译者话语的理论框架
解构主义代表人物傅柯认为,“文本具有历史性,纯粹意义上的原文并不存在,我们对作品的理解是基于不断积累起来的注释,原文因而不断地被改写与重建,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理解”。(许钧、穆雷,2009:98)中国许多经籍文本尤其如此,由于中国古代文字表意的模糊性,古来经学自汉、唐迄于宋,再至元、明、清,注疏之家可谓汗牛充栋。从翻译的解释学研究视角来看,中国典籍的外译,可以说是一种解释的解释。另外,中国许多典籍的作者无从考证,还有一些典籍也非一时一人所作。所以,对于中国典籍的翻译文本来说,其作者相对隐形,而译者则相对显形,这与现代作品译者相对隐形有很大的不同,因而在研究中国典籍翻译时,对译者话语进行梳理和研究也就显得很有必要。从译者话语的角度研究国学典籍的翻译,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
2.1 话语理论与典籍翻译
傅柯(1994:30)认为“话语的本质永远是动态的、意有所图的”。这表明话语浸透着意识形态,即大家可能意识不到,但都接受的假设、价值观、信条等。译者话语也一定渗透有译者的意识形态。从话语角度研究译文,可以避免仅仅对译文文本进行纯学术的分析,责之于忠实、精确与否。
但傅柯的话语分析方法对真正的文本分析疏于关注。费尔克拉夫(2003)在傅柯话语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在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三个层面分析话语,尤其关注文本与文本之间、文本与话语之间的相互建构关系。
中国许多典籍都是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逐渐成书的,是“一个广大的作者群之话语‘稀释’的结果”。(傅柯,1994:32)译本从很大程度上来说,也是对原作的“稀释”。我们需要对庞杂的译者话语进行解读,理清译者不同话语之间,尤其是其他话语与译文之间的互文关系。在分析译者话语时,一方面注重文本的语言分析,一方面注重对文本生产过程的考察,才有可能对译文做出较为合理的解释。而寻求对翻译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本身也是翻译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
2.2 副文本与典籍翻译
若将译文看作是与原文具有同等地位的创作①,而非原作的附庸,那么我们就可借用热内特(Genette,1997)关于“副文本”的概念,把翻译文本看作是原创文本,而其他诸如译者序言、后记之类附属于翻译文本的文字、插图等看作是翻译的副文本。通过研究这些副文本,关注译者的身份、角色和译文的原创性,我们可以探究翻译文本的生产机制。
翻译研究除了研究译文本身之外,还需研究译者于译文之外论述翻译的元话语。于此二者之间,还有第三类资料需要研究,那就是“副文本”:前言、后记、标题、献词、插图等协调文本与读者之间种种关系,以及为“展现”作品而服务的材料。(Genette,1997:1)对这些材料的研究,可以揭示隐含于译文之中或于译文所不可见的翻译现象。因为,副文本有可能与主文本进入一种对话关系,影响主文本的接受。(Tahir-Gürçaˇglar,2002:46)而且在有些情形下,副文本在文本产生之前就已形成,不仅影响文本的接受,而且也影响到文本的翻译。
大多数典籍译本都有丰富的副文本,例如理雅各翻译的《中国经典》第一卷(Legge,1861),从扉页算起,共有526页,其中译文页仅有246页,即使这246页的正文也不全是翻译,每页都有长于译文至少两倍的中文原文和英文注解。这样算来,其副文本所占比例则超过全卷的2/3。这些副文本是译者显形的表现,是记录译者翻译过程的重要材料,是研究其翻译选择、翻译策略等的重要文献。
3.0 译者话语系统与功能
译者话语是指译者在翻译文本内外,翻译行为发生之前、之时或之后,与目标语读者进行有意或无意沟通的具体言语行为。为了对国学典籍译者话语展开系统的分析考察,我们有必要建立一个典籍译者话语系统(见表1),并考察它对翻译文本的解释功能。
3.1 译者话语系统

表1 译者话语系统
在这一系统中,“直接翻译话语”指直接讨论翻译的话语,与翻译实践有直接的关联。另外一些话语虽然不直接谈论翻译,但与翻译的关系较为密切,我们称其为“间接翻译话语”。实际上,注释、献词、按语(或评注)等是译本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Derrida(1985:155)就视注释为“对一篇译文的再一次翻译”。注意,在此系统中,译文也被视作译者话语。
还有一些话语与翻译无直接关联,但可以反映译者对中国文化的观念或译者在“跨语际实践”(刘禾,2008)中所表现出来的意识形态,我们称其为“非翻译话语”,例如译者发表的与中国典籍翻译有关的作品、演讲、访谈、通信、日记等。
这些话语彼此之间的分界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从图中实线箭头指示可以看出,间接翻译话语中也可能隐含着对翻译的直接探讨,非翻译话语也可能投射译者的翻译思想。另外,直接翻译话语和非翻译话语共同指向间接翻译话语的虚线箭头表明,二者对间接翻译话语,尤其是译文的生产有影响,也说明了二者的阐释功能。只有本着互文的理念,对这些话语进行综合、系统的研究,才能对译者的翻译做出合理的解释,从而促进典籍翻译理论体系的构建。
那么,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分类呢?通过研究典籍译者的直接翻译话语,我们可以发现译者在表述他者或自我表述时所采取的策略,并对比其间接翻译话语,尤其是译文,分析其策略在翻译实践中的应用和体现,并且从中发现典籍译者观念上的贯通之处,例如译者对于中国典籍翻译困难的论述,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通过研究典籍译者的非翻译话语,分析译者对中国典籍的理解与阐释,挖掘译本生产背后的历史、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和它们在译文等间接翻译话语中的反映,为的是从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的层面合理解读翻译文本。
3.2 译者话语功能
译者的话语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关系的建立:译者话语是译者思维过程的外显。译者通过翻译话语,建立原作与译文之间的关系;通过非翻译话语,建立译文、读者与原作之间的关系,填补由于文化差异而在这三者之间衍生出来的一个“他世界”。(边芹,2011)(2)译者观的确立:译文的产生是超乎作者及原文之上众多文本和话语互相推衍连结的结果,即傅柯所说的“话语形构”,也是译者主体性发挥的结果。(3)阐释:典籍译者的话语是对之前话语(包括原文及其注疏、前人的翻译等)的一个回响,一项诠释。(4)政治:译者话语除了传递信息之外,往往还隐含有某种权力的施加,表露译者的社会身份、角色和政治态度。
通过对译者话语功能的研究,可以克服翻译研究者本族中心论的视野,而以一种真正的理解和同情的历史眼光和学术规范,寻求译文产生的社会和文化政治原因。
4.0 案例分析
译者话语如何实现以上功能?我们如何通过译者话语解读翻译文本?下面我们就以辜鸿铭的《中庸》英译文为例,从译者话语系统的视角来解读辜鸿铭的翻译思想及其译文,从而探讨这些译者话语功能的实现。
首先我们对辜鸿铭作为儒经译者的话语进行分类。辜鸿铭英译过的中国典籍有《论语》、《大学》和《中庸》。辜鸿铭的英文著述主要有《尊王篇》、《中国牛津运动故事》、《春秋大义》,以及一些在英文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其中有对儒经的引用和发挥,还有对中国古诗的翻译,如陈陶的《陇西行》和杜甫的《赠卫八处士》。辜鸿铭的中文著述主要有《张文襄幕府纪闻》和《读易草堂文集》。另外,辜鸿铭还翻译过科伯(William Cowper)的叙事长诗《痴汉骑马歌》。其翻译话语主要见于《论语》、《大学》和《中庸》英译文。非翻译话语则是其他著述。我们将从其翻译话语和非翻译话语中提及翻译的话语,分析其翻译思想。从非翻译话语中解读其作为译者之外的其他身份和角色,为其翻译文本中浸淫的意识形态找到事实依据。
4.1 译者话语与翻译思想
从译者话语分析译者的翻译思想,是指深入阅读译者的各类话语,从中挖掘译者的翻译选择、翻译标准、翻译目的、翻译策略等。
辜鸿铭的典籍翻译思想主要表现在其《论语》、《大学》、《中庸》英译文及其前言、评注、附录中。还有就是他的中英文著述中谈及翻译的话语。
辜鸿铭为什么选择向西方译介《论语》、《大学》和《中庸》。在他看来,《中庸》阐释了一种“公正恰当的普遍标准”,连同《大学》,可以被称为“儒教的教义问答手册”。它简单明了,同时又完整丰富地阐说了“道德责任感或道”;《论语》是“蕴含着孔子及其弟子一贯之道的言论集”,“在所有用中文写成的著作中,正是这本书给了中国人一般英国人可以理解的智识和道德的装备”。(转引自黄兴涛,1996:346)因此,辜鸿铭的儒经翻译,主要是对儒家思想的道德诠释,具有教化西方读者的功能。
辜鸿铭在其英译《中庸》“序”中提及其翻译标准是:“彻底掌握其中意义,不仅对等译出原作的文字,而且再现原作的文体风格。”(同上:509)可见,他追求译文的“文质彬彬”。
辜鸿铭翻译《中庸》的目的是:“帮助欧美人民,尤其是那些正在中国的欧美人更好地理解‘道德法则’,形成一种更明白更深刻的道德责任感,以便能使他们在对待中国和中国人时,抛弃那种欧洲‘枪炮’和‘暴力’文明的精神和态度,而代之以道。”(Ku,1906:xi-xii)由此可见,在中国内忧外患的那个时代,如其英文著述一样,辜鸿铭的儒经翻译也是对西方政治、文化双重殖民的一种反击。
辜鸿铭的翻译常常采用“归化”策略,主要体现在用西方哲学术语译儒学概念,以及援引西方哲学家和文学家之言来阐释儒家经典的内涵,为的是方便西方读者在自己的概念体系中理解儒学,更主要的是阐明儒学的普遍价值。他认为,西方学者要想理解中国民族的观念和概念,“首先要找到它们在欧语中的对应物。假如这些对应物不存在,便要分解它们,看看这些观念和概念可以归属于普遍人性的哪一面”。(转引自黄兴涛,1996:126)辜鸿铭对儒经概念的翻译,遵循的也是这样的一条原则。
辜鸿铭的这些翻译思想还可从其英汉翻译以及其他中英文著述中得以解读。他翻译的《痴汉骑马歌》,确如其封面标题所示,是一种“华英合璧”。施蛰存(1990:11-12)说其译文“颇有《陌上桑》的神情”。再如他翻译《意大利国贤妃传》,以古译古,颇有林纾之译风。辜鸿铭的这种“借以古衣冠加于无色民族之身”的归化译法,正是一种融合中外文化之精神的翻译(梁实秋,1927),是在寻求不同文化中的“普遍价值”。辜鸿铭的儒经翻译,也正是在去原作的神秘化和历史化的基础上,通过对语言的操控,给中国传统思想以现代诠释,使其成为丰富和改造当代世界的一种文化资源。
辜鸿铭的这些翻译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疑是非常正确的。这从他的英文著述及儒经翻译在西方的受欢迎程度即可看出。其《中庸》译本在英国于1908、1912、1920年三次重印,甚至于1938年林语堂出版《孔子的智慧》时,仍沿用了辜鸿铭的译文。可见其译文的接受度是很高的。
4.2 译者话语与译文解读
从译者话语的视角解读翻译文本,是指把翻译视作“话语事件”,对译者的翻译行为进行“知识考古”(傅柯,1994),即将译者的译文置于知识生产的主体性与历史性(从知识生产的方式,考虑译文所产生的历史条件和译者的处境)的关系中,运用描述法,阐释翻译文本的生产机制。
下面我们就以辜鸿铭对《中庸》标题及首章“教”字的翻译为例,从译者话语的角度来解读其译文。
4.2.1 《中庸》英译题解
辜鸿铭的《中庸》英译文1904年陆续刊载于《日本邮报》,题名为The Conduct of Life;1906年由上海文汇报社正式出版,标题改为The Universal Order or the Conduct of Life(普遍秩序或人生之道)。辜鸿铭这一很有创见的标题英译,充分反映了他对儒家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的深刻理解和体悟。标题中的The Conduct of Life应该是借自爱默生的同名书,conduct一词突出了辜鸿铭所要着重阐述的伦理道德问题。辜鸿铭在《中庸》译文中曾6次提到爱默生,4次直接引用。其中,辜鸿铭将“道”译为moral law,就出自爱默生阐释其宇宙观念的Nature一书,而且在《中庸》英译文第12章的评注中还引用了爱默生此书的一段话来阐释其对“诗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的翻译。另外,在《中庸》英译文第13章结尾,辜鸿铭引用爱默生The Conduct of Life一书中有关个人修养的一段文字,为《中庸》的“君子之道”作注。U-niversal Order体现了辜鸿铭的当代关怀,他希望通过翻译《中庸》这一具有普遍真理的儒家经典,阐释一种道德责任感,从而重新设计人类道德行为和社会秩序,正如其在译序所言:“在下面的翻译里,人们将看到对这种道德责任感的阐述和解释,它构成了中国文明设计下的人类行为和社会秩序的基础。”(转引自黄兴涛,1996:512)同时,这一标题的英译也是他对“中庸”之内涵的深刻挖掘,从《中庸》对“中之用”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将理想的圣贤中德植入具体的君王实践,并在努力保持世界秩序与和谐的进程中向外投射”。(浦安迪,2011:36)
辜鸿铭的《中庸》英译文于1912和1920年在伦敦被纳入《东方智慧丛书》重版时,将其题名改为The Conduct of Life or the Universal Order of Confucius(孔子的人生之道或普遍秩序)。将the conduct of life置前,表明辜鸿铭对于其道德内涵的强调。标题中加上Confucius一词,以及扉页上出现的A Translation of One of the Four Confucian Books,Hitherto Known as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the Doctrine of the Mean是理雅各1861年出版的《中庸》英译标题),是为了提高译本的知晓度和接受度。
4.2.2 “教”与religion
辜鸿铭在《中庸》英译文中把“修道之谓教”译为“The moral law when reduced to a system is what we call religion”(系统化的道德法则就是教)。他译“教”为religion,并非因其不懂“教”在此处之意。根据辜鸿铭于其他中英文著述之阐释,中国的“教”有教化、文明、礼仪、名教、礼教之义。
那么我们该如何解读辜鸿铭这一对译呢?首先,如果抛开原文,仅仅阅读译文,我们会发觉,这一翻译很符合译文语境,前后连贯统一。辜鸿铭《中庸》第一段的译文为The ordinance of God is what we call the law of our being(性).To fulfill the law of our being is what we call the moral law(道).The moral law when reduced to a system is what we call religion(教)。从这段英文时刻不离moral一词来看,辜鸿铭着重传达的是《中庸》的道德诉求。在语言形式上,他采取了“西中格义”的表达,以显示《中庸》内容的“贯穿统一”。林语堂说他的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翻译,古代经典的光透过一种深的了然的哲学的注入”,辜鸿铭扮演的是“东方观念与西方观念电镀匠”的角色。(转引自黄兴涛,1998:61)要说这样的翻译有问题,也只能说是译者“追求统一”之弊。
其次,我们若从译者的非翻译话语考察,如他在《春秋大义》序言所说:“欧洲宗教要人们‘做一个好人’;而中国的宗教则要人们‘做一个识礼的好人’;基督教叫人‘爱人’;而孔子则叫人‘爱之以礼’。这种义礼并重的宗教,我称之为良民宗教。”(转引自黄兴涛,1996:15)而在导论直接表明:“良民宗教就是中国文明中的道德力量。”(同上)并指出中国的“良民宗教”是可以帮助欧洲人维持社会秩序的东西。因此,辜氏或论或译“孝悌”之儒家伦理概念时,总是把“悌”译为good citizen(良民)。
综合以上分析来看,辜鸿铭所说religion并非欧人狭义的宗教,而是孔教中的一种广义的宗教,笼统地说就是一种文明概念和心态,具体说来就是“良民宗教”。这与他在《中庸》英译文的序言中把《中庸》和《大学》比附为“儒教的教义问答手册”和其翻译目的是一致的。
另外,辜鸿铭这一对译也是有其历史脉络可寻的。最早将“教”字对译为religion的是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在其翻译的《中国通俗文学选译》(1812)和编纂的《华英字典》(1815-1823)中,都将“教”与religion对译。其后,高大卫(David Collie)在翻译《中庸》(1828)时将“教”译为learning。理雅各在翻译《中庸》(1861)时将“教”译为instruction。从这一历史脉络来看,辜氏所译religion并无我们现代宗教之意。
根据我们对辜鸿铭英译儒经的语料统计,他在译文中共有9处使用了religion一词,所对应的汉语分别为:修道之谓教(religion)、素隐行怪(abstruse meaning in religion and philosophy)、五十而知天命(the truth in religion)、子罕言利与命与仁(religion)、赐不受命(religion)、人能弘道(religion)、礼乐征伐(religion)、文武之道(the principles of religion and morality)、不知命无以为君子(religion)。可见,辜鸿铭的儒经翻译是常常随文章脉络的需要而变换译法,“与时俱进”地阐释圣人之意。于其上下文看,辜鸿铭在这些地方用religion一词要阐释的仍然是“道德教化”之意。
通过对辜鸿铭作为儒经译者的话语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辜鸿铭的儒经翻译、英文著述等话语起到了一个文化调停的作用,促进了不同文化间的理解。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体现了辜鸿铭对中西文化中“共通价值”的探寻,是在寻求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沟通与对话的途径。
5.0 结语
翻译是译者的一种再表述(相对于作者的表述而言),其中渗透着译者的思想观念。因为译者在迻译的过程中,首先做的是“将原作化为我有”或“以意逆志”(傅雷,2010:157);当译文被生产出来供人阅读时,读者其实在不知不觉中已经置身于译者的再表述之中,而非作者的表述之中。因此,翻译研究的其中一个任务就是考察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行为,从而考察译文的生产机制,最终为说明和解释译者的翻译产品服务。
译者话语研究,认为翻译文本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物质形态,研究者应将其视作一种“历史事件”或“话语实践”,回归到翻译文本形成的那一历史现场,对其客观地进行阐释批评。译者话语,尤其是译者的翻译话语,是“对翻译的直觉判断,是翻译理论的基础”。(Chan,2004:4)它不仅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直接的线索,也使我们得以窥见译者究竟如何理解和接受中国文化,形成真正的思想对话。因此,对不同历史时期典籍译者的话语进行梳理,从话语的角度对其分析,是深化典籍翻译研究,构建典籍翻译理论的重要途径。
注释:
①这是一种“译文中心论”的观念,为许多翻译理论学者所接受,如有学者所提出的“作为重写之翻译”(translation as rewriting)或“作为新的书写之翻译”(translation as new writing)的概念。(Bassnett&Trivedi,1999:8)
[1]Bassnett,S.&H.Trivedi.Introduction:Of colonies,cannibals and vernaculars[A].In S.Bassnett&H.Trivedi(eds.).Post-Colonial Translation:Theory and Practice[C].London:Routledge,1999.1-18.
[2]Chan,L.T.H.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y[M].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2004.
[3]Derrida,J.The Ear of the Other:Otobiography,Transference,Translation[M].New York:Schocken Books Inc.,1985.
[4]Genette,G.Paratexts: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M].Trans.J.E.Lewi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5]Ku,H.M.The Universal Order,or Conduct of Life[M].Shanghai:The Shanghai Mercury,Ltd.,1906.
[6]Legge.J.The Chinese Classics(Volume I)[M].London:Trübner&Co.,1861.
[7]Tahir-Gürçaˇglar,S.What texts don’t tell:The uses of paratexts in translation research[A].In T.Hermans(ed.).Crosscultural Transgressions:Research Model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II:Historical and Ideological Issues[C].Manchester:St.Jerome Publishing,2002.44-60.
[8]边芹.卢瓦河以南,地中海以北[N].文汇报,2011-11-10.
[9]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M].殷晓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
[10]傅柯.知识的考掘[M].王德威翻译、导读.台北:麦田出版有限公司,1994.
[11]傅雷.傅雷谈艺录[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
[12]黄兴涛.辜鸿铭文集[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
[13]黄兴涛.旷世怪杰:名人笔下的辜鸿铭,辜鸿铭笔下的名人[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
[14]梁实秋.辜鸿铭先生轶事[N].时事新报,1927-7-12.
[15]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M].宋伟杰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16]潘文国.新时期中国经籍英译事业的机遇和对策[A].汪榕培,关兴华.典籍英译研究(第三辑)[C].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7.1-5.
[17]浦安迪.浦安迪自选集[M].刘倩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18]施蛰存.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M].上海:上海书店,1990.
[19]许钧,穆雷.翻译学概论[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
On the Transl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lass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or’s Discourse
DING Da-gang,LI Zhao-guo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34,China)
Based on Foucault’s and Fairclough’s theory of discourse and Genette’s concept of paratext,this article builds a system of translator’s discourse.On the basis of this framework,Ku Hungming’s translation of Zhong Yong is analyzed to illustrate the function of translator’s discourse and how to interpret the translation text through translator’s discourse.It is found that translator’s discourse not only provides valuable materials and direct clues for the study of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but lets the researcher perceive the translator’s efforts in the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in the West,and thus forming a true dialogue.
transl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lassics;translator’s discourse;Ku Hungming;translation of Zhong Yong
H059
A
1002-2643(2013)01-0099-06
2012-06-10
本文为上海师范大学第六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项目编号:A-7031-12-001025)和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项目(项目编号:12YS053)的阶段性成果。
丁大刚(1976-),男,河南宜阳人,硕士,上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翻译学。李照国(1961-),男,陕西三原人,博士,上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医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