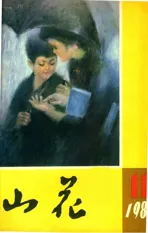春风一度
2013-10-20郝炜华
郝炜华↓
1
遇到王小宇之前,我正为反复不断的咽喉炎烦恼,它的反复发作使我不得不怀疑半年前的一次艳遇使我患了一种难以示人的隐疾。半年前我到一个海边小镇度假,在那里遇到一名白脸长发的男人,与他海滩春风一度,一月后患上了咽喉炎。
现在想来,我在某个清晨突发奇想到海边度假真是一个错误,但是后悔一点用都没有,咽喉炎并没有因为我的后悔而减轻,在吃了无数中成药,做了氮液冷冻,仍然不见效的情况下,我听从一位朋友的劝说,又一次来到那个海边小镇,朋友说:“洁净的空气对咽喉炎有治疗效果。”也许吧。我居住的这个城市空气实在糟糕,我工作的那个地方,空气更是糟得不像话,每天都有各种不同的气味交替着侵扰我的鼻腔,大部分时间我都紧闭办公室的门,紧闭办公室的窗,像个在糟糕空气中的偷生者。
小镇与上次来时没有任何不同,除了不见那个白脸长发的男人。贯穿东西南北的两条宽阔马路成十字形交叉在一起,其余全是碎石子铺就的小路,路两边是红顶白墙的平房或是楼房,楼房没有一栋超过三层。镇中只有一趟公交车,从一个很远的城市过来,转一圈,又去往那个很远的城市。
我在靠近海边的一户人家住下,不是城里人认为的渔家乐,只是一户普通人家,住着一位老母亲与一位在工厂上班的儿子,儿子就是文章开头提到的王小宇。上次来时,我住他家隔壁,另一边是一对和睦的老夫妻,院子里种满了鲜花,妻子每天早晨出门卖报纸,丈夫拿着喷壶浇花。这次来,老夫妻去了省城的儿子家,一把乌黑的大锁锁闭了院门,干枯的腾叶爬过墙头,透过门缝,看得到一地残花落叶,无由地叫人伤感与落寞。
王小宇的母亲站在院门口看太阳,她不像普通的老年妇女那样手里拿着一把扫帚或是正在做着的针钱活,她就是站在院门口,侧仰着头,盯着天上的太阳。海边的空气透明度高,阳光强烈得有些耀眼,王小宇母亲那样毫无忌惮地盯着太阳看,不由地叫人担心阳光会灼伤她的眼睛。
王小宇母亲似乎看出我的担心,放平脸,转头看我,说:“他们搬走了。”又说:“我认得你,你又来住,住我家吧。”
上一次,我在小镇住了半个月,王小宇的母亲认识我最正常不过,不正常的是我不认识她。想来,这是我的错误,我自认为是外地人,对小镇的人与事物视而不见,每天睡到上午九点,吃过早饭便拿着一块大毛巾来到海滩,海滩上搁着一把铁皮椅子,我坐在椅子上,腿上盖着大毛巾,旁边放着一张小桌,搁着一杯咖啡和一本书。咖啡是卡布奇诺,书每天都变,《帕斯卡尔的思想哲学》、远腾周作的《沉默》、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福克纳的《八月之光》,全是朋友介绍必须要读的经典。其实咖啡很少喝,书几乎不读,它们放在小桌上仿佛只为了证明它们的存在。我通常做的事情,就是坐在椅子上看海,其实海上除了浪花什么都没有,海天连成一处的地方是条灰白色的线。看着看着,我便会睡过去,睡着睡着又一个激凌醒过来,如果阳光不太强烈就闭了眼继续睡,如果阳光强烈,就收拾了东西回去。回去之后在院子里小坐,那个院子同样放着一张铁皮椅子,前面是张雕花的木桌,四周是蓬蓬勃勃的花草。咖啡换成了茶叶,铁观音、金骏眉,还有叫不出名目的野生茶。就着商店随便买回来的饼干,吃完了,回房间继续睡觉,一直睡到夜幕降临,然后踏着夜色在海滩闲走。
大约小镇上找不到比我再悠闲再能睡觉的人了。那对老夫妻经常趴在窗户上看我是睡着的,还是活着的,那位妻子甚至跑进房间,试探我的鼻息。我自然感觉到她的存在,睁开眼睛,笑了一下,吓得她差点摔倒。当然,我也不清楚自己为什么如此能睡觉,到了这个小镇,似乎除了睡觉就没有任何事情可做。
拖着行李箱走进王小宇家,是与邻家相同的院子,铺着红白相间的地砖,院角一个白底蓝花的瓷盆,种着一株蓬勃的植物。屋子是三居室,最小的一间让给我住,单人床,铺着湖蓝色的床单,当窗摆着一张写字台,上面放着一只鱼缸,游着十几尾红色的小鱼。
“这是唯一有写字台的屋子。”王小宇的母亲说:“知道你是个喜欢读书的人。”
这一次行李箱里依旧带着几本书,也许它们会像上次那样天天陪我去海边,却没被我读进一个字。
价格、住的时间几句话就商定好了,预支房费与餐费,还有一笔数目不大的押金。每日三餐由王小宇的母亲提供,如果不在家里吃饭,扣除一定的饭费。收拾完毕,我一个人来到海滩。王小宇的家到海滩仅五分钟的路程,出门向前,下一个大坡,再上一个小坡,就来到了海边。
意想不到的是那张铁皮椅子还在,只是长满了铁锈,似乎我走之后再没有人坐过。我用手摸了一下,铁锈立刻粘满整个手掌,这使我打消坐下来的念头。沿着海滩闲走,大海依旧跟从前一样,除了汹涌的浪花没有别的东西,远远的,海天连接的地方依旧是一条灰色的线。走到海滩尽头,是个小小的凹地,后面一块大礁石,可以挡风,也可以阻挡人的视线。我就是在这个地方与那个白脸长发的男人春风一度,他与我一样是个前来休闲的外地人。他将我按在凹地里,阳具像扫帚一样,在我身体里左右一扫,我的心连同每一片肌肉都哆嗦起来。我不是一个没有性经验的女人,知道这样的感受只有跟心爱的男人在一起,心灵与身体相互交融时才会产生。所以,那个白脸长发的男人引起我的好奇,我猜想他是不是我前世的情人或是我一直寻找的那个叫人刻骨铭心爱一次的男人。但是他什么都没跟我说,带给我一场无比伦比的性爱享受之后,转身离去。我至今记得他在海滩上大步行走的背影,长发飘在脑后,头顶是轮大得、明亮得想叫人流眼泪的月亮。
如果没有咽喉炎,这会是我终生都不后悔的一次艳遇。但是因为咽喉炎,似乎一切都变得不好了。
我站在凹地里看着面前的海,张大嘴,对着大海“啊、哦、咿、呀”地喊了无数声。带着腥味的海风灌进我的咽喉,咽喉炎似乎好了很多。
2

晚饭是羊肉炖花蛤、韭菜炒海肠子、清蒸海蛏子,典型的海边家常菜,主食是馒头。王小宇一边吃饭,一边笑眯眯地看我。他母亲用筷子敲他的头,说:“好好吃饭。”王小宇不听,依旧一边吃饭一边看我。
王小宇母亲用手指指脑袋,“前年得高血压,昏迷两个月,醒来,脑子就迟钝了。本来是个很聪明的人。现在笨得叫人讨厌。”
“手机号码。”王小宇打断他母亲的话,跟我说。
手机号码?我诧异,不知道他要我手机号码的原因,要知道我只是一个旅者,一个过客,并不想在这个小镇留下什么,也不想和小镇的人有任何牵扯。
“手机号码。”王小宇又说了一遍。
我说出手机号码,王小宇从口袋摸出手机,一个一个地按数字,赚了很大便宜一般咯咯地笑。
王小宇母亲叹气,说:“因为这病,媳妇跑了。单位也不想要他,是我求爷爷告诉奶奶,差点给人下跪,才留下他的。什么都不能做,怕出工伤事故,只安排打扫厕所。”
我看王小宇的手,担心手上沾了屎。
王小宇母亲扫了我一眼,说:“澡每天都洗,无论干不干活,都洗了澡回家。”
吃过饭,天就黑下来,将近初冬的季节,天黑得早。小镇家家房门紧闭,像所有海边居住的人一样,极少夜间外出活动,我出门,往海边走,感觉背后隐隐约约地跟着一个人,回头,却什么没有。到了海边,听得到海水拍打海滩的声音,却看不真切海水的模样。风一阵一阵地吹过来,那番透骨的寒冷,那番无边的空旷,令我浑身发起抖来。
远处响起“啊啊”的喊叫,我大吃一惊,没想到这夜晚的海边还有人像我这样没有目的地瞎走。奔过去,发现是王小宇在那大喊大叫。见到我,他没有流露出任何表情,仿佛我是只小动物或是我根本就不存在,他依旧张大嘴,对着海“啊、啊、啊”地大叫。我也张开嘴,风立刻灌进来,仿佛要通过口腔,充满我的全身,使我像个汽球一样鼓涨起来,然后飘到空中。然而我仍旧喊了出来,“啊、啊、啊”风并没有吞没我的声音,而是将它送到了很远的地方。王小宇转身向我,手拢到嘴上“啊、啊、啊”大喊,我也转身向他,手拢到嘴上“啊、啊、啊”大喊。喊着,喊着,我突然笑起来,王小宇也笑了起来。
夜黑得更加浓郁了,我,王小宇都成了黑的一部分,影影绰绰,看不真切对方。记忆中我从未经历这样的黑暗,也第一次在黑暗中没有感到害怕。我与王小宇坐在沙滩上,跟他讲我的一次爱情。
曾经爱的那个男人也居住在海边,可是显然他并不爱我。因为他很快拥另一个女人入怀,那是与他居住一个城市的海边女子。他们在餐桌边站着做爱,房子背后就是海,宽阔无边的,叫人想一头扎进去,再也不肯爬上来的海。那个男人不曾拥抱我,不曾亲吻我,不曾给我一点点许诺,甚至在我喜欢他的时候,我都不能确定他是否爱我。后来,我到海边城市找他,在城市走了整整一天,坐在海边的马路牙子上哭泣,夜晚看着巷子的报亭哭泣,海边的马路几乎没有一个行人,那个报亭亮着昏黄的灯光。而他,始终不肯见我。
“知道吗?那是我唯一的一次恋爱。知道吗?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不相信爱情。不再爱任何人。”
王小宇看着我,黑暗中,我看不清他的表情,也不知道他是否听得懂我的话。按照他母亲的说法,他是个脑子坏了的男人,大约理解不了,这平常女子痛彻心扉的爱情。
“手机号码。”王小宇突然问。
我愕然,“不是告诉你了吗?”
“手机号码。”他又说了一遍。
我说出自己的手机号码。王小宇从口袋摸出手机,一个一个按数字,像赚了一个大便宜。
回到家,王小宇母亲坐在客厅的椅子上,手里拿着一把胳膊长短,头上带着弯的棍子,兜头向王小宇打过来,王小宇脱下衣服,背对他母亲,叫那棍子噼哩啪啦地落到后背上。他母亲足足打了二十下,才住手,累得呼哧哧喘气。
王小宇站起身,衣服不穿,进屋,脱得只剩下短裤,来到院子,拧开水笼头,接下一盆凉水,哗地一声倒到自己身上。
“这不行,”我大喊,“会感冒的。”
“不要管他。”他母亲说道,“死了才好。”
3
早餐在一种压抑的气氛中进行,王小宇与他母亲都不说话。埋头喝一种里面放着花蛤的汤。汤的味道鲜美无比,我一口气喝了三碗。然后看着王小宇提着饭盒,推了自行车出门。
“傻呀。”他母亲一边洗碗一边说:“单位的班车就从门口走,他偏偏骑了自行车到另外一个站点坐车。那站点离这两里路。真的傻呀。”
我站在门边看着王小宇的母亲洗碗,一边看一边咽唾沫。咽喉炎似乎减轻了许多,来小镇的时候,唾沫都不敢咽,现在能够咽下唾沫,可是有些费劲,觉得咽喉中间卡着一件东西。我说:“不能这样说他,毕竟是你儿子,他也有自尊心……”
“但凡有点自尊心我也不这样说他。一开始我也是心疼他,娇着,惯着,可是,可是,没有人把他当人,我这当妈的,也就……”说到这里,似乎感觉失言,王小宇的母亲住了口。
我在屋里四处走动,奇怪这次到小镇来,一点没有睡懒觉,那些似乎驱之不去的睡眠一下子从我身体里跑了出去。为什么呢?因为咽喉炎,还是因为换了一户人家居住,这户人家有个在工厂上班的儿子,必须每日早起,吃了饭坐班车到一个很远的地方打扫厕所。
屋子打扫得极其洁净,看得出王小宇的母亲是个爱干净的女人,客厅、厨房、王小宇的房间、王小宇母亲的房间一一看过,我突然发现一个问题,这个家没有一点可以证明王小宇父亲存在的东西,衣服、照片或者是气息。他的不存在不是因为过早逝世,而是从来没在这个家出现过。这个发现令我感觉奇怪,转头看王小宇的母亲,她已经端了一盆东西去了院子。她不是一个很老的女人,五十多岁,头发不算白,身段也算苗条,是个保养得极好的女人。
我叫王小宇的母亲找出一把铁刷子,拿着它来到海边,那张铁皮椅子还放在沙滩上,我用铁刷子刷上面的铁锈,一直刷到手扶上去,摸不到铁锈了为止。然后我就坐在铁皮椅子上面,像上次来的时候,看着面前的海,海依然除了海浪没有别的东西,不,有了一点点不同,一个黑色的小点点在海面上浮动,近了,近了,竟然是条渔船。快到海滩时,船上下来一个男人,穿着到胸的皮裤,拖着船走了过来。
他冲我打招呼,说:“又来了?”
我诧异:“又?你认识我。”
“嗨,谈不上认识呢。不过,你从前在这住过一段日子的,总是坐在铁皮椅子上睡觉。”
“嗯,是这样的。”
“我以为你失恋了,失恋了的人才会天天坐着晒太阳,睡觉。我失恋的时候就天天坐着晒太阳,晒着晒着就睡了过去。心本来是冰凉的,晒着晒着就暖和过来了。等心全暖了,失恋的痛苦也就没有了。”
我笑起来,说:“我没有失恋呢。”
男人从水里出来,手里提着一只袋子,走过面前,递给我,是条活着的海鱼,他说:“嗯,女人怎么会不失恋呢?是女人都会失恋的。”说完,坐在我的身旁,两手扶在脸上,看面前的海。
这是奇怪的事情呀,两个全然陌生的人,不,他也许对我是认识的,坐在一起,看海,说有关爱情的话题。
他说:“你知道吗?你上次住的那对老夫妻,他家的女儿爱上了一个外乡人,是到这里度假的男子,白脸长发的年轻男子,她爱上他,然后跟着他去了省城,然后老夫妻也去了省城,然后你就住进了王小宇家里……”
“什么?等等,等等,白脸长发,他们的女儿爱上了白脸长发的男子,那是哪年的事情?”
“是的,白脸长发,好多年了,那人是个艺术家吧。”
我想起与我春风一度的那名男子,白脸长发,是那对老夫妻的女婿吗?不对的,在我住的时候,没记得他们家来陌生男子。那是怎么回事呢?所有到这里度假的外乡男子都是白脸长发的吗?
海水一层一层地涌到沙滩上,我感到心底里涌上了一层欲望,是被白脸长发男子带来的,像扫帚在身体里左右一扫那般的欲望。我低下头看身旁的男子,典型的海边长大的男子,圆脸,面庞黑红,透着阳光般纯净的气息。如果俯下头吻他一下多好,他的嘴唇必定带着大海咸腥的味道。
我将目光投向海的更远处,问他:“你爱的那个女人是外乡人吧?你因为一个前来度假的外乡女子失恋?”
男子的目光变得忧伤起来,他说:“那是一个非常令人伤心的故事。”
4
回到家,遇到王小宇的母亲出门,说:“王小宇在工厂闯了祸。”
我说:“要不要陪你去?”
她说:“好。”
似乎没有通往工厂的汽车,王小宇的母亲也不打算借用任何的交通工具,她领着我沿着海边走。倒是一次休闲浪漫的行走,道路极其洁净,旁边是浪花翻滚的大海,路边的树木葱郁,仿佛用布擦过一般,没有一点点灰尘。
一边走,王小宇母亲一边说王小宇的事情,其实都是些小事,偷同事的工作服,偷同事的茶叶,偷同事的洗衣粉,没有扔掉,全部拿到家里来。“家里不缺这些东西的,虽然不富,但是也不至于穷,就像他那个爸爸……”
“他爸爸?”
“是的。”王小宇母亲看了我一眼,“他爸爸就是个喜欢赚便宜的人。”
“他现在在哪?过世了吗?”
“我不知道他在哪。”王小宇母亲又看了我一眼,目光中有了一些狠,“赚了便宜就走的人,谁知道在哪。”
是这样的吗?王小宇的爸爸也是个外乡人,20多年前到小镇度假,与王小宇的母亲海滩春风一度,然后走得一干二净。王小宇的母亲怀孕生子,独自抚养长大成人。是这样的吗?只是赚便宜,跟爱情没有一点点关系?
他也是个白脸长发的男人?
我渴望王小宇母亲再给我讲点事情,可是她闭紧了嘴巴,不再说话。
走了大约两个小时才到达王小宇所在的工厂,正是吃午饭的时候,王小宇与工友在休息室内吃饭,王小宇面前一个饭盒,满满一饭盒米饭,没有一点菜,他拿着勺子一勺一勺地吃米饭。
王小宇的工友见到我与王小宇母亲,没有一点的新奇与尊敬,看得出他们嘲笑与瞧不起王小宇习惯了,并且将这种习惯延续到与王小宇有关的人身上。
他们说:“王小宇,你上班又不干活,挣的钱比我们少一点都不行,王小宇你还不如回家去。”“王小宇,吃满满一饭盒饭不怕撑死呀。”“王小宇,你快到一边,我看着你就心烦。”
王小宇一点不生气,没听见一般,一勺一勺地吃米饭。他母亲“叭”地一巴掌打到他头上,然后又一巴掌过去,说:“你要死呀,你要死呀。”
没有人过来拉王小宇的母亲,他们依旧一口一口地吃饭,只是不再说话。打了十几下子,王小宇的母亲累了,坐到椅子上呼哧呼哧喘气。有血从王小宇的耳朵后边流出来。他用手摸了一下,立刻摸满半边脸。
这时,一个班长模样的人走过来,说:“打人是不对的。不过,母亲打儿子也说得过去。”

他把我与王小宇母亲叫到室外,在一张破桌子旁坐下。桌子紧挨着窗户,窗台以及窗棂上摆着挂着高的矮的鲜花,绿得发黑的叶子,紫得近乎透明的花朵,美丽得令我有些恍惚。
班长说了将我们请到工厂的原因。几日前,一名工人的工作服不见,今天,王小宇竟然将它穿了出来,工人跟王小宇要,王小宇硬说工作服是他的,结果被工友扒了下来。为了证明工作服是他的,王小宇光着身子在室外站了一个小时。
王小宇母亲的嘴唇哆嗦起来。我说:“这样,会冻坏的。”
班长说:“他不怕冻。大冷的天,只穿一件短裤,穿过整个厂区到浴池洗澡。我们都穿着棉大衣。他不仅是脑子坏了,身体的感应也坏了。”班长将脸转向王小宇母亲,说:“厂子被城里的大厂吞并了。所有工人都要到大厂上班。王小宇,这种情况是不能上班的,你最好给他办病保,在家里养着。大厂是不养闲人的。”
王小宇的母亲嘴唇又哆嗦起来。那个保养极好的女人消失不见了,呈现在我面前的只是一个软弱的,无能的,正在经受屈辱的女人。
我站起身,走出班组,这样压抑的气氛是我受不了的,再说,我不知道这件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呆在这里与不呆在这里没有任何不同。
工厂确实要被大厂吞并了,因为没有一点生产的迹象。所有应该活动着的设备、机械、工具都静悄悄地趴在地上。房子的拐角处一个工人在拆一件东西。看到我是厂外的人,他笑了一下子。
再回来,王小宇已经换下工作服,跟在他母亲后边。我们一起走出工厂,王小宇的工友没有一个人送我们,他们已经坐在桌子旁边打起麻将,有的躺在木头椅子上睡觉。
很快就到了沿着海边的道路,海风吹过来,工厂带给我的不快立刻烟消云散。王小宇一边走一边说:“他们都偷呢。机关干部偷电脑,工人偷设备,趁着厂子被吞并,发个人的财,我只不过是拿了一件工作服。”
他母亲一巴掌打过去,说:“你呀,你要死呀。”
我说:“王小宇,如果不上班,你做什么?”
“做什么?像你一样天天在海滩上晒太阳,在海滩上睡觉。有饭吃,有衣服穿,上什么班呀。”王小宇一边说一边咯咯笑起来。他母亲又要去打他,他一转身跑掉了。
我问:“小宇的爸爸也是这样的人吗?”
“他爸爸,他爸爸……”王小宇的母亲目光投向大海,眼神变得忧伤起来。
5
第二天早晨,王小宇像昨天一样拿着饭盒,骑了自行车出门。我问:“工厂不是不要他了吗?”
王小宇的母亲在打扫院子,什么话都不说,扫帚扬得很高,弄得院子里尘土飞扬。我无事可做,又出门去海边。通往海边的小路上,遇到一名买菜的老妇人,手里提着一条鱼,鱼尾巴拖到地上,另一只手提着白色塑料袋,里面装着扇贝还有海虹。这些海鲜,放到清水里一煮,便是极好的美味。老女人凑到我身前,说:“你是外乡人吧?”
我笑,点头。
她说:“你怎么住到他们家呢,他们家可不是个好人家。那女人是外乡人,跟你一样的。”

“啊,是吗?”可是我对这样的事情不感兴趣,我只是一个短暂停留的旅者,为什么要对人家的事情感兴趣呢?
可是老妇人没有看出我不感兴趣,她似乎闷坏了,好不容易遇到一个说话的人,她决意要将想说的话说下去。她跟着我来到海边,那把铁皮椅子还在,我要她坐,她不坐,说:太凉。我坐到铁皮椅子上,就那样坐着,看着面前的海,老妇人站在旁边,手里提着她的鱼还有扇贝与海虹。
她说:二十多年前,王小宇的妈妈还是个年轻女人,一个人跑到小镇来,她是失恋的,跑到这个人烟稀少的地方,准备呆一段日子后自杀。要知道,她年轻的时候很美,是我们小镇见过的最美的女人。小镇上的一个小伙子爱上了她,天知道他们是怎么爱上的,我们知道的时候,王小宇的妈妈已经离开了。后来她又来到小镇,肚子大了起来,可是小伙子已经不在了,晚上一个人到海里游泳,淹死了。嘿嘿,你知道吗?听说他们只做了一次,就在海边,还是站着的,真是个风流女人。”
老妇人絮絮叨叨说下去,我不知道她何以得知这些细节,是听人传说还是个人杜撰。不过,有一点可以明确,王小宇的母亲与他父亲也是春风一度,在海滩上,并且是站着的。王小宇的父亲是个白脸长发的男人吗?如果他是小镇上的男人,他应该是个圆脸,面庞黑红的年轻男子。
春风一度。这个小镇何以接二连三地发生这样的事情。春风一度,王小宇的母亲得到的是一颗生根发芽的种子,因为这颗种子,她在小镇上度过自己年轻的时光、中年的时光、年老的时光。春风一度,我得到了什么,久治不愈的咽喉炎?还是别的什么?
那种称之为欲望的东西又在我的体内翻腾起来了。我开始怀疑开自己,在这个小镇上,我像一只母猫一样接二连三地发春吗?如果是这样,我有什么可后悔与埋怨的。那个白脸长发的男人是他自己拥我入怀的吗?也许是我将他幻化出来,主动与他拥抱亲热的。
午饭过后,困意排江倒海地涌过来,这倒是件稀奇的事情。到小镇来,第一次想到睡觉,假如像上次那样无休止地睡觉也是件很幸福的事情。我躺到床上,很快进入梦乡,梦里一个人在海边走,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海水就漫上来了,漫过脚背,漫过腿肚子,漫过胸,很快要淹没了我的头。我大叫一声,醒过来,看到王小宇光着脊梁趴在床头。
“你要做什么?”我大叫一起,拉紧被子。
他说:“手机号码。”
我说:“我都告诉你两遍了,两遍了,你不是记在手机里了吗?”
他又说了一遍,“手机号码。”
我说:“滚。”
王小宇并不生气,瞪着眼睛看了我一会,转身出去了。
唉,我用被子蒙住头,后悔刚才骂他滚,本来对他还是抱着一点点同情与尊敬的,为何现在对他这样厌烦,并且毫不掩饰对他的厌烦。也许跟去了一次他的工厂有关,也许跟今天早上老太太的谈话有关。周边的人都不尊重他们,都鄙弃他们,我这个外乡人为何要尊敬他们?
晚饭是油焖海虾、虾仁鸡蛋汤、清蒸海蛎子。所有的饭食都离不开海鲜,并且都新鲜无比,这倒符合我的口味,吃着这样的美味,想到对王小宇母子的不尊敬,我有些后悔起来。想跟他们聊聊天,却又找不到话题。偏偏这个时候,王小宇又看着我问:“手机号码?”
我脸一沉,一句话不说。他母亲一巴掌打他脑袋上,说:“要死呀你。”
“脑子真是坏掉的。”
“可是有人说他装。工厂里的人,镇上的人,许多人说他装。他也是怪的,一点亏都不吃。有日轮休,听人说厂里要发钱,骑着自行车就去了厂里。有日听说厂里中午管饭,早饭不吃就去了厂里,那是别人骗他的,他硬是早饭、午饭都没有吃。第二日,别人又骗他,他偷偷拿了只火烧放在口袋里,大家笑话他又没有带饭,都取笑他,分了饭盒的饭给他吃,吃完之后,他从口袋里拿出了火烧。这一次,他骗了大家。”王小宇的母亲一边说一边笑起来。
我说:“他爸爸也是这样的吗?”
“他爸爸,他爸爸。”王小宇母亲扫我一眼,“小宇的糊涂是生病生的,没生病的时候是好的。妻子也娶上了,蛮漂亮的一个女人。他昏迷不醒的时候她还没有走,他出院了,生活能自理了,能上班了,她突然就不见了。”
突然不见了?我的脑海中一下子浮现出白脸长发的男子。莫不是跟着人跑了吧?
6
王小宇的母亲拿出一张照片给我看,是个长脸细眉的女人,算不上漂亮,可是眼神中流露出与众不同的气息,这气息将她与普通女人一下子区别开来。王小宇母亲说:“你在城里住,看一下有没有这个人。如果有,如果她过得不好,告诉她,我与小宇还在等着她。”
“为何要等她?一个随随便便跑掉的女人。”
“女人嘛。女人。这个小镇我蛮恨的,如果它不在海边,如果它不这样安静,如果它不是一个小镇,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外乡人。”
“可是你也是外乡人。”
王小宇母亲看我一眼,说:“你都知道?”
我点点头。
她说:“我也是女人。”目光看着前方,眼神变得忧郁起来。“我也是女人。其实,我知道你为什么又到这里来。”
“你怎么知道?”
“有些事情不用说就知道的。有些人,不用说,就会明白。”
我张了张嘴,咽了口唾沫,感觉咽喉炎好了很多。
王小宇陪着我去海边。走到那个凹地。我坐了下来,我发现我竟然有些怀念那个白脸长发的男人。如果他再一次出现在面前,也许我会与他好好聊聊,问问他姓什么,叫什么,有什么爱好,与他拉着我,坐在沙滩上,看月亮,看海水,什么都不说,就那样手拉着手看来看去。
我问王小宇:“你爱过人吗?”
他的脸俯过来,突然问:“手机号码。”
我抓起一把沙子扬到他的脸上,说:“你这个傻子,你爱过人吗?”
王小宇怔怔地看着我,捂住脸,突然哭了。哭了一会,放下手,开始脱衣服。很快,他就光了脊背。
我惊恐起来,两手抱在胸前,说:“王小宇,你要干什么?”
他说:“他们欺负我,他们打我。你看这,你看这。”王小宇手指的地方是一块一块的紫斑。“他们拧我的胳膊,拧我的背。骂我。”
“你也打他们,也拧他们。”
王小宇的哭声大起来,说:“我打不过他们。跟我妈妈讲,我妈妈就打我。从小,我妈妈就打我。”
我说:“王小宇,你是个傻子呀。王小宇,你活该挨打。”
咽喉炎一直没有见效,咽唾沫时总感觉喉咙中间卡着一件东西。小镇的一切也使我厌烦。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感到厌烦,是因为没有白脸长发的男子,还是因为没有无休止的睡眠。其实到现在我还怀疑咽喉炎是白脸长发的男子留给我的。这咽喉炎后面是否隐藏着难以示人的隐疾,每每想到这个,我就害怕不已。
坐在饭桌前与王小宇的母亲清算帐目,她的目光里面竟然露出了留恋。她说:“什么时候再来?”
我说:“明年或者是几年以后。”
“如果到时候我还活着,记着还住到我家里。如果见到小宇的妻子,如果她过得不好,告诉她,我们在这里等她。”
我将头扭到一旁。想到那天清晨老妇人说的话。王小宇的母亲也是外乡人,在沙滩上与王小宇的父亲春风一度,她怀上了王小宇,带着这个无法示人的秘密,来到小镇居住。我第一次到小镇,与白脸长发的男人春风一度,没有怀上孩子,却患上了咽喉炎。这次到小镇,是因为咽喉炎后面那把握不住,无法告人的隐疾。如果患咽喉炎之前,没有遇到白脸长发的男子,那么我不会再到小镇来。由此推算,我是个与王小宇母亲同样的女人。
电话铃响了,王小宇的母亲接听,脸上是淡然的表情。放下电话,说:“能不能再陪我去工厂,小宇出事了。”
到了工厂,看到王小宇躺在连椅上,头上包着一块浸满血的纱布。他的工友围在旁边,出人意料的,向我们投来恭敬的目光。班长说:“要送医院,小宇不让,非叫你过来。”
王小宇的母亲坐到连椅上,抓住王小宇的手,她没有一点点的惊慌,仿佛早已知道事情的发生。是的,她应该知道的,因为她接到了电话。这件事情是什么呢,没有人告诉我们。工友们抬来担架,将王小宇放到担架上,他们抬着他向厂门口走去。我看到一架高高的梯子立在一个铁架子上,铁架子的上空是蓝得仿佛洗过了的天空。
班长说:“王小宇,出院之后跟着我们去大厂上班。”
没等王小宇出院,我就离开小镇。临走之前,我来到海边,冲着大海“啊、哦、咿、呀”地喊了无数声,海水灌进我的嘴里,我咽了几口唾沫,感觉不再有东西卡在喉咙间。也许再待一段日子,咽喉炎真的会好起来。可是我真不想再待了。
离开海滩时,我看到一个长发女子走了过来,不用仔细看,就知道她是一个前来度假的外乡人。
回到家,收拾行李,发现一个信封,里面放着一张照片,一名长脸细眉的女子在照片上愣怔怔地看着我,那种与众不同的气息荡然不见,看上去她就是个极其普通的女子。照片的后面是一叠钞票,一张又一张,加起来是我付给王小宇母亲的食宿费还有押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