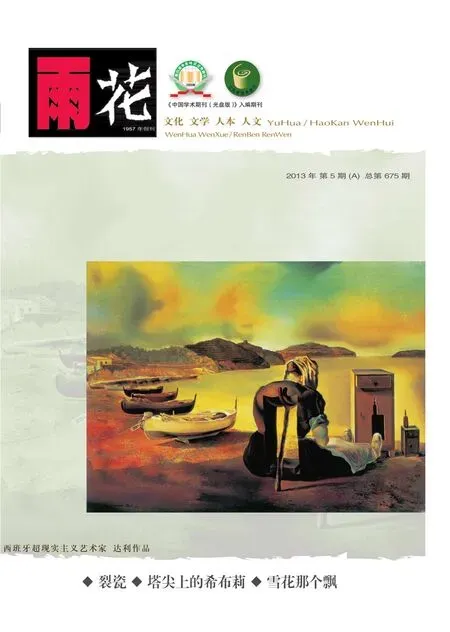杨家屯的男人
2013-09-14严尔碧
● 严尔碧
1
阁楼上氤氲着苞谷的清香。几根八号铁丝拧成一线,从楼楞上垂下来。锁勤坐在满屋金黄里,将苞谷一串一串地捋起,一圈一圈地挂在铁丝上。腰有些酸痛,锁勤看了看手腕上的表,瞅了一眼正在苞谷堆里咿呀玩耍的洋洋,走到楼梯口,探下脑袋来问底下的杨三,要不要做饭了?杨三翘着二郎腿坐在火塘边看电视,头也没抬,吭了一声说还早,吃早了夜里五点钟出窑来太饿。
锁勤就回身挂苞谷去了。
太阳依旧高悬在西天,裸露的院墙像抹上了一层血,红得刺眼。走到院子里,杨三打了一个呵欠,恍然间觉得有些莫名的异样。咋恁个红呢?杨三嘀咕了一句,拿起歪挂在墙上的水龙头,把角落里的污渍和煤屑冲洗干净。一只拳头般大的蛤蟆噗嗤一声跳到他的鞋子上,杨三心头一寒,水龙头本能地对准了蛤蟆,水柱喷涌冲击中,蛤蟆似乎惊恐地瞪了他一眼,扑跳着斑驳粗粝的身子,三五下不见了。杨三不自觉地抹了一下额头,竟冒出丝丝冷汗。抬头看时,墙上的血红似乎淡了一点。杨三有点扫兴,扯开嗓子喊锁勤的名字,说可以做饭了。
杨家屯的男人都这个样,有事没事总爱把婆娘的名字叫得高昂昂的,就像春耕时山野里到处响起的吆牛声。那声音响得果决有力。锁勤是不会拒绝这种声音的。自从煤的价格涨起来后,杨家屯的青壮年都去挖煤了。要是谁家的男人还在靠种地过日子,那日子简直就不是人过的了。于是,杨家屯的男人大多白天在家休息,夜间下井挖煤。男人是杨家屯的天。
锁勤刚把饭煮上,勇克就进门来了。杨三亮出包红山茶香烟,递一支给勇克,自己也点燃了一支,很惬意地吸着。他在盘算今晚能挖几吨煤出来,就算六吨的话,每吨三十六元,六六得六,三六十八,这样就有二百一十六元了。听说城里的公务员都不能挣到这个数。杨三觉得自己的小日子也不见得有多差,就又悠悠地坐在沙发上抽烟,看着锁勤为他做饭。
两人都没说话,待手里的香烟快燃尽的时候,杨三悄悄地看了一眼高卷着袖口做饭的媳妇轻声问勇克:你说我们这里到底有没有煤?勇克说,三哥,嘴巴努努锁勤忙碌的身影,没再吭声。杨三就做个鬼脸,笑了。勇克比杨三更渴想煤。勇克今年二十五岁了,二十五岁该找个媳妇了。勇克做梦都想找个媳妇。可因为煤,他找不到媳妇。煤让落鹰山周围的村子都富裕起来了,只有杨家屯,既没有煤,又远离落鹰山。你说哪个姑娘还愿意嫁到杨家屯?又有谁愿意嫁给没钱的勇克?勇克只有拼命地到落鹰山去挖煤,有钱了,就有媳妇了。勇克很希望顺着杨三的质疑一路猜想、考证下去,但是锁勤敲锅铲的铿锵声和她大喇叭似的嗓音打消了他的念头。
锁勤晃着高卷袖口的胳膊说:杨三,你还不死心吗?还嫌折腾不够吗?这日子还要不要过?
为找煤的事情,杨三动了一年的心思,把发财致富的梦想都寄托在杨家屯四周绵延起伏的大山上,结果除了在山上刨下成百上千个荒洞而外,连煤屁都没闻到一口。庄稼比别人家的差不说,还落得个不务正业的名声。
杨三看着锁勤摆动着的丰满的屁股,看着她时不时回头瞪他的眼神,赶紧讨好地笑了笑。
2
最后一抹的夕阳血色悄无声息滴落时,杨三和勇克已经到达落鹰山。落鹰山上好几口矿井如同蜂窝一样盘布。谁都知道落鹰山煤好,可瓦斯也多,瓦斯是谁也惹不起的,是死亡和灾难,但来上夜班的工人足足有四五百人。他们在泥泞的土路上把摩托车轰得山响。杨三和勇克夹杂在摩托车队伍中间,谁也看不清谁是谁,谁进了哪一口黑黢黢的煤井。
杨三从井里抬出来的时候是凌晨六点钟。勇克把杨三放在急救车上,他拉了拉杨三的腿,企图让它不再摆动,以免失血太多,可他拉了好长时间,根本无法拉动。勇克就哭了。矿上的医生骂他,事情都出了,光晓得嚎丧,赶快把他的裤子脱下来!勇克就手忙脚乱地脱杨三的裤子,却怎么也脱不下,医生又骂勇克没用,没等勇克把手缩回来,一剪子连着裤带将杨三的裤子剪开了,用药棉和酒精给杨三—下一下地洗破絮似的腿。杨三的腿已经断成三截,骨断肉不断地在医生的手里晃悠着。勇克喊了声杨三的名字,杨三微微地睁开了眼睛,勇克才大胆地配合医生把杨三五花大绑地固定在急救车的床上,又用竹简把断腿固定起来。医生对勇克说,回去给他家里人说一声,今天早上必须赶来县医院交住院费,说完救护车便拉响了警报,摇摇摆摆地沿着满是煤屑的土路下山去了。
走进村来,勇克就觉得自己再也没有力气了。洋洋正蹲在门口拉屎,看见勇克来,就伸手去身边拣柴棍,想自己擦屁股。勇克的眼泪就滚了出来,他想伸手摸摸洋洋的大脑袋,可还没摸到,洋洋就说话了:我妈让我拉屎,拉完了等爸爸回来就去赶场买化肥……勇克的手忽然僵在半空不动了,心里一阵绞痛,脚步再也抬不动了。
进去黑如铁,出来白如雪。再不讲究的煤炭工人出窑回家,都会就着白花花的地下水,把敷在脸上身上的煤屑洗净,然后坐在三岔口的清真饭馆,来一碗热乎乎的牛肉米线,斟二两老白干,有滋有味地品。现在,勇克像晒蔫的苞谷秸秆一样耷拉着身子,倚在门框上,垂着黑不溜秋的脸,锁勤的脑袋就嗡地响了起来,那声音像煤车隆隆碾过土路,飞扬的黑尘半天落不清爽。她的胳膊和嗓音一起颤抖。她说勇克,你啥也不要说,你只告诉我——她的声音急促而又抑制着,她害怕听到那个熟悉而又残酷的消息——你三哥现在,在医院,还是在矿山?
勇克的眼珠黑得像一口井。
勇克的牙齿白得吓人。
她的心仿佛悬了一个世纪,终于噗通落了下来。她咽了一口气,又没主意了。这可咋办?秋收的庄稼还活泛泛地在屋檐上挂着,要卖也得到冬天晒干后。圈里的三头架子猪还吊着个狼肚子不见长膘,本打算秋后就卖出去的,可猪不吃食就算是喂龙肉也没办法,怎么筹钱去县城的医院?门外的洋洋已经拉完屎,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站起身来,小鸡鸡还在滴着尿……
锁勤背着洋洋挨家挨户去借钱。村头的王老五家四个儿子全在煤矿上挣钱。锁勤笃笃地敲开了门,王老五嘴里咂巴着旱烟袋伸出脑袋来。锁勤眼泪滴溜溜地在眼眶里转:五叔,洋洋他爸今早出事送去县医院了,我来借点钱。杨家屯谁都知道出事就是指在煤矿上出了事。五叔问,伤得重么?锁勤说,听勇克说腿杆被砸断了。一咬牙,把要掉出的眼泪摁进眼眶里。杨家屯有个忌讳,不能在人家门上掉眼泪。五叔沉吟了一下,回头从墙上摸索出个布袋子来:你把这两千元先拿着,这是老大叫我存着给他讨媳妇的,乡里乡亲的,哪头事重要就先照顾哪头,不要急,煤矿上要负责大头的……
锁勤后退几步,朝五叔家门口磕了几个头。
一转身,任由眼泪哗啦流淌。
3
勇克默默地回到家中,老母亲还没起床。勇克不想叫醒母亲,更不奢望母亲能为自己生火做饭。母亲患有严重的白内障。一天早上,勇克挖煤回来刚睡着,就被弥漫在满屋子的臭味熏醒了。原来母亲竟然把一个不晓得从哪个荒沟里拾回来的牛脑壳当成柴疙瘩用来生火做饭了,腐肉还在滋滋地冒着白烟。勇克一阵恶心,把锅里的饭全倒在门外。母亲听到勇克推门回来的声音就问,今天早上的霜大吧?该晒点洋芋皮了,你把楼上的洋芋拣一口袋扛下来,我上不了楼,等着你回来。勇克说,今天我要去县城。母亲问,去县城做什么?勇克说去县城有事情。母亲咳嗽了几声不再追问。
勇克歪靠在车窗前发呆。怎么也想不通,矿难这事情就这么降临到自己和杨三的头上。本来他们挖到早晨五点钟的时候,又黑又疏松的煤已经足足有六吨了,剩下来的时间就是他和杨三一同装车,拉出井来就完事。可看着灯光下闪着光泽的煤层,金子一样晃着他们的眼睛,杨三说,我来换你挖,你把挖出的煤拉出去。勇克就把十字镐递给杨三,自己一趟一趟地拉煤。他拉到第五车的时候,盘算着怎么说也有七吨多了,回到井里,杨三还没挖足一车煤,他就点了支烟等待着。烟才抽了半支,顶棚上的石块突然哗哗地往下掉。等他反应过来,屁股上已经被杨三狠狠地蹬了一脚,一个狗吃屎跌出好远。他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回头看见一块巨大平整的石块正被杨三用十字镐顶着,他想都没想,奔过去要和杨三一同顶那石块。哗啦啦的石块还在往下掉,杨三龇牙咧嘴地忍着说,勇克,赶紧跑!接着又是哗啦啦的一阵响声,眼前一片漆黑。
想到这儿,勇克的眼泪又涌出来了。他带人进去刨石块的时候是先刨到十字镐的,接下来是杨三的双手,血淋淋地趴在地上,然后就是脑袋,还好,都是些碎石压在上面,扒开那些碎石就听到杨三的呻吟了。刨到下半身的时候,两块巨石一前一后切在杨三的腿上,像两把斧子。勇克想着想着,身上就一阵哆嗦,不敢再往下想了。他看着山林间那些葱郁的树木想,人活着不如一棵松树。
勇克下了车没有直接去医院。他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也要为杨三买张轮椅回来。街道两侧的店一家家地进去看,一家家地问,根本没有卖轮椅的。问遍县城所有的商铺,人家都说轮椅只有在医院里才卖。勇克只好沮丧地往医院的方向赶。
在医院门口,勇克看见了一辆黑色的悍马轿车雄赳赳地开了进来。勇克对轿车的品牌和标志并不清楚,但是矿长王根山的悍马轿车他经常看到。勇克眼巴巴地瞅着那辆车。果然,车停稳之后,走出一个身穿皮夹克、手拎银色茶杯的男人。这个人平常在落鹰山煤矿根本见不着。勇克想起有一次下班的时候,在山路上遇到一辆黄色的汽车风一样地迎面刮来,急忙刹车打龙头让路,但已经晚了,摩托车顶住汽车防护杆后倒在地上。勇克从地上翻身爬起来,看见一颗肥硕油光的脑袋从车窗里钻了出来,找死呀!勇克揉着膝关节,两眼喷火正要迎上去,杨三抢过来说,赶紧走。勇克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这个人是矿长王根山。王根山风一样地把车开走的同时,丢下那句话,小狗日的,以后骑车给我慢点,跌死老子不会出钱的。
勇克不由自主就朝矿长走了过去。
腿断了吗?王根山问。勇克说,断了,断成三截了。能接起来吗?不能,医生说要锯掉。他妈逼,怎么一来个人都说要锯腿?王根山一面骂一面往医院里闯进去。勇克也跟在后面。
勇克不恨王根山了。
4
杨三的截肢手术进行了整整四个小时。锁勤站在手术室外一刻也不敢离开。她害怕自己一走开回来就再也看不到大声喊她做饭的杨三了。虽说男人平时不大管家里的事,还染上抽烟喝酒小赌几把的坏毛病,但一家人的生活是怎么也离不开杨三的,每年种地得来的粮食喂了家里的猪,就所剩无几了,其他的开销,还都得指望杨三上煤矿挖煤。这么想着,锁勤心里就一阵阵抽搐般地疼痛,整个身子像是一条软绵绵的编织袋子,走要人拉,站要人扶。她再也不敢往下想,一屁股软软地坐在手术室门口的凳子上。
妈妈,爸爸去哪里了?我要和他玩,脊背上的洋洋醒了,用双手敲着锁勤的双肩。锁勤把儿子放下来,没心思去理会他,让他呆呆地站在阳光斑驳的走廊上。妈妈,你别哭了,我长大给你买好多好吃的东西,我和哥哥好好伺候妈妈和爸爸。洋洋靠在锁勤的怀里喃喃地说,锁勤的心一阵锐痛,眼泪又哗哗地流出来了。
她咬咬牙齿。她紧紧地把洋洋抱在怀里,觉得身上不再那么冷了。她想,耐心地等待吧,熬吧,等待是会有结果的,一切都是命中注定。一条腿,十万块。不,我不要那十万块。我要完整的杨三。可要万一?天啦,别管那么多了。像杨三这样的情况,这些年杨家屯有八九个。丈夫是幸运的。自己也是幸运的。杨三好歹保住了一条命。只要人在,天就不会塌下来。她把洋洋的小手拉在嘴边来,亲吻着洋洋。儿子,别怕啊!有妈妈在!她轻声地安慰儿子。为了两个孩子,就算上刀山下火海她也要把这个家撑起来。
夜幕笼罩下来,杨三终于在医院苍白的灯光下被推了出来。医生一脸高兴,说,幸好保住了一条腿。说着便掀开被子给锁勤看,那是条左腿,被纱布密密匝匝地缠绕着,像一截刚嫁接上的梨树杆子。另一只腿永远地锯掉了,放置在一边。锁勤不知道是惊喜还是难过,走上前去把杨三紧紧地抱在怀里。勇克却拿起那条断腿,哭得很伤心。
杨三手术后的第四天就可以正常进食了,他在医院的病房里住了一个半月。一个月是死人一样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度过的,后半个月他每天试图用左脚和手杖支撑身体慢慢移动,但每次尝试都让他泪流满面,然后怪叫着把手杖扔得远远的,样子非常吓人。锁勤不敢吭声,任由杨三发泄。她知道男人心里烦,心里苦。渐渐地,杨三平静下来。锁勤弯着腰给他擦拭身子。锁勤的动作麻利而温柔。锁勤的语气平静得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锁勤说,你忘了?我会做凉米虾,会做豌豆凉粉,会做米线。咱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还记得吗?你吃了几碗米线?整整两大碗,馋死了!知道吗?那米线就是我做的。不是吹牛,整个杨家屯,整个来宾镇,整个落鹰山矿区,没一家的米线有我做的好!天,塌不下来!
杨三眼里有了泪花花。
杨三说,这些日子,就没一个人来过?
锁勤扫视了一下病房。别人病床旁边的柜子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营养品,靠窗的那个做子宫癌手术的女人,她的柜子上还搁着一篮鲜花。整个病房里的四个病人,除了杨三,别人都是隔三岔五就有人来探望。
锁勤不知道杨三为啥子会想起问这个。锁勤只知道,从男人出事的那一刻开始,她就没有指望过任何人。
锁勤说,你动手术那天,王根山来过一趟,交了一笔住院费后就走了。还有就是勇克,他在医院里陪了好几天,是我把他赶回去的。他一个大男人,在这里也帮不上啥子忙,除了淌眼泪,就是唉声叹气。回去挖煤,还能多挣几个钱。他想给你买个轮椅,可县城里买不到。他说实在买不到,他就去一趟昆明。
眼泪顺着杨三瘦削的脸颊跌落下来。
杨三说,锁勤,我要出院,带我回家。
5
出院那天,锁勤搀扶着他上了辆三轮车,离开医院到车站坐车。他们觉得在县城里简直是待腻了,每晚做梦都梦见在自家的屋子和篱笆下,在那些熟悉的地方,和花草、猫狗发生着稀奇好玩的事。坐上车,杨三的心情渐渐好起来,愿意说话了。
即将到达杨家屯的时候,他们看见一辆一辆从落鹰山开出来的煤车,装着乌亮乌亮的煤,卷着滚滚黑尘,漠然地疾驰而去。杨三又不说话了。他看着那些煤车出神,看着那些永远消逝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日子。
远处是起伏的山峦和光秃秃的树林。
汽车沿着弯弯拐拐的公路颠簸了两个小时后,噗嗤一声,在杨家屯的岔道口停了下来。天阴沉沉的。一团团湿漉漉的雾气在松树林里缓缓移动,那些枯干的枝条、草叶上,被霜打蔫了缨子的胡萝卜上,都凝着一颗颗亮晶晶的水珠。一条坑坑洼洼的红土路从胡萝卜地里穿过,路的尽头,光秃秃的树林深处,就是杨家屯。
锁勤小心翼翼地搀着杨三下了车。汽车顺着粗糙而又光亮的柏油路,一眨眼就拐到山丫里去了。
来了!来了!杨三!锁勤!三儿……抬头,他们看见黑压压的一群人迎了上来。
两个人愣愣地看着这群熟悉而又陌生的男女。他们有的提着鸡,有的提着五颜六色的营养品。他们嘴里不断地呼着白汽,脸上挂着笑容,话语里流露出关切,连脚步也是那么急切。
杨三和锁勤的目光一个一个地扫过去。大哥,大嫂。二哥,二嫂。大姨妈。大表哥。堂叔。三姐夫……
杨三右手拄着拐杖,左手靠着媳妇的肩膀,木然地看着他们。
堂叔弯下腰说,来,三儿,老叔背你回家。
三姐夫说,还是我来吧,你都这么大年纪了。
大表哥说,你们都走开,看我的!
杨三伫立着不动。
杨三朝人群里张望。
杨三看见了一个人,远远地瑟缩着身子,嘴里含着支香烟,不住地踮着脚尖朝自己张望。
杨三铁青着脸吼了起来:勇克,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还不快过来背你老哥回家!回家!
勇克愣了一下,哎地答应了一声,把香烟扔了,朝杨三小跑过来。
勇克弯腰曲腿,杨三就软软地趴在勇克的脊背上。
一群人你看我,我看你,讪讪地围着锁勤,嘘寒问暖。锁勤哎哎嗯嗯地应付着,默默地跟在勇克的后面。
勇克的脚板稳重而又利索。勇克一边迈着大步一边说,三哥,你刚才咋个骂我没良心呢?我是没良心的人吗?
杨三揪着勇克的耳朵轻声说,说你笨,你就是不承认,连话都不会听。我问你,你咋个站得那么远远的,像个小媳妇!
勇克咳了一声说,他们,他们都是你家的亲戚啊,我不是。
杨三说,狗屁。你以为他们恁个关心你三哥?他们真正关心的是那十万块赔偿费。做梦!
勇克一惊,停下脚步,脑袋歪向杨三,喜滋滋地说,三哥你错了,不是十万,涨价了,刚刚涨的价,是三十万!这回你也算值了。勇克兴奋地甩开步子。勇克说,你住院的这段时间,又发生一起矿难事故,死了四个,其中一个是回族。王根山起先打主意瞒住这件事情,想每人打发三十万了事,结果引来了一百多个回族兄弟,事情就闹大了。省里、市里的人都下来调查,王根山还被公安带走了。后来就涨价了,死了的人每人六十万。呵呵,据说,王根山这狗日的,连悍马轿车都卖了……
勇克说得有声有色,兴味十足。勇克接着说,哎,三哥,跟你说实话,我情愿断掉一条腿的是我,这样我就可以……
勇克忽然感觉到脖子里一阵冰凉,以为是树枝上滴落下来的露水,就没在意,正要继续往下说,忽然想起自己是在空旷的胡萝卜地里行走,哪来的树枝?勇克愣了一下,感觉到脖子的冰凉正向脊背、肩膀蔓延,接着他听到了一声一声使劲压抑着的抽泣。
勇克急了,止住脚步,颤着嗓子说,三哥,你咋个哭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