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鸳鸯曲
2013-09-13文/沈淦
文 /沈 淦
楔子
“狼山镇邓总兵被人刺杀了!”清朝嘉庆某年七月初五日,这个惊人的消息迅速传遍了通州城(即今江苏省南通市)的每一个角落,一时大街小巷,酒楼茶馆,到处都在议论纷纷。这可急坏了城里的大小官员,因为不久前,大家都已收到了总兵署送来的请帖,邓总兵的独生女儿巧姑定于七月初七日完婚,邀请诸位官员至署喝杯喜酒,诸官均已备办了礼物,打算到时候好好庆贺一番。哪知变生不测,青庐竟化为凶宅!于是,知州及其手下的那些州同、州判、吏目、巡检等穿梭般地出入于总兵署;总兵手下的那些游击、守备、千总、把总等更是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又是调兵封锁署门,又是缉查凶手,乱成了一锅粥。到了下午,案子已经有了眉目,凶手竟是邓总兵的爱妾郑氏,也就是巧姑的母亲,而且也牵连上了巧姑。这母女俩为什么要杀害自己的丈夫和父亲?邓总兵虽说妻妾成群,但是除了郑氏外,谁也没有生育,所以总兵最宠爱的就是郑氏,何况总兵还是郑氏的大恩人,郑氏一向对他又敬又爱。至于巧姑,更是总兵的掌上明珠,哪怕总兵暴跳如雷,只要有巧姑在旁边柔声一劝,顿时就会回嗔作喜,笑逐颜开。这天傍晚,邓总兵的快婿、巧姑的未婚夫孙耀宗与其父孙荇洲从江西千里迢迢地赶到通州来举行婚礼,哪知碰上了这场大变故,婚事自然无法办了。由于事关大员被刺,通州知州不敢擅作处理,便连夜将人犯押送金陵,请臬台大人亲自审理。孙家父子放心不下,也追随至金陵观审。邓总兵何许人也?郑氏为什么要杀他?这还得追溯到十六七年之前。
总兵狡谋获新艳淑女舍身复旧仇
邓总兵名叫邓承彦,嘉庆元年,在四川、湖北、陕西等地爆发了白莲教大起义,清廷派大将杨遇春、杨芳等率军“进剿”。邓承彦随军出征,由于他骁勇善战,不断地得到提拔。一晃八九年,终于镇压了起义军,邓承彦也被任命为狼山镇总兵,总兵署就设在通州城内。这样,他便成了坐镇苏北的一位地方大员。郑氏其实并不姓郑,她名叫吴玉碧,十八岁时嫁给了四川叙州书生郑梦泉。小两口恩恩爱爱,日子过得十分美满。由于郑家是当地巨富,白莲教大起义时,川、楚、陕地区一片混乱,某日深夜,一群“教匪”包围了郑宅,万贯家财被洗劫一空,全家老少数十口都惨遭杀害,唯独玉碧藏匿于草堆之中,才幸免于难。第二天清晨,邓承彦率大队清兵蜂拥而至,重新搜索其家,才发现了吴玉碧。邓承彦怜悯她孤苦无依,热心地替她殡葬了公婆、丈夫及叔叔伯伯等死难亲属,最后便提出要将她收纳为妾。玉碧感念他的恩义,再加上自己当时已有了三个月的身孕,腹中一块肉不知是男是女,倘若生下儿子,也能够替郑家留下一线香烟,而一个孤弱女子在这兵荒马乱之中,实在难以存活,便答允了邓承彦。婚后玉碧被称为郑氏,六个月后便产下一女,因为时逢七月初七日,便取名巧姑。十多年来,邓总兵对玉碧毫不歧视,夫妇二人相敬如宾。巧姑的婚期将届,玉碧随着邓总兵为女儿整理嫁妆。她打开了一只精致的小箱子,忽然发现了一块精巧绝伦的汉玉佩,登时惊得目瞪口呆!这块玉佩是吴家的珍宝,玉碧将它作为定情物赠给了前夫郑梦泉。梦泉珍爱无比,一直贴身收藏着。梦泉遇难后,这玉佩不是已被“教匪”劫走了吗?怎么会在这儿出现?玉碧再将玉佩仔细察看,没错,正是自家的传家宝!玉碧再打开箱子的第二层,又发现了婆婆生前戴的珠步瑶与公公用的白金烟壶!玉碧热血上涌,差一点晕了过去,原来当年杀害自己全家的,并非“无恶不作”的“教匪”,而是一位堂堂正正的朝廷军官!自己十六七年朝夕相伴的,哪里是什么大恩人,分明是有着血海深仇的死敌!晚宴时,玉碧支开了侍从婢仆等,乘邓承彦喝得高兴,忽然拿出那几样东西,故作漫不经心地说:“这几样物是从哪儿来的?奴家以前怎么没见过?”邓承彦已经有了七八分酒意,竟忘了忌讳,随口答道:“这是四川一个大富豪家的东西,我派人装扮成教匪模样,杀掉了他们全家,才搞到手中。”玉碧强压下满腔怨愤,又不露声色地慢慢探问详情。邓承彦回答了几句,忽然醒悟,就大声喝叱道:“如今你已在我的手掌心里了,我难道还怕你去告状,为前夫复仇不成?”玉碧笑道:“官人哪里话来,奴家与官人已结了十六七年的伉俪,官人对我又恩重如山,我怎么还会去怀念那死鬼?官人千万不要多心。”邓承彦果然不再多心,又一连喝了几大杯,终于烂醉如泥。玉碧十多年的仇恨如火山般爆发出来,操起一把明晃晃的剪刀,猛然剪断了他的喉管。邓承彦连哼也未哼一声,就呜呼哀哉。玉碧又向西而跪,轻声遥祝道:“公公、婆婆、梦泉及诸位蒙难亲人,我吴玉碧今夜已手刃仇人,为你们报了血海深仇。愿你们在天之灵安息吧,我马上也要追随你们而去了。”在金陵臬署,玉碧将前后经过原原本本地供述一遍,并拿出汉玉佩等作物证。尽管陪审官员中不乏同情者,她还是被判为凌迟处死。临刑前,臬台问她还有什么话说,她长叹道:“我应该忍耐几天,等女儿成婚以后再报仇的。如今连累女儿也赔上了一条性命,真可惜啊!”
邓巧姑自选寒婿孙耀宗惜别娇娥
邓巧姑十岁那年,邓总兵不惜重金,从江西聘来一位著名的老学究孙荇洲,在署中教女儿念书。孙荇洲中年丧妻,无儿无女,他有个妹妹嫁给了李家,因见哥哥无依无靠,便将小儿子耀宗改姓孙氏,过继给了哥哥。此时,耀宗也十二三岁了,孙荇洲一直将他带在身边,在总兵府为巧姑伴读。一晃四五年,巧姑已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少女,求婚者几乎踏破了门槛。邓总兵宠爱女儿,每次都让媒人将男方带进署中,而让巧姑躲在屏风后窥视,由她自己选择如意郎君。哪知过了一年多,竟没有选中一个称心如意的。其实,她与孙耀宗青梅竹马,早已互相倾慕,只是未经挑明,自己又羞于启齿而已,因此看了其他男子,总觉得比不上自己的意中人。那孙耀宗聪颖过人,他从巧姑的一颦一笑,及近来稍觉异常的言行中,也早已有所察觉,但他过于老实,又觉得自己出身寒微,难以高攀总兵大人的千金,故而不敢作非分之想。再说那孙荇洲见巧姑已到了婚配之年,男女有别,耀宗应避些嫌疑,因而平日里不准耀宗轻易与巧姑搭言。耀宗不敢违拗,只得渐渐疏远了巧姑。过不几天,巧姑也察觉了,便乘荇洲不在时,悄悄地询问缘故。耀宗只是摇头叹息,默默不发一言。巧姑终于鼓起勇气,写了一首诗,卷成一个小卷儿,悄悄地递过去。耀宗打开一看,原来是一首七言绝句: “昨夜桃枝莺留宿,今晨绕梁燕报春。含羞欲把芳心许,何故檀郎似路人?”耀宗大喜过望,立即挥毫和了一首:“桃枝无言莺难宿,杏花吐蕊燕迎春。
文君既把芳心许,相如岂是薄情人!”薄薄的窗纸点破了,这感情的闸门一经打开,就再也遏制不住。此后,只要孙荇洲一离开书房,二人便偎在一起,款款而语;荇洲在场时,也是你顾我盼,暗递花笺。孙荇洲终于看出了苗头,这天晚上,在寓所将耀宗痛责一番,又骂他不知自爱,异想天开。第二天,巧姑入书房读书,发现耀宗面有泪痕,不由得奇怪地询问,耀宗摇头不答,巧姑焦虑异常,正想再问,耀宗已乘荇洲扭头他顾时,悄悄地说:“就是为了你啊!”以后直到放学,耀宗一直埋头读书,再也没有和巧姑说一句话。这天晚上,巧姑茶不思,饭不吃,早早地入闺房蒙头而卧。邓总兵与郑氏过来询问,她只说是不太舒服。哪知第二天便真的生病了。邓总兵以为是偶感风寒,连忙请医生来诊视。一连服了几副药,巧姑的病情却越来越重,竟致卧床不起。邓总兵急坏了,再四寻访名医。可是一连换了五六个医生,巧姑的病情还是毫无起色。最后一个医生对他说:“令爱患的是心病,药石怎么能够治疗呢?”邓总兵大吃一惊,把这话告诉了郑氏,二人推测了很久,也未找到答案。郑氏便单独询问女儿,巧姑起初面有羞惭之色,默不作声。郑氏一再追问,巧姑才含羞说出原委。郑氏出去与丈夫商量,邓总兵二话不说,当即将孙耀宗召进女儿房中,让他坐在床头。过了片刻,邓总兵亲手解下耀宗胸前的佩囊,放在巧姑手上。巧姑不知父亲的用意,又因为父亲的姬妾们都在房中,哪好意思接受。邓总兵将佩囊塞在她枕下,凑在她耳边说:“痴妮子,你既喜爱孙家郎君,何不早说?为父的已为你作主定下这门亲事了。”耀宗偷眼瞧那巧姑,只见她脸色蜡黄,容颜憔悴,知她病得不轻,不由得又怜又爱又感动。但是众目睽睽之下,他也不能多说什么,坐了一会儿,便告辞而去。耀宗一回寓所,就将经过情形告诉了孙荇洲。荇洲没有再责备他,只是半信半疑地说:“一个总兵府的千金小姐,当真能够嫁给像我们这样的清寒之士么?”哪知第二天一早,邓总兵果然委托两个统领,带着丰厚的礼品,来为女儿作媒。荇洲与耀宗都喜出望外。巧姑得了这一喜讯,病也很快就好了。又过了几天,孙荇洲辞别了邓总兵,带着耀宗回家乡准备婚事。邓总兵赠给他一大笔银子,婚期定在明年七月初七日,届时请荇洲仍携耀宗来通州,就在总兵署内为小两口举行婚礼。孙荇洲自然一口应允。临行之际,巧姑亲自送至江畔,赋诗一首赠耀宗曰:“相如悠悠千里去,文君盈盈泪湿衣。绣楼唯念梅花约,琴心一片望归期。”耀宗当即和答一首曰:“相如不为功名去,文君莫拚金缕衣。来年纤云弄巧日,五山回首共佳期。”二人互道珍重,依依而别。
伉俪难谐伉俪志鸳鸯共赴鸳鸯冢
那天半夜,玉碧刺杀了邓承彦后,又安详地走进女儿房中,将事情经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她。巧姑顿时惊呆了,心中犹如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咸搅在一处,不知是悲,是怒,是恨,是痛,好一阵才说:“母亲,我们何不赶快逃出城去?”玉碧凄然笑道:“傻孩子,总兵遇刺,非同一般,明天各路口要津,必然严密盘查,我们两个弱女子,能逃到哪里去?为娘的一人做事一人当,绝不连累旁人。”巧姑沉吟良久,忽然跪在玉碧面前哭道:“既然事已如此,母亲何不自裁,免受公堂之辱?”玉碧搂着巧姑,柔声说:“为娘的既决心报仇,已存必死之志。然而我现在还不能死。为娘的必须在公堂之上痛述原委,要让世人知道:邓承彦是个衣冠禽兽,我吴玉碧决非忘恩负义之辈,而是为前夫全家复仇。”第二天,通州知州初审此案时,有几个嫉妒郑氏的姬妾诬陷巧姑是同谋,于是知州便将母女二人一同押往金陵。巧姑不愿在公堂受辱,押送的差役稍一疏忽,她便纵身投入了滚滚长江之中。再说孙家父子兴冲冲地赶到通州,竟撞上了这场大变故,当夜便又乘船赶往金陵。耀宗在狱中见到了吴玉碧,才知道巧姑已投江自尽了,悲痛得几乎不能自持。孙荇洲只得带着他返回江西。耀宗犹日夜思念巧姑,希望她能侥幸脱难,也许还有重逢之日。又过了一年,孙荇洲不幸病故。荇洲这几年因邓总兵赠馈甚厚,也积累了一些家产。他的那些族人们都红了眼,便群起攻击耀宗,说他是李家的人,无权继承孙家的财产。耀宗懒得与他们多争较,便抛下财产,只身回到生身父母处,重又恢复了李姓。二十岁那年,耀宗考中了举人。主考官史玄盛爱其才华,打算把女儿嫁给他。耀宗怀念巧姑,无意婚娶,但因顾及史考官的面子,不便直言回绝,就推说要回去和父母商议一下。哪知父母一定要他应下这门亲事,并与史家订下了婚约。耀宗拗不过父母之命,只得勉强应允。 到了大喜之日,李家张灯结彩,贺客盈门,而耀宗因思念巧姑,经常独自向隅拭泪,只是在人前强颜欢笑,竭力掩饰而已。晚上,鼓乐齐鸣,鞭炮阵阵,新娘子的彩轿到了。众人簇拥着耀宗出门相迎,掀开轿帘一看,一个个都倒抽一口凉气,只见轿顶上悬下一根绳圈,新娘子已红巾系颈,自缢身亡!众人无不惊慌失措,耀宗也惶惧疑惑,急忙凑近仔细一看,忽然止住众人道:“大家不要惊慌,新娘子尚能救活。我当年在狼山时,曾向总兵署中人学得了一个急救之法,大家快把她抬到床上,待我来如法救治。”大家依言而为,耀宗又把众人赶出房间,说:“这个抢救法必须有个十分安静的环境,如果有人喧哗或偷看了,法术就不灵了。”大家都在外面屏息等待。哪知过了两个多时辰,既不见耀宗出来,也听不见任何动静。有人起了疑心,上前敲门,门被插了闩,里面毫无回声。众人拨开门一看,都叫苦不迭,只见原来的那根红绳又悬在屋梁上,新郎与新娘双双投缳自尽,臂与臂相抱持,衣与衣相纠结,足与足相勾连,死者未能生还,生者却已死去了。众人睹此情状,无不失声痛哭。问及女方的父亲史玄盛,才知道这个女儿并非亲生,而是前年从江中救起,因见她聪明伶俐,才貌出众,便收为义女。史玄盛公务繁忙,一时疏忽,订亲的事竟未告诉她,直到出阁这天晚上,女儿才知道要到李家做新娘了,便哭着说:“女儿早已许配给孙家了,誓死不愿进别人家的门!”史玄盛只以为她是耍小孩子脾气,硬劝着她上了轿。哪知她竟真的殉了情。后来的事情当然很清楚了:史女就是耀宗魂牵梦萦的郑巧姑,她因怕受官司牵连,未敢将真实姓名及家世告诉史玄盛。耀宗发现她为自己殉了情,也痛不欲生,遂追随其同赴黄泉,共结鸳鸯于地下。人们又在耀宗的袖中发现了一块白绢,上题绝命诗一首:“良辰佳期悲重逢,镜花水月终成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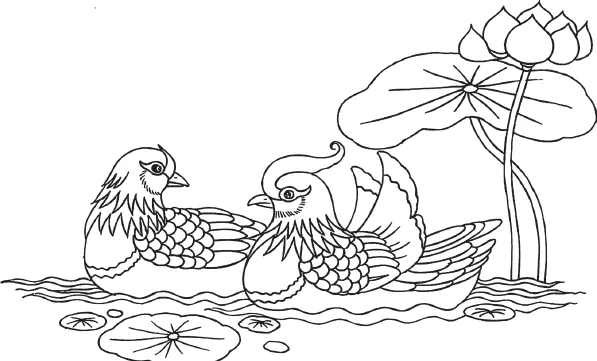
生前难谐伉俪志,死后愿结鸳鸯冢。”
耀宗的父母伤悼异常,便请人制了口大棺材,将两人合葬于祖茔内。人们痛惜这对年轻情侣的不幸遭遇,编成《生死鸳鸯曲》剧本,广为传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