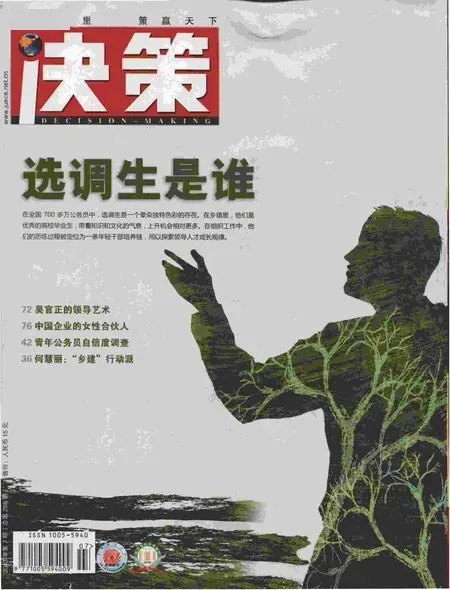“我所做的只是方向和示范意义”——对话何慧丽
2013-08-27吴明华
■本刊记者 吴明华

《决策》:在挂职的10年中,我们看到您做的事情非常多。通过这10年的实践,您有没有找到一条乡村建设的道路?
何慧丽:我们一开始就是以“农民生计为本,合作组织为纲,多元文化为根”为宗旨,10年来探索的核心是“农民合作与城乡合作”。
后来在发展过程中,发现现实的探索具有综合性,农民思想文化不统一。怎么合作?于是发动乡土文化。在发动喜闻乐见的乡土文艺过程中,感到应重视传统文化的发扬,从秧歌、腰鼓和盘鼓等表现形式,转型到以“孝亲”为本的婆媳关系、亲子关系和夫妻关系改善等,乡土伦理道德重建上来。
我觉得,方向是正确的,但路线可以根据条件、资源和宏观环境的改变而不断调适。我们的一个策略叫“关注当下”。
《决策》:在您的乡建探索中,我觉得有两点非常值得敬佩,一是走“红军路线”;二是“能做多少是多少”的心态,尽自己最大能力做些事情。
何慧丽:我们在乡建中注意到了“乡土社会”中金钱交易的不当之处。我们学会了很多与老乡打交道过程中又不欠老乡的,同时又让老乡满意的做法,比如以物换物、以劳动参与换物,等等。
除了走“红军路线”,另外,我们还总结出了“孝亲路线”,即传统文化路线,遵从“敬自己的父母是小孝,敬朋友的父母是大孝,敬天下所有人的父母是至孝”的道理。我们在与老乡打交道过程中,试图深入到传统乡土社会的根上去,从我做起,以行践之。
“能做多少是多少”的心态,是从事乡建事业的行动者所持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论,也是“事在人为”的意思。我作为知识分子参与的那些事情,本质上只是个方向意义和示范意义。合作的历史,无论是经验或者教训,都是群众为主体在做,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决策》:您在兰考做的这些事情,在您离开后是否还可持续?
何慧丽:10年来,我的真正作用有三个方面:
一是讲清农民经济社会合作的道理和政策,起到有关理念、政策、经验的宣讲者和教育者的作用;二是率先示范,在大家没有做或者不敢做的情况下,我们来做;我们很清楚自己不是主体力量,只是示范和参与、支持力量而已;三是协调和沟通的作用,比如把体制内和体制外的资源协调起来;把中部和东、西部不同省份的农民朋友们,搭建起经验交流的平台;把农民的经验性努力和相关部门的政策制度支持沟通起来。
其他真正持续性的努力探索,都是农民合作社带头人带着他们的成员在做。早期我们起到“外发促内生”的作用,中后期他们的组织、人才和资金一旦有了基础,就必然地“内生促外联”。他们已经具备自主发展的能力和一定的条件。
说实话,知识分子的力量若从一个地方撤出,群众在操作中可能更为现实一些吧,虽然多少会从理想状态中偏离一些。因为村庄的力量太弱了,他们很容易受外界各种力量的左右。村庄是“风能进,雨能进,知识分子能进,企业家也能进,政府更能进”的地方,有所偏离和现实化都正常。
你看那黄河,虽说总体上是向东流的,但在过程中还是因地形、地势条件弯弯曲曲的。
《决策》:在学术界,也有人认为您有些另类。您自己怎么看?
何慧丽:我是想探索一下“从参与到经验,从经验再到概念”的学术之路。我在辛苦、积极、认真地探索着,我很庆幸、很踏实、很自信。我想走一条本土化的“回归中国,回归农民”的学问,做一做现代化背景下的“留守群体、留守学术”之路。但我不知道,我另类在哪儿。
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睛雨表。我们有不忍之心,知道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哪儿,我们不想随波逐流,就想做该做和能做的一些乡村建设的事。应该说,10年来做的一些事,不是我一个人做的,是一群人做的。大家心思都一样,互相鼓励支持,共享经验教训。
《决策》:挂职的经历对您的人生有什么样的影响?您今后是如何规划的?
何慧丽:我感到,这10年是我人生中最为亮丽的一段时光,这段时光我主导参与了很多事情。这段经历对我今后的人生有着一些基础性的影响,它决定了我的学术和人生价值走向。今后做做学问,也可能会换一种做法搞乡村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