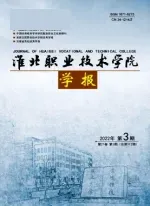简论“新文人画”
2013-08-15周曦曦
周曦曦
(安徽省淮北工业学校,安徽 淮北 235000)
新潮美术以其鲜明的哲学化倾向,使当今画坛大批超现实主义样式应运而生。由于它的出现是一种集体的语言试验,无疑给沉闷的中国画坛带来革命性的变迁;同时,其对于进一步深入探讨新文人画的理论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一、“新文人画”产生的社会必然性
新文人画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陈绶祥、边平山、王和平等人发起,试图借助传统美学中的深层的文化意识,来完成自身这一阶段性的试验,从而达到对传统美学回归意识的重新诠释。社会的改革导致思想界、学术界、艺术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进入反思和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不少青年前卫派作品表现了一种强烈的参与意识,这些作者希图在作品中表达他们对社会、历史以及人生的思考和忧虑,这类作品被称为理性绘画”。[1]然而,随着85新潮以来中国艺术已从大规模的群体式、观念式逐步向个体式、实用式的转变,加上真正与其现象呼应的批评界理论探讨没有展开,新文人画先天不足般地很快夭折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文人画这一产生还缺乏自身逻辑的必然性和对传统文人画的重新构建。
二、“新文人画”是对传统旧文人画的继承和发展
艺术发展有其本身完整的必然性和构建性,忽视这一规律必然导致悲剧的发生,中国传统文人画是传统中国文化精神的一种体现。在其发展过程中,由儒、道、释的导引,达到一种综合的超逸心境,并通过潜化修行,强化了水墨精神中的理性意识,更进一步完成与完善了文人的理想人格,这种人格是非具体的心理体验和具体的笔墨意境形式上的结合。中国古代的知识阶层、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心理结构是复杂丰富的。他们在文化发展史上的作用,及其价值的演变也是极为复杂的,但是文化和思想的创造教化和承传毕竟是由文人士大夫来完成的。因此传统文人画是一种文化的表层结构直接反映深层结构的文化心态。
如果说新文人画是现代文人对旧文人完善人格回归和延伸的话,那么就带有难以摆脱的悲剧意识,“他一方面使我们艺术环境进入开放不多吸纳新东西,更同时催生了艺术创作的浮躁心态”。[2]然而千百年积淀形成的文化却远不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可以完成的,而新文人画以表象的人格精神来掩饰真实的现状,是难以完成传统文人画家自我人品观的暗示和展现的。所以邓福星说:“从一定意义上反映了经过活跃、纷乱的十年之后的中国美术在进入新历程中的自我反思,走向沉潜便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3]“画如其人”、“人品不高、用墨无法”、人品的高下之分构成了文人画的价值观。作品自然也成为其精神价值的外在表现,是人格理性的内在象征。传统文人画不厌其烦地反复咏叹梅、兰、竹、菊,托物言态,必然要同内在的人格精神完善的结合,文人画家的人格正是由此通过自我淡化人生来实现的。明代董其昌最早提出了“文人画”这一称谓,并初步阐述了文人画的历史传承关系:“文人之画,自王佑丞始,其后董源、巨然、李成、范宽为嫡子。王晋卿、米南宫及虎儿,皆从董、巨得来,直至元四家黄子久、王叔明、倪云林、吴仲洼,节气正传。吾朝文、沈,则又远接衣钵。”[4]所以说道德精神的勤修苦练是文人画家的基础。而现代文人的思维意识和心理体验远比旧文人复杂,一方面“返朴归真,水墨精神”,另一方面“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这种半隐半仕的矛盾心理无疑给新文人画家带来极大的折磨。处于当今都市文明的文人,若想脱俗世以入山林,可谓寸步难行。它根除了文人仕隐的可能性,甚至每每俗世滚滚的激流扑面而来时,画家静态的圈层愈来愈小了。而画家的思维只能在静态的空间里固守灵性的纯洁,塑造理想的人格。
传统文人画以空灵、简雅的笔墨方式表现出超功利、现实之外的自我表象,讲究“清心寡欲淡泊明志”。不敢为天下先,柔弱自守,笔墨随着意识的导引而达到一种有目的性的方式。在传统哲学与美学的意义上,笔墨的渲泄是画家心性的表述,它强调来自自身的内省和顿悟,讲究“诗、书、画、印”为一体。在文人画中,处处皆可看到它们相互之间的影响和存在。文人画的水墨写真意味乃是“离形得似”,是对古典绘画技巧追求形似的有意贬抑,作画的过程中画者无需抑制情感的发泄,平衡了心理也净化了心灵,写的愉悦之性激励着画家,传导到画家的意识深层,心灵也豁然开阔了。画家在这些行为过程中,自我封闭于“象牙之塔”,自我神游于飘逸的状态。新文人画正是在此基础上赋予了旧文人画一些更加明确的现代意识,从而达到过去所遵从的价值在当今社会的重新认可。但由于它们只专注于用既定的方式寻找现代的含义,这类艺术只可能被当作权宜之计玩偶般迅速亮相,其结果难以完成自身内在的人格体验。
三、“新文人画”的衰落
90年代以后,中国的经济建设全面起飞,中国老百姓生活在急剧变化的社会中。由经济的快速发展引发的社会变革,令人目不暇接,艺术也越来越趋向个人化、多元化。新文人画在第四届展览之后便逐渐失去了针对性,而且普遍忽视现实感受,日益趋向矫饰主义,并带有明显的商业化倾向,丧失了它最初的活力和生命力。随着新潮美术呼声渐弱,新文人画更显得力不从心,与此同时,当代文人借助西方现代艺术观念来引导中国艺术跨向世界的可能性已彻底失败。
艺术应遵循自身存在的必然性与发展的更新性规律。新潮美术无论以何种恣态反复出现,只能被当作西方艺术形式上的填充,充其量不过是对西方现代艺术的重新注释,传统却被远远抛开。新文人画家花样的翻新是在外力强迫下进行的,因而自诞生起就处于一种工具主义的生存态度中。
当下出于对新潮绘画的反思和再认识,具有较高审美价值和文化意义的文人画艺术形式绝不会因现代艺术的冲击而消失,仍然具有其现在时和将来时的意义,不论今天的艺术家对重新建构新的中国绘画寄予怎样迫切的愿望和对传统持有多么激烈的反叛精神,现代中国绘画的发展一再证明,传统文化艺术的精神仍有其不可磨灭的审美价值。
然而新文人画的出现,毕竟是对传统文人画艺术精神价值在现代的弘扬和肯定,中央美术学院的薛永年教授认为新文人画“不但是新文人画不但是新潮美术中的一个别派,而且也是新潮美术开始根植于本土的一种健康发展”[5]。画家没有旧文人画家那种“十日画一水、五日画一山”的慵懒心理,无疑这对传统文人画赋予了一种积极的现代因素。新文人画正是在当前中国画面临困境的发展之中寻找契机来自觉完成内在的反省。当我们回过头来重新验证历史并与现实状况进行有目的的比较时,可以看出任何变更都不可能超越现存的文化基础。扔进了石头的池塘水面,会泛起不断向四周扩展的环形波纹,并变得愈来愈复杂。传统文化在当代的文化转型正需要艰苦的探索。“新文人画”作为一种艺术现象能够坚持十年之久,颇值得我们思考。“一个民族的特性尽管屈从于外来的影响,仍然会振作起来;因为外来的影响是暂时的,民族性是永久的,来血肉,来自空气与土地,来自头脑与感官的结构与活动,这些都是持久的力量,不断更新,到处存在,绝不因暂时钦佩一种高级文化而本身就消灭或遭到破坏”[6]。正如季酉辰所说“在失去传统审美意识很长一段时期后,新文人画能够在找回这种审美精神,在中国画发展史上绝不会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7]。
总之,中国绘画要走向世界,立足于世界艺术之林,只有沿着艺术发展的客观规律,潜心钻研,去寻找与解析传统中国画的经典元素,归纳其中的发展规律,重新构建内在的心理结构才能发展成为更具有现代意义的深远影响。
[1]陈绶祥.新文人画艺术——文心万象[M].长春:吉林美术出版社,1999.
[2]康明星.95中国新文人画展学术研讨会记[J].江苏画刊,1995(5).
[3]邓福星.走向沉潜——漫议90春季画展与“新文人画”及其他[J].江苏画刊,1990(5).
[4]董其昌.画禅室随笔[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5]薛永年.新文人画小议[EB/QL].(2010-06-12)[2011-11-26].http://www.ssmuseum.com/a/Learning/sm30n/2010/0612/274.html.
[6]丹纳.艺术哲学:上册[M].傅雷,译.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7]季酉辰.关于新文人画的意见[J].美术观察,199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