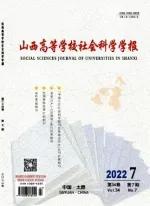完善情势变更立法构建诚信市场经济——以国际旅游岛住房建设为视角
2013-08-15王建文刘宛升
王建文,刘宛升
(河海大学法学院,江苏 南京 211100)
民商事合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细胞,双方当事人本着诚实信用、互惠互利的原则缔结合同,其中一部分履行行为持续时间较长的合同,受国家宏观调控、国际市场波动等影响,面临情势变更的风险。当履约环境发生缔约时无法预见之重大变化,致使维持合同存续的客观基础丧失、当事人之间的利益严重失衡,一方给付负担过于沉重,按照原合同履行明显有悖于诚实信用,立法应及时作出回应:建立相应的调整机制——确立情势变更原则。通过司法权的介入,强行改变原合同确定的条款或撤销合同,以社会本位调整权利本位,促使双方当事人再交涉达成新的合意,重新分配利益与风险,解决经济纠纷,以求获得实质公平,促进市场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
关于情势变更的定义,理论与实务界众说纷纭,各有侧重。著名民法学家梁慧星先生下的定义,概括全面、理解深刻:“合同有效成立后,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原因发生情势变更,致合同之基础动摇或丧失,若继续维持合同原有效力则显失公平,应当允许变更合同内容或解除合同。”[1]
诚实信用原则是法律体系的帝王条款,贯穿于民商事法律领域,较情势变更原则为上位概念,是填补法律漏洞、矫正可能出现的不公正后果的最后手段。情势变更是诚实信用原则的具体体现,出于维护利益平衡、公平正义之目的,赋予并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是现代合同法与时俱进的闪光标志。情势变更原则的实质,正是诚实信用原则的具体解释运用,是合同法律思想和制度革命性变化的自然衍生物[2]。
一、问题的提出:情势变更导致利益失衡、纠纷频发
自2010年1月4日《国务院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发布以来,海南楼市持续“高烧”,携重金而来的炒房团推动海南房价节节走高。6月份,海口房屋售价同比上涨50.6%,涨幅连续第五个月高居全国第一位;三亚房屋售价同比上涨50.3%,涨幅连续第五个月高居全国第二位。工程建设领域通常采用固定价款合同,业主单位为规避工程建设期间要素价格上涨的风险,往往对固定价款调整因素进行条款封堵,从而让承建单位承担大部分风险。因合同履行期限较长,受国际市场影响,钢材、水泥、混凝土、柴油等建材的非理性大幅上涨,新《劳动合同法》的贯彻实施使人工成本增加,这些直接诱发承建单位巨额亏损。
为抑制房价的过度上涨,调控住房销售价格和住房供求以实现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国家先后出台了一揽子房贷新政,改变了二套房、三套房的认定标准,提高了首付比例。海南切实贯彻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遏制投资投机性住房需求,保障群众的自住性需求。飙升的房价、房贷新政造成一部分购房者无法按原计划获得所需的银行贷款;而另一方面,与开发商之间的购房合同已生效,定金已支付,此时无力履行买方义务,需承担违约责任,购房者无权要求返还定金。因房价短期涨幅过大、房贷新政属于国家宏观调控措施,非卖屋买卖合同当事人可以预见,新政使原购房合同中的基础条款即预付金比例和房贷标准发生了重大变化,给购房者履行合同造成了巨大障碍,导致原购房合同赖以成立的基础完全丧失。购房者便以“情势变更”为由要求解除合同,返还定金;开发商则要求购房者严格履行原合同,否则承担违约责任。
二、情势变更原则的渊源与内涵
情势变更原则起源于12—13世纪的注释法学派著作《优帝法学阶梯注解》:假定每一个合同都包含有一个默示条款,即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作为合同基础的订立合同时的客观情势应继续存在,一旦这种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应准予变更或解除合同[3]。
情势变更是契约严守原则的例外。“契约必须严守”要求当事人依据契约自由和意思自治缔结合同,该合同一旦齐备生效要件,便在缔约者之间产生法律般的效力,必须严格遵守;除非违反强行法或当事人双方达成了新的合意,不得随意变更或终止合同,以维护私法自治与合同的严肃性,增强当事人履约责任心,保障交易安全。
现代社会经济飞速发展,情势瞬息万变,如果合同订立时赖以存在的基础性情势发生了当事人不可预料的重大变化,导致利益严重失衡,继续履行原合同便显失公平,给当事人带来有违预期的不合理负担。双方当事人对于特定环境的存在有共同预想,基于此预想缔结合同,因此应对情势的变更施以法律救济。情势变更是对契约严守原则的有益补充,它适应了市场供求状况瞬息万变和政府宏观调控力度增强的社会现实,妥善地利用法律手段解决了市场经济中的难题。
《德国债法现代化法》上的“法律行为基础障碍制度”、法国民法典的“不可预见理论”、英美法系的“合同落空原则”、意大利和秘鲁法上的给付负担过重规则、《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中的“艰难情形”,尽管各有侧重,但殊途同归,其目的都是运用诚实信用原则调适“契约必须严守”与“交易实质公平”理念之间的冲突。在我国,“契约严守原则”的例外就是“情势变更原则”。
所谓“情势”,泛指作为法律行为成立基础或环境的一切客观事实[4],如国家政策、利率、物价、汇率、国际市场波动等。所谓“变更”是指情势发生了异常变动,致使履约基础动摇或丧失。合同履行中情势变更事由主要包括:(1)市场经济固有的风险;(2)物价大幅度上涨或暴跌;(3)国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经济政策的重大变化;(4)产业政策、价格杠杆等各种经济导向措施;(5)国际市场发生大的波动;(6)货币大幅度贬值或升值。这些国家宏观政策的调整、相互依存度较高的国际市场情势变化,都可能导致履约基础的巨变。
三、我国的立法沿革
立法:1981年制定的《经济合同法》明确规定了情势变更原则,该法第27条第4款规定,由于不可抗力或由于一方当事人虽无过失但无法防止的外因,致使经济合同无法履行,应当允许变更或解除经济合同。但1993年修订《经济合同法》时,该条规定被取消了。
司法政策性文件:一是最高人民法院在(1992)第27号复函指出:“由于发生了当事人无法预见和防止的情势变更……仍按原合同约定的价格……显失公平”,当事人可以变更或解除合同。二是《全国经济审判工作会谈纪要》(法发〔1993〕8号文)指出:由于不可归责于当事人双方的原因,作为合同基础的客观情况发生了非当事人所能预见的根本性变化,以致合同履行显失公平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按情势变更原则变更或解除合同。三是200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的暂行意见》第27条明确提出,“因情势变更导致建材价格大幅上涨而明显不利于承包人的,承包人可请求增加工程款。但建材涨价属正常的市场风险范畴,涨价部分应由承包人承担。”
地方政府部门规章:2007年10月广东省建设厅公布的《关于建设工程工料机价格涨落调整与确定工程造价的意见》第5条规定:“在施工合同履行期间,当工程造价管理机构发布的人工、材料(设备)、施工机械台班价格涨落超过合同工程基准期价格10%时,发包人、承包人应秉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调整工程价款,并签订补充协议,作为追加(减)合同价款和支付工程进度款的依据。”
在《合同法》立法过程中,从第一草案到第四次审议稿都将情势变更原则写入草案。但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审议时认为:对情势变更难以做出科学界定,和商业风险的界限也不甚清晰,执行时难以操作,在合同法中做出规定的条件还不成熟,最终没有确立情势变更原则。
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发挥司法解释在统一合同法适用标准、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2009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这一司法解释回应了市场经济中民事法律关系因情势发生重大变化而适时调整的需要,保障了受情势变更影响的企业利益,对于统一自由裁量标准和裁判尺度、维护交易安全、减少合同纠纷、稳定经济秩序、实现实质正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情势变更在两大法系的理论基础、立法规制与司法适用
情势变更原则在两大法系的合同法理论中获得长足发展,通过立法确认,在司法实践中被谨慎适用,随后又在国际示范立法创新发展。
在大陆法系,情势变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情势变更包括不可抗力,因为二者均为不可预见无法避免的客观事件所引发,都是不可归责于当事人的原因。德国的“合同基础消失”理论即为广义,即如果由于不可控制的外来事件引起合同关系不对等,且给一方当事人施加了其事先未预料也不准备接受的不当负担,则应调整或终止合同[5]。而狭义的情势变更则是指不可抗力之外的意外事件。法国采取狭义观点,将影响合同履行的因素分为“不可抗力”和“不可预见”(即情势变更)。
在英美法系,英国上诉法院1903年判决的克雷尔诉亨利案最早确立了合同落空理论。美国将合同落空深化发展为三项主要内容:合同履行的不可能、合同履行的不现实与合同目的受挫。美国以“履约不可行”替代了“履约不可能”,即在许多情况下尽管义务人的义务不是绝对无法履行,但如果依合同履行会给义务人带来异常不合理的困难或可能危及当事人的人身及财产安全,这与履约目的并不相称,那么履约便是“不可行的”[6]。
大陆法系情势变更原则侧重于对变更的起因研究[7],而英美法系合同落空原则着眼于对结果的表述,侧重于该结果对合同履行的影响,二者在适用条件和制度设计上异曲同工,只是截取的时间段有所不同。
我国参加的《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79条第1项规定了情势变更原则,对于该条款我国并未保留。如果案件适用该公约由人民法院审理时,当然可以适用情势变更原则。此外,《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国际商事合同通则》规定的“艰难情形”、《欧洲合同法原则》的“情势变更”,都是为了“以公平合理的方式在当事人之间分摊由情势变更所产生的损失和收益”[8]。
英国、意大利允许合同目的落空时终止合同,德国更为灵活,在发生情势变更时法院不仅可以终止合同,还可谨慎地变更合同。《德国债法现代化法》第313条第1款和第3款赋予了因法律行为基础障碍而遭受不利的当事人以变更或解除合同的权利:“照顾到所有具体情况、特别是合同的或法定的风险划分的情况,不可期待合同一方当事人信守该不发生变化的合同的,可以要求调整该合同。”“合同调整成为不能或另外一方当事人不同意此种合同调整的,受损一方可以解除合同。”
法国相对保守,其民事法院一直奉行“条约必须严守”,只有行政法院允许适用情势变更原则。行政法院主要管辖公共服务合同、特许权协议等与社会公共利益息息相关的合同。如果这些公共合同因情势变更而受阻或被延误,可能会对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造成影响。因此,在发生情势变更时,行政法院认为私人企业有权从政府获得补偿[9]。
美国《统一商法典》第2—615条和《合同法第二次重述》第269条和第270条,在发生合同受挫后,可以调整合同条款:“如果合同基础丧失或有重大改变,一般需要变更合同使其适应新的环境。应当优先考虑尽可能地遵守合同,只有当合同不可能再存续的情况下,才能通过行使特殊解除权来解决或终止合同。”
五、情势变更的效力、立法完善及司法适用
我国市场经济运行中存在情势变更的客观事实,司法实践也确认该原则的适用,但法无明文规定,致使情势变更原则游离于法律的框架之外,审判实践无法可依,这种立法滞后于社会发展的现状亟待改变。正如梁慧星先生所言:“现在的问题是,是否在法律上不规定情势变更原则,就能够避免这种滥用?”[10]基于情势变更原则在我国立法上有确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司法解释不足以替代立法的需要,建议全国人大以立法的形式,在《合同法》或《民法通则》中明确规定情势变更原则,使其在制度上与发达国家接轨,为对外贸易及招商引资提供更多的法律保障,减少因不同国家制度差异而产生的贸易摩擦。
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应以符合其构成要件为前提:(1)事由要件,须有情势变更的客观事实。即因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社会经济形势等客观情势发生巨大变化,致使合同目的落空、双方利益严重失衡。(2)时间要件,情势变更的发生时间必须是在合同有效成立后至合同终止之前。(3)预见要件,即对于情势变更的发生,当事人在缔结合同时不仅没有预料到,而且在正常情况下,作为一个尽到了必要注意义务的理性人,是不可能预料到的。(4)归责要件,情势变更不可归责于任何一方当事人,各方当事人主观上均无过错;如果有过错,则应根据责任自负对各自的过错承担责任。(5)后果要件,即继续履行原合同则显失公平,有违立约初衷;或合同目的落空,履行已无意义,这是适用该原则的实质要件。
对于情势变更导致显失公平的程度的把握,《欧洲合同法原则》第6∶111条规定情势的巨变必须使得合同的履行变得“格外困难”;《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6.2.2条规定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均衡发生了根本改变,并提出了一个参考性标准,即“如果履行能够以金钱的方式加以准确计算,则履行费用或价值的改变达到或超过50%时,很可能就构成了根本性的改变。”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借鉴发达国家的立法经验,制定具体的操作标准,汇编典型案例,规范各级法院的统一适用。
在适用程序上,合同双方负有再交涉义务。即情势发生变更,履行不利方在合同尚可履行时,应本着诚实信用、避免损失扩大的原则,及时与对方就合同的内容、履行方式等重新进行协商。双方通过再交涉变更合同成本低、灵活性大、耗时短、节约司法资源,有助于减少情势变更带来的损失、保守商业秘密,实现双赢。相比之下,诉讼则成本较高、周期长、不利于双方日后的合作。只有协商不成时,才能通过法定程序诉诸法院。人民法院应奉行当事人主义,遵循“不告不理”原则,不得依职权主动适用情势变更原则。
情势变更原则的意义,在于通过司法权力的介入,强行改变合同已确定的条款或者撤销合同,在合同双方当事人订约意志之外,重新分配交易双方应当获得的利益和承担的风险,这就赋予了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可能造成法官的恣意[11]。法院受理后,应坚持调解为主、裁判为辅的原则,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对法官自由裁量权予以限制和规范,减少裁判的恣意性,增加判决的说理性,提升司法的公信力。
关于举证责任,根据《民事诉讼法》“谁主张,谁举证”的要求,主张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的一方,应当就情势变更的发生原因、导致显失公平的程度、与相对方再交涉情况进行举证。在司法实践中,具体判断是否构成情势变更,应以是否导致合同基础丧失,是否致使目的落空,是否造成对价关系障碍,作为判断标准[12]。认定“显失公平”应当进行经济成本核算,以当事人是否遭受重大亏损作为衡量尺度。适用合同目的落空,应以合同双方知道或至少应当知道该目的为前提。
情势变更原则的法律效力有两个:第一次效力是变更合同。按照契约严守原则,应优先考虑尽可能维持原有的合同关系,通过变更使双方利益恢复平衡:如增减合同标的数量、变更履行期限、分期履行或延期履行、变更标的物等。第二次效力是解除合同。当第一次效力尚不足消除显失公平的后果、继续履行合同不可行或者无法实现合同目的时,人民法院应践行诚实信用、等价有偿的宗旨解除原合同以恢复公平。
对于开篇提及的争议,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双方的事由未能订立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并导致商品房买卖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的,当事人可以请求解除合同,出卖人应当将收受的购房款本金及其利息或者定金返还买受人。”根据该规定,当购房者因情势变更无法向银行申请贷款而无力继续履行原购房协议时,可以判令解除双方的买卖合同,然后再根据交易的具体情况决定是给予相对方一定的经济赔偿还是返还其购房款本金及利息或者定金。
[1]梁慧星.中国民法经济法诸问题[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
[2]李 卉,孙 斌.情势变更原则的法理基础研究[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6(3):79 -81.
[3]杨立新.疑难民事纠纷司法对策:第3集[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334.
[4]王家福.民法债权[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3:399.
[5]韩 烨.对德国情势变更制度与履行不能制度的比较和借鉴[J].青年科学,2010(2):56 -58.
[6]车丕照.合同落空、情势变更和不可抗力[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2):52.
[7]袁长春.对《德国民法典》与《法国民法典》的比较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3).
[8]吴德昌.《国际商事合同通则》法律功能研究[M].北京:中国法律出版社,2011:28.
[9]杨 明.给付负担过重规则——情势变更原则具体化的一个例证[J].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
[10]梁慧星.合同法草案征求意见稿专家会议上的争论[J].前沿,1998(2).
[11]孙礼海.〈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立法资料选[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63.
[12]梁慧星.中国民法经济法诸问题[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1:226.
[13]孙美兰.情势变更与契约理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14]李先波.英美合同解除制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5]赵 莉.公平原则对契约严守的修正——国际示范立法中的情势变更[J].法学评论,2007(5):3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