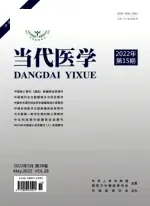腹腔镜胆囊切除术胆道损伤的防治分析
2013-08-15苏钰张亮张晋体
苏钰 张亮 张晋体
自1882年Langenbuch首次实施胆囊切除术以来,开腹胆囊切除术已经成为治疗胆囊炎的首选方法。1987年法国的Mouret医生成功进行了世界首例腹腔镜胆囊切除术(laparoscopic cholecystectomy,LC)后,更是开创了胆道微创手术的新纪元。LC具有创伤小、痛苦小、恢复快、切口小、住院时间短等显著优势,使之已经成为切除胆囊的“金标准”[1]。但随着此项技术的推广,医源性胆道损伤(bile duct injury,BDI)的发生率有较明显增加,由开腹胆囊切除术的0.1%~0.2%上升至LC初始阶段的2.2%,一般认为现在维持在0.32%~0.5%[2]。胆道损伤是LC手术最严重的并发症,后果严重,所以分析LC中胆道损伤的原因、预防和处理措施对于LC有深远的现实意义。本研究从1996年至今进行LC手术4000余例,共发生胆道损伤14例,发生率约0.35%,现将患者资料整理总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共14例,其中男性4例,女性10例,年龄17~76岁,平均46.7岁,慢性结石性胆囊炎(4例)、急性结石性胆囊炎(8例)、胆囊息肉(2例)等胆囊良性病变行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刚开展LC的前5年胆管损伤发生率较高,其中有10例患者均在此期间发生;后续5年发生3例,近6年发生1例。
1.2 胆管损伤的部位及类型 胆总管横断伤1例,胆总管完全夹闭1例,肝总管部分夹闭2例,胆管部分损伤10例;术中发现8例,术后发现6例。
1.3 临床表现 (1)症状与体征:本组术中发现胆总管横断伤1例,胆总管与胆囊管交界处灼伤2例,胆总管部分损伤5例。3例患者术后3~5d表现为黄疸,经手术证实为胆总管完全夹闭1例、肝总管部分夹闭2例,3例术后1~6d表现为程度不同的右上腹或全腹痛、压痛、反跳痛。(2)3例患者当天腹腔引流管引出胆汁。(3)3例胆漏病例经B超检查提示腹腔积液,腹腔穿刺获得胆汁2例,3例经MRI、B超检查提示肝内胆管不同程度扩张,肝外胆管损伤处连续中断及胆总管显示不清。
1.4 处理方法
1.4.1 8例术中发现胆道损伤,立即中转开腹,由于处理及时均痊愈出院。(1)胆总管横断伤1例,行胆管端端吻合+T管引流,T管留置时间为6个月,拔管前行胆管造影检查无狭窄,拔管后无胆漏及其他并发症。(2)肝总管与胆囊管交界处电灼伤2例,经中转开腹用5-0无损伤缝线缝合并置引流管,3个月后治愈。(3)胆总管部分损伤5例,其中4例为胆管壁小部分缺损,开腹后直接修补行肝总管空肠Roux-en-y吻合术后治愈。
1.4.2 术后6例中有3例于术后第1~6d出现腹痛、腹胀,经再次手术发现胆总管与肝总管撕裂电灼伤2例,肝总管与胆总管交界处撕裂灼伤1例,分别于术后3~45d行修补术,留置引流管,术后3~6个月痊愈。3例患者术后3~5d出现黄疸且进行性加重,分别于术后5~7d二次手术,1例行胆管端端吻合,2例行胆管空肠吻合。其中1例发生吻合口漏,经对症治疗6个月后治愈。1例患者因年纪较大,最后因多脏器功能衰竭而死。
2 结果
本组14名患者中13例治愈,治愈率92.9%;1例术后出现吻合口漏,对症治疗6个月后痊愈;1例患者因年老发生多脏器功能衰竭死亡。
3 讨论
3.1 胆管损伤的原因
3.1.1 主观原因 (1)医师腔镜操作经验和培训不足;(2)存在过度牵拉等不当操作;(3)腹腔镜手术指征和中转开腹时机把握不当;(4)医师的心理特质及心境,如过于自信及对危险缺乏足够认识。从学习曲线来说,80%的胆道损伤发生在最初30例,60%发生在50例以下的医师中[3]。本研究开展腹腔镜前5年发生胆道损伤病例偏多,随后逐渐减少,也符合这一学习曲线规律。
3.1.2 客观原因 (1)局部病变因素:起病72h以内行LC,其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低于72h以后患者,发生率为0.11%:1.13%[4]。究其原因为炎症初期,胆囊及周围组织水肿较轻,Calot三角尚容易辨认,随着病程发展,出现胆囊水肿加重、化脓、坏疽,与周围组织发生粘连,伴纤维化,甚至呈“冰冻状”,Calot三角结构不易辨认,再加上过度牵拉,极易发生损伤。(2)解剖因素:术中对胆囊管过长或过短、胆囊颈结石嵌顿或Mirizzi综合征引起胆囊管走形变化、胆囊管开口变异、胆囊动脉的起始异位、行程变异、副肝管和迷走胆管的出现等可能情况缺乏足够认识,导致解剖结构辨认错误、过度牵拉及草率分离、因出血盲目施夹、切割而损伤胆管[5]。(3)电凝钩使用不当:尤其在肥胖患者和急性炎症期,由于Calot三角脂肪堆积,反复使用电凝钩切割分离、电凝钩钩尖朝向胆管,尤其是长时间对大块组织凝切时更易电灼损伤胆管,发生迟发性胆管损伤。此类型更具有隐蔽性,术中不易发现,所以必须更加引起术者注意。(4)其他原因:手术器械设备故障等。
3.2 胆道损伤的诊断
3.2.1 术中诊断 可以通过以下几点进行判断:(1)胆囊切除术中,发现肝门处有异常的胆管断端。(2)术中有一种“不可解释的胆管出现”或正常切断“胆囊管”后又出现一根与肝内胆管相连的管道。(3)术中发现有胆漏。(4)解剖切除的胆囊标本壶腹部异常,如结扎处有两个异常开口或胆囊管残端呈喇叭口状。(5)对手术操作困难、术中出血多,怀疑有胆道损伤时,可行术中胆道造影或关腹前在Winslow孔放置引流管,有利于术后早期诊断。对于术中胆道造影多数学者认为不能明显减少胆道损伤发生率而无需常规使用,但对术中胆道损伤的判定有重要作用。此外还可以采用向胆囊内注射美兰帮助以及时发现胆道损伤[6]。
3.2.2 术后诊断 当出现以下几种情况时,应及时想到胆管损伤的可能:(1)术后出现黄疸;(2)出现腹膜炎的症状、体征;(3)腹腔引流管内出现胆汁;(4)B超检查提示腹腔积液,腹腔穿刺抽出胆汁;(5)MRCP或ERCP等影像学检查发现胆道连续性中断或胆总管显示不清。
3.3 胆道损伤的预防 掌握好以下几点可以较好预防腹腔镜下的胆管损伤:(1)实行严格的专科医师培训和手术准入制度,严格遵守手术操作规程,正确对待腹腔镜技术和操作者自身水平局限;(2)理论上对胆囊局部正常解剖、可能的变异情况以及在术中进行各种操作可能导致的解剖变形有充分的认识,避免解剖认知错误;(3)合理选择病例,术前充分进行影像学检查评估,由易到难,先从单纯的慢性胆囊炎开始逐步放宽适应证,对预防胆道损伤及其他LC并发症有重要意义;(4)操作时要轻柔,尽量保持解剖不变形,切忌生拉硬拽、盲目切割,必须反复提拉放松以助正确辨认;(5)合理使用电外科器械,尽量以冷分离为主解剖Calot三角,防止过度依赖电凝钩而造成热灼伤;始终保持术野清晰,避免盲目电凝或钳夹止血。沿正确的层面游离胆囊,防止分离肝床过深,必要时对增粗水肿的胆囊管以丝线结扎而摒弃钛夹;(6)根据具体情况妥善处理并充分显露胆囊三角,当炎症重,粘连较紧,水肿严重时,三角结构不易辨认,此时可以采用顺行和逆行结合分离胆囊,炎症严重时不必苛求胆囊管残端为0.5cm的标准而大大增加手术风险[7];(7)在局部解剖复杂、出血等不能清晰显示胆囊管或疑有癌变等情况下宜及时中转。中转不是手术失败,而恰恰是为了保证手术安全;(8)不断学习,积极尝试,提高手术成功率。最近几年大家对Rouviere沟逐渐重视,并利用这一解剖标志减少手术损伤。此沟是肝门右侧的肝裂,是右肝惟一的表面解剖标志,>90%的患者术中可以见到,是良好的定位标志[8]。LC术中将胆囊颈向前外上方牵引,显露Rouviere沟后靠近此沟从胆囊三角后方切开浆膜,而不要在肝十二指肠韧带侧进行操作,此时肝脏表面、胆囊颈和Rouviere沟平面便构成一个安全三角。由于胆囊颈向前外上牵拉后,胆囊管和胆囊动脉均位于Rouviere沟平面前方,即使过度牵拉导致胆管解剖变形或病理因素导致胆囊三角区结构模糊,也可以安全地在安全三角进行操作。打开胆囊三角后外侧的浆膜返折可以暴露胆囊颈和胆囊管之间的连接,紧靠胆囊壁进行分离,尽量靠近胆囊颈处分开胆囊管。“V”字形打开胆囊三角前后浆膜后顺逆结合分离使胆囊三角扩大,胆囊管便有了良好的活动度,有利于清晰显露胆囊三角结构,可以有效的减少胆道的损伤[9]。本研究近几年采用此法以来,胆道损伤发生率大大下降也验证了这一方法的有效性和可行性;(9)术后妥善放置腹腔引流管,虽不能防止胆漏,但对及时发现胆漏,并早期有效引流,部分病人可避免再手术,减少痛苦。因此,对于手术困难、急性炎症、水肿严重、疑有胆漏,均应放置腹腔引流。
3.4 胆管损伤的处理 LC手术胆道损伤治疗的关键是术中及时发现,立即中转开腹选择合理的术式是减少并发症的重要手段[9]。胆道损伤后胆汁进入腹腔很快即可出现胆汁性腹膜炎,如果并发化脓性感染,则腹腔炎症和患者病情进一步加重,此时进行胆道修补或手术重建,均可能导致手术失败,因此应先进行近端胆管引流,一般主张3个月后待炎症消退病情稳定再进行胆道修复和重建。对于胆道结扎后局部炎症较轻者,可在3~4周后再次手术,此时梗阻近端的胆管扩张、水肿较轻,术中容易寻找和进行胆肠吻合[10],此种修复方式较为符合生理,如果远近两端对合有张力应选用胆管空肠Roux-en-y吻合术,并通过吻合口置引流管[11]。而胆管部分损伤时,如果局部情况允许,此类损伤一般只需置入T管支撑引流+缝合修补,T管可保留1~3个月[12]。
总体来说,LC是一种安全和有效的手术方法,尤其是治疗胆囊良性疾病的金标准,符合外科向微创发展的趋势。但同时也必须认识到它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手术,同样存在着发生胆道损伤等严重并发症的危险因素,所以必须严格腹腔镜操作准入制度、正确认识LC的优势和局限、术中规范操作、正确认识Rouviere沟并处理胆囊后三角、顺逆结合切除胆囊、必要时及时开腹中转可有效减少胆管损伤[13],早期发现和正确处理胆道损伤对获得良好预后极为重要。
[1]Lau WY,Lai EC,Lau SH,et al.Management of bile duct injury after laparoscopic cholecystectomy:a review[J].ANZ Surg,2010,80(1):75-81.
[2]黄志强.黄志强胆道外科手术学[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10:343.
[3]Waage A,Nilsson M.Iatrogenic bile duct injury:a population-based study of 152776 cholecystectomies in the Swedish Inpatient Registry[J].Arch Surg,2006,141(12):1207-1213.
[4]Harrison VL,Dolan JP,Pham TH,et al.Bile duct injury after laparoscopic cholecystectomy in hospitals with and without surgical residency programs:is there a difference[J].Surg Endosc,2011,25(6):1969-1974.
[5]Kwon AH,Imamura A,Kitade H,et al.Unsuspected gallbladder cancer diagnosed during or after laparoscopic cholecystectomy[J].J Surg Oncol,2008,97(3):241-245.
[6]de Reuver PR,Sprangers MA,Rauws EA,et al.Impact of bile duct injury after laparoscopic cholecystectomy on quality of life:a longitudinal study after multidisciplinary treatment[J].Endos-copy,2008,40(8):637-643.
[7]Andersson R,Eriksson K,Blind PJ,et al.Iatrogenic bile duct injury—a cost analysis[J].HPB (Oxford),2008,10(6):416-419.
[8]刘允怡.肝切除与肝移植应用解剖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0:63.
[9]Giger U,Ouaissi M,Schmitz SF,et al.Bile duct injury and use of cholangiography during laparoscopic cholecystectomy[J].Br Surg,2011,98(3):391-396.
[10]Singh K,Ohri A.Anatomic landmarks:their usefulness in safe laparoscopic cholecystectomy[J].Surg Endosc,2006,20(11):1754-1758.
[11]Hugh TB.New strategies to prevent laparoscopic bile duct injury—surgeons can learn from pilots[J].Surgery,2002,132(5):826-835.
[12]Hugh TB,Kelly MD,Mekisic A.Rouviere's sulcus:a useful landmark in laparoscopic cholecystectomy[J].Br J Surg,1997,84(9):1253-1254.
[13]游晓功,施宝民,荆丽艳,等.胆囊后三角应用解剖及其在腹腔镜胆囊切除术中的临床意义[J].中国实用外科杂志,2008,28(11):975-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