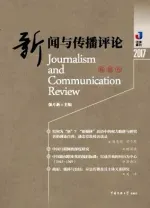组织民主、组织参与与批判组织传播
2013-08-15徐开彬
□ 徐开彬
由政治民主到组织民主
西方的自由民主主要关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民主,却鲜关注组织生活中的民主。组织包括企业组织、政府组织、非盈利组织等组织形式。随着跨国企业的不断扩张,一些学者开始关注企业组织对社会的影响以及组织生活中可能的民主形式。毕竟,社会资源的使用、技术的掌握、产品的质量、员工的工作关系等这些社会要素,很大程度上受企业组织决策的影响。由于绝大多数人要在组织单位中每天从事8小时工作,组织的价值观以及他们在组织单位中的经历,也能渗透到个人、家庭及亲友的生活之中。正因为如此,传播学者Deetz(1992)将企业的活动称之为“公司殖民”。在资本主义社会,私营业主或者大股东(shareholder)有权决定以何种形式来代表他们的产权与收益。但是,从民主的角度来说,其他群体如员工、客户、企业周边社区居民等,在企业中也有相关利益,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也应该有相应的代表形式来体现他们的利益。
在传播学界,对民主的传播形式的讨论,曾主要局限在言论表达自由与观点市场的开放。以这种形式阐述的民主,倾向于将民主描述为各自利益的表达,而不是一种强调促进个体发展与集体利益相结合的社会关系形式(Deetz,1992)。在一些人眼中的民主安排,对另一些人可能却是一种压迫。伽德马、哈贝马斯将传播视为一种参与,对传播民主的定义有所拓展。但是,哈贝马斯强调对一致意见的形成,却遗漏了另一个同等重要的方面,那就是,不一致与冲突能避免一致意见居于主宰地位时压制新矛盾与新观点。如何实现组织生活中的民主,美国的批判学派组织传播学者试图解答这一难题。
组织民主的内涵及形式
员工参作为组织民主的一种主要形式,有其伦理与实际意义上的考量。大体上来说,组织民主是指那些有助于员工在与工作相关的活动中更好地参与或代表不同的人群的原则与实践(Cheney等,1998)。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对“企业文化”的重视,西方国家的企业设计了各种有利于员工参与、有利于提高员工工作满意度的组织架构与项目,如工作丰富计划、质量小组、工作生活质量项目、员工自我管理团队、利润共享计划、员工持股计划等形式。比如“员工自我管理团队”,这一项目让工人接手原先属于监管人的职责,包括制定工作日程,选取最佳工作方式,考核工作绩效、聘用员工,采购货品,协调本团队与组织内其他团队的活动等。这种团队一般由5~9人组成,作为一种半独立组织形式,他们的成功取决于员工的工作动力与对团队的忠诚度。这种团队组织,有助于员工的意见更广泛更深入地进入决策体系,能让他们的人力与技术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员工有更多的自由与更高的士气,员工也有机会得到跨专业领域的培训及工作岗位轮流。从组织传播的角度来说,研究者主要关注员工如何在日常工作中通过传播行为建立有效的团队管理,以及团队管理是否能促进企业的生产效率。
这些组织参与形式,尽管是由管理方所设计和主导,还是有助于提高员工对自身工作的方方面面进行安排的灵活度,比如增加对时间管理的控制,学习和掌握工业与贸易技巧,工资与福利谈判,员工代表的选择等等。这与过去两个世纪世界各地的“合作社”形式生产管理也是一脉相承的,代表了对传统的资本主义企业进行民主化的努力。它们的共同点有三个:第一,超越组织管理中的官僚机制的局限性;第二,使所有员工参与决策过程;第三,克服劳资界限。
从传播学的视角研究组织民主
从传播学的角度研究组织民主,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民主或者员工参与形式的安排,如何在日常的组织生活交往中得以呈现。传播学可以使人们对构成“组织民主”或者“员工参与”的微观过程与具体行为有更深入的了解。这类研究带有深刻的“传播构成组织”的特点,即交流并不只是反映组织生活,而是组织形成的最基本要素。员工参与可以被描述为一种满足一系列标准的特殊传播行为,比如相对平等的参与、深度参与以及修改参与体系与规则等。同时,微观的传播学研究也有助于我们发现各种不同的组织民主模式的区别,发现这些参与模式对员工们分别意味着什么。例如,我们必须了解,员工对讨论、决策及其他组织活动,要到何种程度才构成有意义的参与。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即使是在高度民主的组织生活中,由于员工们的表达能力与技巧存在差别,这对参与也会产生影响。
组织民主化不仅仅是改变组织架构。一个最根本的要素,是组织成员角色的改变以及相应的交流方式的改变。角色转换是构成从传统组织到参与式组织过渡所需要的一系列微观组织过程的基石。有助于增加员工参与的民主形式,通常要求经理或主管们从传统的管理者角色,转换到伙伴、教练(辅导员)与帮助者的角色,也要求员工从传统的下属角色,转换到平等参与者的角色。这样一种转换,有助于形成更灵活的交流网络,也有助于组织成员对组织形成共识。
对领导交流的研究,特别能解释民主的微观形式能如何影响员工、管理者以及组织。众所周知的“转换型领导”,就带有民主的色彩,它强调领导的角色是激励员工,信任并与员工分享权力,与他们交往,激发他们的智慧,并回应员工的需求。对员工角色的转换,则要求他们敢于承担责任,积极参与组织事务,储备技能,向领导与同事寻求反馈意见,关心组织的共同目标,帮领导人分担任务以便他们将精力集中在最重要的工作上,帮助领导人与员工建立积极的关系,在决策过程中提供各种不同的选项,向领导提供真实的反馈意见,给组织创造支持氛围,对领导的正面行为进行肯定,敢于建设性地指出领导有缺陷的政策而同时不对领导本人进行批评等(Hackman & Johnson,2009)。
女权主义理论也对组织民主化作出过贡献。基于这种理论的组织形式,强调扁平组织而不是垂直管理官僚结构,强调合作而不是竞争性的工作原则,强调对员工或同事的支持,强调关爱以及平等待遇。同时,女权主义组织模式也对“工作”与“家庭”相分离的原则不予认可。这种理论认为,要理解员工的完整价值,既有必要认可员工与工作相关的“公”一面,也有必要认可员工与家庭相关的“私”的一面。由于员工在家庭或“私”生活方面存在差异性,了解这一点,可以避免让组织的参与活动使员工觉得超出了他们所希望或所能承受的程度。比如对一些孕妇或家里有小孩需要照顾的员工,她们会觉得过多的组织参与是一种负担,侵占了她们的私生活时间。
对参与式组织民主的反思
虽然参与式组织民主有各种优点,但它也存在一些潜在的缺点。最经典的一个研究发现,来自于Barker(1993)通过对一家美国企业自我管理团队历时三年的跟踪研究,他发现这种团队在实施过程中,逐渐演变成了一种协作型控制机制。这种控制的基础建立在工作中形成的价值观:将团队当作家庭,对工作拥有主动权,致力于团队的成功,所有的团队成员都要学会团队的所有工作职责,以便他人缺勤或离开时能及时填补空缺。Barker发现,这种团队控制机制,越过了原本鼓励员工参与组织活动的初衷,形成了一套紧凑的理性规则系统与强大的自我控制机制,甚至超过了传统的组织官僚机制对人的控制。团队成员之间的相互管理,以两种方式增加了控制:第一,规则和机制,比如比以往更严格的出勤制度,是团队员工基于一定的价值观、通过讨论自己制定的,因此将自己置于自己制定的规则下,这种控制更加有效;第二,由于协作型控制比传统的主管或经理的控制(如直接要下属去做什么)更微妙,团队员工感觉是自己在决策,自己在控制自己的行为,因而更愿意服从这种控制,更难以认识到这种控制机制如何束缚了他们的行动(Barker,1999)。因此,这种组织参与模式,反而成为一种更隐形却更有力的组织控制形式。这验证了社会学家Edwards(1979)早期的预测,这类员工参与模式,并没有改变组织中的权力结构,仍然只是一种管理工具而已。
员工参与的其他缺点包括:自我管理团队工作容易陷于无休止的讨论,不仅非常耗时,而且难以作出决策;为了团队集体,不得不放弃个体性;为了忠于团队价值观,不得不放弃个体的价值观与立场。员工参与,一方面让员工的声音得以表达,但同时也意味着员工在团队活动中要放弃一定的自主性。在很多高度民主化的组织形式中,比如工人合作社,它要包容所有员工的声音,这也是员工们为之所吸引的地方。但是,随着时间的过去,当员工们的自我不断地被合作社所淡化,他们会发现愈加难以改变他们所习以为常的组织结构。这确实是一种悖论。另一个悖论是,员工作为代表参与组织讨论与决策后,随着这些员工参与管理的越多,他们越来越享有多于普通员工的资源或信息,也越来越从管理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最终越来越脱离他们本应该代表的员工群体,员工群体与员工代表出现分裂。所以有学者认为,这种员工代表的机制,可能正是资方为了削弱劳工组织努力的一种企业策略(Grenier,1988)。
以上讨论的这些组织民主形式的问题,有赖于从批判组织传播学的视角去进行研究。除了逻辑思辨,Barker的田野工作研究方法提供了一种更实际可行的手段,它有助于我们从传播学的角度,去从微观的层面,观察员工如何参与组织活动,又如何陷入未曾预料到的悖论。这对于了解组织民主形式的利弊,都是非常必要的。
对组织民主中的传播之反思:传播与物质
作为传播学者,我们理所当然地强调传播(交流)行为对组织民主与组织生活的作用与影响。但是,更客观地说,传播毕竟有它的局限性。虽然组织的传播构成观(即组织由交流行为构成,没有交流就没有组织,见Putnam&Nicotera,2008)在当今非常流行。但是,交流行为只是一种符号象征行为,我们也不能过高地评价它在组织生活中的作用,比如我们就不能说,员工的一切组织活动都是纯粹通过交流或在话语中完成的。在组织生活中,物质有着它不可替代的作用。Bisel(2010)认为,话语交流是组织生活中一种必须的,但不充分的构建要素。话语交流的这种不充分性,使得我们有必要审视物质对组织生活的影响。员工的工作与生活条件,他们所关心的物质利益,他们的生产劳动本身,这些在传播学者的研究中都被忽视了。Ashcraft et al.(2009)特别指出,将组织的建构如果纯粹解读为话语交流而忽视组织的物质性,将陷入一种天真的话语建构主义。组织的传播建构观让组织显得仅仅是话语关系的集中体,它忽视了结构性的物质关系,忽视了正是在物质中,劳动被剥削,剩余价值被榨取。这种观点让人觉得工作任务是在对话中完成似的,以为财富不是通过剥削,而是通过对传播的策略运用来获取的。
尽管日常生活中的组织话语也能揭示出组织中的部分物质关系,但是,各种组织话语(如劳工合同、绩效考评等)根植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体系,有着它们的局限。如果不反思组织的深层次物质结构关系,就容易被表象的组织话语所迷惑,也难以超越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及其物质安排。从这点来说,纯粹的传播构建论反而是有害的。如同由分权机制以及代议制构成的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使得阶级关系不那么明显突出,组织管理中的员工参与机制,也使得组织中的物质关系不那么明显。例如,由董事会所作出的决定,貌似是由整个组织所达成的一致协定,它神话了董事以及少部分关键人物的利益,让它们显得代表了整个组织的利益似的。
虽然不同的组织话语之间存在竞争,但是,它们难以超越现存的资本主义话语体系及其物质安排。换言之,资本主义的物质关系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限制了话语的可能。比如,绝大多数学者,无论他们持有多么民主的思想,都会想当然地认为,他们的收入应该高于蓝领工人。这样一种观点,也是来自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关系安排,难以跳出现有的物质框架来看待这个问题。集中在组织话语本身,却不挑战组织的物质安排,就会陷入简单的话语论。那种认为组织形式纯粹是通过组织话语形成的观点,掩盖了组织成员之间的物质上的不平等,削弱了人的活动的影响。
全球化使得跨国公司为了降低成本,将生产基地迁往第三世界国家。因此,他们本国的经济活动出现了以服务业、知识密集型、金融为主的经济模式,白领工人取代了传统的蓝领工人,经济活动呈现非无物质化。这使得生产领域、特别是传统的劳工劳动过程不那么显眼。对于在这种社会语境下从事传播学研究的西方学者来说,他们当然容易将研究对象集中在组织话语、意义、文化与符号。但是,从全球视角来看,生产活动仍然是价值、剩余价值与资本积累的根本来源。生产活动尽管远离发达国家,它们仍然是西方非生产领域的最终来源。因此,尽管组织话语在西方的组织传播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显得合情合理,但是,将研究局限于组织话语,也掩盖了全球市场中的劳动分工,掩盖了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
当然,正如Ashcraft et al.(2009)所指出,我们也不是要回到符号与物质的二元对立去,而是要强调两者之间的互动。最理想的途径,也许正如社会学中“宏观-微观”辩证的研究方法,如Willis在《学会劳动:工人阶级的孩子如何找到工人阶级的工作》一书中对工人阶级的宏观与微观分析。传播学的优势体现在微观分析中,但如果能结合批判学派的宏观分析,则能做到两者兼顾。
中国语境下的组织民主与批判组织传播研究
1949年之前,中国的企业形式主要是民族资本企业与小规模企业作坊。在半封建半殖民性质的中国,组织民主无疑是一种奢望。新中国建立后,逐渐建立起国营与集体企业。在企业管理方面,最为突出的组织民主探索,是始于1960年的旨在实行社会主义民主管理的“鞍钢宪法”,即“两参一改三结合”: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这一管理模式,打破了资本主义企业的管理层与工人角色阶层固化的传统,在世界范围内,是企业管理史上的一场革命,它调动了工人的积极主动性,赋予了工人主人翁地位,同时也使得企业干部摆脱官僚主主义作风,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这种企业民主管理探索,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赞扬,随后在全国的企业得到了推广。
改革开放之后,在宏观经济领域,从计划经济逐步过渡到市场经济;在微观企业管理领域,实行政企分离,推行“厂长负责制”。从企业对外经营的角度来说,“厂长负责制”当然是无可厚非的,它可以调动企业领导及时把握市场的积极性。但是,在企业对内管理方面,这种“厂长负责制”,取代了先前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民主管理模式,企业领导干部的地位迅速得到加强,企业领导的官僚主义迅速滋长,工人群众的地位受到削弱,因而存在巨大弊端。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国有企业改制的推广以及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大规模下岗(即“员工买断”)的推行,工人的地位进一步削弱,企业组织民主不复存在。与此同时,新兴的私营企业流行“家族企业”管理模式,组织民主局限于管理高层内的家族成员,普通工人没有民主参与可言。在欧美外资企业,由于西方本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益重视员工参与、企业自我管理团队、企业文化,他们对从事中下层管理及技术含量高的中方员工尚能赋予一定范围内的组织参与与民主,相对于同期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与私营企业,组织参与与组织民主要更广泛。但是,与此相应的是,员工的工作时间往往更长,所付出的劳动也更多。在台资企业,虽然管理方能让中方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参与组织管理,参与对技术方面的问题出谋划策,但是在企业决策上基本没有中方员工的参与,一线工人则没有任何发言权,薪水也很低,而且还往往受到中下层管理人员的严苛管理。台资富士康集团在2010年发生的12跳,就是普通员工对台资企业严酷管理模式的抵制与控诉。在日资企业,虽然日方管理层一般比较重视中方的中高层管理职员,也能积极听取中方中高层职员的建议,但是由于中日关系的波动以及日方管理层与普通中方员工之间难以建立信任关系,基层员工也难以享有组织民主。
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部分企业出现经营不善,员工的薪资难以跟上宏观经济发展与通货膨胀的速度,工人对自身生存状况日益不满,企业工会也没有真正代表工人的利益去与资方谈判,工人缺乏有组织的代言人,导致员工只有以罢工等激烈形式进行维权活动,且不断发生。政府出于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往往简单粗暴地进行打压,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员工对企业主与政府的不满同步增长。
在这种语境下,批判学派的组织传播学可以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从以下几点研究组织民主与组织参与。首先,在央企及国有企业,作出决策的具体交流过程是怎样的?普通员工、中下层管理人员的组织参与机制现状如何?如何以微观的民主管理体制(而不仅仅是私有化一卖了之),确保企业高管遵守企业规则而不是为个人谋取私利。其次,在众多的私营企业,员工的劳动过程与交流过程如何?在“家族企业”模式下,通过何种物质及交流机制才能确保普通员工的权益及参与,如何才能避免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下“能对总统说不,却不能对老板说不”的尴尬局面,如何确保员工有对私人老板说不的权利?第三,在外资企业,批判学派也可以揭示一系列的矛盾与问题。例如,虽然很多欧美企业倡导“本土化”,但在管理实践中却并非如此。比如一些欧美企业在发展中国家对本土员工的培训,完全是按照欧美总部的标准流程进行,试图以欧美员工的形象塑造本土员工(Xu,2013,p.392)。再比如,能在欧美企业找到管理工作的中国员工,曾长期被视为比在私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工作的中国员工更加优秀,尽管如此,当这些欧美企业对中国本土企业构成威胁时,这些中方管理人员往往被中国民间视为“叛徒”,让他们遭遇身份危机,备感尴尬。同时,这些中方的中高层管理人员,一方面,在与中方普通员工相处时,要代表外资管理方利益;另一方面,他们在与欧美总部打交道时,又会感受不到充分的信任与尊重,甚至会不自觉地考虑本土国家利益。从交流学的角度研究他们的尴尬处境,对于理解欧美企业的微观管理与组织民主,对于跨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所进行的“新殖民”,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不管是什么性质的企业,微观的批判组织传播研究,可以有助于了解组织权力运用与组织控制的过程,了解员工相应的私下反对甚至激烈的公开反抗如罢工维权的过程,这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与立场,它们如何形成,又应该如何解决。马克思与毛泽东都说过,“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福柯套用他们的话说,“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反抗。”(1978,p.95)。权力与控制无处不在,现代社会的权力与控制运行往往能隐秘进行。按福柯的说法,“权力与控制的成功与否,与它们能隐藏其运行机制的能力成正比。”(1978,p.86)。自改革开放以来,用“厂长负责制”代替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两参一改三结合”为特征的“鞍钢宪法”企业民主管理模式后,企业管理层的权力逐步膨胀,权力与控制日趋明显,员工的反抗也越发激烈。如何促进企业管理民主,这是值得学术界、企业界、政府都必须关注的重大问题。正如本文开头指出的,毕竟,绝大多数人要每天8小时在企业工作,工作场所的民主与否以及如何确保这种民主,影响员工的工作满意度、身心健康与价值观。这些价值观也能带到家庭与人际关系之中,从而影响整个社会。
结语:从组织民主过渡到政治民主
没有组织民主的政治民主注定不会有真正的民主,而只是更有利于资本家的民主;只关心政治民主而不关注组织民主,注定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民主。相反,组织民主更微观更切实可行,能够立即给员工的工作、生活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而且也没有什么负面效果;即使有问题,也可以及时调整,不会如一夜之间的政治民主那样,对社会带来巨大震动甚至社会动荡(毕竟,失去政权,对于领导集团与既得利益集团来说,面临巨大的损失与未知的命运,因而政治民主的阻力往往巨大)。当组织民主逐步得到推广,不管是领导还是民众,在组织生活中逐渐学会以民主、对话与协商机制处理各种问题,则可以在实践中历练民主。由于组织生活对社会的影响,随着这种价值观的推广,政治民主也终究会水到渠成。
[1] Ashcraft,K.L.,Kuhn,T.R.,& Cooren,F.(2009).Constitutional amendments:“Materializing”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3,1-64.
[2] Barker,J.R.(1999).The discipline of teamwork:Participation and concertive control.Thousand Oaks,CA:Sage.
[3] Bisel,R.S.(2010).A communicative ontology of organization?A description,history,and critique of CCO theories for organization science.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Quarterly,24,124-131.
[4] Cheney,G.,& Cloud,D.L.(2006).Doing democracy,engaging the material:Employee participation and labor activity in an age of market globalization.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Quarterly,19,501-540.
[5] Cheney,G.,Straub,J.,Speirs-Glebe,L.,Stohl,C.,DeGooyer,D.,Garvin-Doxas,K.,Whalen,S.,& Carlone,D.(1998).Democracy and communication at work:An interdisciplinary review.In M.Roloff(Ed.),Communication Yearbook21(pp.35-91).Thousand Oaks,CA:Sage.
[6] Deetz,S.(1992).Democracy in an age of corporate colonization:Developments in communic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everyday life.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7] Edwards,R.(1979).Contested terrain: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kplac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Basic Books.
[8] Foucault,M.(1978).The history of sexuality(Vol.1,R.Hurley,Trans.).New York,NY:Pantheon.
[9] Grenier,G.J.(1988).Human relations:Quality circles and anti-unionism in American industry.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0] Hackman,M.Z.,& Johnson,C.E.(2009).Leadership:A communicative perspective.Long Grove,IL:Waveland Press.
[11] Putnam,L.L.,& Nicotera,A.M.(Eds.).(2008).Building theories of organization:The constitutive role of communication.Oxford,UK:Routledge.
[12] Willis,P.(1981).Learning to labor: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3] Xu,K.(2013).Theorizing difference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A critical dialogic perspective.Communication Monographs,80,379-3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