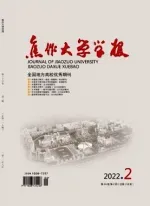回族女性文学与女性形象简论
2013-08-15苏文宝
苏文宝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宁夏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宁夏 固原 756000)
回族是在中国腹地诞生的一个民族,其诞生本身就是文化的有机融合,是伊斯兰文化本土化的坚实表现。在几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大体上表现为“二元”特点:一方面竭力融入以汉文化为主的祖国文化,另一方面也尽力保持本民族的文化底蕴。就前者而言,回族人在社会领域的处事方式几乎没有特别之处,但在后者,尤其是与宗教、民俗礼仪等相关的方面就表现出自身的特点,或者说是伊斯兰文化与生活的完全融一。回族女性的情况也大体如此。“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变成的。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定命,能决定人类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是作为整体的文明,产生出这居于男性与无性之间的女性。”[1](P17)回族女性与国内其他民族的女性在多数情况下的命运是相似的,但在寻求精神独立与心灵空间方面又有自身特点,信仰是其人格建构的重要力量。
“哪里有话语,哪里就有声音。”[2](P19)女性地位的变化与权利的获得,很大程度上反映在其话语表达的程度与范围方面。然而,普遍的事实是,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萨义德用于言明东方的观点也适用于此。威廉·布莱克说:“女性总是被当作空间来对待——反过来男性却总是被当作时间来考虑。”[3](P378)女性受空间的限制十分明显,同样妇女的解放也体现在空间方面。女性话语权随着其所处空间的变化而变化,这一过程也深刻反映着女性权利和地位的变化。由于传统上女性所属空间的狭小甚至悬置,其话语往往被遮蔽着。随着所处空间的增长,其话语媒介也逐步扩展开来。其中,文学便是女性话语的有力表达之一,回族女性文学无疑是其中一支强音。
当代回族女性文学发展取得了很大成绩,形成了一批女性作家作品,白山、霍达、马瑞芳、陈玉霞、于秀兰、丁朝君、阿慧、马金莲、毛毛等,她们一定程度上把这群缄默女性人群淹没在历史中的声音——其间既有历史、社会、经济、男权等方面的限制,更有家庭、伦理、文化等方面的受限——传达了出来。她们在其细腻的感情体验和敏感的社会触摸中深入回族女性生活和内心,打开了这扇尘封已久的大门。虽然在广度和深度上尚有不足,但她们成功开启了女性“自我表述”的话语空间。另外,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在回族男性作家笔下,女性形象亦在其人文基点上呈现出纤弱中的伟岸、素朴中的绚烂,展现出回族心灵的另一面。回族文学在近现代以来,尤其是新时期以来,塑造了一系列形象生动的“沉默”女性,在多个空间表达了女性的声音。
1.家庭空间:规训的话语场
“回族女性文化要比男性文化更具代表性,更具有回族传统文化的特征。”[4](P70)传统上(不仅是时间概念,即使在现代社会,“传统”观念与势力依然存在着),为适应圣俗生活的需要,回族女性几乎与汉族女性一样承受着伦理道德规范的限制,同时回族女性还要遵循伊斯兰教礼法。她们将儒家伦理道德与伊斯兰教礼法有机结合起来,很多情况下,后者成为对前者的调节,因此回族女性对儒家“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等既有遵循又有一定的超脱。但女性的生活空间主要在家庭内部,孝敬长辈、抚养子女、操持家务等,她们生命的时间与空间严重失调。从女性主义角度看,由社会话语制造的家庭空间是对女性自然生命的压抑与控制,使女性生命之流在男权话语塑造的家庭空间得以规训,从而塑造了女性的顺从和男性的优越。然而,这一认知无疑是“现代性”的,从“后现代性”的角度看,家在国人——男人和女人意识中的重要性是无法估量的。或许在很大程度上,家本身就沉淀为了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因此无论“家”是富裕或贫瘠、是团圆或残破、是物理的或精神的,基本上都是人生的支点。从中国叙事文学的发展看,一个鲜明而重要的主题便是家或家族,家族题材至今依然是重要的文学话语场。如果说西方文学凸显个人英雄主义,其追寻主题往往是人生价值、自由、信仰等方面,那么中国文学的追寻目标常常是家或者是此目标须在家(其的外延便是国)的空间中得以实现。
婚姻的规训。家首先是生命最基本的寓居之所,最基本的对象往往最重要,这一点在今天的人们面对高昂房价时的感受应该会更为切己地深刻。对于女性而言,获得家的空间又特别不易,人生的悖论在此显得十分“鲜活”。大致而言,未出嫁之前的女性尚属“未成人”,此阶段她们在父母之家学习准备一系列成人所需的基本技能和品行;出嫁是成人的过渡仪式,从此之后她们的人生将翻过全新一页。艰难与悖论恰在此时显现。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形成的社会无意识通常无视女性生命的独立性、个体性,或者说女性的鲜活生命往往被此无意识所遮蔽,所谓结婚,似乎不是两个个体生命的结合而是两股(两家)社会意识达成共识的结果。“婚姻的悲剧性并不在于它无法保障向女人许诺过的幸福,而在于它摧残了她;它使她注定要过着周而复始的千篇一律的生活。”[5](P544)因此,女性的出嫁充满了变数,自己今后的人生往往被他者决定。也可以说是女性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从此进入新家——自己的更是丈夫的、公婆的。女性的生活绝大情况下是在家庭内,但这个家又不完全属于自己,或许这也是许多女性不能也不愿离婚的重要原因。相反,当真的离婚或丧偶后,她们又会面临失去家的危险,自此基本上失去了自己的家,继续寄居婆家或子女家或回娘家。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几乎没有社会空间的女性,其家庭空间实际上也是被悬置的,其生命支点是由婚姻维系的一系列社会关系,因此独立的女性在传统社会实难存在。
可以说,婚姻是女性人生的新起点,然而也是新规训的开始,因此女性要谋求自己的话语权,就在此问题上表现得尤为强烈。在传统社会,这一要求实际上几乎无法实现,转而通过祖母、母亲等讲的民间故事在人们心间流淌着。如《马五哥与尕豆妹》《吆骡子》《红杜鹃》以及《花儿》中的许多女性形象,她们是艺术中最早“觉醒”的女性,也暗示出现实中压抑在女性心中无法表达的声音。“女性不是为他人、为丈夫而存活,而是为自己的理想、自己的追求而生存。这是一种极端的痛苦抉择,是一种孤注一掷的挣扎。”“女性的价值观、婚姻观表现在她们对自由的完美结合的无限憧憬,这种憧憬是以矢志如一为前提的。”[6](P59)也因此,她们在婚姻自由的争取中表现得十分坚决,甚至以命相争,这也从反面说明了婚姻规训力量的强大。
道德伦理的规训。传统上,女性主要生活于家庭内,但这里却没有真正的、实属自己的空间,那么她们除了生存于由男性奠基的家庭空间之外,大约就是由亲情建构的精神空间。家的重要不仅在其为生命最基本的寓居之所,同时也是一亲情空间,这在国人精神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在此特殊感情驱动下,她们一开始便肩负着对家的责任,久之责任又演化为爱。当她们自身也融入此无意识之中时(或在出嫁前或在其后),社会无意识便完成其规训,进而她们也会成为其规训力量的一份子。“在具体处境下的不同妇女有不同的态度与做法——或屈从和认同强大的主流制度和规范,或抵抗这种规范;或在认同主流规范的前提下,寻求父权性别制度的裂痕和空间,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在男性中心的制度下有所作为,以各种方法表达自己的声音争取自己的利益。”[7](P32)传统上对女性伦理道德方面的规训是“全面”的,从精神(如三从四德)、身体(如缠足)到空间(如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等,其目标大概是要塑造贤妻良母。实际上,“相夫教子”、“贤妻良母”意识也演化为了国人的集体意识。这一点在中国文学包括回族文学中表现得十分丰富,特别是浓重的“母爱”情结应与此有相当的渊源关系。“丈夫和儿女就是命,许多回族女人都是这样。”“阿依舍忽然觉得,女人真的就是一条河,不过这条河流不到远处去,而是流到儿女的生命中去了。”[8](P13-14)人伦亲情为人之天性,然而在此过程中,母亲们无疑牺牲了自我,也因此成就了儿女心中伟岸的母亲形象,“在‘额吉——母亲’这个普通的单词中,含有那么动人的、深邃的意义。母亲——人民,这是我们生命中的永恒主题!这个永恒的主题,是用金子铸成的,无论岁月流逝,无论地动山摇,她的光芒将永远闪烁!”[9](P15)
劳动的规训。由于家庭空间特有的规训场域,使女性将自身完全融入家人家事家务之中,很难超离出独立的自我,因此顺乎其规训便是主要的方式。“生活里的滋味只有当了女人才能真正明白,真正吃透。”[10](P26)“家里是转磨磨活计,忙死了还不知道忙了个啥。”[11](P180)家务活是女性“主内”的主要内容,常年累月没有间歇而且其价值不被重视,在体力和心力两方面构成传统社会的规训方式,即使在今天的家庭格局中仍有一定延续。另外一点是家务劳动的扩展。与城市城镇内取得工作机会的上班族女性不同,农村女性即使参与“男主外”的生产劳动,也没能取得独立的社会空间,或者说,农村女性由此实现的家庭外空间,严格而言尚不属社会空间范畴,在更大程度上是家庭空间的延伸。早在1950年开了“回回写回回”之先声的哈宽贵的《金子》《夏桂》就描绘了白金子、夏桂两个人物的劳动美,“展现了五十年代回族妇女那种忍艰耐苦、坚忍不拔、顽强上进、热爱集体的思想品格。”[12](P168)“这两篇作品,不仅第一次正面展示了解放后回族人民新生活的图画,而且第一次展示了回族妇女的新的精神风貌,形象地反映了在新的社会制度下……把她们从家庭的小圈子里吸引出来,激发了她们创造的活力……获得了独立生活的能力……妇女解放的程度,往往反映了一个民族解放的程度。”[12](P169)确实,这两个人物有一定的自醒意识和独立意识,但女性是早就“从家庭的小圈子里”出来从事田间劳动了,与男性从事着几乎一样的劳动。“女人翻身,从窑里翻到野地里干营生,驴一样苦,百八十斤重的大背斗压得连腰也直不起来。”[13](P189)并且,回家后还要接着干家务,“生活往往迫使我们(女性)出门当男人进门当女人。”[14](P55)就此而言,传统社会结构和农村生产方式下,女性极难实现“翻身”。随着教育的发展、意识的转变、生产方式的改进及进城务工等情况的持续发展,农村女性的社会空间才逐步显现出来。
许多作品反映了“女人之单纯和对婚姻的固守;女人生活的一维性、静止性与男人的复杂性、变动性之间的张力。”“相对于男人的流动性、变异性,女人的生活是静止的、坚守的,她们负载了更多的苦难、沉重,但却平静、顽强地活着,传承着民族的血脉。”[15](P73)无疑,女性的独立平等必须要在家庭空间实现,但由于多种原因,女性在家庭空间的规训下几乎不可能有真正的博弈,因此要直接在家庭内实现是困难的。从社会历史发展的情况来看,基本是由获得社会空间而获得真正的家庭空间和话语权。
2.社会空间:博弈的话语场
“女性,是一个常新而永恒的话题,女性,又是一个复杂的多元主题。准确、精到地描写女性是不容易的,因为,女性追求事业会有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烦恼,面对成功会有高处不胜寒的凄清,涉足爱情会有情到深处人孤独的无奈。”[16](P52)如果说文学表现家庭问题较为长久普遍的话,那么关于社会空间的问题却是伴随着女性现实处境的变化而进入文学,并且成为反映时代生活和女性精神心理的重要触点。“回族近代现代文学是一次人的发现,新时期回族文学又是一次人的发现,它们在不同的理性层次上都醒目地刻着一个大写的‘人’字。”[17](P62)或许,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发现”了女性,重新审视其长期被忽略的“人”的权利与价值。在社会空间尚未向她们张开之前,我们似乎看不到其物理空间的存在,她们的存在被悬置着,她们的声音被遮蔽着。与中国近现代历程相一致,这一“发现”是伴随着现代社会意识的来临和新中国的建立、人们当家做主后新精神面貌的体现。
五四以来,表现妇女问题的作品大多表现如祥林嫂一般受政权、神权、族权和夫权控制的妇女的麻痹、弱势与毁灭,或是知识女性“觉醒”后走向社会竭力反抗,争取自身的权利。但只有到新时期以后,女性的社会空间才现实性地扩大起来。回族文学正是在此期间实现了民族化发展,回族女性文学也逐步成熟起来。“老太奶说过最多的一句话是:‘唉,女人是腊月的蔓菁——受罪疙瘩哟!’”“‘现在的女孩子哟!’老母亲的感叹带着惊喜,‘从前的女人呐……’”[18]11回族女性文学深切关注到女性生活的新变并成为表现女性时代个性的重点。
女作家徐坤说:“生而为女人,本身就是不幸,就是苦命,一道凄婉哀怨的母性血缘,便是我们共同的道路。天生无法选择,而几许未来明亮的去处,却是可以通过抗争而达到。”[7](P68)这种内在的痛苦与抗争或许只有女性作家方能体会,回族女性文学在此做出了杰出成绩。于秀兰较早关注到女性的内在精神世界,她以自己的细腻与敏感捕捉女性心灵深处的声音,表现她们追求自我的努力、欢乐与痛苦。《芹姐》《也有沉沦的时候》《赛买姐》《心愿》《流逝》《在这条山沟里》《疙瘩沟的喜事》《昨天的太阳落了》《无词的歌谣》等探索了女性的人格独立与自我实现。如《芹姐》通过平静、无爱婚姻生活中芹姐的精神苦闷和困惑展现新的社会语境下女性意识的觉醒。《流逝》中的夏玉,既无法割舍对家庭的依恋又要坚持自己的独立人格,这种矛盾心理造成人物沉重的精神负担。可贵的是,在她笔下描摹了一批具有独立意识的理想主义者。如《也有沉沦的时候》中的芳,《无词的歌谣》中“我”、凌玲、亦伊等职业女性,他们在成功进入社会空间之后,又面临新的难题与困惑。为什么“历史过去了,然而,女人命运中的某些东西却一直丝丝缕缕地绵延到今天”[19](P37)?尽管艰难、彷徨着,但燃起于内心的理想是她们奋斗的支撑力量。丁朝君的“女人系列”从不同角度集中展现了女性的现实处境和精神焦虑;还有陈玉霞、阿慧、马金莲等许多女作家,都在这一领域作了深入探索。
总体而言,有这样几个特点。一、以农村为题材的作品反映家庭空间较多,且回族文化色彩浓郁,近些年表现进城务工女性的作品在增加。以城市城镇为题材的作品反映社会空间中女性问题较多,回族文化色彩相对淡弱,这也与回族文化在农村与城市的实际状况相一致。二、城市是女性从家庭走向社会、从家务走向职业的主要空间,因此也是女性争取独立平等权利的主要社会空间。作家们在此领域感受、触碰、发现女性在现代社会的新境遇、新的精神状态,由此又可以返观农村女性须面对的问题。三、许多作家自身未能完全摆脱传统意识的影响,以及对现代女性意识与自由意识感受不够深入,因此她们笔下的现代女性尚不够“现代”,多数人物形象处于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状态,这大概也是许多人物苦闷、焦虑、彷徨的主要原因。而形成这种创作状况的原因,或许与回族女作家大多出身于农村,或生活于现代化尚不充分的城市有关。虽如此,但却因此使回族女性文学不同于其时女性文学的欲望化书写,营构出了纯净、含蓄,富有审美张力的文学世界。当然,这一点也是受回族文化熏陶的结果。四、女性走向社会空间的过程也是女性觉醒的过程,这样她们在获得了一定的社会空间和权利之后,新的精神诉求便产生了。因此,女性在社会空间的博弈,既表现为现实层面,也表现在精神层面,与之前将自己的生命意义寄托于他者不同,此时真正意义上的自我意识萌生了。五、回族女性另一重要的精神空间,即信仰在她们生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信仰空间的影响与人们的虔诚度成正比,越是信仰笃诚的人,其影响越大,对信仰者的意义也越大。
下面以霍达名著《穆斯林的葬礼》试作分析。这部作品有两条主线,一是再现了吐罗耶定、梁亦清、韩子奇、梁冰玉、韩新月等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二是以韩子奇与梁君璧、梁冰玉,韩新月与楚雁潮的爱情为线,表现了他们的情感历程。其中三位女性形象很有代表性。
梁君璧是一位非常典型的回族妇女。没怎么上学,她的生活空间主要在家庭,是传统女性形象的代表,尽职尽责做着自己的事。但是随着时事的变化和社会的发展,她的“落后性”就逐渐显露出来了。当自己的丈夫和自己的妹妹带着韩新月来到她面前时,巨大的刺激使她的性格发生了很大转变。丈夫、妹妹对自己的背叛,爱情的覆灭、亲情的疏离,几乎将她逼入了绝境。其后,她在没有爱情的婚姻家庭中,将心思全部投入到抚育孩子和宗教功课方面。后来,当新月与汉族楚雁潮恋爱后,她极力反对。由于梁冰玉与韩新月的悲剧人生而愈显其“恶”。她与巴金《家》中的觉新一样,虽“守旧”但在忍辱负重中支撑着家,受到的伤害并不比那些“新人”少。她与妹妹、女儿的“矛盾”实际是“旧”与“新”之间时代文化的碰撞,是传统女性意识与现代女性意识的磨擦,是女性的社会话语向家庭规训话语的宣战。在此激烈对峙中显示出作家的老练深刻,使梁君璧成为这部作品最成功、最饱满的女性形象。
梁冰玉,现代知识分子,是摆脱家庭空间束缚而走入社会空间的新女性,但作品对此交代比较模糊,她的现代意识主要表现在爱情方面。她有鲜明的自我意识,在爱情中有清醒的追求和自主精神,拒绝了自己不中意的追求者,果敢地爱上了自己所爱的人。但当她和韩子奇回到北平后,由于姐姐的阻挠更由于对韩子奇的失望,又毅然再次踏上追寻之路。这次出国与前次出国留学不同,“不是找谋生的路,也不是去寻找爱,而是去寻找自己,人可以失落一切,唯独不应该失落自己……从今以后,将开始独立、自由的人生了。”[20](P612)她身上体现了现代女性可贵的自我意识,为心中的理想即使受伤也不屈从。这与梁君璧遇到自己丈夫的背叛只能忍耐完全不同。
韩新月是从梁君璧向梁冰玉之间的“过渡”,是由家庭空间向社会空间的发展。新月是一位优秀的大学生,无疑教育是女性由“旧”向“新”进展的主要方式。如果不是早逝的话,她必将完成自己的过渡而成功进入社会空间。在她这里,作家选择了棘手的话题——信仰不同而造成的分歧,但作家也以人物的早逝巧妙地回避问题的方式化解。在爱情问题上,她与母亲梁君璧之间的意见分歧,不仅是现代意识与传统意识之间的,而且也是自我意识与家庭观念、民族信仰之间的分歧。在新月这里,自我的独立与自由是不可触碰的底线,而在母亲那里,信仰是不可违越的底线。
《穆斯林的葬礼》以深邃的历史视野和细腻的感情纠葛将女性的追求、坚守、矛盾、苦闷等现实与精神命题立体地呈现出来。对一部完稿于1987年的作品,已具有非常强的前瞻意识了,而它提出的问题,即使在今天依然是讨论的热点。
“文学文本并不是简单地或被动地‘表达’或反映它们所处的特定的时间和地点的意识形态,相反,它们是充满了冲突和差异的场域,在这个场域中,价值和前提、信仰和偏见、知识和社会结构既得到了表征,同时也在这个表征过程中被变形”[2](P170)。在国人传统观念中,“男耕女织”、“男主外女主内”等思想将男性划归于社会一域,而将女性自然划归于家庭一域,其间无论女性付出多少,都似乎视女性依存于男性(家庭依存于社会),并因此衍生出一系列伴随人生始终的道德要求。从少女到出嫁到为人妻为人母,女性几乎很难获得自己的独属空间,总是被隔离于家庭内,社会于她们几乎无缘且处处设防并排挤。家喻户晓的祝英台、花木兰等故事,都是在女性假借男性身份之后才展开的。鲁迅说,娜拉出走后要么回家要么堕落,看来不仅适用于其时的西方,或许在中国绝大多数历史时期都是更为适用的,因为社会没有为女性提供其他可以跻身的空间。因此无论是从西方的《简爱》开始还是中国新文化运动以来,女性解放的主要目标是寻求社会空间。随着现代社会的到来和发展,社会空间逐渐向女性张开并扩大着,其时女性社会空间的获得主要是赢得工作岗位即经济独立。这是女性从家庭走向社会的重要方面,但也是最基础的方面。当女性取得一定经济地位,愈加发现自身与男性在诸多方面权利的不对等,因此在教育、政治、精神等方面寻求更加平等的权利和精神独立。大致看来,女性由家庭走向社会、走向精神独立(男女平等),是现代社会思潮的一部分,女性由社会“制造”的性别空间觉醒并“革命”式地追求独立、平等。然而任何事件的意义都必须在其所处语境中被理解,“超语境”的解读往往在获取“一般”的同时容易忽略具体事件的所指,从而使其所指空洞化。与新文化的知识分子启蒙相一致,现代社会的女性主义及其运动,活动主体都是知识女性,而知识女性的活动空间主要在城市,相对于大多数未能“知识”的女性和广大农村,除了“被启蒙”之外,其具体情形是怎样的,反而一定程度上被忽略了。回族女性作家细腻地发现了这一点,审慎地切近、发现、表达着,“文学之于她们,有种对待生命的神圣感,她们在生命与精神的跋涉中完善和充实自己,在跋涉中寻求生命的意义和价值。”[15](P71)也因此可以说,她们是回族女性话语的代表者、言说者,她们以纯净的文学之笔抒发着那些沉默着、压抑着、尘封着的女性心声。随着回族女性文学的茁壮成长,我们看到这声音已穿破历史烟云的遮蔽,淳美而洪亮!
[1]西蒙娜·德·波伏瓦.女人是什么[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
[2]詹姆斯·费伦.作为修辞的叙事:技巧、读者、伦理、意识形态[M].陈永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3]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4]丁宏.回族妇女与回族文化[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8,(2).
[5]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6]马兰,闫国芳.回族叙事诗中反抗的女性形象[J].昌吉学院学报,2008,(2).
[7]荒林.中国女性文化[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
[8]李进祥.女人的河[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2.
[9]张承志.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J].人民文学,1978,(10).
[10]马金莲.碎媳妇[J].回族文学,2008,(4).
[11]石舒清.灰袍子[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2.
[12]杨继国,何克俭.当代回族文学史(上编)[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
[13]马知遥.静静的月亮山[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2.
[14]丁朝君.爱我所爱[J].朔方,1992,(12).
[15]郎伟,赵慧,马梅萍.2004年度中国回族文学发展述评[J].回族文学,2005,(2).
[16]丁朝君.论南台中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J].朔方,2000,(10).
[17]王锋.纯净而深沉的生活之歌:评回族女作家于秀兰笔下的女性世界[J].朔方,1994,(10).
[18]阿慧.皂角树下的女人[J].散文百家,2010,(3).
[19]毛毛.游历西藏[M].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1998.
[20]霍达.穆斯林的葬礼[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
[21]安德鲁·本尼特,尼古拉·罗伊尔.关键词: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M].汪正龙,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