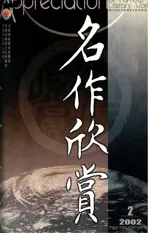以多元化的名义——20世纪末的笔墨语言探索回顾
2013-08-15潘少梅浙江传媒学院杭州310018
⊙潘少梅[浙江传媒学院, 杭州 310018]
作 者:潘少梅,硕士,浙江传媒学院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美术理论。
当20世纪末吴冠中提出“笔墨等于零”时无疑是要受到当时传统国画家的口诛笔伐的。因为这个敏感的“零”意味着一种彻底的否定,几千年积淀的笔墨系统,怎么就等于零了呢?否定了“笔墨”,中国画还剩下什么?但“笔墨等于零”引发的对“笔墨无止境”命题的探索则预示着之后中国画多元化发展格局的形成。实验水墨画家的群起及围绕多元化艺术价值评判方式的改变展开的一系列的实验水墨探索在不同的观念、形式和技术间碰撞,呈现了错综复杂的中国画发展状态。但无论是哪种主张,在中国画多元发展的今天都能找到合理的理由。
一、笔墨的纯化
在20世纪末消解中国画笔墨的暗流中,大多数的国画家并不一概反对笔墨,他们刻意追求的正是笔墨的痕迹,让笔墨成为独立而完整的艺术因素。在这些实验水墨画家看来,笔与墨、点与线及其组合是构成中国画形式美的重要因素,笔与墨的抽象意义是可以单独进行研究的,它好比音乐中不同音高、节奏和旋律的乐音,两者组合起来可以表现出有如音乐一般的画面节奏感和旋律之美。传统笔墨观强调笔墨的叙事性表达而非独立的艺术因素。“笔墨等于零”实质上是把笔墨提升到独立的艺术形式层面进行全新的观照。吴冠中将自己的这种艺术思想在中国画创作中加以实践,作品中的粗点细点、枯线湿线交织回旋,产生一种优美的音乐节奏,形式与心灵同构反抗“以形写神为山川写照”的传统创作方式,笔墨是其心灵的轨迹,形式解释内心的感受。这种心灵的轨迹,不是斧劈皴、披麻皴等各种皴法,而是线与色的音乐空间,抽象、单纯而具有节律。把笔墨看做是表达视觉美感及独特情思的手段而非独立的精神要素,从抽象绘画的形式角度来通融具有独立审美意义的笔墨,以笔墨形式的美感释放笔墨的精神性重负。这种对形式美感的追求成了当时中国画坛一种潜在的自觉。画家们在作品中刻意孤立画中的笔墨,放大局部的笔墨痕迹,摆脱详尽的叙说方式,使图像表现处于朦胧状甚至被逐渐消除,在他们弱化了人物形象的人物画中甚至出现人物画没有“形象”。他们旨在表现笔墨落在宣纸上瞬间的物理性,单一纯粹成了他们的艺术追求,看到了传统水墨为现代水墨提供的可能性。这些水墨画家们关心的是水墨作为一种创作方式和今天的生存经验发生联系的可能性,希望获得水墨性绘画对当代观念问题的发言权,希望寻求新的水墨性话语来表达他们对当下存在和人类共同问题的关注,努力确立自己的艺术语词规范。如朱青生的作品常以数字号码命名,如《09929》《0990》等。从题目的命名方式来看,画家有意摆脱详尽的叙说方式。画面中尽可能体现墨色的浓淡干湿,大面积空白产生强烈的空旷感,笔墨成为独立的审美因素。戴光郁的作品《7.23装置》直接泼墨在纸上,追求墨落到纸上最单纯的物理性美感。石果的作品最大特点就是用“拓印”碑帖的手法取代传统水墨中的“书写”特征,他延伸和强化了这种拓印的痕迹,强调符号的边线力度。他的作品《八大山人殁三百年祭》系列将八大山人的一些艺术语言和当代的符号拼接,改变了传统的随意性、书写性表达方式,强化了画面的语言张力。
二、视觉的冲击
在20世纪末,视觉艺术已经成为艺术中处于支配地位的形式并且成为文化的核心构成。自西方现代主义以来,艺术历史使命的减弱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视觉文化正在发生着从传统形态向当代形态的转变,这个转变是从内容主导型向形式主导型的转变,是从“看什么”向“怎么看”的视觉范式的转变。伴随着视觉文化的发展,水墨艺术创作在其中的针对性逐渐成为自觉。现代水墨画家摆脱了“笔墨至上”的观点,拒绝再承受笔墨的精神重负。他们更乐于尝试审美形式本身所带来的趣味判断和视觉冲击感。现代水墨在创作探索中努力实现的正是以发展审美风格的形式因素来凸现视觉的合法性。具体而言就是在各自的作品中以某种特殊方式组成某种特殊形式以激起观者的视觉冲击。从纯视觉追求方面创作的国画家大多注重装饰美、重复美,强调设计性甚至装置性,以水墨的精神图式撞击现代心灵。也有些画家更新了现代中国画在视觉空间中的体验性。如王南冥的作品《字球》,他把用中锋行笔在宣纸上写满线条的作品一张张揉成一团,采用多种装置手段把无数的字球吊在空中组合成一个大球、一堵墙,通过改变平面性的空间产生全新的视觉效果,让视觉接受前所未有的冲击体验。李华生的水墨作品《99.1—99.2》完全抛弃了书法意味,没有任何图像的述说,只是专注于墨线的规则排列,层层叠加,积线成网,将现代水墨的形式逼至极简,以对抗当时一些以“大”以“满”为特征吸引观众眼球的中国画。这种极简形式使中国画走向自身极限的边缘也就必然导向观念,导向其他媒介和表达方式。“极简”取消了画面有形的图像、色彩、结构等所有传统的绘画因素,同时也取消了绘画本身,让人有一种中国画的笔墨终结了的哀叹。事实上,追求视觉冲击的思潮可能会促成一种新样式的诞生,但新样式未必一定要取代旧样式,它们是并存的。毋庸置疑的是,观念的解放为中国画创造了许多创新的参考。如郑强的作品《静观之图》旨在传递视觉图示的创造性组合,背离了传统中国画的意境追求原则,完全与抒情和优美无关。他借用了中国古代传统针灸图和相命书插图的形式加进一些自己臆想的形象,用这种七拼八凑的样式企图造成画面既传统又现代的印象,它无法归类,它不是写意也不是工笔,一些臆想的形象旁边还加上一些如条形码、CIH病毒、TV等符号,让人感觉荒诞不经。引用作者自己本人的话来说,就是“使观赏美术作品时的愉悦感和趣味性大打折扣,因此,应该向观众道歉”。这些作品直入中国画的色彩禁区,追求光怪陆离的色彩效应,色彩压倒了墨色,甚至淹没了线条,技法混杂,感觉异样,从本体上颠覆了传统中国画的创作思维和观看方式。
三、观念的符号
经过了后现代的洗礼,人们对任何艺术形式与观念进入当代中国画的实验都抱以宽容的态度。有些画家甚至抽空了笔墨的物理属性,从观念艺术的角度来看笔墨,将笔墨仅仅视为一种传达观念的符号,以物质媒材的介入走入多维空间。它以肯定差异为前提,无法用传统经验解读,强调符号能指功能的开放性和多义性为中国画的现代转化提供新的方法论资源。如王璜生的作品《文明祭》用两幅作品展示双子大楼正在坍塌中尘土飞扬的情境,并在两幅作品之间用电视不断播放“9.11”现场画面,这件作品糅合了装置艺术的展示手法,超出了传统中国画的创作范畴。王天德的作品《数码系列》打破了纸墨的平面性。他用烟头烫烧掉文字使文字的形体具备独特的空间感,然后再衬一张完整的文字作品在烫烧镂空的作品下面,让光线透过两者之间的空隙使底下的文字隐约可见,将传统中国画的符号与当代装置艺术、观念艺术结合,打破了传统的欣赏习惯,开拓了一种全新的表达方式。戴光郁的作品《吸纳·冥想》对笔墨做了全新的阐释,把笔墨的书写性消解得最为彻底。他直接将笔墨用于行为艺术,他把毛笔和宣纸看做是一种可用的媒材并非神圣的传统文化资源,他甚至邀请市民观看,参与制作,使中国画变得世俗化、平民化。从创作的角度来说,选择艺术方式是个人的意愿。从接受者的角度来说,虽然创作中的笔墨观念符号化取向也强调艺术中的意义表达以及这种表达的社会学属性,但它往往因为有意识地让艺术形象或者媒介脱离原来存在的空间,或者将不同意向的媒介进行组合造成作品的整体涵义与观众的日常经验在视觉、心理上产生某种偏离使意义的表达陌生化。这对传统水墨的平面性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加上一些看似任意为之的方式手段以及艺术与生活之关系的新视角艺术体验都使“观念中的意义”这个问题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拷问。
四、开放的媒材
贡布里希认为:“如果确实有什么东西标志着20世纪的特征,那就是实验各种各样想法和材料自由。”对于中国画作画材料固定性的质疑源于20世纪初,徐悲鸿、林风眠等人都曾不约而同地认识到工具材料在绘画中的重要性。徐悲鸿在《中国画改良方法》一文中通过中西绘画比较,得出了“中国画通常之凭借物,曰生熟纸,曰生熟绢,而八百年来习惯,尤重生纸,彼生纸最难尽色,此为画求进步之大障碍”①。林风眠指出:“我们的画家之所以不由自主地走进了传统的、模仿的、抄袭的死路,也许因为我们的原料、工具有使我们不得不然的地方罢?”②20世纪末,扩大笔墨范畴则成了大多中国画家的共识。发挥水墨材质特点将其作为当代艺术创作中的一种媒介因素,不必死守笔墨语言的神圣,不能因为坚守笔墨的书法性用笔而阻塞了笔墨技法的发展,材料更新会为笔墨表现力的拓宽提供更多的可能性。左正尧立足于笔墨媒介材料的物质纯粹性提出了“中国纸墨”的概念,把“笔墨”的概念置换成“纸墨”。罗一平认为“纸墨”比起“中国画”、“水墨画”等概念更能避免中国画概念国度的封闭性和文化的模糊性,具有更多的文化开放性、包容性和文化延展性,可以保证纸墨艺术由物质媒介向观念媒介的转化和变革。③“不择手段、择一切手段”的开放态度使笔墨的范畴得以延伸。如刘国松有感于传统笔墨表现的局限性而另辟蹊径,发明了可以层层撕掀的“国松纸”。将纸筋与画面上的山石纹理巧妙地融为一体,丰富了水墨语言。材料的开放性刺激了画家探索水墨新语言的兴趣,也强化了笔墨形式之外的视觉冲击。
20世纪末的这些笔墨语言的探索是在全球化语境下对中国画的转型所面临的表达性的匮乏进行的自觉反思,其动因更多来自中国画内部对传统笔墨在当时中国画中的艺术价值如何的思考,以及在全球化语境下是消解其语言特色走向世界,还是保持其民族艺术特性的两种不同主张在中国画笔墨问题上的反映。民族特色能以“特异”吸引不同眼光,但这种特异会带来陌生感,造成交流的隔阂和障碍。而以消解中国画的语言特色为代价走向世界的观点则带有把中国画的艺术价值停留在别人是否稀罕上的自卑心理。因此在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上,应以民族性的东西反映世界性的内容,表现人类普遍生存境遇,用形式决定中国画的世界性,用内容决定中国画的民族性,从一个新的角度审视这个世界。
① 徐悲鸿:《中国画改良方法》,见郎绍君,水天中编:《二十世纪中国美术文选(上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版,第40页。
② 朱朴:《林风眠话语》,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34页。
③ 卢辅圣:《中国画的笔墨世界》,《关于笔墨的论争(朵云54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1年版,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