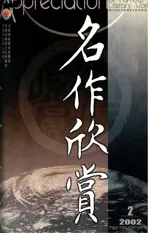论《蒹葭》“秋水伊人”意象及其哲学表现
2013-08-15刘应全云南大学滇池学院昆明650228
⊙刘应全 华 娟[云南大学滇池学院, 昆明 650228]
作 者:刘应全,哲学硕士,云南大学滇池学院中文系主任,讲师,首批青年学术骨干,2011年厦门大学人文学院进修,研究方向:中国诗学与中国文化;华娟,云南大学滇池学院教师,研究方向:民间文学与民族文化。
一
意象是中国古典文论独创的美学概念。理论上的意象,最早滥觞于《周易》大传。《系辞下》云:“《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系辞上》云:“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易》传所说的“象”虽是指符号化的卦象,“意”是指圣人体察的天意,与审美和艺术远不是一回事,但其中所包含的立象尽意、系言明象的思想,对后世的艺术创作和意象理论却有一定的影响。“意象”这个词的出现,最早见于王充《论衡·乱龙》,但其意义与文学艺术仍有较大差距。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经由美学大家刘勰的理论完善和意蕴改造,作为艺术美学范畴的“意象”方才大体形成:“意”是作家的主观心意,“象”是作家主观心意中的物象。①因此,文学意象要得以完成,必须首先经过作家的主观艺术想象。
如上所述,作家寓具体之意于象,形成意象,才能构成艺术作品的意蕴美和境界美。诗歌一味言意,自然无味。即使写了景象,假如与意结合不紧,也同样无味。意象最基本的审美特征,在于意与象的浑融统一,即意中有象,象中有意,相互渗透,契合无间。在一定意义上,意就是象,象就是意,不可分割。文学意象则是融入了作家主观情思的客观物象,既有别于具象的艺术形象,也有别于抽象的艺术构思。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认为“意象”往往是形而上的和超个人的:
每个意象中都凝聚着一些人类心理和人类命运的因素,渗透着我们祖先历史中大致按照同样的方式无数次重复产生的欢乐与悲伤的残留物。②
荣格认为这些意象,一旦经历时间的锤炼和文化的认可,最终将浓缩成为一个极具符号意义的“原型意象”。朱熹《诗集传》卷六《诗经·秦风·蒹葭》中所描绘的“秋水伊人”正是这样一个极富意蕴而又相当深刻的“原型意象”,呈现在中国历代文学文本中,一批优秀的文学家和艺术家不断对其内涵和意蕴进行丰富并使之饱满,成为了人们经久不衰的咏叹对象和书写原型。
二
《诗经·秦风》中的《蒹葭》全诗如下: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凄凄,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
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
是诗共有三章,每章八句,为《诗经》常见之铺排格式,具有很强的韵律感和节奏感。从全诗整体结构来看,每章的前四句皆以蒹葭起兴,隐喻伊人。某种意义上说,类似于这种隐喻是《诗经》中最常用的艺术手法之一,也是最有效的艺术手法之一。这种用物象景象作为诗章或诗句开头的艺术手法,也叫做“兴”。“兴”和“赋”“比”共同构成《诗经》诗歌艺术的表现手法。值得注意的是,《诗经》中大量的起兴,不单单只是起到开头的作用,这些被描写的物象景象往往与诗所歌咏的内容多有某种内在的哲学联系。是诗后四句以情感铺垫,抒情叙事,回复往返,一唱三叹,委婉曲折,惆怅断肠。郑振铎认为《蒹葭》不仅“措词宛曲秀美”,而且“音调也是十分的宛曲秀美”,是近代以来第一位从艺术形式的角度对其进行评价的评论者,特别是从辞藻的运用和韵律的节奏都给予了《蒹葭》极高的评价和认可。③
关于这首诗的主旨,历来成为论者争论的焦点。《毛诗序》曰:“《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礼,将无以固其国焉。”④《笺》则认为:“秦处周之旧土,其人被周之德教日久,今襄公新为诸侯,未习周之礼法,故国人未服焉。”⑤进一步支撑了讽刺襄公主题的这种可能性。清代姚际恒《诗经通论》则认为《蒹葭》是一首求贤诗:“此自是贤人隐居水滨,而人慕而思见之诗。”⑥另一些现当代学者则认为,这是一首爱情诗,如郭英德和过常宝所著《中国古代文学史》中说道:“这首诗表达了一个年轻人对心目中的情人的刻骨铭心的眷念,以及艰苦而无望的追求。苍茫而萧瑟的蒹葭暗示了这一段感情渺茫的前景。宽广而幽冷的河水,既阻断了情人的身影,也激发了追求者的勇气和热情。年轻人沿着这条不可逾越的河流,溯洄从之,溯游从之,作着坚持不懈的努力,但那‘在水一方’的倩影总是缥缈难近。时间的推移,使得这段感情更显执著和凄婉,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给人以无限的惆怅和忧伤。”⑦更有学者将这一爱情主题进行了深化性的演绎和解读,认为诗歌是主人公追求爱情路上的失落和忧伤,寻找“秋水伊人”的过程“显然是一场阻力重重、可望而不可及的追求、向往,‘伊人’那总在前面出现却又总难以接近的身影就是说明,那晚秋水边一片萧瑟、苍茫的景象更是答案,就这样,主人公不尽的惆怅全部写在了诗的画面之中”⑧。
我们知道,蒹葭本是一种植物,是自然界中再为普通不过的一个对象,但当其作为一个审美对象进入艺术领域时,其本身所承载的意义就发生了变化,而且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提炼,与其他客观对象一样,因为“积淀了长期约定俗成的文化意味,因而具有表意的功能”⑨。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类似于蒹葭一样在《诗经》中用来起兴的外物,一旦被作者有意无意地安排到文本的恰当语境,有一些甚至直接参与了诗意的传达,就会使得一些诗作几乎达到了寓情于景和情景互融的艺术境界,能够在某种层面上使得抒情曲折有致,兴味盎然,引人入胜。应该说,《诗经·蒹葭》中,作为植物的蒹葭被作者巧妙地隐喻为“秋水伊人”形象,还是文学史上的第一次,却从此开辟了一条以“秋水伊人”为原型的经典美人形象的文学史旅程,随后庄子的射姑山神人、屈原的香草美人、张衡的《四愁诗》、曹植的《洛神赋》、陶潜的《闲情赋》等表达的美人形象及其语境都属于同一文化模式。⑩从此,蒹葭逐渐从植物对象走向艺术意象,最终被中国文学史赋予极高的哲学意蕴,而成为一个经久不变的原型意象,即“秋水伊人”。当然,这个过程是相当缓慢的,李泽厚先生曾对此类过程进行深度解读,他认为这就是所谓的艺术形象层的变异过程,即艺术从再现到表现,从表现到装饰,从具体意义的艺术到有意味的形式,从有意味的形式到一般的装饰美,是一个艺术积淀的过程,是为“艺术积淀”。⑪可以说,任何原型意象的形成与发展都离不开艺术积淀的环节和步骤,而这个过程恰恰串联着文学、诗学和哲学。
三
回到诗歌本身,我们不难看出,《蒹葭》之所以能够得到历代评价的青睐,确实有着自己独到的诗学魅力,它既是无与伦比的文学经典,也是独一无二的艺术奇葩。钱钟书先生亦曾对其进行解读,认为《蒹葭》不仅没有悲剧感,反倒极具喜感,认为《蒹葭》所赋内容乃是“西洋浪漫主义所谓企慕之情境”⑫。这显然也是有其道理的。不过从诗歌的审美空间而言,“此诗意境飘逸,神韵悠长;措词婉秀,音节流美”⑬。在工整和对仗之中却不乏音乐的节奏感和愉悦感,抑扬顿挫之间流淌出艺术之美质。从诗歌的整体结构来看,该诗别具洞天的叙事方式着实让人惊叹,不仅细数了时间的推移,也道明了场景的流转,更阐发了意境的跌宕:
首章“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写秋晨露寒霜重之景;二章“蒹葭凄凄,白露未晞”,写旭日初升,霜露渐融之状;三章“蒹葭采采,白露未已”,则写阳光灿烂,露水将收。三章兴句不仅渲染出三幅深秋美景,而且恰当地烘托描摹了诗人等待伊人、可望不可求而越来越迫切的心情。故几千年来,一直令人叹之不已,心向往之。⑭
难怪乎连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亦在《人间词话·二十四则》中对《蒹葭》颇多激赏,绝佳认同,拿来与晏殊的词作比对:
《诗·蒹葭》一篇,最得风人深致。晏同叔之“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意颇近之。但一洒落,一悲壮耳。⑮
翻检《人间词话》,《蒹葭》是为数不多的出自《诗经》的引本,可见对王国维诗学观影响之大。不过,王国维在此要想说的是《蒹葭》篇是《诗经》十五国风中唯一最具有风人意味的诗篇,表现得率真自然而又无拘无束。他用“风人深致”一词,即是形容作品带有清新亮丽的民间色彩,不若晏殊《蝶恋花》⑯之句来得悲哀雄壮,显然也是就艺术特色而言,未及深层。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王国维,或是其他的学者,对此诗的解读多停留在文学的意境和艺术的美感等领域,确实未能从哲学的层面对其展开阐释。如陈继揆《臆补》云:“意境空旷,寄托元淡。秦川咫尺,宛然有三山云气,竹影仙风。故此诗在《国风》为第一篇缥缈忽过高超远举之作,可谓鹤立鸡群然自异者矣。”⑱尽管以往这些论者和论述颇多停留于文学的领域,对《蒹葭》进行了深度的解释和欣赏,也有了可喜的发现和成果,但可惜未能在哲学的维度进行深入的解读和阐释,让我们对此诗的解读自然就停留在了表层。
以哲学维度而论,最值得注意的是著名学者胡晓明先生的诠释。他尽管亦是从爱情诗的角度出发,但却对《蒹葭》的深度解读则彻底开创性地打通了文学和哲学的领域,认为“秋水伊人”原型的出现,“凸显了现实和理想,形而上的世界与形而下的世界之间的一种张力”⑲。因此,《蒹葭》当之无愧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表现遇合无期的执著精神之绝佳作品,诗歌所创造的哲学境界,正是中国人文精神一直所期望达到的崇高哲学境界:
诗中所表现者,最表层之意义,为诗人追寻他的恋人之一种心境和努力。然而在中国诗学之观念中,“秋水蒹葭”之美,远不止于此一种意义,更是一种精神境界:一种追求理想爱情而不可得之境界,一种呈现无限向往、无限向上、亦即无限开放而无止域之境界。因而《蒹葭》一诗,有一般爱情诗所不及的象征性;诗中所表现的感情,有一般男女之情所不具的精神。⑳
其实,透过《蒹葭》诗歌的整体阐释,我们似可以发现一个简单的模式支撑着“秋水伊人”意象的饱满和充裕,即“寻者—河水—伊人”。在这个模式里,上述三个基本要素,缺一不可,各富意蕴:充满理想主义的寻者,是一个带着跨文化和超自然力量的主体,永不妥协,永不放弃;先天横亘的河水,是象征一个永远不能跨越的障碍,永远存在,永远阻隔;倾国倾城的伊人,是一个具体而又缥缈的美人形象,若隐若现,不可触及。著名学者张法先生通过对《蒹葭》的结构性阐释,认为这三种因素不仅构成了“秋水伊人”意象的基本框架,也共同铸成了中国文化的早期悲剧模型,继而升华成为一个具有共性的悲剧性结构,贯通着后来整个中国文化史和思想史,我们似可称之为中国文化的悲剧模式,为我们新近解读《蒹葭》提供了新颖的角度和独到的视域。他认为:
伊人是具体可感的存在,又是有距离的。有距离而又可感,对追求者的心理效应是将追求对象理想化,理想化了的伊人激发起人的全部热情、期望、勇气来投入追求。但伊人是有距离、有障碍的存在。阻碍,就其和追求者的关系讲,因其程度可以强化也可以弱化追求。但当目标是追求者的人生理想的时候,阻碍只能强化追求。主人公溯洄从之又溯游从之,一次又一次地追寻。但伊人却忽远忽近,宛在水中央,宛在水中坻,宛在文字,宜以恍惚迷离读之。”⑰再如方玉润《诗经原始》云:“此诗在《秦风》中气味绝不相类。以好战乐斗之邦,水中,总是可望不可即。追求者遇上的是最理想的目标,同时碰上的是不可克服的阻碍。阻碍一开始就决定了追求者的苦味,但对理想的追求是甘受苦味的。一再地努力都不可能逾越阻碍,苦味就转化为悲伤,特别是理想的目标仍在前面具体而又缥缈地闪动,仿佛能够达到,其实又达不到,达不到时又仿佛能够达到……[21]
鲁迅先生曾说过,悲剧就是将美好的东西打碎给人看。显然,《蒹葭》中这种即便是通过了一番百转千回的努力之后,然而最终收获的却依然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人生困境和寻求答案却没有结果的悲惨终局,残忍地将满怀的希望撕裂成一身的失望,这不是悲剧又是什么呢?
四
自然,是人类生活的环境。早期人类对自然的无知,表现为恐惧,《蒹葭》中以“河水”所暗喻的自然,就是诗歌中主人公恐惧意识的最初来源和直接出处。“在《诗经》中,几乎所有的诗句都把天视为可畏之物,常常向天投以怨恨之言,那是因为天的威力过于强大之故。”日本著名学者小川环树在《论中国诗》中讨论中国感伤文学的起源时,特别从早期诗歌中的“风”和“云”起笔,他认为天地之间的自然界中,一草一木一风一雨等,在那时已然被原始艺术家赋予了极具人格色彩的想象。[22]水,同样是自然界最为常见的客观存在,然而在早期人类的认知中,水是作为一种既是生存的必要元素,又是生命的威胁对象。地大物博的华夏大地,恰恰就是水的故乡。无论是大禹时代的洪水滔天,还是上古时期的淫水泛滥,抑或是滚滚长江或是滔滔黄河,甚至可以说,时至今日水给我们人类的依然是恐惧和未知。
我们知道,早期诗人对自然界的书写,或多或少带有敬畏之心,一方面不仅仅是因为强大的上天,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对客观对象世界的未知所致。只要有未知的领域存在,人类就始终与自然存在着对立和分歧。因此,“大自然与人类之间,划清明显的界线,超越之而得以情感交流,在上古是极其罕见的。”[23]值得一提的是,人类因着某种主体内在的强大精神力量,而不会因为这种对立和分歧去放弃对未知领域的探求和追逐。毫无疑问,这种永不妥协式的追求,从来都是中华文化的最精华之处。而且,这种心理模式是人类改造环境、支配自然的心理动力,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进取,而不是消极被动的顺应。追求的目标则是不可企及的社会终极彼岸,追求的基调正是人生悲剧的诗化复现。[24]人类在脚踏实地的同时,也始终仰望天空,从不间断地思索着自己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的问题,这就是人类智慧的伟大之处,也是哲学殿堂的开门之匙。
可以说,《蒹葭》全篇通过对难以逾越的河水的描写,将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纳入到哲学的高度,开古今之先河,足以道尽千百年来中国文化的悲剧之语和悲剧之诉。对于此种文学现象,著名学者刘士林先生在《苦难美学》一书中赋其名曰“二律背反的悲观论”:一方面,诗歌几乎象征性地表达了全人类共同的悲剧性命运,即始终并且必然存在着无可奈何的人生困顿,这是因为“人们所能知道的最凄凉的悲痛,便是奋力去做许多事,却又一事无成”;一方面,诗歌又直率而又褒扬地表达了人类“知其不可而为之”[25]的大无畏精神,绝不放弃,勇往直前,因为“假如没有热情,世界上一切伟大的事业都不会成功”[26]。
恩格斯指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27]看似简单而又轻微的一句话,却暗合着伟大的人类的前进路向,没有了意义的追求和价值的探索,人类的道路还走得下去吗?人类的未来还有希望吗?因此,对中国古典文学中“秋水伊人”的这种悲剧性的追求而言,不仅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精神,是一种使命,更是一种具有超越意义的古代进步文学的典型。当代社会的很多人,之所以会在选择物质还是选择精神的时候觉得迷茫和犹豫,甚至会在历史的道路上用尽一切方法去回避悲剧历史和消解悲剧精神,进而以灯红酒绿的享乐观取代刚毅坚卓的进取观,个中答案或许就在其中。[28]
因此,通过《蒹葭》中主人公在追寻伊人这一反一复和一来一往之中,我们见到的是人生两难的抉择和命运摇摆的踌躇,既让人痛不欲生,又让人勇往直前。两相对立,矛盾重重,这才是悲剧最大的哲学意义之所在,也是悲剧吸引人们驻足关注并反思的核心之所在。著名学者石鹏飞先生所言极是,他认为不完满的人生或许才是最具哲学意蕴的人生。人生一旦梦想成真,既看得见,又摸得着,那文明还有什么前进可言呢?最好的人生状态应该是让你想得到,让你看得见,却让你摸不着。于是,你必须有一种向上蹦一蹦或者向前跑一跑的意识,哪怕最终都得不到,而过程却早已彰显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所以,《蒹葭》那寻寻觅觅之中若隐若现的目标才是人类不断向前的动力,才有可能让我们带着屈原般质疑的口吻发出“天问”,才有可能立下“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豪言壮语。[29]
①参见陈竹、曾祖萌:《中国古代艺术范畴体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397页。
②荣格:《试论心理学与诗的关系》,见叶舒宪编《神话—原型批评》,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100页。
③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5月版,第48页。
④⑥转引自黄念然、胡立新、管春蕾编著:《中国古典诗词名篇选注集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版,第13页,第13页。
⑤转引自何新:《风:华夏上古情歌》,时事出版社2004年2月版,第414页。
⑦郭英德、过常宝:《中国古代文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57页。
⑧⑨陈炎主编,仪平策、廖群著:《中国审美文化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9月版,第138页,137页。
⑩[21]张法:《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1月版,第35页,第34页。
⑪李泽厚:《美学三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579页。
⑫钱钟书:《管锥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10月版,第208页。
⑬⑭⑰⑱聂石樵主编:《诗经新注》,齐鲁书社2000年10月版,第242页,第242页,第242页,第242页。
⑮王国维:《人间词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4月版,第26页。
⑯(宋)晏殊:《蝶恋花》:“槛菊愁烟兰露泣。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
⑲⑳胡晓明:《中国诗学之精神》,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99页,第196页。
[22][23][日]小川环树:《论中国诗》,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8月版,第48—55页,第56页。
[24]李浩著,陈思和、汪涌豪主编:《唐诗美学精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2月版,第10页。
[25]子路属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详见李泽厚:《论语今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3月版,第407页。
[26]参阅刘士林:《苦难美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版,第482—483页。
[27]转引自邱紫华:《悲剧精神与民族意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版,第45页。
[28]《文艺报》理论部主任、文艺理论家熊元义博士在2011年5月云南大学中文系的一次学术讲座中提及了这一观点,并对本文的后期撰写有所指导和雅正,在此表示感谢。
[29]石鹏飞教授在一次私人谈话中提出了这一观点,对本文的写作启发很大,在此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