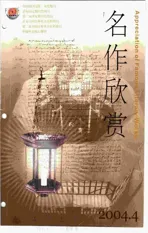对“剩女”生存状态的一种“勘探”
——读裘山山短篇小说《有谁知道我的悲伤》
2013-08-15山西段崇轩
/ 山西_段崇轩
作 者: 段崇轩,作家,评论家,有著述多种。
不时听到有关“剩女”问题的议论,却不甚了然,也未去深想。读了裘山山的短篇小说《有谁知道我的悲伤》(《人民文学》2012年第1期),让人惊心、感慨,不由得思绪万千。米兰·昆德拉说过:“小说家既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政治家,而是‘存在’的勘探者。”这里所谓的“存在”,就是指人的“具体存在”、人的“生命世界”。用这一观点去看这篇作品,就是作家在她的作品里,敏锐地发现和表现了当下“剩女”人群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这样的作品现在屡见不鲜,可贵的是作家把这一人群的生活描绘得那样逼真鲜活、淋漓尽致,让人们看到了社会群体中某一部分女人和男人的情感风景、精神流向,触发了人们对社会、人生、人性等问题的深入思考。
小说通过女主角“我”和潘馨——两位白领“剩女”的情感生活和婚姻故事的描述,揭示了“剩女”们自由而空虚的日常生活与寂寞悲伤的精神情状;还通过对那位求婚者——张力民的插叙,探索了当下男人们的择偶心理以及“剩女”形成的社会、文化原因。应该说,这是一篇具有“醒世”意义的社会问题小说,但却没有那种生硬的理性痕迹和说教意味,作家凭借她对“剩女”人群的谙熟和直觉,对这一社会人生问题的关切和忧虑,自然地、艺术地创造了一个柳暗花明的“剩女”世界。作家在短篇小说创作上已达到了一种驾轻就熟、潇洒自如的境界。因此,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是新鲜、独特的,情节结构是自然、灵动的,叙述语言是智性、细腻的,还夹杂了许多很有趣味的网络词语,整个作品蕴涵着一种朴素、流畅、深切、雅致的审美情调,既具有传统小说的典雅味,又富有现代小说的简约美。也许,它昭示了短篇小说一种新的生长点。
“剩女”世界是一个陌生的、神秘的,让人产生“窥探欲”的世界。《有谁知道我的悲伤》和盘托出了一个氤氲着女人气和香水味的“剩女”世界。先看她们的生存状态。有人说“剩女”就是“胜女”,她们往往有着高学历、高收入、高智商,且漂亮、能干。小说中的两位女主角就是这样的人物,但恰恰就是这样的“优秀者”成了“剩女”,因此她们的生活状态也与众不同。小说中的“我”其实是一个“准剩女”,她因偶然原因而离婚,不想再嫁而忝列“剩女”行列。年龄四十三岁,一直过着单身生活。她是一位有着二十多年工龄的出版社编辑,有房有车、收入不菲,工作轻松、生活优越。日常生活过得马马虎虎、随随便便。做饭、吃饭,凑凑合合。休息、睡觉,处于无序状态。把大量时间耗费在上网、打游戏、看影碟上,以此打发百无聊赖的日子。“自律能力差,又无他律。”这样优秀的女人,却过着这样散淡的生活,令人感慨!另一位出版社编辑——“我”的“闺密”潘馨,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剩女”。漂亮、时尚、聪慧、有活力。年龄只有三十五岁,已成为自认倒霉的“剩女”。她不甘心于命运的捉弄,把大部分业余时间消耗在化妆、购物、保养以及追赶生活新潮上。这样出众的女子,一眨眼就成了焦虑不安的“剩女”,让人惋惜!“剩女”生活耗掉了多少才女的感情、智慧和青春,这是一个多么严峻的现实问题。
威胁“剩女”的,绝不仅仅是生存问题,更是精神问题。生活的寂寞寡淡耗费的只是她们的青春和才华,而精神的悲凉空虚瓦解的则是她们的心灵和生命。作品中四十三岁的“我”,深知在时下男人的择偶标准下,她已没有选择的空间,也不愿意找一个老头子度过余生,因此“抱定了不再结婚一个人过一辈子的坚定的理想信念”。但这样的理想信念并不能填充自己的精神情感。因此为了“有个能说知心话的人”、“身边也有个男人”,她找了一个有家室的男人作为情人。尽管“我”的“某人”也带给了自己温情、快乐、寄托,但这种短暂的、“地下”的、“不道德”的婚外情,常常带给“我”更深重的矛盾、沮丧、失落和悲伤,这已成为她最基本的一种精神情感状态。而生命正处在成熟、丰盈时期的潘馨,因“自身条件不错,一般男人都看不上眼”。但光阴似箭,没怎么挑选就进入了“剩女”群体,在一次次的谈婚论嫁中,她看上的人家嫌她大,人家看上的她嫌人家老。寻找理想对象的美梦一次次破灭,不得不面对离婚老男人的现实摧毁着她的精神情感。她向“我”叹气道:“精神损失大着呢。你根本就体会不到这事儿让我多沮丧,打击好大哦,削发出家的心都有了。”在这略带夸张、无可奈何的感叹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年轻“剩女”悲伤绝望的精神情状。
短篇小说由于文体和容量的限制,一般只有一个主题思想。但《有谁知道我的悲伤》却有两个主题,或者说一个正主题与一个副主题,即对“剩女”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的揭示,以及对“剩女”形成的原因——男性择偶标准问题的探索。应该说作为一个短篇,只表现“剩女”的生存状态,写到第六节“潘馨落荒而逃躲求婚”的情节就可以煞尾。但作家突然笔锋转向,开始描述“我”对醉酒老头张力民的救助和对他内心世界的打探。这自然是对前一主题的补充或者说深化,但毕竟是两条难以交叉的路径。因此,这篇小说在总体构思和情节安排上是有缺陷的,作家在叙述进程中转移了主题思想。两个主题自然可以同时表达,但必须融为一体、整体推进。诚然,由于作家高超、灵活的艺术手法,后一主题的表现也可谓成功,而且确乎起到了对前一主题的补充和深化作用。两位女主角,“我”是因为“很多人打死都想不到”的原因而离婚,曲折的婚恋经历使“我”深知“现在离异男人的行情,他们再婚对象的标准,都是往小十岁到二十岁以上的女人里找”,四十三岁的“我”已对婚姻彻底失望。而三十五岁的潘馨,已成为高级“剩女”,俗称“斗战剩佛”。四十岁的男人嫌她大,六十岁左右的男人她不愿要。“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只有硬撑着、挣扎着。两位大龄“剩女”的症结,全出在男人与女人的择偶标准上。
择偶标准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男性的择偶标准比之女性要单纯一些。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数十年,看重的是女性的出身、文化、人品、容貌等等,而着重点是人品、文化这些属于人自身的东西,年龄上则要求同年仿龄。而90年代到现在的二十来年,选择的是女性的学历、收入、年龄、身高、容貌等等;特别是那些有实力的成功人士,更把年龄要小到多少岁、身高要在一米几之上、容貌要求哪种类型这些外在的东西看做追求的目标。小说中的老头张力民,年过花甲,择偶的条件就是三十到四十岁之间、有文化、身高一米六以上。当男性的这种择偶标准成为一种通行标尺的时候,就给男性人群创造了一个广阔的物色空间,而把部分大龄女性挤入一个死角。特别是那些优秀的白领女性,选择的余地会更加狭窄。
女性的择偶标准,几十年来变化更为复杂、微妙、剧烈。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选择的是男性的地位、家庭、文化、人品、性格、相貌等等,着重点是男人的人品、性格、文化这些本质的东西。但90年代之后,女性的择偶标准发生了巨大变化,除了地位、家庭、学历、人品、相貌之外,还要加上权力、金钱、车子和房子,以至两人的缘分、脾气、习惯是否相投等等。要求更加全面、苛刻。女性与男性的择偶标准发生了严重错位。事实上,十全十美的男人是没有的,求全责备是不现实的。但许多届婚女性特别是优秀的白领女性,坚持她们的择偶标准,左挑右拣,错过了最佳年龄,一不小心变成了“剩女”。小说中的“我”,偶然原因就导致了婚姻的破裂,离异男人的择偶行情又使她彻底放弃了再婚的念头,她只有用第三者的方式寻找情感的慰藉,承受着“纠结的情和爱”的煎熬。而小说中的潘馨,三十岁之前清高自信,等待着白马王子,三十岁之后倏然沦为“剩女”,只有离异的老头子可供选择,一次次地发出“有谁知道我的悲伤”的哀叹,等待她的很可能就是“我”的前车之路。
爱情、婚姻、家庭的问题背后,隐藏着盘根错节的社会、文化、人性之根源。作品中的“我”所以对潘馨的“对象”张力民感兴趣,就是想探讨一下这些“搞不懂”的男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婚姻心理。他们为什么会有那样的择偶标准?这个男人的形象是独特的,但还不够典型,他只能部分地反映当下男人们的婚姻心理。今天的社会是一个充满了欲望的社会,是一个男权主义膨胀的社会。男人特别是成功的男人们,占有了更多的权力、财富、实力。拥有了丰富世界的男人,已不再看重女性的人品、性格、能力等等,青睐的则是女性的年轻、美貌、智商等等。他们要在女人身上宣泄的主要是色欲和性欲,其实已把女人当做了物,并不把女人作为地位平等的情感和人生伴侣。男人畸形的择偶标准,集中体现了现代世俗社会人的欲望的泛滥和陈腐的男尊女卑意识的复活。而有一部分女性,自我贬值,甘愿俯就这样的男性标准,客观上助长了这种风气的盛行。小说中的张力民,并非成功人士。他出身农村,大半辈子当兵,只做到连指导员。只是,同样出身农村且“皮肤黑”、“不好看”的老婆,官运亨通,官至省级干部。他按照“组织安排”,老老实实做了一个家庭保姆。当老婆退休,他断然离婚,要寻找一个年轻的、美貌的、有文化的、高身材的女人,以弥补他人生的缺憾和情感的空白。他知道自己已到暮年,土气而衰老,但有房有车有存款的“硬件”给他壮胆,执著地要重建婚姻,重找爱情。作为个体的人,我们并不否认他的追求的合理性,但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就值得我们深思了。一个老头子依仗财富就想占有年轻美貌的女性,那些年富力强同时拥有更多权力和金钱的男人们,岂不是更要占尽人间春色吗?如此这般,年轻女性的选择空间将越来越小,大龄“剩女”的现象会愈演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