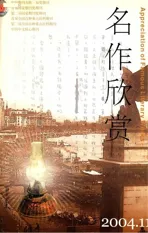汉语社会外向性小论:以《三国演义》的日译为例
2013-08-15吴芳玲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州350007
⊙吴芳玲[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福州 350007]
一、翻译中的信息传递与民族文化性
语言是交流的工具,也是文化的载体,“是储存传统的水库”(伽达默尔,1976)。因此使用表音文字的西方人创造出了“以分析为基础的西方文化”,而使用表意文字的中国人则创造出了“以综合为基础的东方文化”(季羡林,2000)。可是,同属东方文化圈的中国与日本,他们的民族语言又各自有着什么样的特点,分别储存着怎样的民族传统呢?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在“文化与文化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亨廷顿)的今天显得尤为重要并且迫切。为此本文拟以《三国演义》及其日译,亦即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出版的《三国演义》与立间祥介翻译的中国古典文学全集《三国志演义》(平凡社,1969)的对比为手段,来探讨汉、日两种语言的民族文化特点,从而对内更加深入了解了本民族的语言文化特点,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对外增进相互理解,促进相互交往。所以选这两个文本,是因为前者是在作家出版社1953年版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所据底本为毛宗岗本,而毛本的《三国演义》不仅通行海内,流传已久,且被近代所有日译本用做了底本,便于对比研究;后者译者立间祥介为日本著名的三国研究者,对原文的把握比较准确,对语言的理解比较到位,又是中国文学翻译家,并在翻译过程中多得日本的中国古典文学翻译大家冈崎俊夫(译有《老残游记》等)的指导,对汉语的驾驭能力较强,表达比较准确。同时,翻译是信息在不同民族语言之间的传递。这里所谓的信息,除词语本身的客观所指外,还包括其所隐含的精神层面信息,如话语者的价值评判等。这一信息如果能在原文与译入语之间等量传递,那就意味着这两个民族在这一点上的认识与把握是相同的;而如果不能等量传递,在传递过程中出现了增量或减量,那通常也就意味着这两个民族在这一点上的认识与把握出现了差异。而这就为通过对比,通过对翻译过程中信息传递等量与否的对比研究来发现中、日两种语言的不同文化特点提供了可能。由于保存于语言中的文化信息多表现在意义上,而意义又以词及词的扩展组合短语为基石;由于词有虚实,而承载意义的主要是实词,因此本文主要以中文原本与日文译本中的实词和短语为对比研究的对象。
通过大量而详细的对比研究,笔者发现日译本在信息传递中存在有大量的信息不等量传递情况,而增量传递所反映出的主要是日本民族对个人内心情感即非亲历不能知晓,因而不能代言的认识;减量传递所反映出的主要是中华民族对人物事件社会评判的重视。因此,如果说追求个体情感表现真实的日语具有内向性特点的话,那么重视对人物事件社会评判的汉语就具有外向性的文化特点。囿于篇幅,就日语的内向性,笔者将另文详细叙述,以下将主要以名词“宦官”的日译为例,简要叙述汉语与日语的对比中表现出来的社会外向性文化特点。
二、“宦官”日译中的社会外向性缺失
在中文原作中,作者对宦官的指称主要有“阉宦、阉官、阉竖、内竖、宦竖、(妇)寺、中涓、中官”等,于作品前5回中共有用例21个,具体的原文与日译如下:
p1 a)(桓帝)崇信宦官:宦官を重用した (作者)
b)宦官曹节等弄权:宦官曹节らが権力を垄断しており(作者)
c)中涓自此愈横:宦官はいよいよ专横をきわめることとなった (作者)
p2 d)乃妇寺干政之所致:女子と宦官が政治に容啄せるため (蔡邕上疏)
p3 e)结交中涓封 :宦官封 の许へ遣し (作者)
p16 f)陛下尚自与阉宦共饮耶:宦官どもをご相手に何故のご酒宴にござりまするか (刘陶进谏)
p18 g)欲尽诛宦官:宦官をことごとく诛戮せんとした (作者)
h)宦官之势:宦官の势い (曹操议论)
i)尽诛阉竖:宦官を诛灭して (袁绍决心)
j
)中官结党:宦官どもは徒党を组んでおります (袁绍建议)
k)欲尽诛宦官耶:宦官を皆杀しにするなぞ (何太后语)
p20 l)不诛阉宦:宦官らを诛さねば (袁绍建议)
m)昔窦武欲诛内竖:むかし窦武が彼らを诛せんとして(袁绍建议)
n)欲诛中涓:宦官を诛せん (作者)o)中官统领禁省:宦官が禁里の用事万端をつかさどる(何太后语)
p)尽诛阉竖:宦官どもを皆杀しにさせましょう (袁绍建议)
q)若欲诛宦官:宦官を诛せられんとなら(陈琳议论)
p22 r)宦官之祸:宦官が国の大事をあやまった
ことは (曹操议论)
p24 s)阉官谋杀大臣:宦官が大臣を谋杀したるぞ (袁绍号召)
t)但见阉官:宦官とみれば (作者)
p27 u)阉官弄权:宦官ども大権を弄び (丁原骂董卓)
上引21例中,用于作者叙述的有7例(宦官3,中涓3,阉官1),用于间接引用的有1例(妇寺1)。用于直接引用的最多,有13例,具体如下:
阉宦 2:f、l 宦官 4:h、k、q、r
阉竖 2:i、p 中官 2:j、o
内竖 1:m 阉官 2:s、u
从中不难看出原作者对上述8种指称宦官词语的使用是有所差别的。譬如“宦官”一称多用于较为客观的叙述(如例 a、b等)与评论(如例 h、q、r等),而“阉官”、“内竖”等多用于主观色彩极其浓重的直接引语中,表达了说话人对“宦官”这一客观存在的某种情感与评判。亦即“宦官”等8个称谓除物质层面的客观所指外,还带有精神层面的主观评判。譬如袁绍请命要杀尽宦官,“扫清朝廷,以安天下”时,用的是“阉竖”(例ì),而何太后要保张让等,为此责备何进时,用的是“宦官”(例k),两人对宦官的评价不同,态度不同,所用称谓也不同。同为一人如袁绍,情势较缓时劝何进杀宦官,用的是“中官”(例j);张让等重新得宠后情势较急,为力劝何进杀宦官就改用了“阉宦”(例 l)与“内竖”(例 m)等,情势不同,态度有别,称谓也随之改变。但在日译中,所有差异都被抹去,统一译作了“宦官”。
为什么会产生这一信息流失呢?是译者对原文不够理解吗?显然不是。因为从译文看,译者很清楚这些称谓在物质层面上的客观所指,他甚至清楚“妇寺”指的是“女子和宦官”。他没有译出或没能译出的,是隐含了其中精神层面上的主观评判。如果说语言的客观所指是其“物质外壳”,那么日译者在将这些称谓的物质外壳由中国式改造成日本式时就舍弃了它的内涵,舍弃了使用者寓于其中的社会评判,从而造成了信息在中文与日文之间的不等量传递。但这一不等量传递不是缘于译者的无能,而是出于他的无奈。因为他是理解了原文,但或因译入语——日语无法表达或因译文接受者——日本读者不重视、不需要而将之舍弃了。亦即这些称谓所内含的说话者主观评判是为汉语所有而日语所无的,是为中华民族所重视而为日本民族所忽视的,是汉语相对于日语所特有的。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评判呢?相对日语而言,汉语具有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呢?
综合《辞源》①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三国演义》中的相关注释可以知道,汉语中的“宦官”及其各种称谓的意义具体如下:
宦官:宫内侍奉的官。
宦竖:对宦官的鄙称。
阉竖:对太监的贱称。阉,男子去势;竖,供奔走役使的人,于作品中与“阉宦”、“内竖”同为对宦官的贱称。
中涓:秦汉时皇帝亲近的侍从官。《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平阳懿侯曹参”唐颜师古注:“中涓,亲近之臣,若谒者、舍人之类。涓,洁也,言其在内主知洁清洒扫之事,盖亲近左右也。”亦即宫中管理通报、清扫的臣子,于作品中指宦官。
妇寺:即妇侍。寺,古文“寺”。《诗·大雅·瞻仰》“匪教匪诲,时维妇寺”。《传》:“寺,近也”。宋代朱熹的《诗集传》“训寺”为奄人,作品中指宦官。
中官:即宦官,又称“中贵”。
由此可知,“宦官”是从事“宫内侍奉”者的职业名称。“阉宦”、“阉竖”、“内竖”等称谓是对“男子去势”的明言与对“供奔走役使”者语意的添加,表示了对宦官的轻蔑与鄙视,因而是对宦官的“贱称”或“鄙称”。与此相对,“宦官”由于不含此语意,因而是对这一职业人群不褒不贬、不贵不贱的中性称呼。“中官”是对宦官的别称,只强调其居中传递的职业特点,不含明显褒贬。与之不同,“中涓”由于强调了“居中扫洁”者的低贱身份,“妇寺”由于将之与古代社会中地位低下的“妇”并列而多少含有了一些对宦官的鄙视与恶感。由于以上这些原因,于汉语原作中“宦官”一词多用于叙述,以示作者态度客观。用于人物语言的直接引用时,也多出现于立场中立(如例g陈琳)甚至偏袒者(如例k何太后)的话语中,或鄙视者的较为平和的议论中(如例h、r)等。与之相反,出现于鄙视者态度激烈发言中的,则几乎全是“阉官”等明显带有贬义者。考虑到《三国演义》不是个人的作品,而是罗贯中在《三分事略》《三国志平话》等前人创作基础上的再创作,成书后又经后人加工修订,方才成为今日所见的形态,因此其中对“宦官”各种称谓的区别使用,就不仅是作者的个人意识使然,而是包括接受者在内的中华民族集体意识的表现,从中显露出的是中华民族指称某一事物时对其社会地位、彼我关系的关注。相对于日语对个体内心情感表现的关注,或可称之为汉语的“社会外向性”。
三、《三国演义》日译中的社会外向性缺失
如上所述,对名词“宦官”与其日译的对比分析说明了汉语具有社会外向性的文化特点,但能够说明这一点的,绝不仅仅只是“宦官”一词的日译,也不仅只是“贼、寇、豺狼”等贬义名词;不仅只是“大圣人、士、正人、(堂堂)丈夫”等褒义名词,其他如动词“诛、讨、讹言、犯、秽乱(宫禁)、感化”与形容词“(日)非、(愈)坏、私(造)、暗(差)、不臣(之心)”等的日译也都能充分说明这一点。譬如:
1)此等害民贼:こんな不届きな野郎
汉语“贼”是指“危害社会的坏人”或“盗窃之人”②,原使用的是前一种意思。日译“野郎”原是对男子的“骂人话”或“俗称”,用作男子俗称时特指年轻男子,与“女郎”相对,如「家には野郎ばかり三人いる」(家有三口人,都是男的③)。显然,即使用作骂人话也只表达了说话人的一种情感,并不含原作所具有的社会评判——危害社会的坏人。
2)朝廷正人皆去:朝廷の正しき人物はみな去り
汉语中“正人”常与“君子”合称,指品行端正者。“正”不仅有“正确”的意思,还有从道德层面作出的符合正统、人格正直等社会评判,如“正派”(指品行作风规矩、严肃、光明)、“正气”(光明正大的作风或风气)、“正大”(言行等正当,不存私心)等。日语中“正しき”的意思相对简单,只有“对的,正确”之意,“符合道理,符合事实的”之意④,不含汉语所具“走正道的”、“正派”、“正直”等社会评判。
3)(何苗同谋害兄)当共诛之:斩って舍てい
4)(汝罪恶盈天)人人愿得而诛之:みながみな杀してくれようと思っているのだ
汉语中“诛”有“杀戮、讨伐、惩罚”等意,但于语言实践中,被诛对象一般为罪人、无道者。原作中的被诛对象也都是如“同谋害兄”的何苗、“罪恶盈天”的“汝”(董卓)等恶者。日译“斩、杀、攻打、灭亡”等没有对象限制,因而也不具有说话人对诛者与被诛者的不同社会评判。“臣杀君、子杀父母曰弑”(《辞源》),因而用“弑”表述就含有了说话人对杀人者的谴责,含有了说话人对此杀人行为的“无道、非法”评判。与之相同,汉语“诛”一般用于正义对非正义的讨伐,因而通常带有说话人对讨伐者的肯定与对被讨伐者的否定评判。日译未传达出这一信息,造成了社会评判信息的流失。
5)遂一面私造黄旗:かくて密かに黄色の旗をつくって
汉语中“私”的原意是与“公”相对的“属于一己者”,由此出发有了“私自”、“隐秘、暗中”等意思。原作用以写张角为谋反而“造黄旗”,显然除了用“隐秘、暗中”之意外,还带有对未经许可、违法制造的谴责。但日译「密かに」只有“暗中”的意思,没有“违法”语意,只等于汉语的“暗”。譬如:
6)进乃暗差使命:何进は密かに使者を仕立てて
将此例与“私造黄旗”这一例子相较不难看出,无论是张角“造黄旗”抑或“何进差使命”,都是秘密进行的,原作于前一例用“私,于后一例用“暗”来描述,明显带有区别,但日译却不加区别地都用“密かに”来翻译。原作者于区别中表现了他对张角违法“造黄旗”的谴责,日译者以不加区别来抹杀了这一谴责,造成了社会评判信息于翻译传递过程中的减值。此类例子于日译本中极多,仅5回就多达55例。此外还有日译者为实现信息的等量传递而直接借用汉语词汇或增补种种说明的,而且数量也十分巨大,仅前5回就有多达260余例,囿于篇幅,以下只略举数例稍加说明。
7)公真天下忠义之士也:贵殿はまことに天下の忠义の士でござる
8)段 逆贼(安敢劫太后):逆贼段
9)奸臣董卓:奸臣董卓
10)董贼逼我母子:国贼董卓目、われら母子をかような目にあわせた
11)贼以为官兵至:贼は官兵が来たと思い
12)灭国弑君:国を亡ぼし君を弑し
从这些用例的两种文本对比不难看出,原作中说话者的态度或褒或贬,并不一致,但褒贬判断所据标准却都一样:都是社会视角,符合社会正义则褒,反之则贬。日译者都直接借用汉语词汇来翻译,因为日语固有词汇中没有对应者,非借用汉语不能实现社会评判信息的等量传递。譬如例(11)中“弑”的日译是“弑し”,但“弑し”音“ころし”,与“杀し”是一个词,通常只写作“杀し”,只有“结束生命、致死”意思,不含任何社会评判语意。因此日译者只好借用汉语“弑”来传递原作认为杀害君主行为非法的社会评判信息。其他如“董贼”、“奸臣”、“逆贼”、“忠义の士”(“の”:格助词表示定语)等基本就是原封不动的照搬,就连不懂日文的中国人也能看得懂了。
四、汉语的社会外向性
存在缘于需要。某一词语或说法的产生与流传是对现实需要的一种反应。日本民族关注个人内心情感的细微差别,所以有“喜ぶ”、“乐しい”、“乐しそうだ”⑤等多种不同的表现方式;中华民族关注个体外部关系与社会属性,所以有了原作对宦官的近10种不同称谓。创作者——说话者进行语言编码时意识到了自己与受众的这一需求,因而有意带入这层信息,区别选用了较为中立的“宦官”或明确否定的“阉竖”等,为词语在客观所指之外增添了一层社会评判。汉民族接受者与原作者生活于同一文化背景,有着共同的传统与意识,因而能基本等量地接受原作者所要传递的信息。一个民族的集体意识,其思维模式与文化传统有着比语言更加长久的生命力。语言总在不断地发展演变,而由语言保存的思维模式却不轻易改变,因而信息传递在使用同一语言的表达者与接受者之间能等量进行,但在不同语言文化背景下却经常会发生减量乃至流失。
任何一部翻译文学作品都不可避免地要带上译入语的民族特点,这是不同的思维模式与文化传统所决定的。因而在对一部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不具有其思维模式、文化传统的他民族语言虽可以对语言的物质外壳进行成功的信息等量传递,能在物质层面上准确地传达另一语言的客观所指,但隐含于语言深层的民族文化信息却经常被迫舍弃,因为翻译者的民族同胞或不重视或不需要或无法接受这些信息。这就是为什么“罕见的语言天才”,一代翻译家辜鸿铭在给汉诗以不坏的英译之后总要郑重声明“未能传达原诗神韵的高妙于万一”,因为对汉诗进行英译有如以单弦乐器演奏复杂的交响乐⑥,其语言外壳虽可以转换,但其“神韵”,其语言外壳下的丰富内涵,其于民族同胞间可依共同的文化传统等量传递的大量信息却无法传递。
汉诗的英译如此,汉语小说的日译也如此。日译者将原作中指称宦官的近10种不同称谓全都译作了“宦官”。这一处理是传达了原作中这些称谓的客观所指,但忽略了原作者与作品中人物借不同称谓所要表现的、对宦官或贬斥或中立的立场与或平和或激愤的态度,忽略了他们对宦官的社会评判,而该译本在日本的长期流行⑦则说明译者的这一忽略得到了日本受众的广泛认可。
与原作者一样,翻译者也是依着自己的民族思维模式来进行语言的解码与编码的。因而原作者寓于这些词语中的社会评判信息在传递过程中的减值,日本译者与接受者对该信息的集体无意识就说明了这一文化信息是为中华民族所有而日本民族所无的。
日本民族对社会评判的集体无意识,凸显了中华民族对社会评判的关注。表现在语言上,就是相对于具情感内向性的日语而言,汉语明显具有关注个体外部关系、注重社会评判的社会外向性特点。因此,汉语可以一字褒贬,“褒则书字,贬则称名”⑧,以词语的区别使用扬善抑恶,让当事者有“一字之褒,宠愈华衮之赠;一字之贬,辱过市朝之挞”⑨之感,而“孔子成《春秋》”也着实使“乱臣贼子惧”⑩。汉语的这一特点,在对两种文本中信息等量传递情况的考察中也能得到充分证明,但囿于篇幅只能从略,留待今后作进一步的探讨与论述。同时,在与同属东方语言的日语的对比中凸显出来的这些特性是否确为汉语所独有,还必须将汉语放在世界语境中进行对比研究之后才有可能最终断言。这是我们必须努力去做的,因为已有“人大代表建议制定汉语国际化战略”,并指出“对外汉语教材出版现状堪忧——汉语推广遭遇教材浮躁尴尬”。这种尴尬主要体现在“教材编写草率、缺少精品、低水平重复”等方面①,而精品教材的打造需要有对汉语、汉文化的深入理解;有对接受者民族文化的深刻理解作基础。
① 商务印书馆:《辞源》,1998年版。
② 商务印书馆:《辞源》,1998年版。
③ [日]金田一春彦等:《国语大辞典》学习研究社1984年版。
④[日]《新明解国语词典》:三省堂1995年版。
⑤ “喜ぶ”:动词,喜欢。“乐しい”:形容词,说话者内心喜欢。“乐しそうだ”:形容动词,非说话人已形于色的喜欢。
⑥ 黄兴涛:《闲话辜鸿铭——一个文化怪人的心灵世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5页。
⑦ [日]立间祥介译:《三国志演义》,初版于1958年发行,1968年收入中国古典文学大系,井波律子译《三国志演义》初版于2002年发行,其间并无其他《三国演义》日译问世。
⑧ 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孔颖达疏》。
⑨ 范甯:《谷梁传集解序》。
⑩ 《汉大成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6年版。
⑪ 《文汇读书周报》第1048号,2005年3月25日。
[1][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M].夏镇平,宋建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2][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
[3]季羡林.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M].北京:华艺出版社,2008(10).
[4][美]许倬云.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M].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
[5][日]氏家洋子.言语文化学の视点——「言わない」社会と言叶の力[M].东京:おうふう,1996.
[6]刘静.文化语言学研究[M].上海:中华书局,2006.
[7]黄兴涛.闲话辜鸿铭——一个文化怪人的心灵世界[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