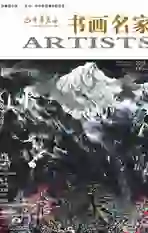水墨家园——李小可访谈录
2013-07-31陈履生

主持语:
艺术大家门第的熏陶与天然的蒙养,使李小可获得了全面的艺术禀赋,他深知中国画艺术的文化魅力在于“精神内涵”,这就有了他走向生活的独辟蹊径。四十多年来他坚持写生、在生活中练笔、在创作中保持写生的即兴感受,用学者的思考关注笔墨,并用笔墨表达现实。无论是《都市风情》组画,还是《藏域高原》组画,他作品中的“笔”与“墨”不仅仅是一种形式,而成为他表现生存空间和自然意境的方式。因此,在中国画坛,李小可的作品和其他山水画家有所不同,他的山水作品更具有人文情怀和文化观照的意味。
地点:李可染艺术基金会美术馆
受访人:李小可
采访人:陈履生
陈履生:小可,在我的印象中您是一位大器晚成的画家。因为您的父亲是李可染先生这一特殊的家庭背景,大家也会用特别的眼光来看待您,应该说绝大多数是善意的眼神,包含着对可染先生的敬重,也包含着对他后人的期待。客观来说,社会对于名人之后,尤其是名画家之后有着一些成见,原因是名画家的后人成才的比较少,往往是吃老本的多。您的家风以及您自己的努力改变了人们已有的一些看法,因此对我而言,除了知道一些您过去的经历之外,还希望能够系统地了解您和您的艺术发展。
李小可:我的绘画最早是从大雅宝胡同甲2号院开始的。解放初期,这个院子里聚集着中国20世纪众多的艺术大家:李苦禅、董希文、张仃、周令钊、黄永玉、吴冠中、王朝闻等等。那时,我以孩子的目光看着前辈和师长们,虽然他们从事的艺术门类有所不同,但他们都有着对人的真切、炽热、亲和的态度。当时白石老人、徐悲鸿先生也经常来到院子里做客,我两岁的时候,白石老人还为我画过一幅《鲶鱼》,这个院子好像是一座20世纪的文化寺院,聚集着一批为艺术理想和艺术发展而努力的探寻者。我十几岁时曾参加过两次世界儿童画展并获奖,院子里的小孩包括李庚、李珠、黑蛮、黑妮都有参加。当时我获过两次奖,一次是参加印度“世界儿童画展”,我画了一幅《千帆图》,画了无数的帆船,很有意思的是现在我画的《水墨家园》中的北京老房子仍旧是特别满的构图,父亲的影响和自己的审美个性可能从那时就有了。
1960年,我进入中央美院附中。在附中实际上接受的是综合性的基础美术教育,老师们的认真和启发式的教学给学生们奠定了艺术发展的基础。当时学的百分之七十是西方美术技法,后来增加了国画学习内容,成立了国画班,曾受到蒋兆和的爱人萧琼先生关于工笔、线描的指导,卢沉、于月川也教我们水墨。当时只是启蒙教育,对中国画的表现并没有太深的了解。高亚光、王德娟、任之玉、张京生、仉凤舞等老师对我们进行基础教学,为我在素描、色彩、速写等方面打下了初步的绘画基础。1962年,因形势紧张,首次在艺术院校征兵,当时我年仅18岁,和六个附中同学一起参军。在部队承担着军事训练和执勤任务。大比武期间是通信兵尖子班成员,也表现得很出色。同时又是部队美术宣传创作的骨干。1968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父亲成为反动学术权威,部队就留不住了,复员后分配到北京内燃机总厂当锻工,打了10年铁。这期间进行了大量的业余美术宣传创作,参加了北京市工厂的业余美术创作活动。当时,王明明、石齐也都在企业中参加各种美术创作活动。“文革”后,父亲从丹江回来开始为宾馆创作作品。这时,我也开始研习水墨山水,这时候的画基本是受我父亲的影响,也临摹一些父亲的作品。
1978年,父亲在“文革”以后重新计划到江南写生,再去黄山、三峡、四川,通过写生重新感受自然生活,进行了一批新的创作。当时父亲已年过七十,就让我跟着他,一是照顾他,帮他做各项辅助工作,同时也能跟着他一起写生,把“水墨山水”传承下去。那时,我跟父亲、母亲到黄山写生一个月。期间,正好有缘遇到日本著名画家东山魁夷。当时我在黄山也画了一批写生,其中有一幅名为《登天都峰》的画,父亲还帮着修改并题字。从黄山下山时,父亲只用了半天,一直走下来。实际上他已是70岁的老人了,下山后就感到心脏不舒服。后来又奔赴九华山并登上山顶,还画了很多速写,心脏的不适就更严重了。从九华山下来回到武汉并检查身体,医生说不能再往下走了,不然会出问题。因此停下了后面的行程,开始在武汉工艺美术研究所作关于山水画的学术讲座。这时,孙美兰、李行简也来到武汉。之后,我又跟李行简到河南鸡公山画了一些写生。随父亲写生、讲学回来后,我把当时写生的一些作品进行了整理。后来,我拿着整理好的作品给北京画院的崔子范院长看,以这批作品写生画进入了北京画院,当时是1979年。
80年代初,我曾跟随父亲的老朋友王肇民及广东美院院长郭绍钢一起到汕头、潮州画了一批写生。其中有一幅画的是两边长满灌木的幽深小路,这幅画是以交错、繁密的“线”为主,对后来的绘画风格产生了一定影响。而王肇民老师刻苦、严谨的艺术态度和大气简洁的画风对我产生了深深的影响。
陈履生:可以说您于1979年进入北京画院是从业余进入到专业层面的一个重要转折,以写生入画院,进而继续写生。可是体验生活和写生在那个时代是一种普遍的行为,并不具有特殊的意义,不像50年代初期李可染、张仃、罗铭先生等前辈的写生那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那个时代基于中国画的改造问题,时代要求画家走出画室,要求画家深入到生活中去反映现实的变化和社会的进步。因此,在这种不同时代的前后关系中,写生也就有了不同的意义。
李小可:第二个对我影响比较大的就是1986年、1987年到中央美院进修,当时选择的是画人物,在卢沉和周思聪的人物班进修两年。期间画了大量的人体速写和人物写生,周思聪上人体速写课时经常拿来一些西方大师的速写范本,如罗丹、席勒、莫迪尼亚尼等人的作品来启发我们,并和我们一起画速写,使我能看到她对造型表现的把握与概括。从这些练习中,我着重解决绘画中的造型和结构问题,由开始画不准和琐碎,练到后来就画得比较准、比较整,人物动态也表现得不错,受到了卢沉老师的肯定。进修的那个阶段正好是美术界的“八五新潮”时期,美院天天都有各种不同学术思想的讲座和交流,非常活跃。这时候多元文化思想的碰撞为我开启了一个文化性思考和比较的空间,给后来的创作选择带来了启发。
在进修期间,我认识到绘画表现中造型能力与视觉结构关系在绘画中的重要性。这个结构造型关系不管是具象表现、抽象表现,还是写意表现,都需要有一个造型结构方式作为表现的支撑点。绘画中的结构如同建筑结构,是建筑的基本框架,在绘画表现中,如果这个框架搭不好,其中的笔墨、色彩等表现就无法发挥作用。同时进修期间使我树立了一种相对比较开放的表现态度,并在绘画中强化个人重表现的感受,以这种思想为指导创作了作品《宫墙》。作品表现的不是套用传统的程式化,而是强化了“线”,强化了“透视”,并凸显一块块城砖的积累与重复,使作品更多地显现了对特殊客观意境的表现。当时《宫墙》参加了“北京风光展”,受到业内外人士包括吴冠中先生的肯定。
陈履生:现在看来《宫墙》具有特别的意义,和许多著名画家的早期作品一样,都具有坐标的性质,都成为人们研究其发展路向的一个参照,它是哪一年创作的?
李小可:1986年。当时我还参加了日本著名画家加山又造举办的人物画短期训练班。亲眼看到加山先生的写生过程,感受到他对艺术的严谨态度与探索的精神。在训练班快结束时,我与同班的姚鸣京到河北涉县王金庄画了一批农舍的速写,对后来我绘画的造型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我在美院的一段学习时间中树立了一个思想,即绘画除了继承传统以外,也要重表现,不管画画成什么样,一定要有自己个人化精神的表现,在画中一定要凸显个人的审美感受与选择。后来,“北京系列”的作品包括《宫雪》、《晴雪》、《夏》、《大宅门》等等,在表现中是把对生活的那种特殊感受转换为部分传统表现的方式而有选择地运用,又必须有新的视觉语言的尝试,以适应新的表现意境,好的艺术作品一定要有艺术家情感、精神和时代精神的融入。父亲讲“千难一易”,表明任何风格面貌的建立要靠条件,只有条件具备,才会水到渠成。“七十始知己无知”、“实者慧”,只有不断地学习、发现、探索,才能产生新的表现可能性。我各个阶段的艺术选择都深深受到父亲艺术精神的不断影响。
陈履生:这是毫无疑问的。每一个人都可能这么认为,您的每一步都有父亲的指引,都有可染先生的影响。
李小可:关于父亲的影响,最初是在他身边看他如何画,如何处理画面的意境、层次和笔墨的整体感。他强调画面只有整体感强,画才会更有表现力。他常说:“我要把画面中针尖大的多余白点去掉,就像京剧舞台上净场一样。”但父亲给我真正的影响还是在后来不断为他的艺术做宣传、出版、研究、办展览的过程中,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他的艺术精神。比如“要精读大自然与传统这两本书”,好的山水画需要把传统与对自然的感动连接起来,探索和发现水墨表现新的可能性。写生时“要像从其它星球来的人一样”,到大自然与生活中去感受,发现美。他强调艺术要“在精微”,艺术表现过程中“在精微”的重要,这就是艺术家在创作中火候与分寸的把握,差一点儿都不行,说的是艺术要精道。
另一方面我的思考是如何把重表现中的开放性状态与传统中国画的笔墨表现、程式化的语言方式连接得更加紧密,所以后来创作的包括黄山题材的一批作品更加强调笔墨程式化语言的研究。《水墨家园》实际上也是强化水墨为主的表现,突出画中线、皴,以线、点、皴去表现北京老城的生活气息。画面的构图也不同于传统一般化的方式,没有更多地强调虚,如果画面留白留得很多,再加上一点儿渲染的鸽子什么的,必然会削弱房顶这个视觉语言整体的压迫感,而画屋顶的线,我会用湿笔去擦,使线变得含蓄、丰富。画中把具体与抽象笔墨结合起来,形成了强烈的表现力。《水墨家园》让你感觉到中国传统笔墨有着自己独特的表现力,试想《水墨家园》的屋顶用油画去表现的话,肯定不如中国画的线与水墨的表现更具效果,这也使人感到东方水墨的表现还有无限的表现空间。
当我回过头来深入研究程式化的语言表现方式时,我也临摹了很多东西,包括沈周、黄公望、董其昌、八大山人、“四王”等作品的局部。通过深入的临摹,让我更加认识到中国画的程式化不是不讲究造型,而是特别讲究程式化结构的造型,讲究笔墨以线概括的造型,这种程式化笔墨造型方式更适合再造山水和笔墨语言的发挥。通过对传统水墨的研究,后来的创作越来越使我感到对水墨的表现只要你打进去,无论在审美境界,还是在水墨语言表现上,都还有无限的表现空间。我的水墨表现在很长的一个阶段里是先抓住线和线的结构,而父亲的画突出的是墨的表现,但在他的墨里头含有很深的造型结构基础。如果没有这种造型结构基础的研究,直接进入到墨,这个墨会比较空洞,所以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强调以线的结构表现为主,这是一个过程。
另外一方面,我还是坚持自己重生活、重表现的态度,画了大量的水墨写生。写生过程中尽量把生活中新鲜的审美感受注入到画面,但不能过度概括。过度的概括和用简单的程式化语言去套,必然会丢失生活与自然中最具生命力的新鲜的东西。在不断的写生中会发现新的审美领域与绘画语言。
关于我的“西藏系列”,水墨表现更关注的是一种特殊意境和人文关注。虽然作品中画的是雪景——《正月的雪》、《冬日》,看上去是雪后的人在那儿转经,实际想表现的是一种使人心灵宁静的意境;那幅《晴》的蓝天,浮动的白云,远处刮来的风与西藏寺院绚丽的色彩,虽然颜色绚丽,但还是会使人感到一种远离喧嚣的宁静,它包含着藏地,体现人与自然、宗教文化融为一体的境界;《山魂》是表现高原雪山的那种瑰丽、圣洁和苍茫、神秘的感觉,我一直在寻找表现藏地雪山的特殊语言方式。
陈履生:您整个创作的历程是经过北京、西藏、黄山三个系列的一个延续的过程,从70年代后期跟父亲去黄山写生,从此写生奠定了主导您的一种创作方法,这个三个系列题材处于您的不同发展阶段,我最感兴趣的是80年代您的“北京系列”,水墨家园,画北京的这种以民居为主题的题材,实际上是应和了这一时期开始出现的乡土题材,应和了西北风唱遍大街小巷的时代潮流。您画身边的乡土,画京味儿,也是在一种潮流之上。从另一方面来看,因为80年代时现代化刚起步,还保留了大量旧的城市格局中老北京的风貌。您的画出来之后,确实让大家眼睛一亮——李可染的儿子没有去画父亲的漓江,而是画身边最熟悉的内容。这一在当时美术界没有可比性的题材和笔墨方式,形式感很强,没人这么画过,当时您为什么想到画这个题材?
李小可:1986年开始有“北京风光系列展”,也已确立了重表现的思想。在我的画里要把特殊性的意境和水墨表现的某些元素结合起来,可能不是全部。比如那幅《宫雪》把带有抽象的红墙与留白的雪结合起来,它不完全是传统的水墨表现,而有一些新的视觉语言方式,但和水墨、写意融在一起,使人们看到时有一种新鲜感。但这种新鲜感如何更深入地与中国画本体的笔墨表现结合起来并不断强化,画北京《屋顶》就是强化水墨本体表现的探索。有一次,我到河北饭店办事正好下大雪,无意中在高层的屋顶上看到雪中北京的老房子,当时新建筑还没有现在这么多,还能感觉成片的屋顶与雪中的树连在一起,这是最早对屋顶雪的印象。我早期画过雪后的四合院参加过画院的展览,画面是线和留白的雪,这幅画现在回头看挺幼稚的。在后来的《古都老屋》中强化了屋顶的线、墨和用皴法表现的树及屋檐下的窗和门;经反复推敲、实践,发展为现在这幅《水墨家园》,成为一个具有以东方笔墨结构为表现特征的语言形式,其中包含着造型、意境、抽象和具体,同时吸纳了一些当代画的视觉经验,强调独立审美的表现;更加强调中国笔墨中线的表现,使它与表现内容融为一体并做到相对极致。人们看到《水墨家园》这幅作品时都会在画前留步。
陈履生: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就是说画现代题材,画身边的内容,像您这样能获得大家认可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形式语言很独特,尤其是用线造型,白的、黑的屋顶,加上树木穿插其中,用树木来调和黑白的笔墨关系,同时又把原来的屋顶用硬的线条做了一种消减的努力。但是在您后来的发展中,我有几次在画展中看到有一幅画,两边是树,中间有一条路,绿色调的,那幅也是您的代表作。那幅画同样是在形式语言上用色彩来表现大家所熟悉的环境,就好像我们看您所画的北京的屋顶一样,可是感觉却完全不一样,使得我们重新来认识现代水墨在发展过程中与家园相关的新题材,进入到传统水墨画中的状况,相对来说人们的理解没有依傍与传统的那种亲切感,那种文化可能更像西画。虽然您在水墨上也做了很多的努力,去寻求它的一些中国的特征,却失去了传统性更强的一种感觉。因此您画这个屋顶有画很大幅的,也有小幅的,只有《水墨家园》中的这个屋顶是以纵横交错的黑白关系来体现。这种题材的基础可能您自己没有发现它的一个特殊性,同样是画宫墙,同样画这个“水墨家园”系列、“北京系列”,唯一成功的或者大家认可的具有小可这种形象符号的屋顶,就这个“水墨家园”,连片儿的小院子,确确实实是北京的感觉。如果您缩小了去画一个局部的写生,画一个胡同的写生,就没有这种效果。把这种感觉画出来,需要一个宏大的气象,要成片儿,要纵横交错,要有这种黑白关系,要有构成这种现代水墨的语言关系。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因为从80年代中期以来,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参展的作品都是这一题材,每次大家看了好像也不厌烦,也没感觉到它多余和重复,人们还是基于这种亲情感去认可。所以要研究一下为什么同样是现代题材中熟悉的内容,其效果却完全不同。
李小可:这个问题在创作中也是我一直考虑的事。我在创作《夏》时,吸纳了一些现代视觉表现的经验,创作的支撑点是重表现,就是说我没有太拘泥是不是纯粹的中国画。如果只是拘泥于“中国画”的概念,在表现中就会弱化“荫”的那种特殊性感觉,但画里又有中国的东西,包含我父亲的东西,就是有一种光感,但这种光并不是西方的光,实际在树干上也隐隐约约好像是有一点儿阴影,这个阴影并不是一个固定光,而是一个黑白抽象处理;树荫如东郊民巷浓荫的深邃;画中的树又借鉴泼彩,把很具象的东西变成泼彩,增强了画面的表现力和生命感,三轮车凸显出北京的宁静。
《神路街的雪》和去年画的《冬日》运用了中国画的留白,雪并没有画,是留白,但会让人感觉到雪后空气的清新。钟楼的墙略带灰色,给人一种通透空间的感觉。在创作期间,当传统的程式化语言表现与特殊性意境需要新的表现形态而发生矛盾时,我选择重表现,大胆地尝试,探索新的笔墨表现方法。这些作品让人感到了新的意境符号特征,也受到了人们的肯定。但我现在考虑如何能在绘画中加入更多的传统笔墨和本体文化,那就是由《水墨家园》的创作到后来为什么画“黄山系列”,这些内容可能会减弱个人符号的标志性,但是作为对水墨本体语言的研究历程却是重要的,需要经过一个由线性表现逐渐走向写意性水墨的过程。我在写生里尽量用墨和线的语言去抓住客观世界的特殊性感受,没有过多地转换为程式化,让特殊性的东西多一点儿而逐渐地把这种感受转为新的水墨结构语言,这也是我的研究和选择。
比如画安徽的民居,皖南房屋上的黑瓦会让我感动,这是徽派民居的特殊符号,也适合中国线的表现,但如果把它画成“框”,可能就失去了它的主要特征。除了房子外,房边多样的菜地、竹子、芭蕉等很多东西,这些你是用简单的“虚”去省略它,还是用一种线性和密密麻麻的点表现出来。我选择用线性语言把密密麻麻丰富的感觉画进去产生一种饱满的视觉效果,这种饱满的效果当它走到比较成熟的时候也会成为一种特殊性的语言,然后再增强它的随意性和书卷气。
陈履生:我感兴趣的是,当1986年“北京系列”出来以后,可染先生怎么看你的这个题材的画?
李小可:当时我觉得那个形象还不是特别突出,但是到1989年我去北戴河的时候却发生了变化。过去父亲每年在那儿休息并画几幅画。在北京特别热闹,没有安静的时间,有时纸一铺,还没画,门口就有人敲门了,心绪安静不下来,只有到北戴河的一个多月才可以安安静静地画几幅画。每年几幅山水画可能就是在北戴河那儿画的,这样在北戴河要住一个多月到两个月,每次都是父亲画幅画感谢人家。1989年时,父亲的年纪大了,由我画了一幅很大的作品,表现鸽子窝。父亲看了很吃惊,觉得这孩子可能会有出息或者说有创造性,他给这幅画题了字,显得非常高兴。
陈履生:1988年,您的作品展出时,可染先生看过您展出的画吗?
李小可:当时展出的时候没有这幅画。
陈履生:我指的是这个系列的画。
李小可:当时是有画北京的《宫墙》。
陈履生:他怎么看?
李小可:我父亲觉得《宫墙》有自己的风格。举办“北京风光展览”的时候,很多大家,包括吴冠中都过去看了,吴先生对《宫墙》给予特别的肯定。
陈履生:经过这个阶段之后,很快就进入到了“西藏系列”。当然,您也讲了在“西藏系列”中追求的是另外一种人文的感觉,包括您的摄影,包括您想要的宗教气氛,但是从画面能看出来在笔墨上跟过去有很大的不同。过去您强调用线,现在可能也弱化了一点儿,有的在色彩上更夸张,加上色彩和水墨之间的对比等等,这些手段的运用及风格上的变化应该说都是一目了然的。那么在沉浸于西藏题材的这么多年中,我想了解的是,是什么让您花那么长的时间、花那么多的精力在这个西藏题材上,这个动力除了对西藏文化自身的感受,包括你用摄影的方式记录西藏人文自然中的一些内容,有没有想到通过这个题材来突破您的“北京系列”,或者用西藏的色彩,或者用色彩提炼出来的文化关系去解决您水墨中的一些问题,从而获得艺术创作上的一个新的突破?
李小可:我觉得还是有的。因为藏地的风景很少在传统的山水画中表现过,苍茫的雪山在历代传统山水中很少画过,西藏这种以雪山为主的苍茫大美和带有宗教人文性的意境已成为我表现的重要领域。从内心讲,西藏地域对于我的感动是巨大的,会使我产生表现它的内发力。在我绘画表现的三个系列中,西藏是感受最深的。现在的创作还只是刚开始,以前是凭着一种感觉,是随意性地画,还没有进入到深入的研究阶段。我想西藏圣洁的雪山和苍茫的大地肯定要用以墨为主的语言去表达,这需要一个漫长探索实践的过程,才能把西藏山水那带有宗教性、人文性的感觉画出来。去年我又去了古格,体验回来,重新画了《远古的回声》,近10米长,描写古格的这幅作品还是延续了以线为主的表现方式。
陈履生:您第一次去西藏是哪一年?
李小可:1988年去的黄河源头;1990年去的长江源头,是青海藏区。
陈履生:真正到西藏是哪一年?
李小可:是1991年。
陈履生:1991年去西藏之前是怎么想的?是属于观光性质,还是因为去了藏区之后受到深深的感染?
李小可:在去了黄河源头、长江源头之后特别向往西藏,西藏是藏地的中心。当时中央美院研究佛教艺术的金维诺教授要去西藏,教授和我的朋友问我要不要同去,这是难得的机会,我决定一起去。第一次到拉萨,我们贪婪地看了桑耶寺、甘丹寺、大昭寺、哲蚌寺等寺,又到了日喀则,准备去萨迦寺。一天,我在日喀则招待所的院中听到有人用北京话交谈,得知他们是中国科学院青藏考察队与瑞典地质学家互访交流,他们要去珠峰。我听到去珠峰就很兴奋,希望他们能捎着我。他们说不行,因为外国专家的东西已经把车堆满了。看到我的迫切心情,他们说你可以到招待所二楼和我们队长争取一下。我又找到了科考队队长章铭陶,问他能否让我一起去。队长说车上的东西已经堆得很满,司机正闹情绪想回北京,所以不可能。这时,我突然看到茶几上搁着一本书—《中国地貌》,书名是我父亲的字,就告诉他我是谁。他感到很惊讶,我趁势又问能不能带上我。经协调,第二天一早,我就和他们一起出发了。就是这么一个机缘,我到了珠峰、樟木,后来又跟随章明陶队长到了灵芝。
陈履生:您在画了一段时间西藏题材之后又进入到黄山题材,从20世纪的70年代后期跟您父亲去写生开始,那时候的写生可能还停留在技法的层面上,后来你再回到黄山的时候,真正进入到中国山水境界之中,一种带有创作和表现概念中的黄山出现在您的笔下,这个时段大概在什么时间?
李小可:因前一阶段主要是画“北京系列”。大概是在2007年、2008年时,又回过头来画“黄山系列”的山水,期间我不断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绘画中客观生活与传统文化精神之间的关系。如果在画中仅仅凸显传统程式化的笔墨表现,就容易缺乏生活气息,但你有了生活气息之后怎么把生活气息转换成更具东方程式化语言特征的作品,这是一个反复实践探索的过程,也是2008年以后我着重探索的问题。
陈履生:我理解从《水墨家园》的“北京系列”到西藏,再到黄山,实际上经历了一个风险,因为您起步的时候是脱离了传统的表现方式,一路走过了两个系列,是十几年的时间走过来的,但是到“黄山系列”的时候,又回到了传统的山水题材、山水的格局和山水的意境之中,人们马上会想到黄山画派、新安画派,想到渐江、梅清、萧云从及现代的黄宾虹,也会想到刘海粟十上黄山,又好像进入到一种规范之中。这个时候怕的是什么?就是人们用另样的眼光看您早期的成就。您回到了传统题材之中,可能过去是不适宜画传统,如此等等。当您回到传统格局之中,比如我们今天来看您的“黄山系列”,可以说10个人中有9个人不会带有当年看您画“北京系列”那样一种惊奇的感觉,因为这种山水图式从古至今,尤其是黄山,在20世纪中有无数的画家画过,所以当您走到这个系列中来,就等于您参加了一个奥运会里的百米跑比赛——有纪录,有准则,有规范,有竞争,而可能性非常小,常常令人叹为观止,望而止步。
李小可:您说的这个太对了。
陈履生:好多名家都在这个跑道上,这就要真正凭您的功夫和学养,甚至还有一点儿运气,真正要凭您各方面的才能,才有可能跑到前面去。当奥运会有100个人报名跑100米的时候,您是其中之一,您能不能跑到前面去,或者您用什么样的方式跑到前面去,大家都在看。很多人甚至用另外一种眼光看——小可终于回到了我们的队伍之中,跟我们一块儿练,这时候要看李家的传人如何解决承传的问题。因为这时候您已经脱离了写生,有关写生状态的问题,我下面会跟您谈。写生状态的可比性不是很强,比如您画天都峰,李可染先生也画,傅抱石先生也画,刘海粟先生也画,可是我们一旦脱离了写生层面,比方您画安徽的民居,也有很多画家画,我认为这里面的差异不是很大,因为我们看眼前的现实,从现实的图像意义上看,彼此之间个性的表现还在其次,但是脱离了写生而进入到山水境界的时候已经不是眼前的现实,山的气势、山的云烟所构成的山水气韵和意境等等,各人用不同的笔墨方式去表现,也就是说大家拥有共同的法则和规律,这就是我说的100米跑的法则和规律,我们有共同的约定俗成的内容,枪一响,大家同时起跑。你用什么样的节奏、什么样的技巧去画是你自己的问题,但是中锋用笔、“六法”等等都会成为您鉴赏的一个又一个的参照,这个时候您怎么看待自己目前的状态?
李小可:我进入到“黄山系列”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2008年黄山风景区管委会为了提升黄山的文化形象,聘我担任黄山书画院的院长。我深知要担任好这个职务就必须画好黄山,如果你只能随便画两笔,那不行,要对黄山与黄山文化做深入的研究,你必须把黄山这个主题画好。第二是因为我的“北京系列”以重表现为指导思想,在表现语言中并没有把传统经验都放进去,如果都搁进去,在这种特殊性语言表现中很多地方会受到约束,如画鼓楼雪景的那种感觉和意境仅用传统的线来表现就会感觉语言不够用,在这种情况下,我会加上一些其他的视觉语言。另一方面我想通过对黄山的表现进一步研究、掌握传统程式化表现的特征,比如画黄山也有不同的表现方式,梅清的表现,渐江的表现,石涛的表现,黄宾虹的表现,也包括父亲、张大千、陆俨少等等,通过研究、学习,以画黄山的实践来掌握传统程式化、多样化的表现。这个过程也是回归传统、深入研究传统的过程,期间我也会有自己的审美选择,与其他画家有不一样的追求。比如我画得很黑、很整,突出结构和量感的表现,从中也吸取范宽等古代大师的经验。我在这个阶段集中解决结构与量感,下个阶段可能解决墨在山水中的气氛,使画面中的线慢慢弱化,变成气象的东西。如果一开始就把气象放在重要位置,而没有对结构和量感的把握,这个气象会比较空洞。量感、结构感也可能是我个人化视觉审美表现特征的选择,画面比较满、密,弱化了空灵。这种满和密增强了山的气势和压迫感。反之,若强化了虚和气氛则会弱化这种量和势,顾此失彼……关键是在这个阶段你希望要的是什么?艺术家是在虚、实两个方面不断地探索和选择着……
这个过程就像排球运动员争夺世界冠军,是从练习接发球开始的,训练对球的控制能力。只有经过反复的练习,才能进入控制自如的状态,绘画表现中同样存在着对画面控制力的掌握过程,如对画面的结构、造型、空间、量感、虚实等方面的控制力需要通过不断的实践来掌握,而中国画的写意状态则是艺术家对绘画语言规律高度掌握后的自由。
陈履生:您这段时间有没有去黄山写生?
李小可:有,而且量很大。
陈履生:那这段时期的写生跟您20年前、30年前的写生有什么不同?
李小可:肯定有很大的不同。
陈履生:主要表现哪儿?
李小可:现在写生中的概括力、笔墨性对整体意境特征的把握,以及笔墨表现更强。写生每个阶段要解决的特殊性问题和目的各不相同,现在更加明确。
陈履生:如果把您这个时候的写生跟您父亲的黄山写生比较一下,这里面有什么异同?或者说您怎么看待您父亲那个时期的黄山写生?
李小可:父亲的写生是以东方的笔墨语言和文化精神到生活与大自然中去发现新的个人化的审美,通过深入的写生感悟、蕴酿着他新的审美语言与意境的产生。如何对待写生的问题存在争议和不同的看法,但艺术家是一个很个人化的选择的艺术道路,决定了其艺术的特殊风格。在写生中,你如何对待客观世界带给你的感动,这是个人化的。有人认为我父亲是用一种西方的观点去写生,我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更多的是用一种贪婪的态度把对这个世界的感动以水墨表现在画面上,他说写生时你要像从其他星球来的一样,以孩子般的新奇感去敏锐地感知这个世界,通过写生把传统、自然、时代与个人化的审美选择连接起来,逐渐形成新的表现可能性。西方大师莫奈、塞尚、梵高、高更,他们的艺术也都是从生活中获取灵感。董希文、吴作人先生早年去西藏的写生,我们现在看到他们的这些作品依然有着无限的生机和感染力。
陈履生:毫无疑问,从“家园系列”开始,以屋顶为主要构成的这样一种构图方式用笔墨表现,有“李家山水”的典型特征。在您的作品中,强化白也好,黑也罢,包括您的树的画法,镂空的、留白的这种格局、这种方式,应该是李可染先生的独创,在他的山水画中常见。这样一种方式也给您的画打下了一个烙印,一个有着血缘上联系的烙印,然后是文化上的联系,再就是笔墨上的传承。您肯定会思考这样一种传承关系,因为人家一看您是李家出来的,是要传承的,这是一种责任。还有一种是您为了摆脱这一责任关系,需要突破,您是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您有没有想到要精心地传承?或者有没有想到要去突破,或者怎么在两者之间既要在传承的基础上突破,又要在这一基础上开辟与父亲完全不同的新天地,或者根本就不想去突破,就是要把李家的东西继承下来。当然,这不是李小可,这可能是另外的李家弟子。在“李家山水”的传承人中,不乏完全要把李家的风貌传承下来的人。可是您首先已经有突破了,包括现在所画的“黄山系列”,我们也能够看到这种突破,但是黄山的这些松树以及其他一些画法,一看还是“李家山水”。我想每个人都会怀有这样的心意去探寻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一种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不是理论形态上的一种简单化的阐释。这就牵扯到中国画的传统,包括很多有名的画家后人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比如潘公凯画的荷花,可以说几乎没有他父亲的样式和面貌,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一种联系,一种相似的感觉——霸悍之气。
如此来看您的画,即使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家园系列”刚出来的时候,人们看到的是一个水墨老北京的表现,但人们一看这是活脱脱的“李家山水”的变体,有关联,又确确实实不是李可染先生笔下的东西。从画面的具体表现中,人们可以从路的画法,包括行人,看出和可染先生的画很像,但可染先生又不是这样一种形式整体的。在这种传承的问题上,您是怎么想的?又是怎么做的?
李小可:当艺术进入到文化层面上,人们对于传统经验的继承是必然的。传统是人类文明的经验结晶,其中包含着艺术表现的共同规律与特殊性规律。在任何有感染力的艺术作品中,尽管一定有艺术家个性的创造,同时也必然涵融着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借鉴。我的借鉴是必然的,这不仅仅是对父亲的艺术经验的借鉴与吸收,也包含着对其他艺术大家的借鉴,如傅抱石、陆俨少等,同时也有历代的大师,但最终在作品中,我的表现意境、审美选择和笔墨特征是有区别的。在作品中必然会保留这个流派的特征,同时会增添新的表现可能,《水墨家园》线性的表现就更为突出,在表达的内容意境上与先辈有所差异;表现西藏题材在父亲的作品中不可能找到直接的借鉴,但会从中吸收某一点经验,最终要发展为另外一个新的东西,包括蓝天颜色的尝试,在有些用水墨表现的藏地题材作品中能找到墨的浑然一体,这肯定跟父亲的山水有很深的联系,也有一些作品会凸显我个人的审美追求。《老城遗韵》这幅作品里的老墙,以父亲的方法是不会把砖一块一块地画出来,当然也可以不画一块一块的砖,而用淡墨渲染就很难把城墙上那种历经沧桑的肌理感表现出来。我在绘画中要用一种特殊性的视觉语言来表现对客观的感受,以线性的语言描写城砖的秩序与错落,以及岁月带来的沧桑感,但如何把城墙与树的语言变得浑然一体则是一个实验的过程,如同怎样把音乐的元素组织到统一性的旋律中一样。
陈履生:您有没有临摹过您父亲的画?
李小可:当然临摹,而且不少。
陈履生:是在20世纪的70年代后期,80年代初期?
李小可:是的。不过再晚也临过。
陈履生:再晚一些就是80年代中期?
李小可:中期那会儿也临了一批傅抱石、宋文治、亚明等画家的作品,近期又对历代名家作品的局部临摹有一批。
陈履生:近10年来,您有没有临摹过您父亲的画?
李小可:没有。现在我对父亲的作品更多的是理解他的视觉表现特征和笔墨韵味的感染,力图吸纳他作品中墨的表现力,“墨”在他的绘画中好像能发出声音。目前,我的绘画主要以线性语言为主,下一步会着重吸取父亲墨韵的表现特征和增强绘画的表现意境。
陈履生:话题转到另一方面,您去西藏的时候拍了很多照片,而且那个时候您对摄影如此狂热,后来您又把您的摄影作品转化为一批丝网版画。您怎么看进入到摄影和版画这个阶段和水墨的关系?
李小可:实际上摄影是我对藏地的人文关注和感动,是人生的一种体验,甚至这种感动在某种程度上不低于水墨表现,人生旅途上对我心灵震撼最深的是西藏。黄河源头、长江源头,西藏的宗教文化,藏地雪域的博大、苍茫、瑰丽又带有一种苍凉、严酷,当你走进去的时候,你会有莫名的感动,这感动既是对自然的感动,也包含着一种精神。这里有藏地宗教文化与生命本源的真切状态,有精神与信仰的坚持,在这儿还保留着“真”,这正是现代社会所缺失的。在感动中拍下的这些照片,对我来说可能是人生不可磨灭的经历,创作丝网版画的意义与一般艺术性创作还有些距离,实际上更多的是想把那些心灵的感动记录下来,这就成为一种迹化的过程,带有一种行为的含义。有点儿像藏族人民把佛像与经文刻在玛尼石上或印在经幡上。这个过程是我内心世界的一种对藏地、藏人的敬仰与崇敬。在创作中,我只对原有的照片稍加艺术处理,增强岁月的流失与沧桑感,也把自己的某些心境表现出来。实际上这也是对水墨语言表现的一个补充,它不需要受更多的约束,但在表现中我觉得生活本源的东西不能丢失太多,这里含着对生命与自然本体的感动。很多外国大使和专家们看到这些丝网版画时都被这真切的形象所感动。下一步我会做得更加精到,更强化人文的痕迹性。“藏迹”使我想到巴黎圣母院,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的故事是从教堂墙上刻着的字母开始,写的是痕迹背后承载着的那个使人震撼的故事,“藏迹”也希望有着相同的表达。
我想艺术是从感动开始的,艺术也是生命所经历的岁月的痕迹。当你回顾过去,自己好像是一个不断经历着人生命运旅程的行者,而我的作品就是行者在探索的荒途中所做的“活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