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诗歌对中国新诗发展之影响——“白屋诗体”对杜诗的接受
2013-07-04彭超
彭 超
作者:彭超,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610064。
吴芳吉于1896年生于重庆。他一生致力于诗歌创作。创造出独树一帜的“白屋诗体”。“白屋”一词源于吴芳吉重庆江津老宅名。其父鉴于当时江津民风、民俗混浊不堪,将所居住之宅刷为白色,并取名“白屋”,取其出污泥而不染之意。吴芳吉将自己创作的诗歌取名为“白屋诗体”,一方面表达自己人格高洁之意,另一方面表示自己诗体探索的独树一帜。“白屋诗体”在形式上,表现为不拘格套,律诗、自由诗、歌谣体皆可自由用之;在语言形态上,呈现为不拘泥于文言与白话,而是根据诗歌表达需要而选用之,并不为所谓的新体诗、旧体诗所限制。“白屋诗体”的创作宗旨是“三日不书民疾苦,文章辜负苍生多”。在内容上多是关注底层大众在战乱之中的颠沛流离。
“白屋诗体”的诞生既缘于中国新诗运动,也得力于传统诗歌的影响。前者体现在“白屋诗体”对于中国新诗诞生之际“新”、“旧”两派的批判接受,后者体现在对杜诗的传承创新。二十世纪初叶,中国新文化运动正开展得如火如荼,诗歌也经历了有史以来最激烈的变革。“诗界革命”、“白话运动”分别从内容与形式上对诗歌提出新的时代要求。诗坛上,新旧两派之争使得中国诗歌发展面临一条非“新”即“旧”的二元选择。在此时代潮流之下,吴芳吉并没有随波逐流卷入其中,而是坚持独立创作。吴芳吉坚持诗歌独立创作的精神依托很大程度在于他对杜诗艺术的传承。吴芳吉一生最爱杜甫:“幼读少陵诗,深识少陵志。一生爱此翁,发愿为翁寄。”并发誓追随杜甫足迹,“老杜所游诸地,今追步殆遍矣”。
“白屋诗体”对传统诗学的继承主要表现为杜诗对其的影响。吴氏诗歌创作在对待前人的态度上与杜甫是一致的。杜甫“转益多师是吾师”的态度,使得他不轻易排斥前人的诗歌成就,子美在“集大成”的同时又“开诗世界”。杜甫在继承前人诗歌成就的同时又有革新和创造,并不只是简单地一味继承。吴氏诗歌创作在对待前人成就与今人创作的态度上与杜甫是完全一致的,并没有简单地以“新诗”或“旧诗”的标准来进行诗歌创作,而是创作出了以继承杜诗精神内涵、融汇时代文化为实质的“白屋诗体”。
一、杜诗艺术对吴芳吉诗歌创作的影响以及“白屋诗体”的诗歌艺术
1.语言艺术
吴芳吉认为“所谓白话、文言、律诗、自由诗FreeVerses等,不过是传达情意之一种方法,并不是诗的程度。美的程度,只为一处。至于方法,则不必拘于一格。今新诗旧诗之故意相互排斥,都是所见不广。”其语言观既受杜诗影响,也是时代思潮影响所致。
杜诗语言艺术具有创新精神。唐人主尚含蓄蕴籍,而杜诗大量引议论入诗。这与当时诗歌主流创作在语言上是相悖的,但却被后人誉为首开宋调先声。杜甫为增强诗歌的表现力,大量吸收、提炼和运用民间俚语、俗语和方言入诗,使得其诗歌语言既有新鲜、活泼、明白晓畅的特点,又能准确、生动地反映和描写普通百姓的生活和思想,具有很强的表现力。杜甫的“三吏”“三别”的语言,其口语化和通俗化是其主要的特色,如《新安吏》中“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新婚别》中“生女有所归,鸡狗亦得将”;《无家别》中“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等,语言皆明白如话,通俗易懂。“七律本宫廷应制之作,多华贵之气,而杜甫却偏以口语入诗。他如‘秋水才深四五尺,野航恰受两三人’‘春山无伴独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等皆属此类。虽无丽藻,然朴素深挚,情真意切,杜甫之前未曾有。至元和、长庆年间,元、白之流相袭不弃,竟成风气。及至晚唐李山甫、杜荀鹤手中,依然如此。然首创此风者,当为老杜。”
杜甫这种以表现诗歌内容为中心,不避以民间俚语入诗的诗歌表达方式,对吴芳吉诗歌创作的影响是很大的。吴芳吉“白屋诗体”语言不拘泥于文言、白话,而是根据诗歌内容的表达需要而定。吴芳吉认为语言形式只是表达情感的载体而已,所以其选择语言不为追逐潮流而刻意“创新”。如《两父女》,内容描写的是父女俩相依为命的苦难生活,“月光皎皎映土室,冷如冰浇。衬出个断柏支床,离地盈尺高。正父女两人,蜜甜甜,睡悄悄。烂絮一幅用麻包,麦杆一扎作枕靠。鼠子叨叨,翻弄他床头锅灶。”“月光皎皎”是古典诗歌常用词汇,但“正父女两人,蜜甜甜,睡悄悄。烂絮一幅用麻包,麦杆一扎作枕靠。鼠子叨叨,翻弄他床头锅灶。”则为明白晓畅的白话语言。再如《婉容词》,描写的是婉容投江自杀后天地萧瑟之景象,“野阔秋风紧,江昏落月斜。只玉兔双脚泥上抓,一声声,哀叫他。”前句以秋风、旷野、落月传统意象勾勒出一幅萧瑟之景象,后句则以纯口语白话写出婉容孤寂一人离去,无人为之哀悼,只有白兔为她送别。
“白屋诗体”的语言艺术既有对传统的继承和借鉴,也有现实依据。当时文坛新派主将胡适也曾谓“白话运动”非中国文化史上开天辟地第一回,而是文化变革经历中一个环节而已。“革新”精神是新诗坛的主流。“白屋诗体”大量采用口语、俚语入诗,较之杜甫诗歌在语言“平民”化上可谓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例如《婉容词》“他说:‘我非负你你无愁,最好人生贵自由。世间女子任我爱,世间男子随你求。’”诗歌几乎全部运用口语白话入诗。这也有时代思潮如平民文学”、“启蒙文学”的烙印。
但是“白屋诗体”并没有新派的激进,欲以白话代替文言,因而受到新派阵营的排斥与责难。康白情是胡适的学生,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也是吴芳吉的四川(重庆直辖之前)同乡。他抱着以“拯救”吴芳吉,避免他陷入旧派文人行列之好意,极力劝说吴芳吉放弃以文言入诗,但被吴芳吉严加拒绝。与此同时,保守派阵营对吴芳吉以白话入诗深表不满。“学衡”派代表吴宓,也是吴芳吉的良师益友,对此严厉指责,甚至以绝交相威胁。殊不知,新派阵营主将胡适推崇的“元白诗派”实乃渊源于杜甫诗歌创作,保守派阵营对诗歌语言革新的强烈抵制却是相悖于杜诗创新之精神。“白屋诗体”被当时诗歌主流派别指责为“非驴非马”,受到新旧两派文人的抵制与排斥,但吴芳吉始终坚持创作理念,并没有作任何妥协和放弃。这种执着精神与杜甫精神是一脉相通的,亦彰显了他“幼读少陵诗,深识少陵志。一生爱此翁,发愿为翁志”的人生宏愿。
2.诗体形式
新诗在传统诗学的浸润之下,根深则叶茂,也才会有独具特色的“白屋诗体”产生。“白屋诗体”对杜诗艺术的传承还体现在诗歌形式上。
乐府诗产生于汉代,自汉武帝正式创立乐府官署,乐府诗也就成为了中国诗歌文学中一种新的表现形式。汉乐府大部分以描写社会底层人民生活,反映社会现实,表达社会底层民众的心声为主要内容,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班固《汉书·艺文志》称其“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且“可以观风俗,知厚薄”,这是乐府诗的本质特征和精神内核,但是乐府诗发展至六朝到唐代,所表现的题材范围日趋狭小,内容也愈加空虚,逐渐脱离了社会现实。杜甫的“新题乐府”诗就是对传统乐府诗体式的开拓与创新,对汉代乐府诗歌本旨与精神内核的回归。杜甫不仅在表现内容上对当时的乐府诗歌进行开拓和创新,而且在形式上也是不拘条规旧习,进行大胆的变革。杜甫对《兵车行》、《丽人行》、《石壕吏》等题目的命名,便是完全抛开传统乐府诗命题方式,依据内容自行命题,这就是元稹所说的“率皆即事命篇,无复依傍”(《乐府古题序》)。杜甫对乐府诗的内容和形式都作革新,开创了“即事名篇”的“新乐府”,使得乐府诗从此有了“新乐府”、“旧乐府”之分别。
吴芳吉的“白屋诗体”诗歌所表现出来的创新精神与杜甫是完全一致的。“白屋诗”也是“即事名篇”,不拘一格,例如《摩托车谣》、《曹锟烧丰都行》、《非不为谣》、《卖花女》、《短歌行》、《痛定思痛行》等等,皆表现出了与杜甫“新题乐府”诗相同的特点和精神实质。而且由于时代的不同,吴芳吉更具有自由之精神,表现在诗体形式上即是更加具有多样性。“白屋诗体”有绝句、律诗、赋、自由诗、歌谣体、乐府诗歌,例如《清明》:“小妇缝衣趁晓明,春衣和暖受风轻。……日暮推窗闲展读,蜀山争入晚帘来。”《儿莫啼行》:“儿莫啼,儿啼伤娘心。啼多颜色减,心伤瘦不禁。朔风凛且烈,气凉夜已深。忆昨洪宪初,兵马来骎骎。驱男作俘虏,驱女作浮苹。”《赋丈人八首》:“丈人在山南,结庐江之浒。庆生四十春,蔼蔼上眉宇。……”《秧歌乐》:“秧歌乐,溪山冰解湿云薄。草地乱莺飞池塘群鲤跃。春田平似玉磨琢,春泥软腾毡毹托。残兜装毂两三回,密密撒去疏疏落。撒了山腰又山脚,石矶小憩村烟廓。一粒之栗万颗获。秧歌乐,秧歌乐。……”《巴人歌》:“巴人自古擅歌词,我亦巴人爱《竹枝》。巴渝虽俚有深意,巴水东流无尽时。……我非排外好兴戎,我为正义惩顽凶。我知前路险重重,我宁冒险前行峰。我今遭遇何所似?我似孩提失保姆,倭儿蠢蠢似蠛蠓。群盗嚣嚣似虮虱,诸公衮衮似蛔虫。荡涤行看一扫空,还我主权兮还我衷。和平奋斗救中国,紫金山下葬孙公。”
形式自由灵动的“白屋诗体”消解了中国新诗坛对旧体诗的顾忌,避免了散文化、形式化的不良趋向。其大胆革新对于中国新诗的发展无疑提供了又一面可供借鉴的镜子。由此可见,吴芳吉诗歌创作随物赋形,率事名篇,真正做到了新文化所提倡的“自由”,即不以传统定规为藩篱,也不以当代权威为偶像,同时也不以派别为标签,对新旧文化之优长皆采用之。吴芳吉“白屋诗体”的诞生,说明“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诗歌艺术的探索精神,也证明当时诗坛的丰富性,而并非今天我们在文学史教科书上看到的那样一个贫乏的诗歌园地。
二、“道”之延续流变
其诗歌创作主旨“三日不书民疾苦,文章辜负苍生多”的爱民思想便是对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传承。
中国传统诗文创作皆讲究以文载道,所谓“道”,主要是指儒家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概而言之主要是“仁政”和“民本”的思想,体现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则表现为对民族、国家的一种担当精神和责任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岳阳楼记》)便是其具体体现。杜甫被称为爱国诗人,其诗歌充满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一生心系国家和人民,儒家的“仁政”和“民本”思想在他的诗歌里是随处可见。宋人以“道”论人论文,对杜甫极为推崇,并将其诗歌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最高典范。吴芳吉自幼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和熏陶,和杜甫一样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称自己“一生爱此翁,发愿为翁志”,在其诗文创作中表现出了与杜甫同样的爱国忧民的伟大爱国主义和人道精神。杜甫精神在吴芳吉的诗歌里被得以延续和弘扬。
1.道之传承
首先,两者都同样具有同情弱势群体的人道主义关怀。杜诗《石壕吏》、《兵车行》、《无家别》等都是关注底层百姓生活之困苦。“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杜甫在自身遭遇不幸之际,依然关心天下寒士之命运。吴芳吉和杜甫一样,具有高尚之人格。吴芳吉非富家子弟,生活贫苦,正如其诗歌《海上行》中描绘的一样:“棉衣破兮夹衣裂,寒气入闱横砭骨。手如冰兮足如铁,蒙头伏枕梦不发。”甚至连恶狗也会仗势欺人侮辱吴芳吉,“主人见吾窭,藏其箕与帚。箕帚值百钱,防我暗伸手。邻犬见吾吠,张牙嫌我秽。”纵然条件如此之艰辛,但吴芳吉对弱小的乞食儿童依然会倾囊相助。正因为主体具有高尚的人格特质,所以杜甫和吴芳吉的诗歌皆关注社会底层百姓的苦难生活,使诗歌具有了“史诗”的品格。
其次,两者诗歌皆以史诗的笔法展现历史真实。“诗圣”杜甫以史诗的笔触写出唐朝安史之乱后人们生活的艰辛困苦,为后人展现一幅幅历史画卷。杜诗《兵车行》描写战争造成千里荒野,百姓的生命之轻,还不如鸡犬“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兵车行》)。杜甫笔下之悲剧非历史终点,到了民国年间还在继续上演。吴芳吉之《儿莫啼行》“愿为太平犬,勿作乱世民。为犬犹为主,为民谁与亲!”诗歌以简练的语言,生动描绘出袁世凯称帝带来的社会动乱,以及百姓生命如草芥的沉重灾难。老百姓的困苦无人问津,老百姓的冤屈无处述说。《两父女》从幼女的视角写出家庭的离散之痛,幼小女童眼睁睁看着母亲被杀,家产被抢,自己无奈被送与他人,而离开了自己唯一的亲人——父亲。诗歌语言通俗质朴,以白描手法勾勒父女俩穷困凄凉的处境。吴芳吉诗歌创作以现实主义手法为主,描绘底层大众的生活状况,以史诗的笔触写出民国时期民众在军阀混战之下生灵涂炭的一幅幅历史画卷。《赴成都纪行》写出军阀混战,官吏虐民,人民在死亡线上挣扎而朝不保夕的一系列惨状。吴芳吉的诗歌就是当时一幅幅老百姓苦难生活的素描。他行至永川时看到的则是“路死谁家儿,半身滥泥涴。云是远行客,疾发无人管。门内游子栖,门外冤魂潸。”从永川到邮亭铺六十里之间,触目所见皆是荒僻之景象,民家尽为兵匪所毁。“一年三预征,年复兵戈创。有田不足耕,父子难相养。……空山无一人,寒鸦守亭鄣。”这和杜甫“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兵车行》)展示的历史画卷何其相似。到隆昌时看到的又是“君看城边路,累累挂人头”。行至简阳时看到流民众多,娼妓比良家妇女还多:“就坐不及瞬,流民聚若毛。前方围乞丐,后席列娼僚。……诸姬闲不语,但笑自垂髻。眼枯知泪竭,身软步摇摇。”娼妓也是可怜人。及至成都又与往昔相比:“忆昔来此日,正当宣统时。夜行无吠犬,草木有华滋。涵濡忘其美,但如不自私。今我重来此,竟日见人稀。望颜皆可畏,交语互生疑。黠猾移天性,礼让转惊奇。”
吴芳吉对现实苦难的关注,师承杜甫,实现了其“幼读少陵诗,深识少陵志。一生爱此翁,发愿为翁志”的人生宏愿。
2.“道”之嬗变
吴芳吉与杜甫之忧患意识在具体表征上却有所不同。吴芳吉传承了杜甫的爱国情怀,但这份情怀由于时代、地域、文化等因素的不同,两者之间亦存在有差异性。
杜甫是儒家文化的典型代表,遵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秩序,视天子为真理、光明的化身。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其中“风俗淳”的核心是关心大众,但其“致君尧舜上”依靠的力量却是君主。近代“民主”、“自由”之风,使“天子”之地位被“大众”置换,体现为吴芳吉之“三日不书民疾苦,文章辜负苍生多”。同样关注天下苍生,大众中的知识分子成为了坚强诗文力量,文人以“文章”为武器寻求救国之道。杜甫生活在封建帝王时代,天下是帝王一人的天下,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那时的知识文人报效国家,欲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梦想,唯一的途径只能依靠科举之路,方能面见圣上进而谏言献策。杜甫滞留京城,即使生活窘迫,遭受“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酸楚,亦坚持了十年之久。这般坚守背后的动力来自于他相信唯有在君王侧才能施展自己的政治理想。封建时代儒家思想一统天下,儒家核心便是忠君思想。杜甫诗歌中的“故园”往往非指杜甫出生地河南,而是指当时的京城长安。因为长安是他人生理想实现之地,被寄予杜甫太多的期待和向往,例如“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杜甫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仰视君王,寄希望“风俗淳”于君王也是自然而然之事。再者,便是地域文化因子也参与其中。河南与巴蜀之地域文化特质不同。河南是中原文明重镇,深受儒家文化浸染。杜甫出生于儒家思想氛围甚浓的中原河南,杜家又是儒家世家,地域文化与家风的熏陶与时代背景相结合,铸就杜甫典型的儒家文人性格。
吴芳吉处于帝王思想崩溃、民主自由之风盛行的民国时代。吴芳吉生活的时代封建帝制土崩瓦解,西方民治维新思想席卷中国知识界。忠君思想被“民主”、“自由”所取代,爱国情怀也不再以君主为依靠力量,而是民众。当民众还处于蒙昧状态之际,对其的启蒙则成为近代知识分子持之以恒的追求。中国文化的变革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开始,文学革新不是为“文学”而“革新”,而是为国家和民族。文学已经被赋予了拯救民族危亡的时代重任,鲁迅、郭沫若的弃医从文便是典型的案例。吴芳吉生处于这样的时代,同样也相信文学能担当此重任,所以吴芳吉爱国情怀视角不是向上仰视君王,而是体察民众之苦并诉诸于文学,以此期待能唤醒大众的反抗意识,拯救国家民族与水火之中。同时,从地缘位置分析,吴芳吉生为巴人,其深受巴蜀文化影响。巴蜀在历史上是化外之地,民风民俗迥异于中原河南,文化内涵既有浪漫飘逸之风,又充满叛逆精神。巴蜀文化具有不崇尚权威、追求自由的精神特质。近代的邹容写出影响时代的《革命军》,同代的郭沫若喊出打破偶像权威的时代最强音《女神》,这些都是例证。时代的浪潮与其天生具有的叛逆特质,都使吴芳吉对杜甫“道”之传承具有异质性。“道”的嬗变也使吴芳吉诗歌中爱国情怀在表达上与杜甫不同。吴芳吉诗歌较少“故园”意象。吴芳吉诗歌关注百姓在战乱之中遭受的颠沛流离。诗人归结其祸根,将矛头指向鱼肉百姓的军阀与侵略中华的外来势力。这也彰显了巴蜀文化不惧权威之精神特质。
忧患意识是中国知识分子具有的一贯情怀。忧患意识在不同时代则有不同的内涵,吴芳吉对杜甫精神之传承,其忧患意识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相同之处便是对国家民族的热爱,不同之处便是这份热爱因为时代、地域等因素的不同,使得这份情感具有不同的视角,昔日万能的“君王”换为今日的芸芸“大众”,所以便有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到“三日不书民疾苦,文章辜负苍生多”的传承演变。
小结
“白屋诗体”的形成与产生标志着吴芳吉诗歌创作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个人风格,同时也标志着吴芳吉诗歌创作的成熟。吴宓誉其为“天地英灵气,古今卓异才。”于右任盛赞吴芳吉:“生大文豪天亦难,遇大文豪世不易。今读遗集诸大篇,大笔回环我无泪。祝此独立特有之雄才,再以文章为世瑞。”
吴芳吉,这位当年被梁启超钦慕并预言定能为诗坛开辟新世界的诗人却英年早逝。1932年,他离开人世,年仅36岁。吴芳吉生前坚持独立的诗歌创作,不为派别束缚,虽然遭来众多的非难,但其人品精神与诗歌影响力却赢得文化界人士一致的尊重。在成都召开的追悼会上,聚集了当时社会名流便达三百多人。在南京国立中央大学任教的柳贻徵教授,常为《学衡》撰稿。他闻此噩耗,立即赋诗一首,以表哀悼,诗云:“倭奴寇浏河,曾读巴人歌。巴人之歌声未已,河端白川相踵死。我意巴人闻之必狂喜,更将摇毫吮墨,为吾沪太崑嘉作诗史。一书天上来,未启心疑猜,蜀中挚友何事咨询哉?开缄读未竟,酸泪随声进,白屋诗人乃短命。”(《哀吴碧柳诗》)。毛泽东在分析中国新诗发展道路时,曾高度评价吴芳吉为“芳吉知春,芝兰其香”,喻其为现代文学早春的芝兰,香满诗坛。台湾学界则追悼吴芳吉为民国开国诗人。
在今天,“白屋诗体”的影响力依然存在。吴芳吉曾踏足过的地方,如重庆、成都、长沙等地,分别有自愿组织的民间团体“吴芳吉研究协会”。吴芳吉开创的“白屋诗体”在中国新诗坛具有独特之意义。对其的挖掘整理,不仅丰富了新诗发生的历史现场;在中国新诗发展的当下,对于新诗之未来发展也具有借鉴的现实意义。
注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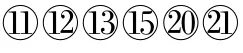
⑤孙琴安:《唐七律诗精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1版,1990年,第2版,101-10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