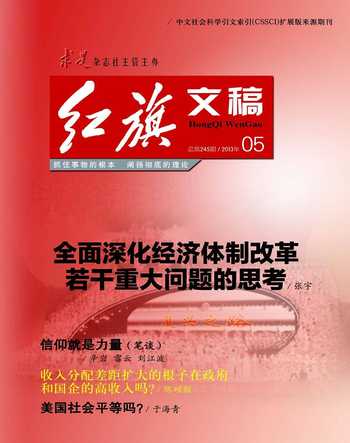铭刻在肉体和心灵上的信仰
2013-04-29刘江波
刘江波
共和国开国将领唐凯身上有块印记,是刺青。刺青不鲜见,然而,唐凯身上的刺青似乎有一种非凡的魔力,以致老人家过世多年,仍引来史学家的反复考证,文学家的一路追捧。这是为什么呢?为寻求答案,我曾找上门去与老人的儿女们一起探寻。
唐凯出生的1916年具有划时代意义。这一年,袁世凯死了,黎元洪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第二年,即1917年,北方的俄国传来了十月革命的炮响,从孙中山的变革中生长出一股新鲜的力量,借五四运动呼啸着奔涌而出,开启了共产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篇章。唐凯五岁那年,中国共产党诞生,青年毛泽东一步步走上历史舞台,开始影响中国革命的道路和方向。
1927年,共产党人在国民党的屠杀中丢掉幻想,走上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的道路。8月,江西南昌起义。9月,湖南秋收起义。11月,湖北黄麻秋收起义。然而,仅仅21天,这个有着20万百姓助威,4万农民义勇队、240支枪的农民自卫军参加的黄麻农民新政权就被摧毁。野蛮的杀戮过后,仅存的72条好汉辗转来到湖北黄陂木兰山一带打游击。革命就这样来到赤贫少年唐凯的身边。
1929年的一天,20岁的共产党人余尧之来到唐凯家中。无数次促膝谈话、考察培养之后,他认定唐凯符合共产党员的条件,就和一个名叫五哥的共青团员一道,介绍唐凯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助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这是唐凯的第一次政治洗礼。当激动不已的他在穷乡僻壤的一间破草屋里,面对墙壁上的那块红布握紧拳头的时候,他被余尧之称之为代表共产党的镰刀斧头图案深深地震撼,执意要把镰刀斧头刺刻在手臂上。他毅然伸出右臂,五哥紧紧攥住他手臂的两端,余尧之从炭火盆里取出一枚钢针,向他的手腕上方刺下去。
这是不是乡间顽童的一时冲动,是不是雅皮士的玩世不恭,抑或是江湖好汉的豪壮与义气?是什么力量让这个13岁的少年在血肉之躯上刺刻镰刀斧头的图案?
让我们将这块刺青放到历史的显微镜下,来看看20世纪初叶中国农村真实的样子吧。
那是山河破碎、国弊民穷的中国,到处是民怨沸腾,到处有剧烈的冲突。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几万万农民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毛泽东语)”对唐凯而言,刺青是一杆秤,用它称量中国,它一头盛着农民的苦难,另一头盛着农民的仇恨,压迫有多深重,反抗就有多强烈。用它称量唐凯从宿命中醒悟的内心,它一头盛着孜孜以求的梦想,另一头盛着叛逆旧制度的呐喊。这仇恨刻骨铭心,这反抗积蓄了太久,这梦想以致长夜难眠,这呐喊令人心雄胆壮、热血沸腾。
再将刺青放在历史的风向仪下,我看到,在中国大转折的门口,刺青不经意间推动了60多年前东北平原的战事变化。
那是1945年8月9日,150万苏联红军在一夜之间突破了中苏、中蒙、中朝边境3500多公里防线,长驱直入中国东北,向70万日本关东军和30万伪满洲国军发起全面进攻。14日,裕仁天皇颁投降诏书。胜利突然而至,共产党与国民党,谁捷足先登东北,谁就取得了打天下的主动权。
毛泽东准备与国民党一争高下。蒋介石则日发三令,命国民党各战区部队加紧作战努力,“八路军就地待命。”愤怒的毛泽东拒绝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共军”的两条腿跑在了“国军”前面。其中,由中共冀热辽军区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副政委唐凯率领的一支队伍,且战且行,顽强挺进,于9月5日最早乘火车到达沈阳。
先期占领沈阳的苏军对这些几乎是从天而降的中国军人一无所知,他们用火炮、冲锋枪、机枪一齐对准车厢,盛气凌人地发出命令:“你们,不许下火车!”曾克林多次派人与苏军接洽均遭拒绝。八路军拉撒在车上,吃饭成问题,加上烈日暴晒、没有水喝,2000多名官兵成了名副其实的“人在囧途”。
曾克林、唐凯再次来到苏军卫戍司令部,唐凯一把撸起袖子露出镰刀斧头标记,指着自己的胸口用生硬的俄语说:“格米萨(政治委员)!格米尼斯特(共产党)!”然而,尽管唐凯提出了严正的抗议,曾克林把桌子拍得山响,苏联军人依旧毫不通融——他们谁也听不懂对方在说些什么。
或许是“政治委员”在苏联红军中所享有的崇高威望(1934年通过的苏共党章曾对红军政治委员的工作职责做出过明确的规定),抑或是被唐凯身上特有的气质所吸引,一位苏军政工干部终于看出了一点门道。几个苏联军人拉住唐凯的手臂,反复端详后大吃一惊,唐凯右臂上的刺青与苏联的国徽图案竟是何其相似!于是,请示的电报迅速从沈阳飞向身在长春的远东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元帅,飞向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八路军这才下车进城。
对唐凯而言,刺青是身份证。由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徽的镰刀铁锤图案演化而成的苏联国徽标识,是共产国际领导下各国共产党通用的标志;在世界反法西斯战线上,是中国八路军与苏联红军特殊关系的印鉴。你看,一个人的命运就这样被嵌入历史命运,一小块刺青不可思议地成为风云变幻的记忆印证。
当我再次收回思绪的时候,我愿将刺青放到历史的扫描仪下看一看,啊,满视野透视出来的,竟是那一代人的集体图像!
1927年底,“红军”的称号首次在鄂豫皖的土地上出现。在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影响下,大批共产党人深入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的乡村,将一向苦战奋斗的贫农组织起来,用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凝聚起他们的共识,并将其中的坚定分子吸纳进共产党。
唐凯,这个意志坚定的少年,在终日乞讨而变得黝黑粗糙的皮肤上,十分情愿地刺刻镰刀斧头图案,因为对唐凯而言,刺青是史碑上的勒铭,用它记载的人间真理,引领着他前行;用它记载的崇高信仰,渗透到他的骨子里,哪怕被砍下头颅也绝不会动摇。
正是为了绝大多数人谋求利益,才有了八路军纵横驰奔“向北发展”,东北同胞得以在整整14年后第一次见到了老百姓自己的队伍;才有了中共“让开大路,占领两厢”——黑土地上迎来了与1927年湖南秋收起义、湖北黄麻秋收起义不同版本的“农村包围城市”,农民得到了被剥夺已久的土地;才有了东北人民全心全意的支持,17万八路军出关、100万解放大军进关;也才有了共产党与国民党真刀真枪的较量之后,共产党终于叩响了新中国的大门。
对唐凯而言,共产党与国民党,其各自政党的宗旨对于历史走向的顺应与悖逆之分,或许早就在这红与黄、镰刀与铁锤的构图中定格。
······
以天下之大,人,该有多么渺小!一块刺青更加微不足道。然而,它见证了世纪更替,见证了时代轮转,它承载了誓愿,承载了信仰,所以,这块刺青很大,很重。它是共产党人信仰的印记。但凡崇善、向善的人,恐怕都有信仰。只不过共产党人的信仰更加高远,其宗旨也更加实际。刺青以跨度70年的沉默记录了唐凯的人生磨砺,记录了那一代人的集体信仰,也记录了共产党人一代又一代赓续不断的抉择。
(作者:中国东方航空集团公司原副总经理)
责任编辑:李艳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