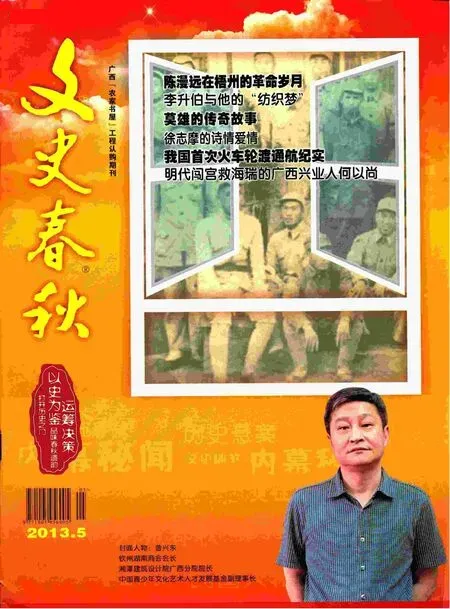陈三立与庐山
2013-04-29贺伟
贺伟
在庐山松树路的西端,有一片奇形怪状的岩石,其中一块巨石上写着“虎守松门”4个大字。这4个正楷大字遒劲有力,如果不看边款,谁都不会相信它出自20世纪30年代一位70多岁的老翁之手。这位老翁,正是被誉为清末“维新四公子”之一的近代大诗人陈三立。
陈三立搬到庐山居住时已是77岁高龄,但一点都不显得老态龙钟、神志迟缓,仍然精神矍铄、兴致勃勃地游山玩水,神思敏捷地吟诗作赋。在他的眼里,写着“虎守松门”的这块巨石,就像是卧在他的居所“松门别墅”那里日夜与他相伴的壮虎。
陈三立1853年出生于官宦之家,父亲是晚清赫赫有名的“封疆八大吏”之一的湖南巡抚陈宝箴。陈三立自小天资过人,受过极严格的传统文化教育。但他偏偏生就一副桀骜不驯的脾性,参加科举考试总是不守规则,率性而为,屡屡落第。1882年再次参加乡试时,他拒绝用他深恶的“八股文”作文,而胆大妄为地用古散文体作文,置个人的前途于不顾,险些又因文体不合而落第。陈三立1886年中进士,官授吏部主事。可他不久就弃官离京,跑到长沙去协助父亲陈宝箴推行维新新政,时人誉他和谭嗣同、徐仁铸、陶菊存为“维新四公子”。戊戌变法失败后,陈宝箴和陈三立同被革职,后陈宝箴被慈禧太后赐死。陈三立发誓不再入仕为官,自谓“凭栏一片风云气,来做神州袖手人”。
陈三立从此便潜心于诗文写作,成为清末民初诗坛泰斗。1924年印度大文豪泰戈尔访华时,专程到杭州西湖会晤陈三立,交流诗学诗艺,两位大诗人的见面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陈三立和他的父亲陈宝箴、儿子陈衡恪(师曾)、陈寅恪都以不同凡响的作为和业绩入选《辞海》,祖孙三代四人同入《辞海》,为目前中华第一家。
1929年11月,陈三立离开居住多年的上海,前来庐山定居。庐山紧邻陈三立的家乡——九江修水(古称义宁),陈宝箴、陈三立为官时曾多次游历庐山,甚为喜爱,早有归隐庐山之意。陈寅恪于1929年夏买下庐山一栋别墅,接老父上山居住,以了老人的夙愿。
这栋别墅位于庐山松树路西端,建于20世纪20年代初,面积约170平方米。别墅四周怪石嶙峋,万松挺立,环境极为幽雅清静。别墅二层,有敞开式与封闭式相结合的门廊。别墅北墙还用坚石砌筑了3块撑壁柱,以加固墙体的稳定。陈三立入住时,将别墅做了一些改动,别出心裁地在院子前面的两棵古松之间装上石头门阙,并刻上“松门别墅”4个字,使周围的松树、庭院和别墅融为一体,以后人们便将这栋别墅称为“松门别墅”。陈三立还在二楼开一后门,建一小桥通达后花园。
松门别墅当时成了庐山文化活动中心,常是宾客盈门,热闹非凡。1930年,时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的徐悲鸿暑假上庐山,时常来松门别墅拜访三立老人。他还邀三立老人同游庐山美景,评点山川胜迹,使陈三立很是开心。陈三立特意写了一首《徐悲鸿画师来游牯岭,相与登鹞鹰嘴,下瞰州渚作莲花形,叹为奇景,戏赠一诗》给徐悲鸿。1931年,陈三立再次邀请徐悲鸿上山。这次徐悲鸿索性住在松门别墅,一住就是1个多月,与陈三立一家相处甚欢,他为陈家老老少少10多人每人画了一张画相赠。
颇受赞誉的续修的《庐山志》也凝聚着陈三立的心血。陈三立居松门别墅时,江西实业家、方志学家吴宗慈常来拜访。吴宗慈告诉陈三立,自清道光年以后,庐山志书研修便陷于停顿,200多年来庐山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庐山牯岭如何被洋人租借、开发的详情极少为人知道,应该把《庐山志》续修下去。陈三立当即表示支持,随后马上联络在山的众学者、名流,倡议续修《庐山志》,得到热烈响应。陈三立总负责,吴宗慈负责具体撰写。陈三立还延请常居庐山的著名科学家胡先骕、李四光等撰写有关庐山植物及地质方面的篇章。1933年3月,志书告竣,陈三立亲为审阅点定,为之作序,并请章太炎为《庐山志》写跋,为庐山增添了一笔极为珍贵的文化瑰宝。
陈三立与忘年交李一平还闹过一次笑话。出生于1904年的李一平在1927年就担任了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社会科科长,后因不满军阀混战、社会腐败而脱离军政界,于1930年上庐山避居,后创办平民学校,义务教学,在当时的中国产生了很大影响,黄炎培、杜重远等都撰文予以褒奖。20多岁的李一平常向陈三立求教,陈三立十分赞赏这个年轻人的所作所为,将几个孙辈也送到他的学校读书。一天,李一平对陈三立的一个孙辈说:“等花开了,请你姑公来赏花、喝酒。”不料8岁的孩子没听清,放学回家就说:“姑公,花开了,李先生请我们全家去赏花、喝酒。”陈三立乐不可支,立刻带着一大帮家人直奔学堂而来,弄得毫无准备的李一平十分尴尬。三立老人朗声笑道:“花没开,酒还是要喝的。你没准备,就到我家去。”说着拽起李一平就走,一大帮人前呼后拥地回到松门别墅。
陈三立的后半生虽然以文人著称,但桀骜不驯的脾性并未改变。陈三立在庐山定居时,常来庐山避暑的蒋介石几次想见见这位久闻大名的“维新公子”,但陈三立对蒋当时奉行的不积极抗日的政策极为不满,每次都断然拒见,根本不怕得罪这位灸手可热的权贵。有一次蒋介石在松树路散步,随从告诉他陈三立就住在松树路附近,蒋介石当即去陈宅拜访。陈三立听到家人通报后,立即从后门溜走。蒋介石也只能笑着说了一句:“此乃真名士也。”
陈三立在庐山居住的近5年中,为保护、开发庐山文化遗迹和自然景观作出了很大贡献。庐山著名景点——花径的重建有他的功劳;庐山另一个著名景点——碧龙潭的开发,他更是居功至伟。“陈三立”这个名字也和这些景点紧密联系在一起,永存于庐山的山水之间。
唐元和十二年(817年)4月上旬的一天,被贬在江州(今九江)任司马的白居易和一群好友同游庐山大林寺。此时,山下的春花早已谢尽,而山上因气温较低,大林寺一带却是桃花吐艳,姹紫嫣红,开得正好。白居易欣喜异常,脱口而出一绝:“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白居易此诗很快流传开来。之后,前来大林寺山谷品赏桃花、缅怀白居易的历代文人雅士络绎不绝,这里便慢慢被称为“白司马花径”。近代之后,随着大林寺的逐渐衰败,无人管理的桃花也逐渐消亡,这里便慢慢冷落下来,最后成了荒草萋萋的山谷。
1929年的一天,长住庐山的晚清学者李凤高陪友人去仙人洞游览,路过大林寺山谷时,看见路旁石工从泥土中挖出的一块大石上写有字,便停步仔细察看,见是“花径”二字。他忙嘱咐石工切勿损坏这块石头,当即转身回去,找来陈三立和吴宗慈。3人围着石头细细研究,可惜因为边款已被毁,实在无法辨认作者及年代。他们断定,此石刻一定是后人景仰白居易,为纪念他在这一带咏赞桃花而刻。
陈三立和李凤高、吴宗慈决定以此为契机,重建“花径”景点。他们向山上各界人士募捐,作为修路、筑亭、种桃及园林建设费用,响应者十分踊跃。他们在刻有“花径”两字的巨石上建起“花径亭”,对石刻加以精心保护;又在花径亭旁建一座“景白亭”,亭前立碑,陈三立亲自撰写了《花径景白亭记》碑文,详细记载了发现“花径”石刻、重建花径景区的过程。他们还在山谷中修建了石板小道,道两旁广种桃树;还修建了一座石门,李凤高题“花开山寺咏留诗人”8字刻于两边石柱,并题“花径”二字刻于门额。至此,荒废已久的“白司马花径”获得了新生,引来政界要人、文人雅士和游客的关注,影响越来越大。后来政府不断拨款对花径景区加以扩充、完善,使之成为今日游人必至的著名景区。刻有陈三立撰写的碑文的石碑至今保存完好,后人细读之,追思当年三立老人及仁人志士重建花径景区的义举,焉能不心生敬重之情!
如果说,陈三立与友人重建花径景区颇为不易,那么,他四探碧龙潭,终于将这沉睡万年的“山北第一绝胜”开发出来的故事,更充满传奇色彩。
庐山瀑布很有名,东有三叠泉瀑布,南有香炉峰瀑布,西有石门涧瀑布,惟独很长时间山北没有名瀑。1930年,陈三立偶然听人说,10年前勘探庐山地形的外国人曾在庐山山北王家坡一带发现了一个瀑布,十分壮观,但因道路太艰险,多年来一直人迹罕至,至今仍默默无闻。
陈三立当即兴致勃发,要去寻幽探险。家人劝阻说:“你已是快80的人了,山里路都没有,无法抬轿子,你如何能去得?”陈三立不服气地说:“别人能走,我也能走;别人能爬,我也能爬。”家人再三劝阻,陈三立仍是倔强地要去。家人只好多雇请些有经验的樵夫,护送陈三立往王家坡而去。
王家坡距牯岭5公里多,之间的山路越来越陡,越来越窄,很快就消失在荆棘和乱石之中。陈三立下了轿子,前有壮汉挥刀砍路,左右有人搀扶老人,艰难地向前行进。
一行人跋涉了几里山路,渐渐听到前方山谷里有水声。循着水声前行,路越来越难走,陈三立走不了几步,就要停下脚来大口喘气。但他决不退缩,非要探个究竟。
又转过两道山梁,众人猛然看见峰峦间两条瀑布飞泻而下,如同两条蛟龙在山间嬉戏,时而合拢,时而分开,最后双双跃入巨大的深潭中,溅起晶莹的水花。
众人欢呼着来到潭边,但见潭边怪石嶙峋,绿荫如盖,潭水清澈碧透,倒映着天光云影。陈三立一行都被奇景所深深吸引,流连再三,不忍离去。
20天后,陈三立再次带人前来。他和有关设计人员沿途仔细察看地形,选择最佳筑路方案。陈三立还特意带了石工来,在潭边精心选了几块山石,将写好的“憩石挹飞泉”和“洗龙碧海”等题词刻在石上。陈三立在“憩石挹飞泉”的边款中简要记述了探访瀑、潭的经过:“王家坡泉石之胜冠山北,而径路翳塞,阻绝人境。近十载前,海客始发其秘。庚午八月结侣来游,导者杨德洵、颜介甫。跌坐双瀑下,取康乐句(注)题记。散原老人陈三立,时年七十有八。”(注:东晋诗人谢灵运被封为“康乐公”,故又称谢康乐。“憩石挹飞泉”出自谢灵运《初去郡》一诗)此后,庐山山北便有了名瀑——王家坡双瀑。人们又根据“洗龙碧海”的题意,把双瀑下的深潭叫做“碧龙潭”。
不久后,陈三立好友、佛学大师欧阳竟无上庐山,陈三立特陪他再游王家坡双瀑。欧阳竟无既为胜景所折服,又为老人寻幽探胜的壮举所感动,特提议请陈三立根据自己所号“散原”而将此潭另立别号“散潭”。三立老人笑而婉谢道:“如此天工之美,老朽安敢擅夺。”于是,欧阳竟无自书“散潭”二字,刻于潭边山石。虽然此别号未曾传开,但三立老人的功劳不会埋没。
陈三立三探瀑、潭回来后,在庐山发起募捐,用于开发山北绝胜,捐者极为踊跃。陈三立将捐款交给庐山管理局局长,请他代办此事。管理局局长极为重视,立即着手操办。不到半年,一条便于行走的小道便出现在峻岭之间。局长在潭边题刻了“碧龙潭”3个大字,并在潭边的山坡上建了一座听瀑亭。
山路建好后,陈三立四游双瀑、碧潭。他兴奋异常,回来后充满激情地写下了《王家坡听瀑亭记》,对瀑布、龙潭作了生动细致的描述。管理局局长将陈三立此文刻于碑石,立在听瀑亭旁,留存至今。
陈三立因年事太高,于1933年底恋恋不舍地离开庐山,去北平儿子陈寅恪处居住。1937年7月日军占领北平后,鉴于陈三立的名望,多次请他出任伪职,均遭到他的痛斥。为了表示不与日军合作的誓愿,陈三立有病也不服药,当年9月竟绝食5日而死,终年84岁。临终前,陈三立曾希望归葬庐山,但因战乱未能如愿,最后归葬杭州牌坊山。
陈三立在庐山居住近5年时间,时时涌动的诗兴撞击着他那颗并未衰老的心,他写了大量诗作,从中精选出103首,编成《匡庐山居诗》,其中他最为喜爱的是《中秋山居看月》:“笼湖摇海中秋月,移向匡君卧处看。洗露峰峦迎皎洁,带星楼观出高寒。一生阅世丹心破,万里传辉白骨残。犹有酒杯邀对影,石根虫语落栏干。”
1945年,陈寅恪在成都养病时,曾写过一首《忆故居》的诗。诗序中说:“寒家有先人之敝庐二:一曰峥庐,在南昌之西门;一曰松门别墅,在庐山之牯岭,前有巨石,先君题‘虎守松门四大字。今卧病成都,慨然东望,暮境苍茫,因忆平生故居,赋此一诗,庶亲朋览之者,得知予此时之情绪也。”诗中有“松门松菊何年梦,且认他乡作故乡”之句,读之令人倍觉凄然。陈寅恪自己可能也未曾料到,2003年6月16日,他和妻子的骨灰由后人护送至庐山,落葬庐山植物园内。在此之前的1993年,陈寅恪的侄子、中国著名植物学家、中国植物园创始人之一的陈封怀已归葬植物园。陈三立未能实现的遗愿,他的儿子和孙子却做到了。
而今,松门别墅仍在,皎洁的山月仍然将清辉洒满别墅,洒满松林,洒满匡庐的山山岭岭。然而,对月吟诗的老人却不在了。人虽不在了,可情还在,意还在,魂还在。不然,为什么总有在庐山松树路赏月的人说:“在很多年以前,这里住过一个老诗人,总爱在这样的夜晚,举杯邀月,对影吟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