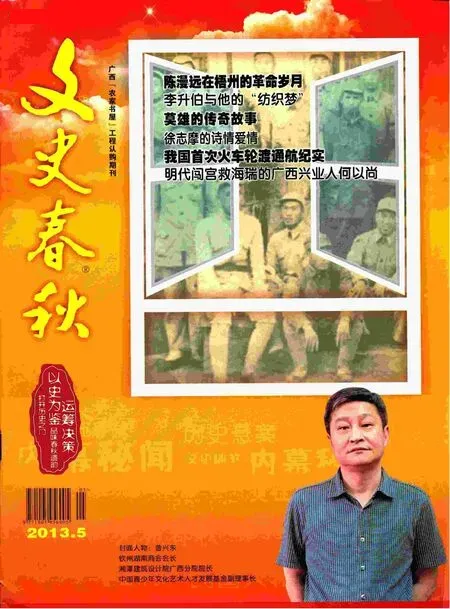齐白石的“情”结
2013-04-29马军
马军
齐白石(1864─1957),原名纯芝,字渭青,后改名璜,字濒生,号白石、白石山翁,湖南湘潭人,近现代中国画大师,世界文化名人。他将中国画的精神与时代的精神统一得完美无瑕,使中国画得到国际的重视。他朴实谦虚、自信自强的精神,使他的作品刚柔兼济、工书俱佳。他一生有情有义,而且“情”结还挺浓。
师 情
齐白石幼年时家境并不好,因而没怎么念书,只随外祖父上过半年的家塾,连识字都十分有限。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做了一名木匠。但是他禀赋过人,聪明好学,对其中的细活——雕缕花纹图案,甚有兴趣,也甚为用心,因此这样的活计便多由他来做,一个后来震惊世界的艺术大师就在这里起步了。
他人生转折的第一个贵人也是他的启蒙老师叫胡沁园。胡沁园是湘潭有名的绅士,能诗善画、会篆刻、会写汉隶。胡沁园看到齐白石是个可造之才,就主动提出收他为徒,不仅不收他的学费,还给他家送钱,送粮,免除他的后顾之忧,让他只管安心学诗、做画。
胡沁园给弟子取名叫齐璜,字濒生,别号白石山人。后来“白石”、“白石”的叫多了,齐白石这个名字就逐渐成了他的名号了。在胡沁园的精心培养下,齐白石愈加发愤努力,诗书画艺进步很快。胡沁园还四处推荐齐白石的画,卖画所得全部归于齐白石,不管齐白石如何推辞,也一文不留。在胡沁园的努力下,齐白石这个小字辈渐渐融入到当地的士绅文人圈子中。
胡沁园的知遇之恩,齐白石铭记肺腑,牢记一生,不仅称胡为自己的恩师,而且是“生平第一知己”。胡家及其亲友,凡有求,则必应。齐白石离开家乡后,与胡沁园信件和诗词书画来往频频。当他闻知恩师去世的消息后,嚎啕大哭,悲痛欲绝,他不停地写诗、做画,以表达对恩师的无限崇敬和怀念。他笔下的恩师,慈祥、和蔼、智慧、可亲、可敬,融注着他对恩师的一片真情。
1899年,齐白石再拜鼎鼎大名的王闿运为师,这使他视野大展,向着更广泛的社会认同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王闿运曾官至清末翰林院检讨加侍讲衔,民国初年任中华民国国史馆馆长兼参议院参政之职。他一生著作丰富,被誉为“一代经师”,门生弟子遍天下,为文坛领袖级的人物,影响力非常之大。
投师王闿运的门下,齐白石在艺术上的长进之快是毋庸置疑的,同时王闿运亦为齐白石不遗余力的做了推介工作。1904年,王闿运为齐白石撰《白石草衣金石刻画序言》,对齐白石的人品和艺术水准大为赞誉。他还让他的弟子陈毓华以自己的语气撰《齐山人传》,为齐白石鼓掌叫好。齐白石还常随侍王闿运的左右参加各种诗会,结识了不少文人和社会名流。
王闿运为齐白石做了不少的序跋、信札、楹联等等,如1911年为齐白石题写“寄萍堂”,并附以小字箴言,齐白石将其制成匾额一直挂在北京的家中。王闿运还曾应齐白石之请为其去世的奶奶做墓志铭,这对于王闿运的身份和地位来说,能屈尊做此等文应该说是不易的,从中也可见他对齐白石的欣赏和厚爱。齐白石后来亲自运刀勒石成碑,并将拓本和这篇《齐璜祖母马孺人墓志铭》的原本一直随身珍藏。
多年后,齐白石再忆起这一幕幕时,不禁百感交集,作诗如下云:“忆旧难逢话旧人,阿吾不复梦王门。则思处处堪挥泪,食果看花总有恩。”表达了对恩师深深的怀念之情。
友 情
1902年初冬,齐白石应友人夏午诒之请,赴西安教夏午诒的夫人学画。授课之余,便多是为夏及朋友们作画和治印。很显然,他是夏午诒专门聘请来的,是要付银子的,可是一位慕名而来的求画者忍不住想出钱买他的两幅画。按说,这并没有影响和耽误朋友的事情,就当作是加出来的活也完全说得通,相信朋友也完全能够理解,哪一个画师会拒绝送上门来的生意呢?可是齐白石却坚决地拒绝了。在他看来,夏午诒聘了他,他为夏及朋友们作画是理所当然的,如果再去卖画就有点“重金轻情”了,对不起朋友。在他的内心,道德底线是清楚的,那就是“钱”与“情”相比,后者分量更重。
就是这次西安之行,他结识了一个对他一生十分重要的朋友——樊樊山。樊樊山,湖北恩施人,曾任陕西布政使、护理两江总督等职,喜艺术,有诗名,在当时官场和文坛都有不容忽视的影响。他对齐白石的的诗、书、画、印极为推崇,并亲自为其书写润格,使齐白石的声名大振。樊氏的充分褒扬令齐白石在艺术圈中的地位和身份上升不少。这对于尚未破土而出的齐白石而言,不啻是及时雨、雪中炭。
当时齐白石由湘乡初到北京,日子过得并不顺畅,圈内人对他并不认识,对他的画风也不认可,以艺养家糊口的生活自然潇洒不了。闲居北京的樊樊山义无反顾地挺身相助,他写诗赞誉齐白石:“平生三绝诗书画,乐石吉金能刻划。前明四家白虎尊,扬州八怪冬心亚。”第一次将齐白石与清代画坛巨擘“扬州八怪”之一的金农并提。并两次为齐白石的诗集《借山吟馆诗草》作序。特别是最后一次,樊氏已年过八旬,虽老眼昏花,不能亲作细小之字,但仍在自己孩子的帮助下,完成了作序的心愿。在序中,樊氏对齐白石的诗歌评价之高,为序之诚,实不多见。齐白石非常感激这个肝胆相照的朋友,不但时常到他家看望,而且还在寒冷的冬季为他送去了温暖的鹅绒被。樊樊山去世后,齐白石极为悲痛,他亲往吊唁,并在诗中尽吐肺腑:“似余孤僻独垂青,童仆都能辨民音。怕读赠言三百字,教人一字一伤心。”真乃椎心泣血之言,令人不忍卒读。他还刻下“老年流涕哭樊山”印章以志怀念。
亲 情
齐白石之恋家,在艺术界似乎是人所共知。“家”的情结一直伴随了他一生,甚至成为他创作的情感资源和原动力。
1919年,齐白石定居北京,但他的家眷都还在老家。后来,只是把他的三子齐良琨和长孙齐秉灵接到北京读书。当然了,将家彻底搬到北京固然是他所愿,可是当时的他实在是有心无力,一大家子的开销可不是当时的他所能承受的。因此,齐白石就像候鸟一样来回跑,年年还家探亲。
长孙齐秉灵非常聪明,齐白石对他疼爱有加,而且对其寄予厚望。遗憾的是齐白石的这个掌上明珠的体质不是太好,身体状况经常让人揪心。1921年6月,齐秉灵患病,齐白石经常煎药守夜直到天明。不久后,齐秉灵还没有病愈,齐白石的夫人在产子过程中遇到了危险,于是齐白石又匆匆收拾行装火烧火燎地返回湘潭老家。他在北京和湖南老家之间来回奔波照顾,颠沛流离,艰辛备至。
1922年7月23日,病中的长孙齐秉灵思念家中亲人,齐白石便让他回湘调养。那年头信息不畅,由于不能及时知道长孙的病况,齐白石“日不饱食,夜不安寝”。终于在8月初他收到长孙的家信,可是这封家书并没有给他带来惊喜,因为他发现信笺上似有斑斑血痕,他“不胜忧思,不觉大哭”。22日,他携妻子返湘,延请良医,煎汤侍药,忙得焦头烂额。两个月后,他见长孙病情平稳一些,不免又挂念起北京的家。可回到北京没有多久,长孙亡故的噩耗就如惊雷一样将他震呆,他“大哭数声,却无泪出。即睡去,亦不知忧。初十日始有眼泪,如是痛哭不可止矣”。
齐白石是享誉中外的艺术大师,但他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人,更是一个真真正正纯纯粹粹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