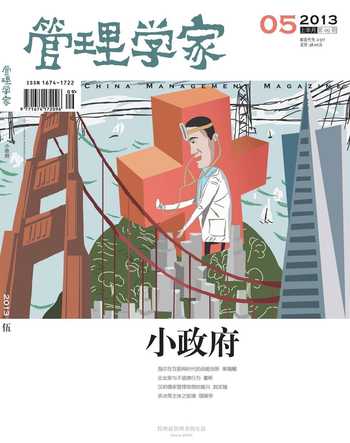《新书》和贾谊的治国策略
2013-04-29
贾谊的治国思想,以脍炙人口的《过秦论》为其立足点。正因为他对秦朝的政治失误有深刻的揭示,所以能够对汉初政治提出全面的转变方略。后人谈到贾谊,往往赞许他“其才雄,其志达”;“卓卓乎其奇伟,悠悠乎其深长”(均见明人《新书》序)。他力图使汉朝克服秦制之弊,实现长治久安,可以说,贾谊是在陆贾之后,为西汉进行全盘战略设计的第一人。
贾谊是主张“顶层设计”的。他在刚刚进入决策中枢时,就提出对汉初制度进行彻底变革。“贾生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馀年,天下和洽,而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今人可能觉得这些变革都属于形式,但在古人眼里,改正朔,易服色,相当于重新搭台另唱戏,是最大的变革。贾谊甫涉政坛就提出这些建议,说明其志向宏伟。这种整体变革尽管因为汉文帝立足未稳而“谦让未遑”,但其重要性却摆在那里,并最终在汉武帝手里得以实现。更重要的是,从秦到汉,在国家治理上需要这种变化。秦朝的体制下,皇帝只相信自己,对所有人都高度戒备,“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过秦上》)精明如始皇,则大权独揽;愚蠢如二世,则奸佞当道。这种体制的要害,在于得志的大臣不是唯唯诺诺就是奸诈小人。好一点也只是算小账而不识大体的刀笔吏执政,差一点就是架空皇帝排斥异己的赵高之流掌权。秦朝之亡,亡于“其道不易,其政不改”,“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没有从兼并战争的暴力欺诈走出来。汉初陆贾倡导儒术,但执政者仍然是打天下时的功臣集团。贾谊的改弦易张,表现出由暴力向仁义、由功臣向文官、由夺天下向治天下的转变。西汉军功集团向文官集团的结构性转变,是从贾谊开始的。
但是,秦汉之天下已非三代之天下。大一统和君主专制已经成为时代特色。所以,儒学要成为帝国时代的治国主旋律,就需要找到儒学之仁义王道与帝制之大一统王朝的切点。贾谊把这个切点定位在加强中央集权上。他的《治安策》被毛泽东称为“写得最好的政论”,就是从中央集权角度评价的。其主旨有三:一是强化中央威权,二是富民安定天下,三是教化移变风俗。在手法上,礼治、法治、人治三位一体,并由此确定了汉代儒学的发展方向。
首先,贾谊对汉代的王国问题和匈奴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主张。王国问题是内政问题,秦朝彻底废除了分封制,把一切大权集中于中央,中央权力又集中于皇帝,郡县制成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本制度。然而,秦朝郡县制下中央与地方的矛盾迅速显现,尤其是对原属六国地区郡县的高压统治很快激化了社会矛盾,反秦战争以原六国后裔与秦国的冲突展开。因此,在秦亡之后,无论是项羽还是刘邦,都采用了分封制。在大一统王朝尚未找到有效直辖不同地区的方法之前,人类的基本经验就是沿用过去的方法,哪怕这种方法已经显露出弊端,在没有更好的替代时,只能用它。那些批评项羽与刘邦采用分封制是“开历史倒车”、是“错误的选择”的说法,不过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而已。刘邦先封异姓王,又待时机以同姓王取代异姓王,实际上是很稳健的策略。但到文帝时,同姓王的问题也逐渐显露出来。尤其是在平定吕氏之乱时,同姓诸侯王不遗余力同讨诸吕,而文帝本来与他们平起平坐,甚至势力还不及他们,朝廷与诸侯王的裂痕开始扩大。对此,贾谊提出自己的解决办法,他强调:“诸侯王虽名为人臣,实皆布衣昆弟之心,虑无不帝制而天子自为者。”(《亲疏危乱》)给他们以优厚待遇,但“权力不足以徼幸,势不足以行逆,故无骄心无邪行,奉法畏令,听从必顺,长生安乐而无上下相疑之祸”(《藩伤》)。从以往的经验来看,藩国强者先反,只有长沙王因其实力最弱,故能忠于朝廷。以此推论,贾谊主张,“欲天下之治安,天子之无忧,莫如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藩彊》)。后来汉武帝实行推恩令,正是采取贾谊的策略。
对于匈奴,贾谊提出“建三表,设五饵”的策略。所谓三表,即用适当策略向匈奴示之以信、爱、好,讲信义,表关爱,显喜好,以德服人;所谓五饵,即“赐之盛服车乘以坏其目;赐之盛食珍味以坏其口;赐之音乐妇人以坏其耳;赐之高堂邃宇府库奴婢以坏其腹;于来降者,上以召幸之,相娱乐,亲酌而手食之,以坏其心”(《汉书·贾谊传》师古注)。三表是以儒术感召,五饵是以权谋引诱。可见,贾谊的思路,是把本来水火不相容的儒法两家兼用并举,一切以维护汉朝利益为宗旨。
为了保证汉朝的统治秩序,贾谊主张,以礼制规范社会等级。为了解决诸侯王问题,贾谊主张在制度上改变诸侯王与皇帝君臣不分的各种称谓和待遇,清晰界定皇帝与诸侯王的尊卑等级衣服物品号令规范,“见其服而知贵贱,望其章而知其势”,“下不凌等,则上位尊,臣不逾级,则主位安”(《等齐》、《服疑》)。除诸侯王外,整个社会都要建立明确的高下尊卑等级,“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亲各得其宜。”“故古者圣王制为列等,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有官师小吏,施及庶人,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阶级》)为此,贾谊专门强调,履虽新,却不能戴在头上;冠虽弊,却不能踩在脚下。
尽管贾谊的思想掺进了法家的术和势,但在对儒家的民本思想陈述中,还是承继了儒学的基本观点。“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大政上》)由此,在具体的管理中,推导出疑罪从无、疑功从有的原则。“诛赏之慎焉,故与其杀不辜也,宁失于有罪也。故夫罪也者,疑则附之去已;夫功也者,疑则附之与已。”(同上)单从这一论述看,贾谊的思想,即便比起孟子的重民思想来也不算逊色。
在推崇儒术上,贾谊特别强调礼乐教化,“厉廉耻,行礼谊”,主张“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向道”。他认为,从秦以来,包括汉初,重用刀笔吏,以法规条文为务,以细节害大体。管仲曾言“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当今为了追求利益而不顾一切,杀害祖父母者有之,伤害养母者有之,刺伤兄长者有之,盗窃国库者有之,抢掠祭器者有之,伪造朝廷公文诈取粮食钱财者有之,不胜罗列。造成这种道德沦丧的根源是从商鞅变法开始的利益角逐。廉洁奉公遭人嘲笑,为富不仁被人羡慕,秦亡教训在前,需要下大功夫矫正(《俗激》《时变》)。矫正的路径只能遵从儒学。所以,贾谊在批判商韩之术败坏社会道德的同时,即便吸取法家的某些策略,也力求用儒学修正其过分逐利的一面。
值得注意的是,贾谊在反对奢侈浮华的同时,注意到了政策逆反问题。他专门论证了“瑰玮”之政,即政策意图和政策效果的相悖。所谓瑰政,就是“予民而民愈贫,衣民而民愈寒,使民乐而民愈苦,使民知而民愈不知避县网”;应对这种瑰政的方法是玮术,就是“夺民而民益富,不衣民而民益暖,苦民而民益乐,使民愚而民愈不罹县网”(《瑰玮》)。说穿了,贾谊开出的药方很简单,即崇本去末。只要真正做到驱民归本,智巧诈谋自然无所用,淫邪奸盗自然不得生。这一观点并无新意,但贾谊把它和政策评价结合到一起。正如当代的行为主义心理学所揭示的那样:仅仅强调诚实是美德,但现实却给欺诈者以优厚回报,永远也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道德,只有讲诚信者的回报超过欺诈者,才可能走上真正的道德建设之路。儒法两家的结合,正是在克服主观意图与客观效果的反差上能够体现出新意。
按照贾谊的设计,君主的个人品德和示范作用,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决定意义。所以,他专门论证了太子制度和保傅问题,对太子的教导培养有详细论述。由于他重视礼与法的结合,重视人对礼法的作用,因而对辅政官员的培养、选择、任用和考察都有相应的论证,具体内容在此从略。
整体来看,贾谊的儒学,在先秦儒学的心性修养方面并无大的推进,然而在实践运用方面结合秦汉以来的政治需要有着新的发展,其学说省略内圣而鼓吹外王,使儒学的发展方向变为政治儒学。即便是外王,贾谊也具有某种国家主义的倾向,尽管他用的词汇是天下,但天下的内涵却是王朝。此后,这一方向一直是帝制时代的主流,直到宋儒的理学,才把儒学发展轨道重新扭转到性理儒学。可以说,贾谊奠定了帝制时代政治儒学的基本取向。
有一个细节可以反映出政治儒学的实际效用。汉代有一个很有名的不成文制度“将相不辱”,就是来自贾谊的建议。他强调,仁义和法制,是君主的两种工具。“仁义恩厚者,此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此人主之斤斧也。”(《制不定》)君主运用这两种工具要格外慎重。儒家主张“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并不是简单的特权,而是要给士大夫保留几分体面。儒学特别强调“耻”文化,士大夫的约束也主要靠廉耻。贾谊直接批评高级官员遭受刑罚的副作用,说:“今而有过,令废之可也,退之可也,赐之死可也。若夫束缚之,系绁之,输之司空,编之徒官,司寇牢正、徒长、小吏骂詈而榜笞之,殆非所以命众庶见也。”所以,贾谊主张恢复古礼,高级官员犯错需要谴责的,以“白冠氂牛,盘水加剑”示意其自行面壁思过,而不需要执缚系引;犯错需要问罪的,听到追究命令即自行前往有司,而不需要械梏镣铐;犯有大罪需要处死的,指令下达即北面再拜,跪而自裁,而不需要刽子手行刑。贾谊认为,这样做,高级官员保持了尊严,朝廷维护了体面。“上设廉耻礼义以遇其臣,而群臣不以节行而报其上者,即非人类也。”(《阶级》)此后,西汉逐渐形成了相应的规矩,以丞相为例,得到皇帝的信任为丞相执政的前提,如果有人弹劾丞相(以御史大夫弹劾最为常见),皇帝将弹劾奏章留中不发,则表明保持对丞相的信任。如果皇帝在奏章上批“诣廷尉”(字面意为到司法部门接受审理),那么丞相就必须自杀以表清白。这种“将相不辱”,从儒学角度看可以保持丞相的尊严,从皇权角度看可以保证丞相对皇帝的绝对服从。政治儒学的内在矛盾,就产生于这种细节之中。当然,政治儒学的学理构建,贾谊只是开其端者,到董仲舒方告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