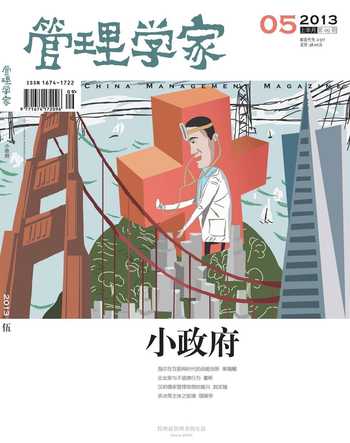政府与企业的关系: 日本的经验与教训
2013-04-29
日本的经济体制,曾经因为日本的高速增长奇迹而广受赞誉,现在又因日本的长期萧条而备受责难。我们将在这种毁誉参半的日本经济体制框架下,聚焦于日本的官僚制及其人格化的官僚,去讲述关于政府与企业关系的日本故事,及其经验和教训
冷战结束后,经济学家对经济体制的兴趣,由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比较,转移到资本主义内部的差异上,他们意外发现,在通常被认为是市场经济的同义语的盎格鲁-萨克逊模式(Anglo Saxon model)之外,还有像日本这样迥然不同的经济体制。在这个被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撬开的“暗箱”里,存在着主银行、相互持股、系列下包、终身雇佣等一系列日本独有的制度安排。这些彼此之间具有互补性的制度,其集合就构成了日本型经济体制,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了我们今天的讨论对象: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
行业协会-审议委员会:一个有效的协调机制
在经济学家的眼中,日本总是与美国形成一种明显的对比,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上也不例外。美国几乎是世界上最后一个经济自由主义的“古典国家”,在私人企业和个人自由的理念下,政府防范企业进行垄断,而企业则警惕政府进行干预,因此政府与企业之间是一种紧张的、抗衡的关系。与此不同,在日本那里,政府与企业之间则是一种密切的、协调的关系,由此产生了日本特有的“行业协会-审议委员会”这一协调机制,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经济效率,从而引导经济沿着符合政府战略意图的特定政策方向发展。为了理解这一点,首先要清楚“行业协会-审议委员会”这一协调机制的基本含义、产生的背景,以及它发挥协调作用的制度环境。
历史起源
简单地说,行业协会和审议委员会分别代表企业一方和政府一方,但政府人员不参加行业协会,而企业人士则参加审议委员会。日本的行业协会是层级制的,比如在机械工业联合会之下,分布着汽车工业协会、机电工业协会等数十个行业协会,它们对应着政府部门比如说通产省的各个次级职能部门。审议委员会则是根据法律在政府职能部门中设立的附属行政机构,其任务是在政府与企业之间交换信息、提出政策性建议。
日本的这种“行业协会-审议委员会”协调机制,起源于战时统制经济时期。日本发动全面对外侵略战争后,为扩大军工生产能力、完成军工生产计划,在各产业部门中设立了一系列“统制会”。这些统制会在战后经济恢复时期,演变为现在的行业协会,比如钢铁统制会变成钢铁工业协会、产业机械统制会变成产业机械工业协会、汽车统制会变成汽车工业协会等等,继续在政府和企业之间发挥协调作用。在日本实行“道奇计划”,完成由统制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后,这种“行业协会-审议委员会”协调机制不但继续保留下来,而且不断壮大。在其鼎盛时期,比如1970年,与通产省各次级职能部门对应的行业协会多达528个,按照数量排序,其中归口于重工业局的有137个,纤维杂货局123个,贸易振兴局76个,化学工业局74个。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日本的这种协调机制在制度层面上为高速增长做出了突出贡献。
制度特征
通过以上简单的讲述,我们会观察到什么?首先,归口于通产省各职能部门的行业协会,除“夕阳产业”外,集中于重化学工业部门和出口部门的数量最多,反映出战后日本政府实施的重化学工业化战略和贸易立国战略,也反映出战后日本政府实施产业政策的重点领域,并且不难看出这种协调机制成为战略和政策获得成功的制度性原因。其次,作为民间利益集团,日本的行业协会显然是以产品市场为基础形成的,这与欧美国家的产业工会、职业工会等以要素市场为基础形成的民间利益集团完全不同。欧美国家的政府在资本市场层面上与资本家发生关系,在劳动市场层面上与工会打交道。日本政府只在产品市场层面上与生产者保持密切的协调关系,至于企业所有者与工人之间的利益协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企业经营者在企业这一层次上裁定的,因为日本的工会是企业内工会,而不是西方国家那样的跨企业工会。
如何发挥作用
接下来的问题是,日本这样的“行业协会-审议委员会”协调机制,不可能单独发挥作用,它的绩效表现了一种体制效率。这就需要追溯到战后日本大规模的制度变迁以及由此形成的国家形态和经济体制。
在战后日本大规摸制度变迁之后,实际出现的是一种具有权威主义倾向的“官僚制多元主义”(由日本经济学者青木昌彦提出)国家,其政治基础则是自民党与官僚之间长期、稳定的结盟。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日本的“行业协会-审议委员会”这一协调机制,是如何在以上给定的制度环境中发挥其作用的。
在官僚制多元主义国家中,政府内部是分权的,其构成单元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职能部门,如通产省、农林水产省等;另一类是协调部门,如大藏省。各职能部门的管辖权通常是规定明确并相互独立的,在各自管辖领域内与民间利益集团保持密切的关系;协调部门不与民间利益集团直接接触,而是对各职能部门之间由于与民间利益集团保持密切的关系而产生的利益冲突进行协调。
民间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裁定,是在市场调节的基础上由分权的官僚机构来进行的,而与分权的官僚机构直接保持信息交换的就是我们在上面提到的各种行业协会。它们通过这种长期接触而形成的接口将所代表的行业共同利益的诉求输入到公共政策形成的过程中;职能部门则代表所管辖领域内的民间利益集团的利益制定政策,并展开与其它职能部门之间的讨价还价。这种官僚机构内部的讨价还价,由官僚机构中的协调部门进行协调,比如说通常由大藏省的主计局通过预算分配进行协调。
在这种利益博弈重复进行的过程中,对民间利益集团的利益裁定实际上逐渐演变为由行政过程来完成,而不再由政治过程来完成。由此我们也许可以判断,在日本的公共政策形成过程中,官僚比作为政党政治家的议员更具有比较优势。由于官僚制人格化的官僚不跟随执政党同进退,也不因政权更迭而变化,从而保证了政府与企业之间长期、稳定、密切的协调关系。
面对控制者:如何避免大规模寻租
马克斯 · 韦伯(Max Weber,1864-1920)曾深刻地论述了组织的理性化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现代社会的规模和复杂程度,决定了需要组织这种角色发挥作用,理性化的官僚制是最有效的行政管理方式,具有形式上-技术上的合理性,也许是一种无奈,人们只能在行政管理的“官僚体制化”和“外行化”之间进行选择。就一般意义而言,战后日本的政府治理和行政管理也是如此,高技术效率的官僚机构和高素质的官僚队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除此之外,战后日本的官僚制及其人格化的官僚,在实际政治经济过程中,其权力、作用还具有一种超出一般意义上的国家行政管理的特殊性,或者说具还有一种超乎寻常的统治地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统治地位正是在战后日本“民主化改革”过程中奠定起来的。在战后日本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过程中,财阀垄断大企业、地主阶级、政治集团、军队等政治经济势力或被弱化或被消灭,只有官僚制,由于成为美国占领军实行间接统治的利用对象,不但完整地保留下来,而且相对地位还获得了提高。到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即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开始的时点上,在官僚制奠定其权力基础的同时,保守派政党通过合并也开始了长期执政的历史,自民党与官僚的结盟从此诞生。
自民党与官僚的结盟,共同构成了一种相对集权的政治结构,但官僚制具有相当大程度上的相对独立性,这是一种“日本式的党政分开”。在大多数技术性问题上,行政效率优先于政治上的权衡,政治干预一般仅出现在重大目标的制定上。实际上,由于自民党的长期执政,使政策和长期规划具有超常的连续性,这些政策的实施一般已不需要采取进一步的政治干预措施,从而导致了实际上的官僚制控制,这一点在日本的立法过程中突出地表现出来。
日本的官僚制及其人格化的官僚,是日本政府行为的实际控制者。从制定发展战略、实施产业政策、进行经济规制,一直到非正式的却效力非常的“行政指导”、与企业保持密切的关系,日本政府对经济生活介入的深度和广度,是所有其他发达国家都难以望其项背的,以至日本一再被称为“规制过剩国家”。但是,如此大的权限,如此广泛的干预,与企业如此密切的关系,却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寻租。
日本政治家时有腐败丑闻发生,而官僚被公认为是“干净”的。在学术研究领域似乎也能印证这一点,如果你对日本经济学界的研究成果进行检索就会发现,利用寻租理论提供的研究方法去分析日本经济的著作和论文,一直到今天几乎就是零,图洛克(Gordon Tullock, 1922- )、克鲁格(Anne. Krueger, 1934- )在日本没那么幸运,远不像在中国那样走红。日本在由后发展经济向工业化经济转变的过程中,面对权力巨大而又与企业关系密切的控制者,何以避免了大规模寻租的发生?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但目前我们仅仅能提供如下的解释。
首先,“行业协会-审议委员会”这种协调机制,维系了政府与企业的密切的关系,企业通过这种协调机制,向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输入利益诉求;政府则通过这种协调机制,向相关企业输出政策意图,从而使经济沿着符合政府的战略和政策意图的方向发展。但是,官僚面对的是行业协会,不会直接接触企业,政策也不会直接落实到企业决策层面上。寻租通常在官僚与企业之间发生,因为企业是利润单位,而行业协会则不是这样。也就是说,在官僚和企业之间存在着行业协会,它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一种降低寻租可能性的隔离带作用。
其次,高级官僚退职后通常都有机会到民间部门另任与其地位相符的高级职务,而且履新后的总收入,会高于他在职期间的总收入,这种现象在日本社会中被讥讽为“天神下凡”,饱受诟病。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天神下凡”,是由其任职的官僚机构正式出面斡旋、安排的,并且向社会公布,长久以来已经制度化了。这样的制度安排的确可能产生种种弊端,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为退职后有机会另任新职,高级官僚有激励在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廉洁奉公,并且有激励监督下属的行为与自己同步,上行下效,使这一支官僚团队在相当程度上避免了腐败的侵蚀。
第三,对官僚个人的受贿等腐败行为进行事先防范和事后惩罚的有效治理。事先防范,其主要措施就是频繁的转换工作,而且极有可能是在性质上完全不同的政府部门之间,今天你是国土交通省北海道开发局的官员,明天也许会被调到日本驻里约热内卢总领事馆任文化领事。频繁的工作交接使腐败更容易暴露,同时可以阻止往往导致腐败的长期关系的形成。至于事后惩罚,在发达国家中日本对腐败官僚的惩罚可能是最严厉的,只要因腐败被判监禁,哪怕是缓期执行,自动被开除公职,并且剥夺其退职金和养老金,使其名誉扫地,一文不剩。法律惩罚叠加上机构惩罚,使受贿的成本大于、甚至远大于受贿的收益,官僚就会做出保持廉洁的理性选择。
发展后问题:
为何陷入“发展导向型陷阱”?
我们上面讲述的日本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典型地发生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它所依托的制度环境和相应的经济体制,也都典型地体现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但自从日本完成由后发展经济向工业化经济的转变,成功地跻身发达国家的行列以后,经济环境、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都在发生变化,特别是泡沫经济破灭陷入长期萧条以后,这些变化更为显著 。
制度环境之变
许多日本型经济体制的典型构成要素已经趋于消失或淡化。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企业自有资本率的上升,个人大股东和外国机构投资者持股比率的提高,主银行制和相互持股趋于消失;公司控制权市场随之出现,劳动市场开始流动化,企业的内部人控制以及终身雇佣制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与此同步,日本政府进行了继战后“民主化改革”以来最大规模的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大幅度放松规制,并对官僚机构本身进行了大刀阔斧的重组。这一期间,随着自民党长期政权的终结,日本的政党制度出现分化,官僚与政治家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官僚的地位下降而议员的地位提高。在2000年的中央政府机构重组中,数量由原来的1府22省厅减为1府12省厅,特别是官僚的“圣地”大藏省更名为财务省,通商产业省更名为经济产业省,同时废止了121个审议委员会。
日本型经济体制的微观、宏观构成部分都发生变化,不能不引起政府与企业关系的变化。日本型经济体制由于路径依赖的原因尚未完全转型,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仍然是密切的,尽管政府各职能部门的竞争关系发生了变化,“行业协会-审议委员会”这种协调机制也还在运行。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中会注入越来越多的市场因素和法治因素。
在完成向工业化经济转变之后,日本已不再是追随者,其产业结构与先发展国家日益趋同,以引进和模仿为基本内容的“后发优势”不复存在,进入了以经济和政治不确定性为全部特征的新格局。在这种新格局下,民间部门的自由竞争,比政府的干预更有效率。民间部门可以充分地利用当地信息,独立地进行多样化的试验来完成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其向整个经济的扩散,则通过竞争者的进入,经由超额利润向平均利润的转化获得实现,从而实现比政府干预更优的资源配置。相应地,更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制度安排不再是官僚制多元主义的,而是立宪民主的,因为后者在国家退出市场领域的条件下,通过维护法治和秩序为民间部门的创新提供自由竞争的环境,尽管日本还远未完成这种转变。
政府“大小”之变
我们在这里感兴趣的是,日本政府与企业关系的历史和目前正在发生的趋势性变化,与日本政府的“大小”之间的关系。日本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最终完成由后发展经济向工业化经济的转变。在此之前,日本是“小政府”,公务员占就业人口的比重是主要发达国家中最低的,而且不断递减,到完成向工业化经济转变之后,这一比重仅是主要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甚至只有法国的三分之一,日本也没有实行福利国家政策,长期实行财政收支平衡,法律禁止发行赤字国债;而在此之后,尽管日本在主要发达国家中仍然是属于政府规模小的,公务员数量也没有扩大,但政府支出规模不断扩大,目前政府累计债务占GDP比重在主要发达国家中是最高的,日本俨然已成为“大政府”,这也是小泉内阁为什么高举起“小政府”旗帜进行经济结构改革的原因。
这里似乎出现了一个悖论:日本政府在干预经济生活最深最广的时期,是“小政府”,而在不断放松规制并进行市场取向改革的时期,反而成了“大政府”。换一种说法,似乎还是悖论:当日本还属于发展中国家时,是“小政府”,而当日本步入发达国家行列后,反而是“大政府”了。这和人们通常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恰恰相反。
因此,在如何处理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方面,日本政府“大小”的案例不太可能给中国提供更多的经验。尽管“小政府”在日本和中国都是热议的对象,但面临的问题不一样。就目前而言,日本面临的是少子化、老龄化,以及如何摆脱长期通货紧缩的问题,所以政府的社会保障、刺激总需求的支出不断扩大,这是政府规模维度上的。而中国面临的是如何继续深化体制改革,消除行政权力替代市场的问题,这是政府职能维度上的。在这一点上,日本倒是可以给中国提供经验和教训,那就是如何避免陷入“发展导向型陷阱”。
来自日本的启示
日本、中国以及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在由后发展经济向工业化经济转变的过程中,都属于发展导向型国家,与纪律导向型国家不同。根据查墨斯 · 约翰逊(Chalmers Ashby Johnson, 1931- )的论述,纪律导向型(regulatory state)国家,以法规来维持市场秩序,政府的功能在于维持经济纪律;而发展导向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则以发展为国家的最高目标,政府的功能在于促进经济发展。并且认为美国是前者的好例子,日本则是后者的好例子。
日本的经验 在向工业化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为了工业部门的增长,政府与工业部门的利益集团结盟,但是必须对这些特殊利益集团的侵蚀进行有效的控制,避免政府为特殊利益集团所“俘虏”。日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首先使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成为一种促进增长的制度资源,而不是成为一种攫取利益的共谋机制;其次,增长的成果不仅仅限于在政府出于发展战略目标的需要而扶植的工业部门中的大企业内部分配,而是超越这些部门,使本来处于比较劣势的农业、中小企业等更为广泛的利益集团均沾。
日本的教训 在完成向工业化经济转变之后,政府的职能没有相应的转变,仍然是发展导向型的。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大幅度升值,日本政府采行的货币政策首先是降低中央银行贴现率,支持企业、特别是出口企业进行大规模的设备投资,目的是降低这些部门的生产成本。过低的利率激励了借款者不仅进行设备投资,还进行投机性投资,促进了泡沫经济形成。结果是重化学工业同时也是出口工业部门的利益集团成为最大的受益者,由于重化学工业的生产特点使其占有广大的土地以及庞大的厂房等固定资产,能在地价和股价疯狂上涨的过程中坐享其利,使本来在完成向工业化经济转变之后应该退出市场的重化学工业的一些部门得以继续存在,并形成了新兴产业部门的进入壁垒。发展导向型模式已经历史地终结,但发展导向型政府依然故我,发展导向型政策仍在继续,最终落入“发展导向型陷阱”。
从更长的历史进程看,发展导向型模式是过渡性的,它仅仅产生于由后发展经济向工业化经济转变这一特定阶段,并且仅仅在东亚地区获得成功,随着向工业化经济转变的完成,它不可避免地要迎来历史的终结。在已完成向工业化经济转变的国家中,日本是一个典型,它成功地解决了“后发展”问题,但至今仍然面临着严峻的“发展后”问题,发展导向型模式的历史遗产的影响至今犹存,其经验,其教训,对正致力于解决“后发展”问题、但已经局部出现“发展后”问题症候的中国来说,在现实和学术的双重意义上极具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