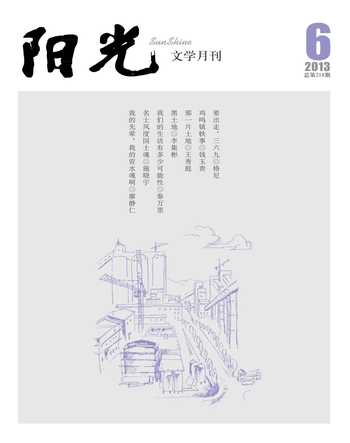黑土地
2013-04-29李集彬
坂头秋天的原野格外明媚静谧。七月初秋,下季稻谷大多成熟,原野呈现出一派金黄颜色,稻谷的芬芳吸引了一切生物:爬虫、蜻蜓、蝴蝶和鸟雀,未开始收割,庄稼地里已经酝酿起一种收获前的喧闹气息。
黑——黑——天刚微明,太阳刚从山岙那边冒出一点尖尖,一束光线射进山间,落到稻梢上,把沉甸甸的谷穗烘托得金光闪闪,金子一般。这时候,一条黑色的狗从坂上下来,跳着蹿着上了田埂。接着,一个胖妇人荷一把锄头一边叫着那条叫黑的狗,一边下到田野里来:好一幅乡村生活的图景!
缓坡的这片庄稼地平坦,宽阔,肥沃。有泉水从山上下来,滋润得这里的草木和庄稼蓬蓬勃勃。谁都可以看出来,这是一片好土地。
这一片山地,偏居一隅,空气清新,离城区不太远,是一片未开发的处女地。山上的矮松层层起伏郁郁葱葱,山间有叮咚的泉水,有啁啾的鸟鸣,坂上是村庄。
这片山地里,除了树林和村庄,其余都是庄稼地。山梁上有庄稼地,缓坡里有庄稼地。山梁上是黄土地,是旱地,适合种花生、大豆和小麦。种出来的花生有小番薯一般大小,大豆乳房一般结实饱满,小麦呢,更不用说,穗大粒圆,一箩筐小麦硬是要比其它地方的小麦多出十来斤。缓坡是黑土地,是湿地,适合种稻谷、地瓜和芋头。春夏两季是稻谷,田野里黄了绿了绿了黄了,谷穗沉甸甸地挂在梢头,谷粒一颗颗滚圆饱满;芋头永远是松的,到集市去问,坂头村的芋头没有人不知道。这样的村庄,一年四季呈现出勃勃生机。
山梁上那个叫坂头的村庄,不大,人口一千多。几十座房屋,全挤在那一坎山梁上。房屋挤挤挨挨,其余全是庄稼地,明眼人一眼看得出,这个村庄的人,全在给庄稼腾地。是的,自从实行农田承包责任制,农民们看到了前途,边边角角开垦荒地,把所有荒草滩全都开垦出来种上庄稼。农民们一年四季守在田里,傍晚时光歇了工,吃饱饭,一切事情全都做好了,有月光从山上斜射下来,落到天井里,无事可做,便坐在那里抽一泡水烟,喝一壶小酒,唱几句北管:
春色妍,日融和,暖气喧,景物飘飘美霄新,花开三月天,妖娇嫩蕊鲜,草萌芽,桃似火,柳如烟,仕女王孙,戏耍秋千……
这山里,很奇怪,早起的太阳总是很圆,可是炊烟怎么扯也扯不直。当山梁上的炊烟弯弯曲曲腾挪起来的时候,缓坡的农田里,早已分布着星星点点的农人。远远听见有人叫,丰收婶,您这么早!那个被叫做丰收婶的六十多岁的胖妇人,这时候已经走到这一片缓坡的庄稼地中央,那里一块长方形稻田,便是她家的土地。她扛着锄头沿着田埂围绕着自家稻田走一圈,驗看了地里的庄稼,喜滋滋地笑起来:又是一个丰收年!
这块土地,有点儿特别:五六分大,四四方方,十分齐整。这样的地难得,一犁铧可以走到头,没有边边角角犁不到的地方,不用动锄头,能省许多力气。丰收婶至今十分得意,要不是她,就凭她家老头子丰收那臭手气能拿到这块地?当初生产队分配土地,缓坡的这一片地因为是肥地,争执不下,后来选择了抓阄。相信运气吧,抓到好地是好地,抓到坏地是坏地。原先是她家老头子丰收要去抓阄,幸亏没让他去。多少人盯着那块宝地,没想到被她抓到了。那时候,一圈人围着那个石磨,纸阄撒在石磨上,生产队长把石磨转几圈,她犹豫许久,不敢下手,后来一狠心,随便就近抓一颗,一颗心怦怦跳,打开一看,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念出那一地块的编号。那块宝地被她抓去了,所有人呀一声,身上就像抽了筋,一下子没了力气。
那块地水汪汪的,一年四季没干过。一次,她拿锄头偷偷掘一下,掘了一尺深,土壤肥得流油。那时候她就想,要是能得到这块地,那是上辈子积来的福分。多少人梦里都想得到这块土地,没想到被她拿去。
除了山梁上那几块旱地,她一年四季守在这块地里:不让一棵草落到里面,不让一条虫爬进这一丘田,不让一只鸟飞进这块地。田岸修葺得笔直平整,春天种的稻谷,秋天种的地瓜,每一畦,每一垄,一横一竖,整整齐齐,行距列距,分毫不差。她想,总要对得起这块好地吧。所以她的稻谷总要比别人的多打几箩筐,她的地瓜总要比别人的个头大一圈。别人开玩笑说,丰收婶,肥人种肥瓜。她非但不生气,而且笑呵呵。只要庄稼丰收,管他怎么说。对于农民来说,还有什么比庄稼更重要?
春种秋收,日子一天天过去,年景一日日好起来,吃饱了,穿暖了,种田人就有闲心思想其它事情了:学一门手艺,搞一点儿副业,村里这里那里盖起新房屋。后来步子迈得更大胆了,有人开始丢下田园出门跑生意,腰里别上寻呼机,很快寻呼机不用了,又换上手机。不仅村里人蜂拥着出去,到外面工厂去做工,逐渐工厂也开到家门口来了。这几十年间,世界变化太快,快得让你反应不过来。世界的变化也带来了村庄的变化:年轻一辈,不论男女,争相往外去,村里只剩下年纪大的人和小娃子,这个叫坂头的村庄,一下子空旷起来。山梁上的地没人种了,荒草一人高。后来连中年人也坐不住了,带上行囊出门去,这一下,连缓坡上的土地也丢下了。丰收婶越来越感觉到这一点:这个村庄的人早晚要跑光。原先一庄稼地的人,那多热闹,说话,做活儿,吵架,生龙活虎的。哪像现在,一天见不到几个人,一颗心都空成荒草滩了,一个人蔫蔫的没有半点儿精神劲头。在地里做活儿,四围空旷寂寞,安静得可以听见自己的心跳,一个世界里只有风吹来吹去的声音和你自己呼吸的声音,想了都让你心慌。这时候,她多么希望能有一个人和她说话,甚至吵架,可是没有。她觉得这个世界是变了样了。没有了庄稼,你吃什么?她自小就教训她的儿子爱国,说,你是农民的儿子,这一点你不要忘了。你就是土里爬出来的人,不管多有出息,这一点不敢忘本。爱国早不种田了。爱国争气,高中毕业,考上大学,毕业后进了镇政府,年轻有为,三十多岁,现在已是副镇长,在城里成了家、立了业。她种这田,收获的庄稼,一个人哪吃得完?都是为他准备的。爱国每个周末都不嫌麻烦开车回来,大多一个人,有时带着老婆和孩子。他的老婆是城里人,城里人讲究,农村住不惯,嫌蚊子多,嫌没有浴室洗澡不方便。城里人白,蚊子专爱盯着她们咬,她可受不了。来一次,第二天一早就带着孩子回城里去,第二次就不敢来了。这一点丰收婶很看不惯,说,城里人咋那样娇贵?说,没有农村,哪有城市?说,城市人一日三顿吃的还不是农村种出来的粮食?没有农村人你喝西北风去。现在城里人时兴吃绿色食品,每次回来,爱国都要让娘弄些地瓜、花生、芋头带回去,塞满一后箱子。爱国说,还是自己种的粮食香。这话她爱听,说,这才像我的儿子。这样一来,丰收婶种庄稼就更来劲了。
丰收婶是种庄稼的行家里手。她种的粮食爱国吃得最多,最有发言权,他说,我娘种的庄稼没得说,全村第一。这句话不是王婆卖瓜,镇里张副镇长是爱国同学,就喜欢吃他娘种的地瓜,说,我走遍全镇,也只有丰收婶家的地瓜好吃。经常到他家来,就为了吃一碗他家的大米地瓜粥。
丰收婶十八岁嫁到坂头村,今年六十八岁,算起来种田整整五十年了。其实不止五十年,在娘家,她十三岁就跟着娘下地,学会插秧。种了一辈子的田,她都种上瘾了,她从来不觉得种田有多苦,反而觉得其乐无穷。在她看来,种田完全是一门艺术:翻耕,平整,上垄,剖沟,撒种,除虫,施肥,收割。就像一门手艺的许多工序,每一道工序都有讲究,要根据这一块地、作物和季节的特点灵活处理,一点儿也不敢马虎。她认为,种田不只是体力活儿,更是脑力活儿。对她来说,种田这种事情,最有意思的是过程而不是结果。由于体会到其中的乐趣,种田对她来说简直是一种享受。
然而,农村里现在田都没人种了。一方面粮食是贵了,可和打工比起来那点儿钱就少了。所以即便有政府补贴,许多人还是放弃了土地出门打工去。缓坡的那片庄稼地里,荒地越来越多了,整个田野一天也见不到几个人。有时她就怀念起以前来了:以前多好,庄稼地里到处都是人,人们比赛着种田,你追我赶。人的声音,牛的声音,狗的声音,热火朝天,哪像现在一片死寂?种田没啥用处,爱国也希望她不要种了,说,娘,您年纪大了,不要种田了,跟我到城里去吧。她说,到城里去干啥?整天关在屋子里,我可受不了。她是一天不下地身上就不舒服的人,哪里离得开这片土地?爱国说,要不少种点儿。少种点儿,也是,不服老不行啊。以前风里来雨里去,现在人一老,毛病全来了:风湿痛,关节炎,腿脚抽筋,闹得你不得安宁。挑一挑土到地里去,以前一阵风似的,现在一路要歇好几次。土挑不到山梁上去,前几年她就把山梁上的旱地弃了,现在只剩下缓坡的这一块土地了。这块地她无论如何也不会放弃的,除非她再也干不动活儿了。这可是她的宝地。这是全村最好的土地,当初好不容易得到这块土地,村里不知多少人羡慕,现在把它弃了,怎么说也说不过去。
土地没有人种作,人少了,鸟雀多起来。每年稻谷成熟的时候,就有一大群鸟雀飞来:最多的是麻雀,也有乌鸦、白头翁和喜鹊。这几年,又不知从哪里飞来白鹭,不是一只,而是一大群,远远飞来,落进这片庄稼地里。这些鸟雀,栖息在山上。山上已经很久没有人上去了,树木丛生,百草丰茂,连上山去的路也被野草封住了,隔离了人类,成了鸟雀的乐园。鸟雀们在山上树林里筑窝,繁衍出更多鸟雀,白天飞到田野里来觅食。对付这些鸟雀老办法是无啥用处的。这一年,丰收婶早早就在稻田里支起稻草人:用竹竿、稻草裹个人形,穿上她和爱国不穿的衣服,戴上斗笠。没用,麻雀照样飞来,大摇大摆地走进稻田里糟蹋粮食,甚至飞到斗笠上拉屎,气得她火冒三丈——那顶斗笠她还想用一季呢。由于没有效果,只好靠人力,每天她早早来到这里,挥一根长长的竹竿,来回奔跑,驱赶鸟雀,累得够呛,幸好稻谷很快成熟了,就要收割。
她已经把镰刀、箩筐和粟桶全都收拾出来了,清理干净,拿到太阳下面去晾晒。又筹备着雇一个人力——一个人是干不动这活儿的:把粟桶扛到地里去,把稻谷挑到山梁上自家门前来晾晒,这些都需要力气。她是不行的,年纪大了。以前时兴互帮互助,现在没有人种田了谁来帮你?幸好这些年,村里一些没有出去的女人专门来做这件事:农忙时节,出租劳力。一天几十块,给需要人力的人家雇请。这样也好,不需要看别人脸面,欠人家人情。当丰收婶琢磨着雇谁的时候,村里突然涌动着一种異样的空气。
那几天,不知怎么,村里的人突然多起来,许多在外面打工的人都回来了。又不是什么节日?她疑惑起来。往年只有节日,或者村庄普渡,人们才把积累下来舍不得用的那点儿假日请了,远远从外面赶回来:一来和家人团聚,二来也做身体和心灵的休息。可是这时候没有什么节日啊?起初她想,也许农忙,稻谷就要收割了。也不在意。
这一天早晨,吃完早饭,她依然像往常一样早早荷一根竹竿下到田里去。那条叫黑的狗早跑到前头去。每次她到地里去,它总要厮跟着,不离左右。她挥着竹竿驱赶鸟雀,赶累了,喊它去。它原先卧在那里,听到主人的召唤,爬起来,前后奔跑,替她扑赶鸟雀,她就能够歇一口气。这时候尚早,草叶上的露珠还没有干透,一闪一闪地耀着光。鸟儿早醒了,或远或近,带着微薄的兴奋,叽喳喳叫。她惦记着地里的庄稼,加快了脚步,下到田里,发现田野里这里那里都是人。比她还早,这可少有,那些人在做什么?或者叉着腰,站在那里,指指点点,或者低下头去,比比划划,似乎在察看什么。她疑惑着。这时候,有个人从坡上下来:
丰收婶早!是她邻家妹子,叫土妹。
土妹,几时回来哟?
昨天刚回。您这是要去哪儿?
赶鸟啊。
是啊,这两年鸟雀多起来了。
你这是要去收割稻谷?
我们家的田园早没种作了。
丰收婶这才想起这一家子出外挣食去了,两扇白木板大门长年锁着,庄稼地早已成了荒草滩了:那这是……
那女子这才停下脚步:丈量土地啊,把自家土地大小量下了,心里也有个底。
量土地做啥?土地要重新分配?听到这里,丰收婶紧张起来。她最怕的是土地重新分配了:那块地可是她的宝贝。
分配个啥?都啥时候了?
那啥事由?
征地。您不知道啊?
征地?啥征地?
爱国哥没和您说?这片土地政府要征收了。
啥?!丰收婶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以为自己听错了。
去问爱国哥。
土妹还想说什么,那边有人喊,土妹土妹,你在磨蹭什么呢?她丢下一句话,急匆匆走了。
丰收婶站在那里愣了半天,狠狠拍打一下自己的肥脸,这才清醒过来:这是不是真的?这么重要的事情爱国咋没说呢?得问问去。这样想着,丢下竹竿,一个人急匆匆往回赶。
上了山梁,气喘吁吁回到家里,站在门前歇一口气,推开门,厅堂里个电话。这是一个四房看厅(左右各两间房间,中间一个小厅堂)的石头房子。闽南这一带,古代是出砖入石悬山式燕尾脊皇宫起古大厝,现代是四房看廊四房看厅的石头房子,这几年,出门做生意、出外打工有了钱,一些人开始盖起两层三层的小洋楼:钢筋水泥结构,外墙贴上瓷砖,宽大的窗户全都装上铝合金和玻璃,十分气派。原先她也想让爱国回来盖房子。一层的老旧石头房子夹在许多小洋楼中间显得低矮破旧,她家爱国又不输给别人,大小是个副镇长,让他在家里盖个房子她在村里也有个脸面。起先爱国也说行,地是没有问题的,张副镇长是他同学,刚好分管这一块。她都筹划好了,把屋后那块杂地腾出来,盖个两层楼。可是后来爱国那边情况起了变化:原先他在城里买的两房一厅的七十平米的套房,嫌小,又折腾着要换一套大一点儿的房子,资金有限,这边盖房子的事情也就搁置下来了。房子里面有些昏暗——窗户小,以前的房子都这样。屋里家用电器:电视有,电话也有。去年爱国说要买一台冰箱,她说,农村人买那个啥用?爱国说,偶尔有用。他每次回来,大包小包,鱼啊肉啊买了一大堆,她舍不得吃,舍不得吃的结果是坏掉。她说,你以后就少买点儿,浪费钱。后来爱国又说要买一台洗衣机,她说,买那东西啥用?筋骨活动活动有好处。后来也就不买了。
电话号码抄在墙上,字写得很大。她不识字,爱国就把手机号码抄在纸条上,贴在那里。她抄起话筒,拨了墙上的号码,起初由于紧张拨错了一次,第二次再拨,通了,却没人接。怎么没接?这孩子,忙啥呢?搁了话筒,搓着手在那里走来走去,急得团团转。这样重要的事情也不和娘说!难道他不知道?不会不知道的,他和张副镇长那么熟,三天两头在一起,就是不问,他也会说的。会不会是真的?该是。要不那些人回来干啥?土妹是她家邻居,自小看着她长大的,不是爱说谎的人。这土地,咋说收就收了?以前调整土地,至少要開个村民大会,把政策和群众讲清楚了,听听群众意见。把土地收回去,农民靠啥过活?虽然很多人不种地了,可还有些人靠种地过日子。把耕地全都毁掉,以后怎么办?没有了土地,农村还叫农村吗?没有了土地,农民还叫农民吗?……一个人正在那里胡思乱想的时候,电话响了。她抄起话筒:
爱国吗?
娘,是我。
忙啥去了,找不到人?
还在睡觉呢。
都几点了,你不上班?
昨晚喝了不少酒,头疼。
这孩子,说了多少次了,少喝点儿酒少喝点儿酒,喝酒伤身啊。说到喝酒,她又唠叨起来了。爱国以前喝酒少,自从当上副镇长,每天喝个没完,她都替他担心:喝那么多酒这身体咋受得了?
应酬,没办法。娘您有事吗?这么早!
当然有事。我问你,村里那些地咋回事?
爱国停顿一下,似乎这才想起那件事,说,哦,这事啊,我忘了和您说了,是有这事,说要征收呢。
她愣在那里。
看她没说话,爱国以为娘生气了,赶紧解释,张副镇长前天才和我说的,这不忙吗,我就忘了。
咋说收就收了?
现在到处都在征地啊。
也不会轮到我们这样偏僻的地方。
说我们那里空气好,一个开发商要来开发房地产。现在外面不都污染吗?
为什么偏偏是缓坡地?那可是村里最好的耕地?
说那里风水好。
…… ……
事情定了吗?
定了。
我们家那块地呢?
大概也在范围内。
爱国知道他娘把那块地当成自己的宝贝看待,有点儿担心她想不开,宽慰她说,娘,您看现在地也没啥用,多少人盼着征地呢,一亩一万五,多好的价格。是啊,这不,村里那些人特地跑回来,原先那些没人管的庄稼地里又围满了人,把荒草扒开,找出原先的地界,在那里丈量土地。这下子她明白了。土地她可不想卖,别说一万五,就是十万十五万她也不卖。钱总会花光的,地可是子孙万代的事。想到这里,她的心似乎被谁用刀割了一下,急起来,说,儿子,你和张副镇长说说,看能不能把我们那块地留着。
娘,这恐怕有点儿难,这是县里定下的事情。
不管怎样,这一次你可得出力。
娘,您是知道我的难处的,我是政府的人,怎么能带头抗拒征收土地呢?
我不管,我只要我的地。
娘,您怎么这样?
我怎么了?丰收婶似乎是生气了,镇政府可征求过老百姓的意见?要是国家的事,我把所有土地都献出来也可以。
娘……
我不是你娘,你要不和张副镇长去说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忘恩负义的家伙,你不是吃地里的粮食长大的?
那些地……有用吗?现在谁还种地?
那是我们的根啊,没有那些地,我们还算什么?
那些地留给我我也不要。
不是留给你的,是留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的。
…… ……
爱国知道自己缠不过娘,说,反正我是没有办法。
听这话丰收婶似乎被谁击打了一下,一下子蒙了,呆呆地立在那里,话筒从她手里脱落。
爱国一惊,在那边喊,娘,您咋了?娘……娘一个人在家他不放心,开着吉普车风驰电掣回到坂头村,吱一声把车停在坡底,一路小跑回到家里。黑看见他,十分欢喜,摇头摆尾迎上来,厮缠着他。他把它赶开,冲进门里,见娘一个人痴呆呆坐在那里,扑过去,喊一声:娘,娘,你咋了?
丰收婶似乎这才从梦中惊醒过来,一颗泪滚落下来:儿呀,你可得帮帮我。
爱国说,娘,您知道我的难处。
再难也得办。
我……
对于那些土地,他不是没有感情,小时候整天跟在爹娘身边在地里捉青蛙、扑蚂蚱,玩耍嬉戏,长大后又跟着娘帮娘捡稻穗、挖地瓜,整日在地里扑腾,怎能没有感情?他也想把这块地保下来,可是县里定下来的事情是很难改变的。去找张副镇长?自然没有效果,可是他还想试试,总得给娘个交代。从门里出来,打了张副镇长电话,张副镇长说:
我说你娘那么大年纪了种地干什么?
他说,你不知道她那人一辈子离不开土地?上次我请她到城里去,只待了一天,就吵着要回乡下来。她一辈子就和土地有感情。
张副镇长说,要不你和上面说说。
他怎么去说?
进屋去,娘问他,怎么样?
他说,没办法。
娘扑过来,拉住他的手,说,儿呀,你可得再想想办法!
他说,我再想想办法吧。其实他心里一点儿也没有底。
告别娘,下了山梁,钻进汽车,他启动油门,开着车回镇里去。
风刮过一阵,似乎又没有了。从外乡回来的人丈量完自己家的土地看看还没有什么动静就陆续回去了。收获的季节到了,丰收婶以为这下子没事了,雇了个人,把稻谷割了,又筹划着种上下一季庄稼。缓坡的这块地,一年四季都不能闲着:稻谷收上来了,又要种下地瓜。地瓜秧子已在屋后菜地里备着。屋后那块地,爱国没回来盖房子,她把它收拾一下,又种上菜。她都准备好了,这时候又起了风波。这一天,她扛着锄头准备下地去,村里的喇叭响了。村里的喇叭好久不响了,除非要妇检,或者征兵,一年到头沉默着。是村长的声音,村长在喇叭里喊:
各位村民大家好!接镇政府通知,咱村坂下那块缓坡地征地工作开始了,赔偿标准一亩一万五,请各家各户通知到位。下周一开始丈量土地……
听到这里,她呆了,愣愣地站在那里:看来这件事是无法挽回了。这时候,牛倌傻二狗扛着犁铧吆着牛从那边过来了,喊,丰收婶,您看地还犁吗?她回过神来,说,还犁个啥?地都要被征收去了还犁地?把锄头扔在那里一头扎进门里去打爱国的电话。
拨通了电话,她还没有说话,电话那头爱国说,娘,有事吗?我正要去开会。
我问你,那件事情办了没有?
哪件事情?
征地的事情,你忘了?
哦,那件事情啊,没忘,我哪敢忘了呢?我问过了,上面说那是赵县长牵头办的事,谁也没有办法。
她呆住了。
电话那头爱国喊,娘,娘,有话快说,我还要去开会呢。
不知怎么,她无来由地发怒了:我养你这个儿子还有啥用?自己家的一块地都保不住还当什么副镇长?我不管,你去给我想办法,我只要地!说着就把电话挂了。
爱国刚出镇政府,想去县里开一个会。全县掀起新一轮开发,招商引资,大批企业涌进来,开工厂,建楼房,征(地)拆(迁)安(置)工作成了乡镇工作的重头戏,每天不知多少事。这一类事情,要求增加补偿都好说,县里有政策,可以灵活处理,只要不违反原则。最头疼的是纠缠不清,现在轮到他娘,他就更加头疼了。娘那边,他理解娘的感情,一辈子和土地打交道,没有土地她怎么活?山梁上也有地,主要是那块地是宝地,是她的心肝宝贝。开发商那边,那个房地产企业老板和赵县长熟,征地那是铁板钉钉的事,谁也无法改变。上一次,赵县长遇见他,还说,爱国啊,你是坂头村人,这件事要起带头作用。他还怎么敢去说?现在娘又抓住不放。两头施压,夹在中间,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坂头村开始做征地动员工作了。征地不像拆迁那么难,现在粮食不值钱,地没有人种了,人们也不看重,正盼着能卖出点儿钱呢。一些人家犹豫,无非为了多争取一点儿补偿。一切进展得很顺利,几乎没有什么阻力。丰收婶这边,张副镇长特别交代过,这一天,村长亲自登门。丰收婶知道村长来找她做什么,可是同一村庄的人,乡里乡亲的不好却了人家的情面,给他端茶倒水,请他坐。村长是个很有工作经验的人,一进门,就把所有笑容都堆放在脸上,见丰收婶一个人坐在那里发愣,也不提征地的事,扯到丰收,说,我一辈子最敬佩的人就是丰收哥和您了。
她家老头子丰收是一个八棍子打不出一个响屁的人,生产队的时候做队里的牛倌,是生产队里的劳动能手。牛倌那时候是很重要的人,担负着一个生产队大部分土地的耕作工作。丰收是一个实心眼的人,生产队安排的任务,一天的地犁不完,他起早贪黑也要把它犁完。他是耕作的好手。生产队把一张犁铧和一头牛交给他,他把一张犁铧保养得坚固锋利,把牛调教得十分出色。每一次犁完地回来,他都要把犁铧上的泥土剔除干净,支在那里晾干,不像别人,随便把犁铧扔在地里。别人一张犁铧用一年,他一张犁铧要用好几年。还有牛,他的那头牛是村庄里最优秀的牛。牛没有夜草不肥,每天犁完地,他都要去割一筐草做牛的夜宵。照顾那头牛他比照顾自己还细心。那头牛不仅力气大,而且技术好: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走道不偏不斜。这一些都需要调教。丰收就这样把一头牛和一张犁铧调整到最佳状态,牛、犁铧、人保持高度一致,他犁的地整齐划一,即便再弯曲的土地,每一垄,每一畦,他都要整出优美的弧形。那年夏天,他一个人在缓坡地里耕地,犁不完,大中午不回来歇息,中了暑,死在地里。丰收,丰收婶,夫妻俩都是地疯子,这在当时整个公社都是出了名的。
村长说,老嫂子,您一辈子也不容易,丰收早早去世,您一个人拉扯爱国,把他培养成那么出色一个人,不要说我敬佩您,就是整个村庄的人都敬佩您。
这一说,触动了她的心事。一辈子,一个家,里里外外全靠她一个人,又要拉扯孩子,不知多少辛酸!幸好爱国有出息,日子这才好起来。原先紧绷着神经,正想着如何对付村长,这时候被他这一说,动容了,说,命,都是命,生成这命你有啥办法?
村长说,老嫂子啊,所以我说,您该歇歇了。爱国都当副镇长,很快就是镇长了,那是一个镇的父母官啊,您该跟他到城里去享享清福了。
她说,我也想享清福,可是咱生就土里翻滚的命,一离开土地就浑身不舒服。就说上一次吧,爱国用小车载我到城里去,才去几天就这里酸那里疼,又感冒了,折腾好几天都不见好,又是打针又是吃药,没想到一回来,嘿,毛病全好了,你说怪不怪?所以我说,还是咱农村好。
村长说,老嫂子啊,那大概是水土不服吧,住上一阵子就好了。
…… ……
这样拉着扯着也不知说了多少话,临了村长说,老嫂子啊,咱都是农村人,我也不再绕弯子了,我的意思是,您老年纪大了,也该歇歇了。我们理解您的感情,一辈子和土地打交道,不知流了多少汗水在地里,说一粒土一滴汗也不过分,每一天吃的粮食都是这地里生产的,谁会没有感情?可是这征地是县里的大政策,咱拗不过。张副镇长和爱国关系好,特别交代我,要我做好您老的思想工作,充分尊重您的意见。他的意思是,补偿尽管说,只要不违反政策。说完,又靠近来,压低声音说,他私下和我通了气,说,最高两万。又交代她,这是特殊照顾,对谁也不能说的。
丰收婶见村长这样说,说道,你们的情我领了,我不要钱,我只要地。
说了一箩筐话,没有效果,村长心里自然有些不高兴,可是仍然满面堆笑,站起来,说,老嫂子,这件事情是赵县长定下的,爱国想帮也出不上力,除非他副镇长不想当了。您再考虑考虑。说着,把这句话撂下,告辞回去。
丰收婶一个人站在那里,想起那块土地。
分到那块土地后,她不知花了多少心思在里面:翻耕,施肥,锄草,种作,每一步都做得比别人细。她都把它当作宝贝看待,细心呵护。这块地融合了她的汗水、热情和希望,就是她的一生。在这块土地里面,寄托了她的所有感情。这块地也和这个家庭的命运联结在一起。现在说收就要收回去,把它铲平,在上面盖房子,以后再也见不到,她怎么割舍得下。这样想着,一个人痴痴呆呆坐在那里。
日子一到,村里动起来了。不仅村里的人,镇里、县里的人都来了,十几辆小车一溜排在那条乡村公路上。田野里到处都是人,下到田里,找到地界,拉皮尺,量亩数,登记在案。村里的人们怀着一份复杂的感情:就要永远告别这土地了带着一种微薄的兴奋,跑来跑去,临到最后,想到未来,不知为什么,却又觉得茫然了。
第一批土地的丈量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就剩下十来块地了。镇里开了会,总结成功经验,针对剩下来的没有签征地协议的几户人家逐户分析,提出针对性意见。很快,第二批征地工作又开始了,镇里派得力干部配合村干部下到农户,或者提供其它方面补助,或者帮助解决劳动力,把剩下来的未签协议的农户都解决了,最后剩下丰收婶一户。
这一天,村长带路,镇长亲自下来了。进了门,村长没有说话,镇长说,丰收婶啊,我们是理解您老人家的感情的,可是您看这工作还得推行下去。现在只剩下您老一户了。我们也只是执行者,上面交代下来的事情不能不办。补偿的问题我们一定做到您满意,您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只要我们能够做到。您看这协议……村里的人都把协议签了,只剩下丰收婶,这并没有对她形成打击,反而使她的立场更加坚定,这时候执拗起来了,说,我不管,我只要我的地!村长看看场面尴尬,说,老嫂子啊,开发商答应了,把水泥公路修到咱村里,又要帮咱解决部分征地户劳动力,安排他们到小区物业公司做事,您说这多好的事,咱可不能因为一户人家的问题拖了全村的后腿。别说丰收,您一向也是明白事理的人啊。把水泥公路修到村里来,这是全村人盼望了一辈子的事。坂头村在山梁上,每一次下雨,路就要被冲毁一次,铺上水泥路,就可以一劳永逸了。爱国每次回来都要抱怨,要不是吉普车,小车走一次底盘就要报废。自己修路,哪来的钱?可是现在,她已经没有退路。其他人可以放弃,她绝对不可以。想到这里,她又固执起来了,说,别的事情我不管,也管不了,我只要地!镇长摇摇头,拉着村长从里面出来了。
丰收婶好多天没有到地里去了,一来没有心思,二来不愿意看到地里的情形。多好的一片庄稼地,小麦成熟起来,一片金黄,一眼望不到头,一阵风吹来,波涛一般起伏,看了让你打心里笑出来。现在地里一片狼藉,已经开始平整土地了,铲车开进来,把一片庄稼地搞得不成样子。这一片膏腴的土地,从此就要被一只无形的巨手从坂头村的历史里抹去。想到这里,她的心就疼起来。
这天夜里,她做了个梦,梦见丰收扛着犁铧、赶着一头牛在一片高楼大厦之间转来转去,找不到往田里去的路。惊醒过来,在黑夜里坐了许久,突然,她做出一个决定,一定要把那块地保下来,无论付出多大代价。
自家的事处理完,剩下的事情和自己无关了,从外面回来的那些人又陆续出去,村庄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下过一阵雨,推土机无法工作,工人们都回去了,田野里阒无人迹。这天早晨,黑在前面带路,丰收婶穿着蓑衣戴着斗笠扛着犁铧吆喝着牛下到地里,像往常一样,起垄,整畦,栽下地瓜苗子。风中,地瓜秧子在细雨里斜着身子,精神抖擞地站立起来了。丰收婶扶着锄头,站在田埂上,望着这一片庄稼地,无声地笑了。
雨过天晴,人们走进这片土地,惊讶地看到眼前的一幕:被铲平的庄稼地一片零乱,在这片零乱的工地中心,有一丘田园,田垄收拾得整整齐齐,地瓜苗子精神抖擞,迎着朝阳,向你微笑。这一切,呈现出一派生机,似乎在无声地抗拒着什么。人们在惊奇赞叹之后打听这块庄稼地的主人,都觉得十分稀奇。
这一天,来了一群人:有镇里的人,有县里的人,开发商也来了,带队的是分管土地的副县长。黑压压的一群人,副县长大手一挥,推土机轰隆轰隆开过来了。所有的鸟儿都飞走了,所有的鸣虫都噤了声。阳光下,丰收婶扶着锄头,昂首挺胸,从容镇定,站在田地中间。双方无声地对峙着,围观的人们紧张了起来。这时候,一支队伍,有老人,有小孩,还有鸡、鸭、狗,列着队,井然有序,默默无声,从山梁上下来,肩并着肩,手挽着手,把这块土地,把丰收婶围起来。在那条叫黑的狗的带领下,那些鸡、鸭、狗蹲在他们的前面,沉默镇定地注视着眼前的这些人。推土机停下来了。那些人惊呆了,嘴巴张得大大的,眼神里充满着意外、惊讶和恐惧,一点点向后退去。这时候,整个世界安静下来了,没有一点儿声音,人们只能听见自己急促的心跳。嗬一声,不知谁发出一声赞叹。这声赞叹似乎从地底下发出:空旷,寂寞,震撼人心。再看丰收婶,在阳光里一点点高大。
李集彬:1973年生。泉州市作家协会散文创作委员会副主任。作品发表于《阳光》《文学界》《青年作家》《山花》《中国散文》等报刊,被《儿童文学选刊》转载,获得福建省第22届优秀文学作品奖二等奖、福建青年散文奖第二名、福建省政府第六届百花文艺奖二等奖、第18届孙犁散文奖单篇散文一等奖第一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