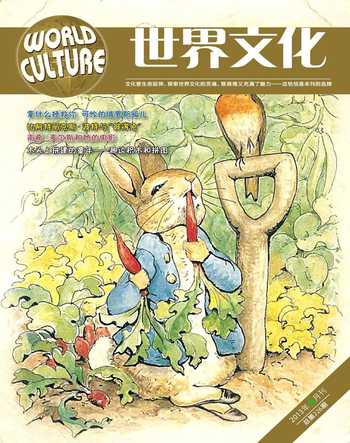寻访艾布·努瓦斯及其它
2013-04-29彭龄章谊
彭龄 章谊
翻开《阿拉伯古代诗选》就像走进了长满奇花异卉的花园,令人流连忘返。
阿拉伯民族对世界文化的突出贡献,除了世称“天下奇书”的《天方夜谭》(《一千零一夜》)之外,恐怕就该数那浩如烟海的被视为阿拉伯民族史籍的诗歌了。
自古以来,阿拉伯民族生息繁衍在地跨亚欧非三大洲交界的广袤地域,承袭了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地中海的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巴比伦、亚述文明,至伊斯兰帝国阿跋斯王朝时期,更通过陆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与波斯、印度及黄河文明相互交融、借鉴,蓬勃发展,如日中天……上世纪60年代,我们初到西亚工作,曾随友人去沙漠夜猎,在篝火旁,听他们谈及祖上游牧生活的情景:当夕阳坠落,星光笼罩大地,贝都因们拢好骆驼、羊群,围坐在已成断垣残壁的废墟旁,面对一蓬篝火,满天繁星,一边撕吃着刚烘好的大饼,喝着驼奶,一边听祖辈讲述远古先贤的传说,其中穿插着许多诗体韵文,一代代口口相授,延绵不息……不由忆及在北大求学时,曾听马金鹏老师介绍,早在伊斯兰帝国建立前的贾希利叶(蒙昧)时期,生活在阿拉伯半岛上的各游牧民族传统的欧卡兹集市上,照例要举行赛诗会,那隆重场面远胜于赛马、赛驼。各部落著名诗人在族人簇拥下逐一登台朗诵,最后遴选出公认的佳作,用金水抄录在亚麻布上,高悬于克尔白神庙前,供人们吟诵、观赏,称为“悬诗”,被誉为“王冠上的珍珠”……或许正是这独特的地域条件与自然环境:长河落日,大漠孤烟,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和那些令人热血贲张的先贤们跃马征战的传奇故事,不仅培养了他们崇尚独立、自由、正义,坚韧豪爽又放荡不羁的性格;也培育、训练了他们海阔天空的想象,机智、敏悦的思辨和妙语如珠,出口成章的语言运用能力……
我们多么想见识见识那“王冠上的珍珠”呀!可马老师却不无遗憾地说:“译‘悬诗需要丰厚的学识,至今尚无人尝试。”他随口背诵了一句阿文诗,解释说:“这意思是:要想摘取星星,就得插翅上天,不能徒托空言。”他勉励大家努力学习:“希望你们之中将来能有人把‘悬诗译成中文。”那时,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搞翻译,常被看作“成名成家”,走“白专道路”。所以,大家也未往心里去。毕业后,大部分学友的工作又与文学无涉,甚至随着时间推移,距文学越来越远。
那时,以至其后的若干年,除纳训先生译的《一千零一夜》和为支援巴勒斯坦等阿拉伯地区独立、解放斗争出版的有数几本译著外,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阿拉伯文学作品被译成中文,更遑论这古典诗歌了。记得我们的启蒙老师邬裕池有次私下谈及,也不禁感慨连连。可惜,他英年早逝,未及赶上改革开放得以施展才华……改革开放带来了可喜变化。随着“阿拉伯文学研究会”的成立,纪伯伦、马哈福兹、塔哈,侯赛因等著名阿拉伯作家的作品、文集不断被译成中文,尽管良莠不齐,但毕竟开创了阿拉伯文学研究、出版的繁荣局面。
然而,对阿拉伯古典诗歌却依旧少有问津。究其原因,大约是:“译事难,译诗尤难,犹如戴着枷锁跳舞”吧。可喜的是,有一位学友却义不容辞,勇于担纲,他就是后来曾接任阿拉伯文学研究会会长的仲跻昆教授。他说:“作为阿拉伯语言、文学的教师、翻译、研究工作者,时时觉得未能尽职尽责而惴惴不安。”而“向人呼吁不如从自己做起”,他下定决心:“吾往矣!”像负重的骆驼,硬给自己“戴上枷锁”,去摘取那辉映在“天方”夜空里的星辰……
这部《阿拉伯古代诗选》就是他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教学、科研,以及繁忙的社会活动之余,在研究、译介阿拉伯古代诗歌方面取得的可贵成果。它囊括了自贾希利叶(蒙昧)时期(公元475—622年)至近古衰微时期(公元1258—1798年)一百三十余位诗人的四百余首诗。其中包括被誉为“王冠上的珍珠”的乌姆鲁勒,盖斯、祖海尔、安塔拉等人的“悬诗”。无怪乎翻开它就像走进长满奇花异卉的花园。我们不只—次踏进这花园了,而这次我们只为寻访其中的一位诗人——艾布,努瓦斯……
自公元758年阿跋斯王朝第二任哈里发曼苏尔定都巴格达后,阿拉伯的军事扩展基本结束,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科学、文化和百姓生活也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至哈伦,拉希德(公元786—809年)及其后的马蒙(公元813—833年)任哈里发时代,更是如日中天。正如我国被认为是自秦汉以来政治经济快速发展“鼎盛时期”的唐朝开元时期,那时的西安与巴格达,恰如“丝绸之路”上相互辉映的两盏明灯。而提到盛唐,不能不提及李白;提到阿跋王朝,自然要提到毁誉参半,却独领一代风骚的艾布,努瓦斯……
我们是从《天方夜谭》里描述哈里发哈伦,拉希德微服私访的故事中知道艾布,努瓦斯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在巴格达工作时,在艾布努瓦斯大街上,看到根据《天方夜谭》故事雕塑的山鲁亚尔和山鲁佐德的栩栩如生的雕像时,艾布,努瓦斯随同哈伦,拉希德在底格里斯河的游船、酒肆、风月场中演绎的那些风流韵事,便又浮现脑海。后来又听到许多有关艾布,努瓦斯的传说,并在友人指点下,在一个高档住宅区的小广场上找到他的雕像。那是雕塑家伊斯梅尔,土尔克1963年创作的:艾布,努瓦斯身着长袍,头缠布巾,坐在基座上,右手扶膝,左手擎着酒杯,那神情,让我们联想到国画家蒋兆和差不多同期根据杜甫诗意“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创作的李白像。不过那时,我们只知艾布,努瓦斯与李白同是站在时代顶峰的诗人,却未读过他的诗。所以打开这部《诗选》,就像当年寻访他的雕像一样,急切切地想读读他的诗……
也与出生于中亚碎叶(今吉尔吉斯和哈萨克斯坦一带),素以“布衣”自诩的李白相似,艾布,努瓦斯(公元762—813年)生于波斯胡齐斯坦农村,幼年丧父,家境贫寒,成年后去巴格达,由于才华出众,得到宫廷,特别是哈伦,拉希德的赏识,一度成为其“新宠”。然而,伴君如伴虎,布衣出身的他,不惯宫廷的繁文缛节,又恃才傲物,不耻于效仿穆,本,瓦立德等宫廷诗人,一味承袭古风,不惜用铺张、华美的词藻向哈里发及显贵们献媚取宠。即便是受命赋诗,也不甘逢场作戏,沿袭自“悬诗”起,便形成的以荒漠中已成废墟的先贤或情人的旧居起兴的呆板模式,他在《遵命照办就是》一诗中直陈:“还是得在诗中写上那些废墟遗址/尽管比起咏酒,那些玩意儿不值一提/是权贵让我去描述废墟/我对他的命令无法抗拒/信士的长官,纵然你强我所难/我也只有遵命照办就是……”刚直不阿,诗如其人。也正由于艾布,努瓦斯来自民间,其诗多受民风、民谣影响,直白,明快,甚至以日常俚语人诗。这倒为惯于书写冗长铺垫,华美绮丽却又呆滞、陈式化颂诗的阿拉伯诗界引来一股清风:“我随心所欲,不受羁绊,岂管人们蜚语流言。/我觉得最大乐趣是夜晚,裸体舞女伴着管弦。/一旦下榻于济·图鲁赫,歌女放喉,曲由我点。/享乐吧!青春不会永存,举杯畅饮,从夜晚到白天!”(《随心所欲……》):以及“她没有罪过,只是/爱情好似枪尖,/总在这颗心中刺戳,/于是——心被伤遍。”(《她没有罪过》)等等,无不朴拙,平实,直抒胸臆,深受人们喜爱。却也受到某些习惯于因循守旧的宫廷诗人的妒恨与诟病……
而今,每当看到酒馆中高悬的“太白遗风”的匾额,总会想到杜甫的那首:“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艾布,努瓦斯诗作,也几乎首首都飘着酒香:“勿为莱拉哭,勿为杏德悲,/手中酒红如玫瑰,且为玫瑰干一杯!/一杯美酒喉中倾,两眼双颊红霞飞。/酒如红宝石,杯似珍珠美,/面前窈窕一淑女,尽握掌心内,/手自倾酒眼倾酒,能不令人醉复醉。/同座一醉我两醉,谁人能解此中味?”(《我两醉》)“莱拉”、“杏德”均系阿拉伯女人名,此处指美女。诗人自酙自嘲的放浪神态活灵活现,让人想到李白的《月下独酌》:“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而艾布,努瓦斯的“美酒似能随心愿,/愿它是啥就似啥;/岁月似水洗其身,/世上唯留其精华;/望去恰如一束光,/只能眼看不能拿”(《咏酒》);“管弦声伴美酒香,/手舞足蹈心欲狂。/声色似海任我游,/道统外衣弃一旁。/随意戏谑何为羞,狂欢豪饮敢放浪。”(《管弦声伴美酒香》);“是酒就说明白,让我豪饮开怀!/别让我偷偷地喝,如果能公开。/人生就是酒醉一场又一场,唯有长醉岁月才逍遥自在。/在清醒时我总是失意潦倒,醉如烂泥才走运发财。/大胆指名说出我之所爱,欢乐幸福怎好遮遮盖盖!/寻欢作乐难免放荡不羁,循规蹈矩岂能欢快?/哪个酒徒不似新月当空,周围美女如群星大放光彩。”(《人生就是酒醉一场又一场》)也让我们联想到李白的诗句:“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酒中趣,/勿为醒者传”;“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
早在伊斯兰教产生之前,西亚各游牧民族己掌握酿酒技术,尽管伊斯兰教义禁酒,但也并不妨碍诗人借酒托物兴怀,如女诗人、哈伦,拉希德的胞妹欧莱娅,宾特,麦赫迪就曾写过《知心者唯酒》:“我孑然一身,知心者唯酒,/我们卿卿我我,谈个不够;/我与它结为密友,是因为/无人愿陪我一醉方休!”表明阿跋斯王朝的社会生活、民族文化与宗教信仰等方面,还是比较宽松的。但它毕竟是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政教合一的国家,许多犹太、基督、火祆先等异教徒,纷纷改信伊斯兰教。而艾布,努瓦斯不仅屡屡触犯教规,还公然嘲讽阿拉伯人和社会地位崇高的宗教人士:“……当年洪水一片,把大地淹没,/这酒正是挪亚方舟所载的货色。/几度沧海桑田,几度悲欢离合,/直至一个波斯王将它收藏,舍不得喝。/他把它深深地埋在地里,/此后又是几多春秋度过!/那里,凯勒卜人从未到过,/也没有什么阿布斯、祖卜彦部落……/那里没有阿拉伯人充饥的沙漠苦果。/有的只是石榴花红似火,/还有桃金娘、玫瑰和百合……”;“研究宗教的人啊!/什么这个见解,那个见解,/在我看来,你所说的一切,/唯有死与坟墓千真万确”;“……我们如果不急于进天堂,在世上又怎能把关酒忘掉!/说教的人!让我喝,别管我!我至死同酒都是莫逆之交。/—旦我死了,把我埋在葡萄树下,让葡萄的汁液把我骨头浸泡!”;他反对禁酒:“我要为酒大声地哭泣,/因为经书竟把它列为禁忌。/纵然禁忌,我也要开怀畅饮,/因为我向来不肯循规蹈矩”;甚至公然把伊斯兰教徒视为神圣功课的诵经与被列为“犯禁”的饮酒并提来嘲弄、戏谑:“酒囊摆一边,/经书共一起;/美酒饮三杯,/经文读几句。/读经是善举,/饮酒是劣迹。/真主若宽恕,/好坏两相抵:对责难,他大声反驳:“啊,责骂我的人没完没了,/玩乐是我的事,不要你唠叨!”;“我碍着人们什么了?何必对我大肆诽谤!/人们有他们的宗教,我有我的信仰”;“若有地方能让我喝个痛快,斋月里,我不会等到开斋。/酒这东西喝起来可真奇怪,纵然担罪名,也请豪饮开怀!/啊,对美酒佳酿说三道四的人,你进天堂,进地狱,且让我来!”……显然,这已远远超越了伊斯兰教规的底线。他纵有天纵之才,哈里发的宽容也是有限度的。再加上哈里发身边那些察言观色的宵小的谣诼、谗言,艾布,努瓦斯失宠、下狱便无足为奇了0据说,他获释后曾远赴埃及,依旧穷困潦倒,后又返回巴格达,投奔新任哈里发艾敏门下,但艾敏遇刺后,失去依傍,不得有所收敛。其诗也多为劝世、苦行、乞求真主宽恕等内容,早年狂放却敢怒敢骂,灵动、明快的诗风已荡然无存……而李白面对谗毁与流放,虽然也曾满怀积郁、愤懑:“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但他的诗:“抚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依旧是“器度弘大,声闻于天”的时代强音。其饮酒,也“非嗜其酣乐”,而是“取其昏以自富”:“愁来饮酒二千石,/寒灰重暖生阳春”。虽际遇多舛,也始终以“布衣”身份与“田舍翁”等息息相通:“相携及田家”,“美酒聊共挥”,从不唐突颓废。这一点较之李白,艾布,努瓦斯怕还难以企及。
但对艾布,努瓦斯,百姓们心中,自有另一杆秤。他们除喜爱他直白、豪放又朗朗上口的诗歌外,更爱他敢于蔑视宗法、权势,追求自由、公正的个性。干百年来,人们不仅把他作为阿拉伯民族伟大诗人缅怀、景仰;而且像我国民间流传的李白命位高、权重的奸宦高力士为其脱靴的传说一样,将艾布,努瓦斯的奇闻轶事演绎成一个个勇于蔑视宗法、权势,嘲弄奸佞的智者的故事,代代传颂
艾布,努瓦斯的诗作不过是曾辉映在“天方”夜空的繁星中的一颗和花园中那奇花异卉中的一朵,却已令我们像饮下一杯醇厚、浓烈的美酒,兴味盎然,感奋不己。正由于跻昆学长勇于担纲,不畏危艰的敬业精神和他一贯坚持的“既要对得起作者,也要对得起读者”的负责态度;加上他对中国文学,特别是与诗歌相关的各种文学形式的深厚功底,翻译时像古代苦吟诗人那样,不放过每一处难点、疑点,反复斟酌、推敲,既考虑原诗内容、形式、韵律,语言运用技巧,又兼顾中国读者的要求、习惯,力求作到“意美、音美、形美”。亦即严复老先生提出的“信、达、雅”,方取得这可贵的成果。自然,这选本中也未必每首诗都译得尽善尽美,个别句子,也有为押韵而影响通顺,如“酒通过他们的各个关节/好似痊愈在病中行走”,似需再斟酌为好。然而,瑕不掩瑜。毕竟他是第一个敢向“天方”星海摘取星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