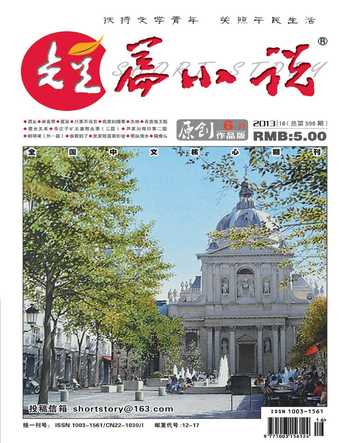亲情和理解之旅:解读孙睿小说《路上父子》
2013-04-29尹传芳
尹传芳
出生于1980年的作家孙睿2004年以小说《草样年华》“出道”,被媒体称作“青春小说的最后一个酷哥”。之后他陆续发表了小说《活不明白》、小说集《朝三暮四》、小说《我是你儿子》《跟谁较劲》《盛开的青春》和《路上父子》等。其中具有转型意义的作品是两部表现父子亲情的小说《我是你儿子》和《路上父子》。尤其后者以其稳健和成熟得到文学期刊“老字号”《当代》的连载,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一、 主题基调:理解、温情
与其他80后作家及孙睿早期的青春小说不同,《路上父子》表现的不是青春的叛逆,也不是青春的迷茫,作者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社会生活,关注点落到了永恒的话题——父子关系上,以成熟、包容的心态理解父辈的艰辛和他们看似落伍的价值观。
能从青春的情绪表达转到对社会现实的关注,是一个巨大的转变,也是一个巨大的跨越,曾经的青春小说写手孙睿在走向成熟,并且得到了主流文学的认同,《当代》杂志编委周昌义在看《路上父子》的书稿时,觉得不像“80 后作家”写的,“我们以前所感受到的‘80后‘90 后的情感出发点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孙睿写得不一样,虽然是站在儿子的角度写父子关系,但是完全能够理解父亲,而不是站在儿子的角度批评父亲,埋怨上一代说‘你们不理解我、你们限制我、你们什么什么我……”[1]
难得的就是这份理解,整部小说就是以“理解”为主题的。丁大民和丁小天和谐的父子关系是在儿子上大学时开始疏远的,大学毕业后儿子再次回到家庭时,两人的心理距离更大了。当父亲把开照相馆的设想告诉儿子时,儿子没有表现出父亲期待的兴奋,儿子认为这个设想不太现实,他说:“你知道现在的人喜欢什么样的照片吗?审美变了,早跟你们那时候不一样了。”[2]69在好多事情的看法上,丁小天觉得父亲“是和社会脱节的人了,体会不到现代人和社会的关系”,简直是“不懂事”,“人老了,跟小孩一样,需要教育”[2]129。而父亲认为儿子待人不够热心,老是把人往坏里想,还没有责任心。在心理上,父亲在儿子成年后渴望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实现开照相馆的梦想,儿子想要的是更加独立的空间。可见,父子俩的分歧一方面来自于世界观的差异,另一方面来自于心理上父子双方既渴望独立又相互依恋的矛盾。在第二次找寻骗子的路上,父子俩经过多次误解后,儿子理解并成就了父亲的理想,不仅找到了骗子,还成为父亲照相馆的第一个顾客,经过父亲的积极沟通,儿子与女友恢复了恋爱关系。
小说对父子之间的理解和亲情来自于作者对生活的体察和感悟,孙睿在大学毕业后,待业期间与父亲有了更多的相处时间,也正是那个时候产生了最初的创作亲情小说的冲动,他说:“随着年龄的增长,觉得两代男人之间也有很多温情可以写,也可以说后来真的开始懂得父母了” [3],“有一天当我不再叛逆,发现父亲两鬓斑白时,我突然意识到父亲已然老去,这才感到父子亲情的存在”[4]。当众多“80后”青春写手还在抒写青春的叛逆和迷茫的时候,孙睿理解了生活中痛苦和爱的关系,他说:“最近我发现,大师级的艺术家,虽然也有痛苦,但是他们更懂得爱。” [5]于是他把笔转到对亲情的表达,文学评论界对孙睿这样的转型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好评,并将其看成“80后”思维的回归,人性的回归,温情的回归。
二、 语言风格:幽默、轻松
《路上父子》以现实主义的精确笔法,记叙了父子两代人的两次上路,也是精神的回家——离家——回家的过程,写出了一代人成长之后的思考和担当。作者也因为对题材的开拓和主题的反思赢得了赞誉,但该小说并不是凝重、厚实的作品,它仍保持着作者一贯的轻松、幽默风格。
小说《路上父子》中幽默的语言有多种意味,有的含有智慧和机警,有的表达揶揄和嘲讽,有的透着洒脱和豁达,读来让人回味不尽。如丁大民没有告诉孩子妈妈去世了,而是给孩子编织了善意的谎言,告诉孩子他妈妈出差了,去趟火星,这样的幽默里透着智慧,让人能在会心一笑中感觉到长久的酸楚。再如,描写丁小天与女朋友吵架是“妙语连珠,酣畅淋漓,直指人性,把多日积蓄的不满都发泄出来了,两人都痛快了,但也没把对方征服,平局”[2]86,这样的描写调侃和揶揄中又不乏机警。
有了幽默,苦难就会减轻甚至升华,以局外人的眼光打量苦难,苦难就缩小了。如丁大民在等妻子骨灰盒的时候听到其他失去亲人的家属的哭声,“他突然想起来,刚才自己应该悲伤点才对,但是他确实哭不出来” [2]1,乍一看让人误以为丁大民是个无情无义之徒,可后来他因为想到妻子爱吃韭菜馅饺子他以前不让包,哭得收不住,这样,作者就轻松地刻画了丁大民有情有义又不伪装自己的个性特点,也可以看出小说对感情的表达很节制,不夸大、不滥情,从反面衬托出感情的真实和深沉。
幽默是孙睿自觉的创作追求,特别从2006年开始,孙睿的创作进入多元化阶段,除了纯文学写作,他还拍摄《草样年华》系列情景喜剧,创作漫画图书绘本《倒霉催的猫》,主编幽默杂志《逗》等,转型后他在自觉地挖掘语言的幽默元素,并用以实现他所提出的“三上书”(即最适合在车上、床上、马桶上看的书)的休闲价值,因此即便是《路上父子》这样相对正统的亲情小说,作者也是以轻松而幽默的笔调行文。
有人说孙睿的语言在模仿王朔,对此,孙睿并不介意,他坦言王朔对他的影响很大,大大解放了他的语言,他说:“王朔的书应该是我主动看的第一本课外书。当时我应该是初三或高一,之前看的文字基本就是语文课文和报纸上的新闻,看了王朔的小说后我很兴奋,跟听相声似的,原来小说还可以这么写,一切道貌岸然都成了嘲讽的对象。可以说王朔解放了我的语言。”[6]图书策划人沈浩波评价他:有着王朔式的幽默,却没有王朔的油滑;有着王小波式的睿智,却没有王小波的炫耀;有着石康式的浑不吝,却不像石康那样一味地颓靡。这些评论能抓住孙睿作品的主要特点,但有些美化。
孙睿的幽默有时也因为调侃过了尺度,未免有些油滑,比如副厂长在丁大民刚刚安葬完妻子后让他以后有困难就跟厂里说,丁大民却说“厂里有困难也尽管跟我说”,这样的话与当时丁大民的心境很不相符。也有的是有意识地设置笑点,如在第二次的路上,父亲弄清了路上撞狗的肇事者并不是自己的儿子,当地的村长因为赖钱不成还不死心问了一句,“咱们村子真只死了一条狗?”再如,丁小天在第一次无意中使用了成语得到夸奖后,接着在吃蛋糕时说了一句“真他妈香”,他以为四个字就是成语了,这句话其实对情节没有作用,只是丰富一下细节,多一个笑点而已。总之,这样行文固然轻松、好玩,但雕琢痕迹太重,有失自然,有时冲淡了小说的严肃性。
三、情节结构:紧凑、大团圆
《路上父子》的情节设置是有明显的谋篇布局的意识的,其针脚细密,注意细节的照应。父子两次上路,像跨越20年的两幕戏剧。第一次的路上,父亲一个人独自承受失去妻子的痛苦,一路上还想出各种办法哄着儿子,让儿子感觉不到失去母亲的痛苦,儿子对父亲内心的痛苦浑然不觉,他无忧无虑地享受着温暖的父爱。第二次上路是20年后,这时候发生巨大变化的不仅仅是他们所生活的城市北京,父子的关系也变得生疏了。用两次上路安排情节,集中紧凑,形成总体的对照,在对比中发人深省。
不仅两次上路总体是对照的,在很多细节安排上,也常常前后呼应,产生对比的效果。如第一次路上父亲谎称自己因为开车撞死了一条狗,单位不让他再开车了。第二次路上儿子开车压了一个黑色的东西,父亲误以为是狗。两次都是误解,误解的消除就是父子相互理解的开端。再如,第一次上路,父亲开车捎了个中途汽车没油的司机,第二次儿子开车中途没油,父亲站在路边拦了好多次车,终于有司机愿意捎他到加油站。两次路上,类似的场景,相反的境遇,像是历史开的一个玩笑,绕了一个圆圈,考验着不同时代的世道人心,出现了因果报应、好人好报式的结局。不可否认,《路上父子》有些情节过于巧合,如丁小天去仿古董门店正巧就碰上骗子,给人感觉牵强、不真实。还有部分章节不太精炼,如第二部分写北京的变化占用的篇幅太多,影响情节快速推进。
小说总体情节框架是“圆满——冲突——和解”,结构简单,最后的结局是父亲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儿子也与女友重新牵手,达到大团圆。完满的结局固然无法产生悲剧的力量,但与整部小说轻松的基调相吻合。当然,这样的结尾方式还没有超越中国古典小说的套路。
四、结 语
《路上父子》是作者继2007年的《我是你儿子》之后又一部写作父子亲情的小说,作者在驾驭小说的布局和语言方面显得更加老到了。整部小说结构安排巧妙紧凑,语言轻松幽默,以父子俩不同时代两次上路为线索,写出时代的变迁、世道人心的变化以及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父子二人如何沟通和相互理解的问题。透过故事不难发现,小说的主题是亲情和理解,是两代人的成长,特别是儿子由自我中心到理解和宽容的飞越。当然,小说的思想深度还有待提高,在艺术上有待新的探索和完善,期待作者的新作有更大的突破。
[参考文献]
[1] 尹平平.“80 后作家”孙睿:该把“标签”撕掉了[N] .新华每日电讯,2012-06-29 .
[2] 孙睿.路上父子[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3] 赵玮晶.孙睿“王朔系”的高材生[N].中国青年报,2007-08-09.
[4] 卜昌伟.孙睿写《我是你儿子》回应王朔《我是你爸爸》[N].京华时报,2007-08-08.
[5] 麦坚.孙睿:告别《草样年华》之后[J].新作文(高中版),2011(04).
[6] 赵丽肖.孙睿:《我是你儿子》[N].河北青年报,2007-08-10.
[作者简介]
尹傳芳(1971— ),女,江苏淮安人,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讲师,文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