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我的电影是从真实生活当中去找
2013-04-29木雕
木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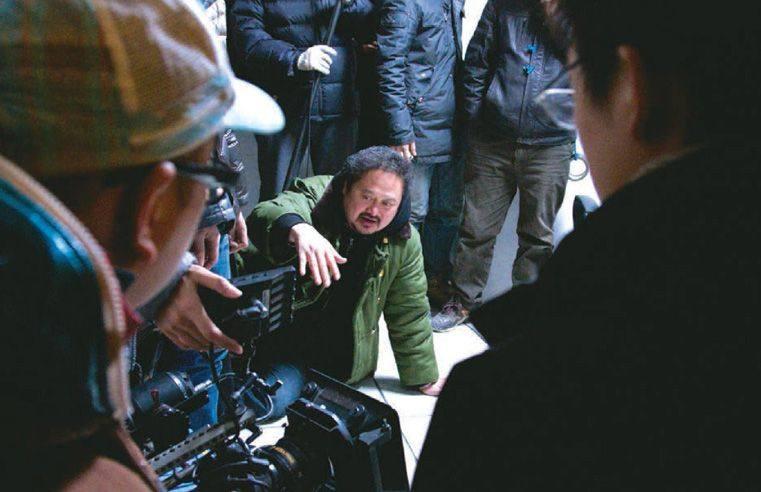


这个构思真正起源于九三年我自己的一部影片——《北京杂种》。电影是用纪录和剧情结合的方式完成的。当时我大学毕业不久,生活在这古老的皇城,北京当时的气氛是有一股按捺不住的躁动,生活节奏在不断的加快。在影片中有躁动摇滚乐,和肆无忌惮的谩骂,结构了那部影片。当时我在这个城市中看到了年轻人肆意宣泄的力量,歌手崔健和窦唯,何勇的音乐,架构一些模糊不清的故事线索。《北京杂种》已经近20年,那一代人已经年华已去,那么新一代年轻人他们在做什么呢?在这个巨大的城市中,那些八十年代出生的人,他们又是以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去生活呢?我充满了好奇…
这一次我使用了这个方法,在网络的微博上发了一个报名启示。我和我的工作团队用三天时间面对两百多个八十年代出生的年轻人,进行了访谈。所有的来访者的故事都让我们惊喜,他们都是完全不同经历的,但是都希望在北京实现他们的梦想。虽然都是年轻人,但他们的经历比想象的坎坷得多。这些人都是来自祖国各地,也有从国外来的。在北京他们艰难的谋生,每一个坐在摄影机前面的那个人都是按耐不住的去表述他们的生活,畅想他们的未来…经常使我们忍俊不禁,也经常使我们泪流满面。他们有摇滚乐手,艺术家,演员,股票操盘手,保镖,社会工作者,大学生,无业者…面对这些人物,这些动人的故事,我们最后的选择是艰难的。
电影中国:您是中国第六代导演里的先锋人物,拍过纪录片,做过音乐录影带,是什么样的机缘?
张元:小的时候,我的梦想是要做个画家。上小学的时候,由于身体不好,经常没有办法上学,所以总是待在家里没事儿做。周围邻居中有个画家,所以我开始对绘画感兴趣。后来上了电影学院,开始接触电影的影像,然后又学习摄影,这样一个经历,加上后来又对文学感兴趣??刚才提到音乐录影带,在我上电影学院的时候,整个中国可能还没有音乐录影带的概念,也没有纪录片的概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没有纪录片,只有“新闻简报”,就是很短的新闻,如毛主席接见了谁,或者诸如此类的。有段时间,国内有个很大的批判运动,就是批判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中国》。纪录片和音乐录影带,在某些方面从精神上看是与社会主流价值对立的??但只要牵涉到影像,我自己就很感兴趣;只要有新鲜的东西,我就愿意去实践它。
电影中国:您拍的大部分音乐录影带的题材都是关于青年文化?
张元:我拍音乐录影带最初是因为崔健。崔健那时刚刚创作并演出了《一无所有》,一时间在中国成了一个文化英雄。那时候我刚刚拍完自己的第一部电影《妈妈》,有次偶然碰到他,他提出能不能一起来做一个音乐录影带。当时,我们都没看过所谓的音乐录影带,也不知道什么叫音乐录影带,就一起看了些英国和美国的作品,然后实验性地拍完了我的第一个音乐录影带——《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那是1989年,我刚从电影学院毕业,我们完全把它当做一个大制作的电影在拍,当时用到了飞机头、鼓风机,用了非常多的泡沫去制造雪。所以那首歌带拍完后很多人喜欢,也是亚洲的歌手第一次得到美国的MTV最佳录影带奖。所以我从那时候开始对自己的视觉表达能力有了些信心,后来就一起开始构思《北京杂种》。
电影中国:您所有作品有一个共通点,就是边缘化的个体。为什么您对边缘的个人和群体有这样的兴趣?
张元:我没有特别去考虑要有怎样的兴趣,可是印象中我拍第一部电影《妈妈》的时候,就觉得拍电影、做艺术应该有一个针对性。那时候,国内已经出现了我们电影学院的毕业生,如陈凯歌、张艺谋,他们已经拍出了《黄土地》、《一个和八个》、《红高粱》等,这类的片子都已经拍出来了。这些东西虽然对我有一些影响,也让我有所震动,但我总觉得他们用的东西和视角都太高了,把文化的含义提得太重了。我在电影学院的时候已经开始对《妈妈》这个题材感兴趣。开始是被两个电影制片厂选中做摄影师,拍摄《妈妈》的前身,叫《太阳树》。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两个制片厂都没能拍成这个电影,可是我已经花了很长时间,作了很多对弱智孩子的母亲的采访,并开始对这个题材特别感兴趣,后来就自己筹集了钱拍了我的第一部电影。拍摄第一部电影也让我找到了一个观察人的角度,我觉得这个角度特别地适合我,而且后来拍《北京杂种》和《儿子》等很多题材时,好像都是这些边缘化的题材自己找到了我,很多边缘化的人自己找到了我,比如护士找到了我。
电影中国:您觉得这些边缘人与中国固定的思维模式难以交融?他们如何融入现代中国社会?
张元:当然,在创作影片的过程当中遇到过很多问题,因为像《北京杂种》、《儿子》,或者《东宫西宫》这种题材,当时没有办法在国内公开上映,但今天像同性恋或者摇滚乐的话题,大家已经可以摆在桌面上去谈了。可是那个时候我就已经觉得这种题材的电影也是应该拍的,因为它提供了一个新的可能性或者角度,而且也真的很值得我们先去把它们拍出来。
电影中国:您觉得中国经济的急速发展怎样影响到那些边缘人物?
张元:这也是我自己一直在想的,实际上我自己也很好奇那些驱动我的东西。急速的发展催生了很多种生存的可能性,有多种方法都可以生存下来,而且这些生存的人本身就会影响这个社会。现在即使不在大的机构里,不在国企当中,还有很多所谓边缘人能够生存,有些虽然非常艰难,但也可以充满理想地活下去。
电影中国:您的代表作《北京杂种》反映的是20世纪90年代初的北京摇滚圈,您对中国先锋文化的看法是怎样的?
张元:是否先锋并不是由我们自己来定义的。我只是觉得有意思,感受到了不同于以往的音乐,不同于以往的绘画,或是不同于以往的表达方式,讲话方式。《北京杂种》的拍摄是非常即兴的,没有剧本,拍摄对象都是我周围认识的朋友,第一天拍摄的时候可能不知道第二天要拍什么??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的氛围下,我捕捉到了当时一些真实的气味。今天回顾这个电影,如果说有什么优点的话,那就是它似乎闻到了当时一些胡同里、画室里,那些演出场合里的味道,我觉得这点我是捕捉到了。我们那时都是二十多岁,回头来看恍如隔世,今天又出现了很多摇滚音乐家,很多新的艺术家,但当时我们先锋与否,并不是由我们自己来决定的。
电影中国:“北京”和“杂种”是语势强烈的词吗?怎么想出这个标题的?
张元:当然,我觉得“北京”和“杂种”是两个连在一起很有劲儿的名字,实际上也是希望通过这个名字去寻找真实的北京气味。任何一个东西都需要有个入手点,当时我的入手点就是从周围朋友的真实生活当中去找。
电影中国:《妈妈》这部电影和第五代导演的作品是有所区别的。先锋不是您的诉求,那是什么促使您做出和第五代导演不同的风格?
张元:我曾经提到希望能把我的摄影机的角度放得低一点,能进入到人真实的生活里边,能真正面对人,而不是简单的大的文化概念。《妈妈》那部电影我觉得就实现了这一点。我采用一个残疾孩子的母亲的观察视角,以母亲与残疾孩子间的关系和他们生活的本质作为最主要的故事线索,抛弃所谓的大的文化概念,也不用所谓五千年的文化来压制自己,电影讲述的是我们个人的生活困境和所面临的问题,包括人性面临的问题,生存状态,从这个角度讲,我已经和第五代导演有绝对的区别了。有时候我觉得作为创作者不需要强调所谓大的文化概念,因为它本身是在我们身体里面的,只要你的摄影机摆对了,只要你真正能够深入到人的生活里面,你也可以创作出有意思的电影。
电影中国:《东宫西宫》和《回家过年》是否延续了您对边缘人物的关注?
张元:边缘人物都是生活在我们社会当中的人,而且我从来没觉得谁在尊严上比谁低一点,不管是在监狱里的人,或者性取向不同的人,我觉得都应该生活得有尊严。没有不可以做主角的人。
电影中国:这些电影怎样解决社会问题?
张元:要说电影能解决什么问题??电影的力量是很小的,它只能给大家提供建议或想法,提供一个可能性。电影可能实现人的尊严,但在社会中,一个艺术家到底能有多大力量?导演或艺术家没有多大力量的。
电影中国:您觉得您的电影在社会当中扮演什么样的文化角色?
张元:电影在人类历史上才出现一百年,中国电影自1949年后(至今)都还是延续苏联的一套;斯大林和列宁说电影是暴动,电影是革命,所以中国电影一直被管理得非常严格。在我们拍《妈妈》和《北京杂种》之前,中国只有十六家电影制片厂可以拍电影。你可以想像一个导演拍电影的困难:所有题材都要经过电影局批准才可以拍。但从《妈妈》和《北京杂种》这样的电影之后,很多导演,像王小帅和贾樟柯,都开始拍摄类似题材的电影了,从这点上讲,我们开创了一种拍电影的新的可能性。今天回想起来,我们真是做了件非常有意思的事,就是用摄影机像画家或作家一样表达自己,从这个角度上讲,电影(创作者)在中国也可以作为一个作者出现了。
电影中国:所以您以前拍电影曾经不写剧本不画分镜头,也是为了保持更多的自由度?
张元:可以说是。但也有很多电影,像《东宫西宫》,我不仅写剧本,而且画了很多分镜头。每个电影创作方法不一样,最重要的是让大家知道用这种方式我们也能够拍电影。像《妈妈》这个电影我是在自己家里拍的,我们自己住的房子,当时用摄影机,不用很多场景,不花很多钱,但是拍出了自己想要的一部电影。
电影中国:新一代人和您这一代人的关系如何?
张元:我自己认为年轻人永远是对的。只要想到是比我年轻的人,我就觉得他们的想法就都是对的。你要说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年轻。年轻人很美,我们这一代人实际上都老了。
电影中国:《有种》和《北京杂种》的不同点在哪?
张元:肯定会是完全不同的。中国一下变了多少年了,1992年到现在有十八年了,肯定会是完全不同,完全变了。新的一代人,新的时代气氛,新的感觉,每个人都是不同的生存状态,这些是完全不一样的。
电影中国:您对中国社会和文化从过去到现在的改变是怎么看的?
张元:最大的东西没有变,就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到底是生活在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还是封建主义下——这个大的问题到今天我也不知道答案;我们到底身处怎样一个真正的所谓明确的社会环境当中,我知道现在找不到答案。
电影中国:您认为新一代人在社会环境中是迷失的?
张元:是的。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自己本身是很迷茫的,也真想通过这个电影,通过这些图片,去看一看那些年轻人是怎么认识这个社会的。
电影中国:您对中国电影的现状怎么看?
张元:近些年中国的电影市场越来越好,电影院越来越多,也因为好莱坞电影在中国的影响,现在票房也很好,国产的大电影也越来越多。但是实际上,真正作者化的电影可能也越来越少,是的,越来越少。
电影中国:同辈和年轻一辈的电影人,哪种令您感觉更近?
张元:最初我们同届的像娄烨啊,王小帅啊,包括比我们稍微晚一点的,像贾樟柯啊,我觉得他们都还在坚持做自己的电影。年轻一代的,前段时间我在南京参加一个电影展,发现实际上年轻影人很多都在拍,每一年能有十几部新作,很多年轻人都在拍。
电影中国:中国当代艺术家里有很多是您的朋友,哪些是您感觉上较接近的?
张元:我的这些艺术家的朋友,大家年龄差不多,像刘小东、方力钧、岳敏君等,我们可以说是一起成长的,刘小东我们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就在一起了。这些艺术家,我觉得他们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