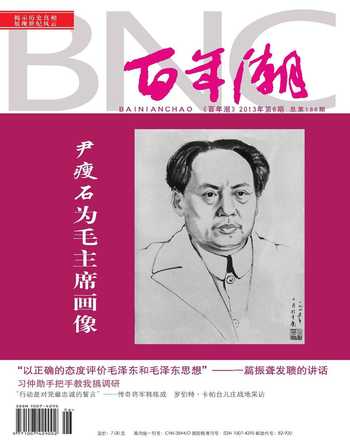革命年代情书一瞥
2013-04-29桑一伟

人物简介
龚子荣,原名龚允济,1914年5月生,福建福州人。1934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8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央国家机关委员会第一书记。1995年逝世。
1937年7月7日,我正好到北平投考北京大学,亲耳听到日军点燃的侵华炮声,但并未意识到它会产生怎样的重大影响,仍然怀着读书救国的愿望,转赴武汉投考武汉大学(因形势紧张北大停止招生)。那时的武汉,抗日声浪逐日高涨,抗日救亡的各种活动不时出现在街头。由于武汉大学高考发榜久拖不决,令人无法等待下去。而报纸不断登载华北形势吃紧的消息,我挂念兵荒马乱中孤独无依的母亲,不顾三姐桑耘的劝告,毅然独自回山西与母亲共患难。
山西的政治空气与武汉不大相同,抗日活动搞得比较红火,晋西南更洋溢着一派抗日救国不愿做亡国奴的新鲜气象。老家山西省赵城县成立了牺牲救国同盟会,在那里汇集了一批青年人,他们那高涨的抗日救亡激情,大大感染了我,我不由自主地汇入到这股革命洪流中。这年10月,我参加了牺盟会,开始在赵城县城区做抗日宣传工作。1938年初,日军侵占同蒲铁路沿线,赵城失陷,我携母亲转移到赵城河西孔庄,这样与牺盟会暂时失掉了联系。
1938年春节过后,牺盟会的韩湘琳同志与我取得联系,邀我共同组织赵城妇女儿童工作团,开展赵城妇女工作,并说是县委的指示。受此重任,我十分激动,毅然完全脱离家庭,投身到革命中去,并随即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踏上了革命道路,开始了漫长而曲折的革命生涯。就在此期间,我在赵城河西韩侯村初次见到了龚子荣。那时我并不了解革命队伍中的组织状况和干部职务高低,只知道龚子荣是党的主要负责人,常给大家讲革命道理和新鲜事情。乍一接触,他给我的印象是既严肃又活泼,不像有些干部那样简单生硬,在我的心中留下了可敬可爱的形象。后来,我在工作中不断听到其他同志对他的评价,这使我对他的模糊印象逐渐清晰起来。大家说,子荣很有水平,遇事有办法,工作劲头大,没有私心杂念,他成了赵城县名人。记得有一次,他传达北方局宋家庄会议精神,充满激情地讲了许多革命道理,极大地鼓舞了与会同志,我也钦佩不已。
由于他很关心妇女工作,经常了解妇女儿童团的工作情况,我们之间便有了不少接触。子荣自然也在有意无意对我进行观察。在他的印象里,我是一个单纯无瑕的青年知识分子,热情忠实,有工作能力,更有着温柔文静的性格和不加修饰的女性美(那时有人指责女同志有女人气),认为是当时女同志中的佼佼者。在互相倾慕的情况下,1938年9月9日,我收到子荣给我的第一封情书。
桑同志:
恕我唐突,我觉得写这封信是必要的,而且正确。原因是这里许多敬爱的同志们,十分关切我的生活,计划给我介绍一个适当的伴侣以期能帮助我的进步与事业的成就。同时又直截了当将您介绍给我,当然这件事情基本上没有什么不对,我也完全同意,听说你也不反对,使我非常兴奋。但我觉得问题却不是简单的,因此需要将我对这件事的认识搬出来。一方面要在我们这件事情上找出些根据来,同时,作为我们今后生活的方针;另一方面也可以拿这一套来教育许许多多青年男女们,他们正为着这件事情终日苦闷与恋爱中,您说是不是?
(一)我以为这件事固然是生活问题,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我要求您必须要郑重地考虑。好同志,老实说,我个人能力本领仅是有限的一点,这不是虚伪,同时也不必夸张,我觉得比我能力本领更大的还有千千万万在,比我能力本事小的也同样有千千万万在,你要在这复杂的人群中不要着急,郑重地选择,正确地瞄准。同志,一时不慎会造成终身的遗恨。但我却始终相信我的志愿是远大的,我可以保证共产主义的事业是我唯一的依靠者,因此我的一切已经完全献给“革命”及“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我不断地要求进步,同时也因为如此我的生活经常是极端穷困与恶化,流动与漂泊的。但我觉得精神上是非常快慰的,我认定这是人生的意义。这里一定有人问:难道愿意终身遭受这样境遇吗?我的回答是否定的,我同样也要争取我自己的利益,憧憬着将来光明的前途。但我却十二万分厌恶那些势利眼,投机取巧,他们会暂时受眼前痛苦,希望将来“做官”、“发财”过痛快生活,我始终要站在大众利益上,拿我的头和血争取自由幸福的新社会。这样的办法我已经数年尝试,直到今天,我还坚定认为是对的,而且现在还继续着,相信将来还是这样办法。
(二)我不仅是极端厌恶所谓的“一杯水主义”,我简直视为那是一种流氓行为,我们这里暂且不谈它。然而即使一些青年男女纯粹感情冲动,高兴就随便乱拉,不顾一切什么都可以牺牲;不高兴就一脚踢掉,于是失恋、消极悲观,我以为这是十分无聊的,实质还是“一杯水主义”。在另一方面,我特别提出一些青年男女随便和有夫之妇、有妇之夫胡搞,尤其我们自己的同志,这是万万不应该的。这种行为简直是欠缺政治人格,我们应该坚决反对。我们的根据是:人是社会的人,是感情的动物,一切的事情应该是科学的了解。两性的结合是人人都需要,恋爱本身是没有错误,同样失恋也必然会痛苦。问题的关键在,我们青年,尤其共产党员必须将自己伟大的事业与工作放在第一位,亦即使其成为生活的轴心,一切事情都是围绕着这一轴心,服从这一轴心,丝毫妨碍这一轴心的事情,那宁可牺牲不做。列宁说:“无产阶级并不是没有感情,他们的感情是全部用在革命事业上。”最后我们要坚决执行列宁的“一夫一妻制”。我们认识上述一切即是列宁一夫一妻制科学的根据之一。
(三)根据以上,我们还要共同认识如下几点:今天我们都是在抗战的前方,游击战争中的环境,这一环境是要加倍力量奋斗,同时我们要在救亡战线上也负有相当责任,我首先要以身作则;进一步说我们又是共产党员,尤其我们今天在肩上负有相当的责任,我们一切行动,哪怕是细小的行动,我们都应该站在一切人的面前,做一切人的模范,最低限度也得保持着领导的威信;今天在这里周围环境是不太好,当然会有许多幼稚青年们可能误会或嫉妒,这很容易影响工作,因此我主张:
我们创造一个模范的“爱情”,同时拿我们这一套的经验教训教育给许许多多的青年男女们。
我们现阶段只能做到订婚程度,不能过快结婚。
在现阶段有保守秘密的必要。
不用任何方式欺骗家庭,对家庭我们应该用说服的办法,同时用我们事业上的表现。
同志,请你来一封信好吗?最后一个(要)求:你有什么,说什么,哪怕是细碎的事情我都爱听,万勿拘束。完了。
此致
布礼
龚子荣
一九三八年九月九日
子荣在信中,虽然不乏革命言词,但爱慕之情也跃然纸上。我情不自禁地无数次捧读,不敢相信世界上竟有一个人如此倾心于我,这令我浑身增添了一股无名的力量,按捺不住喜悦之情,感到生活有了新的意义。于是,革命的热情和爱情的火焰自然地融会在一起。那段时间我工作劲头特别大,我亲手组建的赵城妇女儿童工作团,成为一支活跃在赵城河西一带的抗日宣传队,当地群众亲切地称呼我为“团长”。我们到处唱抗日歌曲,自编自演救亡戏剧,唤起群众抗日救亡的热情,同时训练培养出一批骨干力量。由于妇女儿童团的工作很有成绩,受到各方面的赞扬。
在子荣给我的第一封信中,提出爱情要反对“一杯水主义”,这是当时青年们在恋爱过程中犯的通病。我在给子荣的复信、也是我的第一封情书中,也明确表示,要以慎重的态度对待爱情,只要“有了真正的爱,是绝对会坚持到老、到头的”。这成为我们爱情的基石。我们五十年如一日,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从未逾越这一原则,才有了五十年来美满幸福的家庭生活。
龚同志:
来信收到了。
正如你所说的蒙各位知交同志的关心,而提到这里,我们当然是十分感激。但是这件事的确不能随便忽视的,它会一失足成千古恨,也会因而造成人生欢乐的源泉。我自己虽无经历过,听到看到的很多了,使我们不能不加以十二万分的注意。我相信你是更会注意的。现在我将对此事的始终意见叙述如下:
(一)问题的注意,我本身不反对恋爱,但我总感到“恋爱”是有几分痛苦的。其实爱情本身是正确的,无痛苦的,但跳到爱情网中的都感到是苦的。所以我不愿开始这段。自己也认定这是不对,但总是如此坚持着。这次我出来,我感到工作是很有意义的,我下决心要全部精力放在工作上。但是相反地,周围环境,偏要逼使我产生了无谓的苦闷和烦恼,不能不影响到工作。什么……什么,这位,那位,连我都莫名其妙,提醒我不能不再注意了,不成问题却成为严重的问题,所以才开始考虑这个问题。
(二)既然开始了,我料想到万一使人知道会批评我们的,尤其对女性方面会给予严重的批评,甚至轻视你,在工作上会受到别人的不信任,再一点是路线把握不适当更会造成别人的口实,在此新旧社会中是难到十二分了。一般所见到的是一对一对的情人,他们所用的方式是不够的,是使人不满意的,更讨厌的是在字里行间和谈话中表露爱情……这些是太费精力。所以我感到要取消这些做法,要干脆的、坦白的、纯洁的、始终的“爱情”,要坚决地把握住它的路线,不受任何人的批评,正如你所说的“模范爱情”。
(三)使我兴奋的是我已经有了有意义的人生,有了我一生努力的中心轴。我相信这是一条光明大道,我决心要为“共产主义”努力奋斗,更要贯彻始终。更使我兴奋的是得到了一个能够教育我、指导我的你,我承认你不是完美的、无比的。但我总知道至少是比我强的,正好作为我的老师。所以我相信我今后的进步是会快的,有了努力路线的指示。只要有了“大我”的幸福、自由解放“小我”一定不成问题,假使把“小我”放在目前,那就是太幼稚,无意义了,我们要为新社会努力到底,任凭他中途的流浪遭遇。
(四)我对此问题是有了一番考虑的,我认定是这样的。须有思想认识的正确,即会决定一半的人格;人格正直、行动正确,生活中无任何不清的问题,如你所说的有妇之夫、有夫之妇的欺骗手段,对恋爱有正确的了解。为了一时的冲动和要求,那简直是更卑鄙到了极点,年龄的相当,这是生理上的讲求。双方能如此了解这些条件是会满意的。有了真正的“爱”,是绝对会坚持到老的,到头的。
(五)目前一个困难的问题,使我十分痛苦。是妈妈在反对着这件事。反对的理由是很好笑的,是因为她老人家痛爱自己的女儿造成的。她认为这样一来,女儿再不属于她的了。一切的一切都是属于别的人了,她是十二万分的舍不得,在极度的痛苦之中。不管我怎样地解释都不成,还坚持着不让我再走出去工作了,这点倒着实吓了我一跳。费了很大劲最后才同意我出来工作。因此,我想对这件事暂时瞒过一段时间,再向妈妈说服。所以我要求你要竭力保守秘密,不然我会遇到很大的危险。我现在为这点是痛苦的,我正处于初尝到爱情中的痛苦和矛盾。我不愿看着妈妈痛苦的面貌,她老人家在内心的痛苦中更加倍地爱着我,这加倍地使我痛苦。这种滋味真难忍受!
本来我有许多话要写出来,由于内心的烦恼什么都写不出来了。我希望你替我想个办法。我还希望你暂时地离开这里。我呢,我要克服这些不痛快的事,仍旧努力工作。最后我要求你,把我应该知道的党的一切都告诉我。我实在不满意现在的认识和知识。我希望能把我的工作做得更好更出色。请来信。我盼望你的来信。
致
敬礼
桑一伟
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三日于孔庄
往事如潮,我好像又回到初恋的时光,那金子般的岁月,有多少美好甜蜜的回忆。1938年6月初,子荣调往洪赵特委任特委书记。特委机关在距赵城百余里的汾西县勍香镇附近。直到那年冬天,我才有机会到牺盟会中心区开会,顺便去看望子荣。尽管已通过数封热情而亲昵的信,可见面后,在严寒冬夜的昏暗灯光下,两人相对面谈,却生疏得手足无措。我看到子荣身上穿的是件空心棉袄,便将自己贴身毛背心脱给他穿。他穿上后说:“你的暖流已流向我的心窝。”直到1941年我们再见面时,毛背心上长满虱子,我不得不拆了打成了草鞋。这件珍贵的毛背心,可算是我们的定情信物了。

1939年春,子荣有任务到赵城罗云村。他从汾西县勍香镇一天奔跑百余里,傍晚就到了赵城罗云村。正当通讯员纳闷,首长何时成了飞毛腿时,见到我时,才解开这个谜。最值得回忆的是在汾西县回朱里村的那次会见。千言万语的彻夜长谈,无拘无束地谈啊,说啊,甚至谈到结婚和未来的家庭。面对老乡窑洞墙上贴的“连生贵子”的年画,子荣说他也要一个“五子登科的家”。这在50岁后果然应验了。
我们的结合是纯洁高尚的,没有任何附加条件和其他考虑,相互间充满真挚、深情的爱。所以,当我告诉母亲我的选择时,尽管老人家极力反对和挑剔,说子荣没有学问,不像大姐夫那样是国民党的大官,二姐夫那样是高级知识分子,三姐夫那样是研究生,既没有学识,又没有家业,又是个流浪汉、八路军的穷鬼,我还是于1939年春调往洪赵特委妇委会工作,在“五一”节的前一天与子荣结了婚。婚礼是那么朴实简单,机关的同志吃了一碗炒黄豆以示庆贺。我的嫁妆更是无产者的典型:一条线毯和一床被子,还有好心的邻居老太太送来的一条褥子。婚后几天,子荣就奉命调往晋西南区党委任民运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