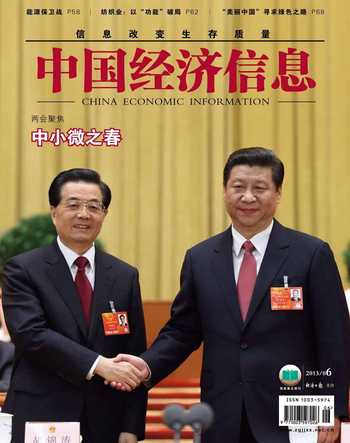悲惨世界
2013-04-29吴春晖
吴春晖
谁也别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判断谁,如果你没跌落到那样的窘境中。
看《悲惨世界》,问题萦绕脑际:尼采的那句“上帝死了”到底该不该相信?失去神的看守,人性还能葆有多少良善?没有永恒做背景,人能否当好自己的评价者?
就像冉·阿让,19年的苦役并没有改变什么,开始是偷一块儿面包,后来是偷收留他过夜的主教的银器。但他就是恶的代名词吗,在皈依上帝之前?不。他是为了一个挨饿的孩子去偷面包,这行为本身就掺着善的成分;19年之后他偷了主教家的银器,亦是为了最低程度的生存要求,因为揣着一张终生假释证明没人愿意给他一份工作,没有工作依然没有面包,这次,是为自己。在悲惨的世界里,他只是一个被严酷的生活推着走的普通人。谁也别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判断谁,如果你没跌落到那样的窘境中。
人性有无尽可能,在生存线上挣扎着的人,最易露出丑恶的部分,冉·阿让便是如此。但人,还有没有救?指望尼采的“超人”哲学吗?世上心灵的强者本就不多,芸芸众生,并不都懂得为自己的生活探索出一种意义,无论是19世纪的法国,还是21世纪的中国。
上帝托主教给冉·阿让指了一条道儿,一条布满爱愿、充满意义的道儿,告诉这个习惯于仇恨的人:你也有灵魂。像奥古斯汀抱着一棵树痛哭流涕终于皈依了上帝一样,冉·阿让也涕泪交加地在某一个必须如此的时刻皈依了神。他看见上帝了吗?没有,他只是感觉到了。
可“眼见为实”啊?是的,在物质事实的领域这一标准也许适用,但在精神价值领域务的不是实,而是虚。周国平说得好,“理想,信仰,真理,爱,善,这些精神价值永远不会以一种看得见的形态存在,它们实现的场所只能是人的内心世界。”不要因为看见神迹而相信上帝,也不要因为不见神迹而否定上帝存在,上帝的显现与否不应成为你信与不信的理由,耶稣说啦:“没有看见而信的人有福了。”
冉·阿让“有福了”,从此走上了救赎之路,撕毁那张黄纸,重新做人。只是一个人的历史不是改个名字就能重写的,8年后,他与对手遭逢,那个一直在寻找他的恪尽职守的警官沙威。
雨果笔下的这个表情严肃的沙威代表了什么?是规则的捍卫者吧,可这规则是人定的。沙威就是《圣经》中的法利赛人,脑袋里装的都是律法,与爱无涉。他在监狱中长大,满眼所见都是别人的罪,从不怀疑自己的正确,坚信将冉·阿让绳之以法是正义之举。可上帝不喜欢一贯正确的人,因为在这个充满原罪的世界里,所谓一贯正确不过是自以为是与狂妄罢了。耶稣是痛恨狂妄之徒的:“不要评断人,上帝就不评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上帝就不定你们的罪。”
这个自以为是的人还是价值崩溃了,当本可置他于死地的冉·阿让放了他一条生路,他不习惯这种方式,他习惯的是“以暴制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三观”被毁的沙威选择了自杀,望着那个坠落河中的影子,我在心里唏嘘了一声。在价值困境中,他选择了带着怀疑的逃离,或者说是雨果为他做的选择。世界于他,亦是悲惨的。我很想问问雨果,上帝为什么不救他呢?站在河边的那一刻,他也是只迷途的羔羊。
沙威是还没有学会爱的人,至死也只是价值观松动而已。冉·阿让也曾无爱,不公正的生活教给他什么是仇恨。可仇恨只能复制仇恨,“以眼还眼”只能得到“以牙还牙”的回敬。直到主教以爱的名义代上帝为他赎回灵魂,直到幼小的柯赛特充满信任的躺在他怀中,他才感受到什么是爱,无条件的爱,从此活在神的光照中。
你信也好,不信也好,上帝不在一个地方,上帝不是一处实存,他在另一维时空中观看着芸芸众生,他在人的忏悔里显现。
木心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给一批中国艺术家讲课时说:“雨果是公共建筑,走过,看过,不停下来。他不是我的精神血统。”愚顽如我辈,还是要停下来,走进去,一看究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