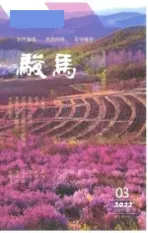草木味道
2013-04-29刘学刚
刘学刚
作品散见于《山花》《雨花》《芒种》《散文》《鸭绿江》《百花洲》《散文百家》《散文选刊》《特区文学》《山东文学》《四川文学》等刊,有散文、小说多次入选全国年度文学选本。现居山东安丘。
苘麻的进化
在洪沟河南岸,曾经有那么一大片地方,我们叫它苘麻地。腾出一块敞亮的地方,让一种野草安家落户繁衍生息,这实在是发生在洪沟河南岸的一个重大事件。至于许多年以后的冬暖式大棚栽培荠菜,那可就是穿新鞋走老路了,一棵棵青春菜水灵灵地出现在城市的餐厅和下水道,绿茎嫩叶上闪烁着的,是露珠一般的钻石。
既然是野草,就有哪里都想闯荡一番的野性。苘麻喜生水边,旱地里有,房前屋后也能发现它们的行踪。只要有落脚的地方,哪怕是一粒极小的土屑,它也挺着身子,长出心形的叶子,把大地都长绿了;开着金黄的花朵,把太阳都开亮了。苘麻地,地瓜在这里做过梦,高粱在这里晒了米,墒好,光照足,苘麻的个子猛蹿,一蹿三四米,都高过洪沟河南岸的果树们了。
果树们自然住在果园里,果园四围是花椒葛针长成的篱笆,篱笆爬满了刺,刺得人眼睛生疼,热热乎乎的疼,恨不得生出一对翅膀,飞过去,飞到白里透粉的花蕊中,落在青里藏红的苹果上。真的,做一只飞进飞出的蚂蚱,都比我们潇洒得多。有时,我们站在苘麻地里,望着果园,发呆,眼睛里伸出一千只手,也摘不到天界的一颗奇珍异果。看着果园的工人们从绿云里飘出,想,他们要是苹果哪怕是毛桃,多好,离眼睛越来越近,黑眼珠里一个变俩,让眼睛尝出一些甜味来。果园的木栅门却常年板着脸,把果园搞得神秘兮兮的,就像一个深宅大院。事实上,果园已经单独划出去了,一个袖珍的“经济开发区”,隶属乡镇直接管理。它周边的小麦地、玉米地、棉花地、苘麻地依旧是小村的口粮地或者经济田。心思好比茂盛的野草,一旦分枝发杈,就会长出一些新鲜的叶子温润的呼吸。在洪沟河南岸,有这么一个果园真好,大地的黄土盘里常年供奉着甜水梨红富士,求一个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呢!
苘麻地在洪沟河南岸的位置非同凡响。蜜蜂吻了苹果花的芳唇,成群结队,向着苘麻们飞来,自西而东,也指引着洪沟河流水的目光,使得流水所到之处,香气涌动,逗引着地下的泉眼,咕嘟嘟冒出来,就是一些绿绿的茎株。一行行的苘麻直挺挺地站立着,站在村庄和风调雨顺之间,站在果香和五谷丰登之间,一个盛大而隆重的田野入场式。
说说春天的苘麻吧。有两瓣草芽拱出来,嫩嫩的,泛着淡绿的亮光,仿佛暖煦煦的春风一吹,热乎乎的阳光一照,大地的眼窝子一下子浅了,涌出两颗晶莹的泪滴。这样的泪滴看上去娇嫩柔弱,它的作用可大啦,嫩叶嫩枝哪一个不在它的摇篮里度过自己的幼年?叶子大了,茎枝也直了,像泪滴一样的托叶就悄悄地脱落,苘麻的茎枝和叶子开始了一场竞赛似的生长。茎枝喀吧喀吧往上长,好比一群乡间孩童在阳光里玩一种“跳跳长长”的游戏,跳一个高,长一大截。叶子一声不吭,随着茎枝向上攀升,仔细看,叶子们是在攀云梯,不纠缠,不粘着,一个茎节就是一个新的高度,如此,交互攀升,不遗余力;同时,叶柄擎着叶子,横向扩散,一根根叶脉犹如伞骨,打开一枚饱满的团叶,硕大如桐叶,形态似桃状,仿佛心形的基部弯出两道好看的水流,遥相呼应地漫向叶子两边,无论相距多远,都保持着和谐的对称,优美的弧度,正是这种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大默契,两道水流又不约而同地绕着弯,彼此靠近着,在叶子的先端揉成一个柔和的心尖,蓝天的私语、空气的激情、幸福的颤抖和即时的快乐全都搁在这心尖上。
茎枝独立,单叶肥硕,如此生长繁殖,要是长成高大粗壮的梧桐树,那可是大自然最大的败笔。大自然不会在不同的物种之间制造混乱的血缘关系。它总是在不断地摸索、尝试,让每一种植物都与众不同,都有丰富的智慧和优秀的特质。
夏日繁华富丽。苦菜花是很结实的花朵,一开上百朵,平地起黄云;苹果们郑重自持,掩隐在绿荫里,默默酿造内心的蜜。在探出第五片也许是第六片叶子之后,苘麻突然有了一个新奇的想法,它想改变茎叶各自生长的单一局面,凝神聚力,共同关注整个苘麻家族的未来。这是一次勇敢的思想冲动,很多伟大的创举就源于最初的那么一次内心的美妙冲动。这冲动使得茎和叶的相接处冒出一根类似于叶柄的花梗,约莫两厘米长,挑起一个绿色的花萼,有金丝一般细小的花蕊从萼的绿里凸鼓出来,过了一些日子,金丝铺成了丝绸,黄灿灿的,是苘麻全心全意的笑容,绿的杯状的花萼上密生的软毛,被花的金芒辉映着,仿若少女脸颊上好看的绒毛。苘麻最初的黄花谢了,其上的花蕊正青春,最上的叶腋刚刚冒出一个绿绿的苞蕾。一株苘麻,自下而上,呈现的是一个家族前赴后继的探索和努力,是对伟大愿景的不懈追求。黄花一谢,苘麻结果了,嫩青嫩青的,果实顶端的长芒有一种突兀的性感,犹如美女妆饰的长长的睫毛,一根睫毛顾盼流连着一瓣果实,细端详,果实一瓣一瓣的,心手相牵,结构成一个稳固的半磨形的家园,每一瓣里都住着一些白白的米粒儿大的苘麻子。我们知道,一种植物往往有许多洋溢着爱意的名字,这些名字是朝霞和日月之光铸就的徽章,是所有的赞美之中最崇高最真诚的赞美。苘麻开了花结了果,人们的赞美也纷沓而至。“金盘银盏”,超豪华的器皿,盛着蓝天和白云吧。“野芝麻”,香得鲜,也香得野,它的周边一定长着许多想尝鲜的小嘴巴。“八角乌”,是成熟的果实吧,这名字保存着山野的气脉和时间的痕迹。在洪沟河南岸,我们叫它“苘饽饽儿”,“饽饽儿”是白面馒头的昵称,逢年过节才能吃上几顿的白面馒头,我们到田野里就可以一饱口福了。苘麻子有着好看的颜色,比白还白的颜色,小心翼翼地伸出舌尖,一舔,麻酥酥的凉,夹著一些甜丝儿,心里给苘麻加了一个感激。
金盘银盏八角乌,这些灵动在诗歌里的优美意象,只是一种场景的渲染,一种朴素而又庄重的乡村仪式。苘麻就在这样的场景里抵达了天空的高度。苘麻收割了,它不是小麦也不是谷子,它的收割意味着新一轮生长的开始。首先,它们不再各适其适,各安其份,而是一捆一捆地集结在一起,就像一个握紧的拳头。然后,离开熟悉的大田,去洪沟河里潜水,其上放着重重的石块,压了沉沉的麻袋,真是抱着石头跳河,义无反顾,以此接受水的潜移默化,让苘的麻疏离苘的杆,个体生命呼吸着群体的气息,个体的某个特质被发现被承认,苘的麻对自由的祈向,是个体精神的回归。就是说,集体的确立,并不是删除个体自由空间;社会的进步,来自于个体生命潜能的最大释放。苘麻走出水面的时候,黑不溜秋的,活像一群走出煤窑的汉子,裹着一些浓烈的体臭。清水里洗个澡,树干上砸砸拳,黑黑的苘麻成了一些俊俊的小伙,白白的,一脸金灿灿的笑容。
生在大田里,长在河流中,苘麻思想的纤维不易腐烂,坚硬而又柔情。苘的麻一根一根编织起来,这一股叫春秋;一截一截越接越长,这一股是冬夏。把两股缠在一处,拧在一起,就是一年四季硬实粗壮的乡路,把五谷丰登拉回村庄,把幸福吉祥拉回家乡。
云星菜
云星菜是洪沟河南岸的人们给取的名字。我“百度”了一下,它的学名是“刺苋”。好端端的云星菜怎么就“刺苋”了呢?心里就生出一个小难过。约略一想,就咂摸出洪沟河南岸这方大野的智慧和厚重。
云星菜,这名字包含着人们一次次仰望着的云头,云是雨的头,天上下雨地上湿,湿了的土地膨松酥软,不愁长不出一个五谷丰登来;也包含着乡村夜空的无数美丽的辉光,星是乡村的灯,星星一亮,脚印就醒了,脚印一醒,田野上的庄稼也醒了,你长我也长吧,长成一个梦的形状。
云星菜的叶子和豆叶差不多大小,颜色比豆叶要深邃一些持重一些,撑开叶子的中脉有隆起,就像一根暴突的青筋,很男人的青筋,不过,这隆起在叶子背面,不露脸不显身,却使得叶面形成一个优美的好看的凹陷,犹如摊开的双手并拢了,很虔诚地捧着几缕阳光。云星菜有着苘麻叶的辽阔,但是比苘叶更具有纵深感,叶子拓展到先端,微微弯,敛成一个柔润的圆,又如柳叶的两端向内收束,细长的叶在凝聚它的智慧,增加它的宽度。形状像豆叶,开阔如苘叶,伸展似柳叶,这就是云星菜的叶子。就说它像云吧,云卷云舒,一朵一朵好看的绿云,在风里摇着绿,还不时翻出一些碧绿深绿墨绿的层次来,绿浪一波一波的,推推搡搡着,荡漾出无边的绿海。
云星菜的花儿太多了,星星点点的,单个的花很小很碎,似乎不像是花朵,密密麻麻地挤成一团,排成一个阵势,就有繁星满天的气场了,在叶腋之间簇生成一个个神秘的星球,在植株顶端直立为宝石的塔。叶柄和植株相接,结构成一个安静而牢靠的窝儿,叫叶腋,细眉细眼的雌花们就在这里扎堆,细丝细嗓地说着私房话,甜滋滋的目光温嘟嘟地仰望着遥远的雄壮的宝塔。相对于叶腋,雄花们生存的空间就是一个江湖了。它们很清楚自身的卑微,不想篡改成强悍的油菜花,被蜜蜂和赞美诗簇拥着,也不能指望像豆苗那样生活在舒适宽敞的大田里,它们必须有所担当,要多开花开好花,抱成一团,连成一片,组成一个强大的穗状的集体,长风浩荡或者微风轻拂,就一起去寻找各自的爱情和归宿,那等在叶腋间花房里的容颜正青春。
这样的花,这样的草,让我想起佛的一个偈语:一花一世界,一草一天堂。云星菜,生在大田里,它就被认定为“杂草”,就有被斩草除根的可能;长于沟渠边,那就是生在帝王家了,得天独厚,拥有植物的一切特权;扎根瓦砾间,活在石缝里,也要挺直身躯,创造一个绿云绕绕繁星点点的世界。因此,即使有且只有一棵云星菜,也是一个美好而又宏伟的天堂。云星菜,它有着天才的预见性,让雄蕊和雌花同一个植株,并且实现性别解放,把植物家族的理想投向了高尚的未来。就是这一棵植株,每年都要举行成百上千次婚礼,自初夏至深秋,雄蕊雌花们都在相亲相爱,“一草一天堂”,原来如此。
我的故乡洪沟河南岸,真的是一个天堂世界。洪沟河自西而东地流,把落山的夕阳流成初升的旭日,把投向水面的光线反射为一棵棵绿草。空气像甜水梨一样蜜甜多汁,风吹草籽,一落到地面就能长出一群健壮的牛羊。云星菜喜欢热热闹闹地挤在一起,就像和和睦睦的一家人,吃饭的时候往饭桌上凑,七杈八股,好几双筷子沉浸在香喷喷的青菜里,到了晚上就挤热炕头,做个梦都是热气腾腾的乡间生活。也许,在初始之地,只是那么孤零零的一两棵,仿佛羁旅他乡的异客。过不了多久,就有一片一片的绿云生出来,让大地碧透,让蓝天碧透;就有一颗一颗的星升起来,让田野亮透,让梦境亮透。叶一丛丛地,厚成一个群落;花一簇簇地,竖起一个图腾。天明地阔,叶子铺天盖地,花儿就纷繁密集。
云星菜,这绿色的奇迹,它把天堂的光景搬迁到人间,把天上的美好化为大地的奇妙。试想,如果人间没有云星菜这样的先知,天空距离我们会更加遥远,就像无形的幸福一样难以感受。在洪沟河南岸,人们总是主动把身躯弯成一张弓,一种熔铸力与美的劳动姿势。在过路人看来,这姿势是美的,犹如激情的诗人亲吻着大地。但是,这是肢体的劳动,以力求胜的劳动,面朝黄土背朝天,背负着繁重的农活和生计,自然无暇欣赏天空的风光。黄土之上还有一个比蓝还蓝的蓝天呢,它在不断地呈现新奇的云朵和星辰。云星菜的出现,使得这种弓形的姿势得到了放松和舒展。它尊重这种姿势,它在比低还低的低地里安身立命,以七杈八股上的云星打动人们的目光,导引着他们扶直疲惫的腰身,踮起脚尖,去欣赏远天的生活,此时,眼睛里就有两颗星在熠熠闪光,脸颊上就有两朵闲云,野鹤一般从容。这实在是天空和大地赐予的劳動之美。云星菜,无疑是大自然最富人性的创造。
云星菜真是一种普世的野菜。它的嫩茎叶可以食用,春夏秋三季均可采收。采收了的云星菜,不几天就会长出新的枝枝叶叶;采来的嫩茎叶可凉拌,可做汤,无论哪种做法,都是一次美丽的身体旅行。清爽的菜一碰上饥饿的牙,牙却怜香惜玉,门户大开,让渴盼已久的舌头抱个满怀,满口的鲜嫩清香,走吧走吧,肚子空着呢,舌头一卷,这菜就驶上喉咙的高速公路,顺顺当当舒舒服服踏踏实实地落到肚里,情不自禁,打一个赞美的饱嗝,就有一股清爽通透之气往细里憋,再向上猛蹿,蹿一喉咙绿,开一口腔花,长成一棵大野的菜,要有云,要有星,要有比爽还爽的好味道。 责任编辑 王冬海